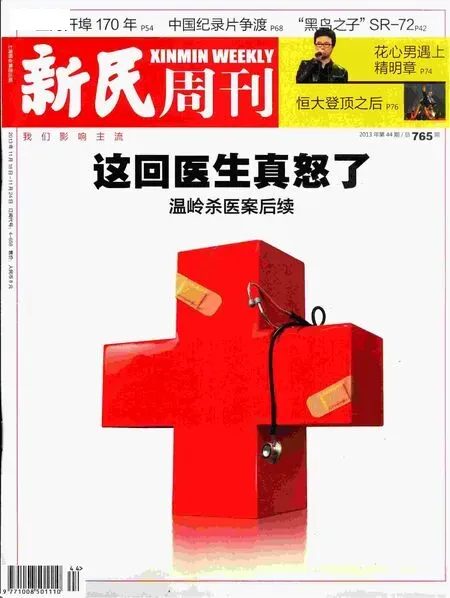“爛英語”才是全球語言
苗煒
90年代初,一個月黑風高之夜,我跑到人民大學轉了一圈,校門口假山石后的小樹林里,就是當時頗有名聲的“英語角”,樹林里有百八十人,三三兩兩地聚集著,我湊到這圈里聽聽,再湊到那圈里聽聽,到最后也沒好意思加入談話,訕訕地離開。過了些日子,我轉移到了人民大學對面的理工大學,參加“實力英語”的托福培訓班,教課的老師叫宮東風,當年的名氣可不在俞敏洪老師之下,班里的同學大多打算考托福,拿獎學金,去美國念書。
我當時不知道,法國人正掀起一場抗擊“美國文化”入侵的運動,目標直指巴黎郊外的“歐洲迪斯尼樂園”,一位法國戲劇導演說,示威者應該在迪斯尼樂園點一把火,那是“文化上的切爾諾貝利”。1992年7月,250名法國知識分子,包括作家和詩人,上書密特朗政府,要求“光大法語”,在教學、會議、電影中使用純正的法語,“御英語于國門之外”。
轉眼到了2008年,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我還在學習《新概念英語》第二冊。這一年,盧旺達政府忽然宣布,該國對外交流將使用英語,學校里要教英語,那些父母都說盧旺達語的孩子,也要學英語。有評論說,盧旺達棄法語改英語有政治上的原因,他們埋怨法國政府沒能阻止盧旺達大屠殺的發生。但盧旺達負責產業和貿易的部長說,“只有法國人說法語,還有西非的部分地方,和加拿大和瑞士的部分地區,說英語的地方要更多,英語正在成為全球語言。要加入全球化進程,就要學英語。”2009年,繼馬達加斯加之后,盧旺達申請加入英聯邦,這是“后殖民時代”語言的力量。
我學了20多年英語學得痛苦不堪,忽然有一天,有個人跟我說,現在的孩子瞎學什么英語考什么聽力啊,電視里要是有CNN,有HBO,看電視就行了。我覺得吧,電視里沒有CNN,沒有HBO,互聯網上沒有GOOGLE,都是抵御文化入侵。咱們是大國,得有大國的風范,不能像新加坡似的,領袖總嫌國民英語不好。
李光耀畢業于劍橋,1970年代,在新加坡推行“英語優先”政策,新加坡是個語言混雜的國家,馬拉語、中國話、英語、泰米爾語都被民眾使用,中國話里又有廣東話、潮州話等等,1978年,李光耀上電視,專門講“新加坡式英語”的問題——我們說的英語不夠純正,新加坡人講英語不夠完美。他舉例說,新加坡式英語一個很不好的習慣是,說完一個句子,總要加上LAH這么個音節。1979年,新加坡政府又發起了一場“講好普通話”運動,想讓那些說潮州話、客家話的華人都講普通話,這一運動沒能持續展開,1987年,新加坡政府規定,不管小孩子在家里說什么,到了學校一概用英語教學。2005年,李顯龍總理又發表了一個電視講話說,我們要全力以赴地說好英語——在家、在工作中、在社會活動中。我們可以用新加坡口音來說,要表達完整,不要在句子結尾還要加上Lahs\Lors這些音節。看看新加坡,政府講了20多年,領導人那么重視,句子結尾還老是“啦啦”的。
咱們改革開放初期,也有一陣英語熱潮,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之前有一檔英語教學節目,叫Follow Me,里面有個花老師Kathy Flower,80年代紅極一時。如今花老師退休,生活在法國,有個叫《英語的故事》的紀錄片采訪了花老師,花老師說,中國人學習英語文化的熱情是我20年前不能想象的,中國家庭非常重視教育,特別是在獨生子女政策的影響下,很多家庭都愿意在教育上花大本錢。不過,你要離開城市到農村看看,你會發現,數億人能完成基礎的母語教育,就已經是畢生了不起的成就了。
英語的霸權地位,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有一位法國人奈易耶說,他在IBM工作期間,發現母語非英語的巴西、韓國同事,只用1500個單詞就能順利溝通,英語不掌握在英美人手里,而是掌握在全世界人民手里,英語不是“全球語言”,“爛英語”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