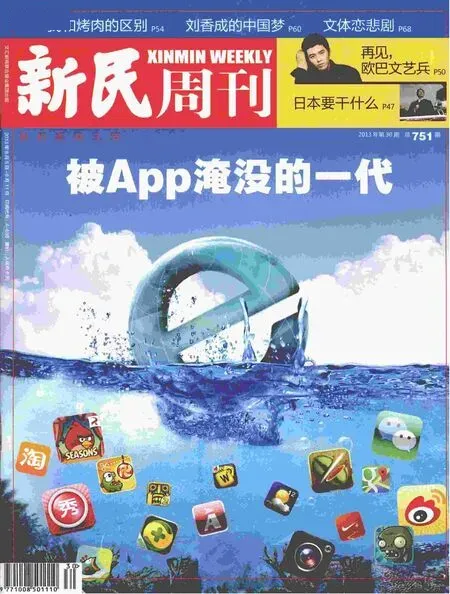去杠桿不容易
聶日明
近來政策頻出。7月16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強調,要保證經濟運行處于合理區間,其下限就是穩增長保就業,上限就是防范通貨膨脹。26日,國務院發特急明電,審計署將對全國范圍的政府性債務進行審計。這些顯示,政府關注經濟增長,但政府也不希望出現風險,呈現糾結的局面。
李克強自任總理以來,開始推動以經濟轉型為目標的政策,巴克萊資本亞洲區首席經濟學家黃益平定義了“李克強經濟學”來總結這些政策,包括“不刺激、去杠桿和搞改革”。其中“去杠桿”是短期內最核心的政策目標,“不刺激”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所謂杠桿,通俗地講,就是借別人的錢,辦自己的事,通過借債,用較小的資本金來控制較大的資產規模,以擴大盈利能力或購買力。負債率、負債收入比等是衡量杠桿的指標。
“去杠桿”就意味著過去中國各部門的杠桿過高。與歐美居民過度消費的高杠桿不同,中國杠桿主要體現在企業和地方政府主導的過剩產能和過大的基建規模。分解到各部門來看,中國企業的杠桿最難以為繼,以A股非金融企業為例,已經有近半數企業股東回報率低于一年期貸款利率,債務擴張帶來的不是超額利潤,而是沉重的財務負擔。
政府債務總體來看不高,賬面上只有10萬億有余,不足GDP的20%,但令人擔心的是地方政府的債務。以融資平臺為核心的地方債務正處于失控狀態,為此中央不得不展開全國性地方政府債務審計。
過高的杠桿,嚴重抑制了經濟的活力,原來債務擴張是為了超額利潤,但中國杠桿率快速上升的原因卻是為了應對經濟衰退。經濟下行周期時,大量的企業處于破產邊緣,政府推出的經濟刺激政策,信貸擴張,企業提高負債率成為可能,也讓它們躲過被淘汰,勉強維持經營。但這只是權宜之計,企業長期的穩健經營靠的還是自身創造利潤能力的提高。經濟刺激政策使得優不能勝、劣不能汰,影響了市場效率。
所謂“去杠桿”,就是讓市場回歸,不搞刺激政策,不再主動給企業(包括企業和融資平臺)注水,沒有競爭力的企業自然會退出市場,“去杠桿”的目的也就達到了。但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去杠桿意味著劣質企業、過剩產能要退出市場,對應的是經濟規模的縮減、失業人數增加,更意味著財政收入規模降低、社會維穩壓力增加,這些都是去杠桿的后遺癥。這也是為什么李克強要強調經濟增長要有下限。
但要維持增長下限,就要維持較高杠桿水平,甚至有可能還需要一個小規模的經濟刺激。從今天的現實可以推演出明天的局面,如果說目前高杠桿所體現的“過大的基建規模和過剩的產能”是一個泡沫,那我們面臨的選擇就是要么讓它今天破裂,要么推遲到明天破裂一個更大的。
今年“國五條”出來后,房地產市場在短暫的停滯后,從5、6月起,開始火爆,房地產融資放松、地王頻出,這或許預示著政府希望通過提高居民部門的杠桿,來抵消地方政府與企業“去杠桿”的負作用。但居民收入就那么多,房地產多了,勢必擠壓其他消費,還妨礙了經濟結構的轉型,會出現全社會房地產化,這并非一個好的選擇,更多是在維穩,效果不比刺激政策好多少。
所有的經濟政策都是有代價的。今天我們要避免為了規避昨天的代價而在明天付出更為高昂的代價,這也是黃益平教授提出的“李克強經濟學”的內涵。從這一點上講,今天的窘境還不足以讓全社會形成共識,無法下定去杠桿的決心。去杠桿的過程,也是一個凝聚共識的過程。15年前,亞洲金融危機來臨前,我們才被迫明白改革迫在眉睫,國退民進勢在必行,今天的“去杠桿”也是如此。但我們是不是一定要到不得不付出更大成本的時候,才能明白去杠桿是一個必要的程序?或許我們可以讓這些共識來得更早一些。
(作者為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