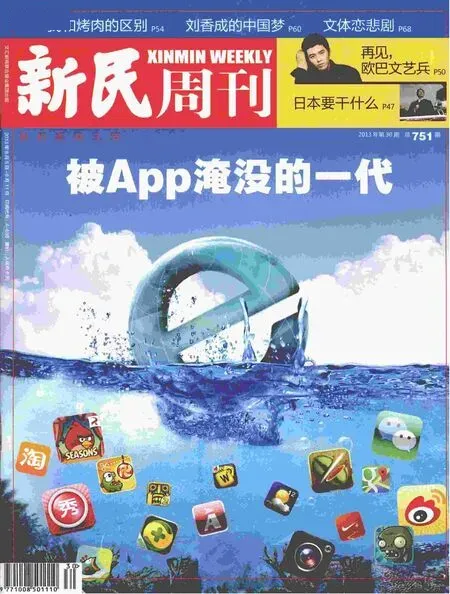從美術史中閃出的一抹亮色
肖凡
上海大學美術學院的李超教授是研究中國近代油畫史而馳譽遐邇的,特別是他對上海一百多年來的油畫發展脈絡的梳理,讓人們看到了油畫在中國登陸后,在知識分子和平民中間的回響,特別是對上海這座城市氣質的培育。在研究的同時李超也在進行著創作實踐,日前,他拿出數十件彩墨作品在朱屺瞻藝術館進行展出。這個《云間千蕖——李超繪畫作品展》清晰地向外界昭示:李超不僅在理論界豐富藝術的內涵,也在實踐上探索藝術,擴展藝術的外延。這些作品將李超的獨特藝術語言、意趣及性情體現得淋漓盡致,反映了他在藝術創作實踐上的追求和探索。
王劼音回憶他與李超共事的二十余年里,算雖不上特別緊密,卻留下深刻印象。“1989年李超特意陪同美國亞太博物館館長卡曼斯基到我家尋訪,卡氏購藏了我的一幅油畫,并入選他在美國策劃的一個重要展覽。這一事件就此淡化了我對版畫家身份的專注,某種程度改變了我藝術之路的軌跡。前不久李超來電約我觀看他的彩墨新作。我早就知道他筆耕之余作畫的‘秘密,因而并不感到意外,但卻存有一分懸念,難以想象他這些新作是什么模樣。”
王劼音還認為:“李超超越了名人作畫的局限,既沒有因為自己在美術史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名望而趾高氣揚,自視甚高,以為必然在繪畫實踐上也是天下第一;也沒有因為自己不是‘畫圖出身而自慚形穢,內心深處藏著縮手縮腳的自卑。更重要的是他對‘玻璃規則頗有所悟,畫出來的東西自然就對頭了。”
從展覽本身看,早先李超畫油畫,諸如《不和塞尚玩牌》、《看不見凡高》等作品記錄了他介入繪畫的軌跡。這些作品的表現形式是意向的,也就是說用的不是寫實方法。著意在用哲學的理念去重新解讀大師的經典。這也是當時激進的潮流,李超年輕,有激情,有思想,理應合在時代潮流之中。
而現在,李超于近兩年創作的水墨畫,讓人感覺繪畫風格有明顯的轉變。看這些在紙上的墨塊和線條的交錯;品那片濃淡暈化的色彩和點厾的組合,都流露出他用性情寫出的意趣。他畫的水墨,或者是彩墨,他也會把這種水墨意味用油畫顏料寫在油畫布上,而更多的是那些紙本的彩墨。誠如李超的朋友、畫家黃阿忠所說:“這些作品看似展現了西方的點、線、面抽象表現構成的理念,卻又融入許多中國畫的審美趣味。就以他先前的油畫作品而言,與其說是他繪畫風格的轉變,還不如說他審美取向的轉身。在那些融入了東方審美意味的作品中,我們看到了李超從早先解構大師經典開始到崇尚意趣的轉化。我以為意趣是繪畫的一種境界,也是藝術作品中的重要元素。意趣者,意味與情趣也。意味是深遠,是詩性,是境地,是品格;情趣為曠野,為感覺,為性情,為純真。或許,藝術創作之真諦亦源于此。”
李超對美術史的研究,自覺不自覺地都在他的作品中流露出來,似乎在許多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他與前輩大師的對話,對大師藝術觀念的折服,比方他會將齊白石的山水移至自己的作品中,那些由簡約線條組成的山巒,以及隨意揮灑的水紋構成的抽象意趣,很難說是齊白石的,但處處有齊白石行過的足跡。還有潘天壽筆下的石頭、老鷹、荷花等等,都有作為一種構成存在于李超的作品中。李超對西方諸位美術大師的風格也是相當熟稔的,于是在他的作品中又可以發現馬蒂斯的線與色塊、塔匹埃斯的抽象觀念和意趣。當然,李超是以謙恭的態度與大師對話的,但又從不丟失自己的性格與風度,這也使得他的作品具有自己的品位與調性,以及或激情與逸趣,還有無處不在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