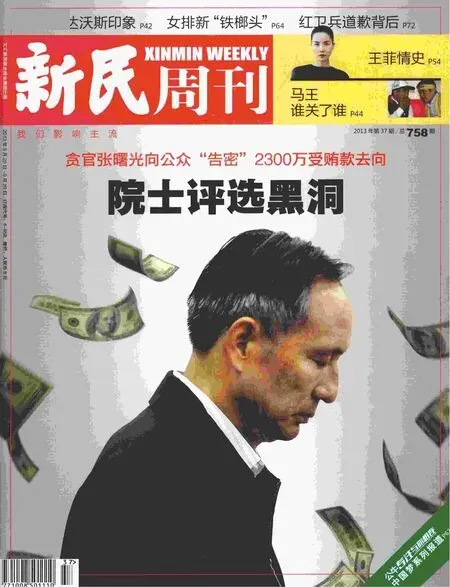當美國貨幣風向轉變時……
任蕙蘭



1997金融危機重演?
9月,大連,“夏季達沃斯”論壇。
再一次,會場里彌漫著無數的預言。圍繞的是這個夏天的隆隆雷聲:量化寬松即將成為歷史。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亞洲一直是國際資金流入地區,新興國家股市、債市和房地產被熱錢推到高位。而隨著這一輪量化寬松結束,資金將撤離東南亞回流美國。澇著澇著就旱了?轉折點來得很迅猛。
8月21日公布的美聯儲7月底會議紀要表明,如果美國經濟復蘇情況符合預期,那么美聯儲官員有望開始縮減每月850億美元購債計劃,時間最早可能在9月份。美國貨幣政策轉向的時間表逐漸明晰,量化寬松淡出成為9月中旬“夏季達沃斯”論壇熱議的焦點。
幾個月前市場上就有關于美國量化寬松政策淡出的消息,而觸動點是在今年6月出現。6月下旬,美聯儲議息會議宣布,將于2013年下半年開始逐步縮緊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并可能于明年年中全面停止刺激措施。
隨之,印度、南非、印尼、巴西等新興經濟體金融市場出現大幅波動,尤其印尼、印度成為重災區,匯率大幅下滑,印度盧布貶值21%,且股市與債市面臨拋售,市場出現恐慌情緒。中國的情況相較印尼和印度要好得多,但也出現外資拋售國內銀行股票的狀況。
靴子什么時候落地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們都知道它很快會掉下來。在資本項和經常項之外,市場上存在大量熱錢,高速交易方不放過市場的任何微小變動,而轉向的美國貨幣政策立刻成為新興金融市場被阻擊的理由。
很多人擔心,這會引發又一場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
事實上,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貨幣政策,美國在歷史上已經玩過很多次。當美國國內經濟疲軟,美聯儲推行寬松貨幣政策之時,資金由美國流向利率相對較高的新興市場,并催生新興市場資產泡沫和信貸繁榮;而當美國國內經濟復蘇,美聯儲逐步退出寬松貨幣政策之后,資金由新興市場回流美國,新興市場資產泡沫和信貸繁榮破滅,金融市場動蕩和經濟衰退隨之而來。上世紀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起因正是的美國放水和收水。
“美國此次量化寬松是前所未有的。”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表示,美聯儲賬上累積了規模達2萬億-3萬億美元的貨幣,因而此次量化寬松退出成為市場上最大的不確定性。
但在美國學者看來,山姆大叔不應成為新興市場波動的被問責者。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國際貨幣體系全球議程理事會理事Adam S. Posen坦言,美國很難在制定政策時把其他國家情況考慮在內,要求美國考慮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并不現實。而且美國幾個月前就放出了QE淡出的消息,令市場受到的沖擊最小化。
Posen還認為,新興市場國家因本身脆弱性導致的金融動蕩不應該歸咎于美國。“新興市場國家要做好自己的家庭作業。”
美國量化寬松政策淡出,確實將會成為檢驗新興市場功課的標尺,每個國家的抗風險能力取決于經常性盈余、外債依存度和杠桿負債率等基本面情況。
印度和印度尼西亞顯然沒有做好功課,在2008年至今的全球流動性寬松期間,滿足于流動性寬松推動的經濟增長,制造業發展緩慢,并未對國內存在的經濟結構性問題做出調整。兩國經常賬戶逆差不斷增長、信貸繁榮和資產泡沫浮現,金融風險只是個時間問題,貨幣貶值不可避免。
香港、泰國和新加坡市場開放程度高,這些地區的問題在于貨幣和匯率體制脆弱,風險系數也在提升。而且香港房地產大起大落,新加坡的家庭投資也過度集中于樓市,房地產可能會成為這些地區的軟肋。
摩根士丹利亞太區聯席首席執行官兼管理委員會成員孫瑋認為,與印度、印尼等這些經常賬戶項目赤字嚴重的新興市場國家相比,中國的狀況要好很多。中國握有3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外債只有1萬億,經常性項目盈余很大,經濟基本面情況良好。更多投資者現階段在觀望,沒有進行拋售,也沒有出現大規模資本外逃。
“以后人們可能不會再談金磚四國,而是談中國和其他那些新興國家,因為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發展情況不同。”李稻葵說。
但周邊市場受害也會影響中國經濟,巴西、印尼、印度是中國的貿易伙伴,這些國家市場低迷將影響中國的出口。而廣受外界關注的中國GDP增長放緩、信貸擴張、非直接融資以及金融市場開放程度問題,也增加了答案的不確定性。
不過從亞洲整體看,1997年危機重演的概率不大。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前,以泰國為例,外債余額/國民總收入(GNI)超過200%,其中短期債務占比超過50%,同時股票、房地產等資產價格在大量海外資金流入的推動下大幅上漲,資產價格泡沫明顯。亞洲金融危機到來后,泰國成為損失最為慘重的國家。
與此前新興市場金融危機爆發時相比,當前多數新興市場經濟體已做好準備,新興國家現在共有8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各國通過降低外債尤其是短期外債比重,轉固定匯率制度為浮動匯率制度,以及加強資本管制,提升了抵抗跨境資本流動沖擊的能力。
歷史上不斷看到這種重復:一旦美國患上流感,新興市場國家就會被傳染。大量快進快出的熱錢足以摧毀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幾年都難以復原。人們急于尋找抗流感藥。
李稻葵認為,美元波動對新興國家影響很大,最好的抵御方式是建立多極世界貨幣市場,隨著歐洲復蘇,歐元逐步走強,以及人民幣在區域內發揮作用,將和歐元、美元構成世界貨幣的三極。當美國量化寬松淡出,人民幣和歐元可以起到緩沖作用。
外部市場的波動提供了人民幣崛起的機遇。人民幣要躋身世界儲備貨幣之列,呼之欲出的人民幣資本項下開放顯得尤為重要。
貿易戰更激烈
全球金融危機過去5年,當前中國的貿易順差幾乎已經歸零。美國量化寬松結束后,美元將進入上升通道,隨著人民幣貶值,以及美國經濟復蘇態勢確立,外部市場回暖,很多人樂觀估計,中國工業出口將會從年底開始提升。
但更理性的觀點是,美國經濟上行對中國貿易將會是把雙刃劍,因為“中國出口”迎上的正是美國逐步恢復競爭力的制造業。2013年上半年美國制造業貿易逆差從上年同期的2270億美元縮小至2250億美元,且制造業連續兩個月實現增長。
從上一輪金融危機以后,美國意識到重塑制造業的重要性,奧巴馬在第二個任期內把振興制造業作為首要任務。美國目前的失業率為7.4%,預計到2020年,美國將新增250萬至500萬個與制造業有關的就業崗位,使失業率降低2到3個百分點。
大型制造業企業正在響應總統的號召重回國內。卡特彼勒和通用電氣等大型公司近幾年已將一些生產環節轉回美國。普利司通輪胎等公司擴大了在美國的產能以便為美國客戶提供服務。
這也在降低中國、印度和巴西等新興國家的吸引力。尤其當中國制造業正在向價值鏈高端提升,隨著一部分中高端制造企業回流,中國世界工廠地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美國不會發展低端制造業,不會去和孟加拉國制衣廠搶生意。而中國制造業正在向產業鏈上游走,從代工向設計DIY發展, 現在Nike品牌有50%的設計是向中國購買的。當我們在塑造品牌時,和美國重塑的制造業正好撞上,競爭不可避免。”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社會責任辦公室首席研究員梁曉輝說。
中國出口將面對更激烈的競爭環境,而爭奪貿易規則的話語權就是關鍵。
多哈回合貿易談判陷入僵局以來,世界貿易組織推動自貿談判的進程陷入停滯。世界上許多國家逐漸將目光投向跨區域貿易協定。新西蘭、新加坡、智利和文萊等發起成立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美國隨后加入;新興市場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則多次舉行金磚國家(BRICS)領導人會晤。此外,美國和歐盟還計劃啟動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
多到讓人無所適從跨區域貿易協定,本質是強國在爭奪游戲規則的制定權。美國推動TPP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設定一個標準,要求中國加入并遵循其游戲規則。
“美國設定標準,讓我們去遵守,這樣的事情在中國入世的時候已經發生過一次,現在要讓中國再按美國人制定的標準加入TPP,相當于二次入世,這是不可能的。”北京對外經貿大學副校長林桂軍表示,標準和規則的制定應該由各方共同參與。
重要的是,目前的國際格局已經改變。中國進出口銀行董事長李若谷表示,世界貿易規則是五六十年代制定的,那時是發達國家主導國際貿易,現在是發展中國家主導。“不能在發達國家強勢時,就要求打開大門,自由貿易;走弱時就要保護貿易,用勞工條件環境保護設置障礙,有些條款對發展中國家不適用。”
中國政府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心也在向外部展示誠意。8月,國務院批準設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探索外商投資負面清單管理等制度,成為達沃斯熱議的話題。
海外并購趨于謹慎
當美國貨幣風向轉變時,立志“走出去”的中國企業家需要考慮何時換帆。
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中國企業掀起了海外投資熱潮。美國長期寬松貨幣政策下美元一直處在貶值通道,加上美國制造業低迷,去收購“白菜價”的海外企業成了時髦。2009年中國國內的4萬億量化寬松,讓國有企業急切為資金尋找出路,有資本響應“走出去”戰略。
熱錢刺激著中國企業去海外開疆辟土。2012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創下流量878億美元的歷史新高,首次成為世界三大對外投資國之一。瑞銀集團中國區主席兼總裁李一表示,加上香港的800多億美元,總量達到1700多億,因為香港的資金大部分來自內地,將香港作為對外投資的橋梁。
去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增速16%,根據官方公布的目標,在2015年“十二五”末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將達到1500億美元;2020年達到2000億美元。
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主要領域在交通、能源、零售和批發,前期粗放式的投資中有不少折戟沉沙的例子。比如中鋁、中色、中鋼、中鐵等央企向國外礦山“進軍”,民營企業也緊隨其后。然而隨著金屬礦業也開始面臨去泡沫化過程,中冶、中鋁等大型國企開始爆出巨虧。
美國MMC集團董事Elaine la Roche認為,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問題不是出在錢上,問題在于收購戰略和企業的本地化過程。
“海外并購不是那么簡單,問題不在于并購的價格和你擁有的資金,而是你投資的方式。” la Roche分析,中國企業進行海外并購的方式,習慣是用一張大支票搞定一切,比如買下一座礦山,他們通常不注重并購后的整合。而成熟的跨國企業會在當地尋找合作伙伴,和當地企業合作成立一支主權基金進行投資。中國企業不愿意建立基金,只在乎控股,追求拿大股份,做大股東。
“中國在資源領域的并購不應該是一場資本游戲,要和當地政府溝通,適應新的規則,而中國企業普遍缺乏管理技能(management expertise)。”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外方院長蘇里達博士說。
中國進出口銀行董事長李若谷坦言,中國企業在海外融合度很低。他曾去40多個非洲國家考察過當地中國企業的發展情況。中國企業一般做法是在海外成立一個分公司,建個宿舍區,中方人員就在廠區和宿舍區活動,和當地人幾乎零交集。因為派駐的中國人只會英語和法語,不會當地語言,所以文化融合很差,也很少有關于企業的宣傳廣告。加上中國企業不了解英國判例法體系的當地法律,難以處理經濟糾紛。
隨著中國企業投資目標從自然資源、大宗商品轉向服務業和制造業,企業以買礦山的思路并購海外企業,資金為王,因此中國企業在美國醫療、汽車領域的并購有很多并不成功。
而在美國人看來,上世紀80年代日本“買下美國”的風潮似乎在重演,只不過這次主角換成了中國。美國商務部副部長桑切斯在“夏季達沃斯”論壇上宣稱,中國對美投資以每年70%的速度增長。而中國對外投資的高速增長也引起美國的關注,一些中國企業的并購被美國的安全審查攔在門外,其中最知名的是三一重工和華為。
中國進出口銀行董事長李若谷認為,三一重工因為“毫無根據的否決,借口不到位”而發酵成話題。三一重工不是國企,也不在TMT高科技領域,而且它的并購案也符合美國制造業重振的政策,因此美國的拒絕是“把毫無問題的事變成一個問題”。
桑切斯表示,大部分中國對美投資沒有遇到安全審查的問題,被拒絕的是個案。但從數據來看,2012年中國在美國投資的否決率雖然只有百分之十幾,但在全球其他地區對美投資中排第一。
除了憂慮安全審查,隨著美國量化寬松政策淡出,預示美國經濟復蘇以及美元走強,人民幣也出現貶值的跡象,出擊海外的中國企業還要做好準備在逆風下開船。粗放式的投資將被更謹慎的戰略布局替代。追求短期投資、快收益的企業家,要重新衡量對外投資創造的價值。
“企業要有清晰的戰略,要明白角色是什么。”招商銀行前行長馬蔚華表示,招商銀行在美國建立代表處用了5年,升為分行用了8年,其間在美聯儲交了很多朋友。但現在并購企業對通盤問題考慮得很少。
“交易只是一個開始,對并購而言,有沒有戰略思維最重要,企業想清楚要干什么。為了實現商業目標,除了海外并購有沒有其他代替方案,替代方案的好處是什么,并購以后能否做好和當地文化政治上融合。” la Roche說。
在李一看來,中國企業需要從海外投資獲得的,除了資源,還有技術和品牌的軟實力。未來5-10年大量并購會發生在醫療衛生以及高科技領域,并購的目標是離消費者更接近。以PE、主權基金合作方式代替控股,下一步會出現更多不同并購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