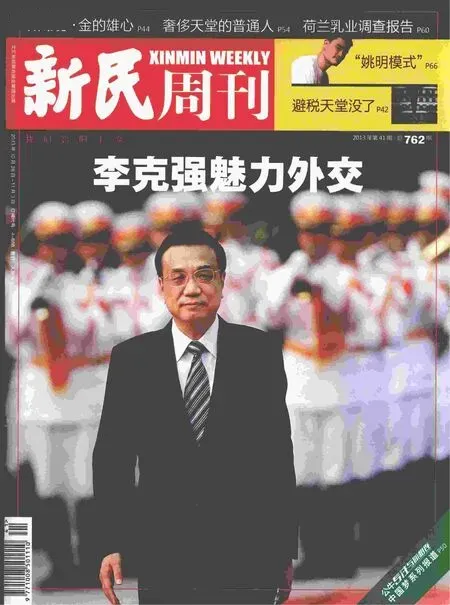E時代的劇評
林奕華
戲劇要追上時代步伐,劇評又如何?
時光當然不能倒流到劇評扮演一部舞臺劇的生死判官的年代——尤其那也不是屬于我們的風光。是的,曾經有過那么一種心跳,來自一臺新戲首演之夜過后,它的主演、導演和制作人對新鮮出爐的劇評的期待。破曉是報章上街和評論面世之時,一干人等干脆守候至成績單派發才算長日告終:成功抑或成仁,到底有個對己對人的交代。
只是,劇評受重視脫離不了戲劇本身的尊貴——字里行間滿是對創作人的“打躬作揖”,以先生女士的稱謂提及有功有勞也可能有過的每一個人。近乎社交禮儀的姿態即便被應用在某種的消費指南上,上世紀紐約百老匯與倫敦西區全盛時期的戲劇同行,還是相當重視文化和修養。例子是,口誅不如筆伐,筆伐又不如以錦心繡口把罵人的話包裝得既體面,又富有殺傷力——對于不符合劇評人預期的戲,他們下筆可以重如千斤,但亦不乏綿里藏針。
換句話說,劇評人不僅要能“評”,更重要的,是能“寫”——雖說是一筆在手的權威角色,但若不能從觀眾角度出發,卻獨沽一味自說自話,說是劇評,變相成了讀者要花上更多心思才看得明白的作品,豈非有違為觀眾解惑與分出一部戲的高下的劇評人職責?
在戲劇沒有演化成愈來愈多種類、面貌和功能的過去,劇評人在商業戲劇世界里的任務卻較現在簡單許多。就以王爾德的戲劇作品來說,觀眾與劇評人之所以同一陣線,是劇場的定位十分清楚:分明是講故事的地方,故事可有講得人信,進而有幾分動聽,動聽的意思,是演員(也就是說書人們)有沒有把戲演得入木三分,讓看戲的人全程忘我,待得一戲既終,全院觀眾在一聲鑼響大幕落下時警覺南柯夢醒,衡量這一切的妙與不妙,好或不好,都在一種狀態的有還是沒有:投入。
然而,在21世紀的今日,隨著人類被多媒體的生活語境切割得昏頭轉向,“投入”已沾染了對現實的諷刺意味:休說在看一部舞臺劇時很難百分百專注,就是出了戲院回到現實世界,誰不是在橫過馬路或開著汽車時皆一心多用?朋友圈有不知多少人在發放象征每個人的存在價值的圖像與文字,如果說那也算是串門子,怪不得“專誠拜訪”早成歷史名詞。
投入,聽似是生活的基本態度,其實很奢侈——人的精力與時間有限,把它給予了甲,乙就不可能分到同等分量,快速養成人人都是淺嘗輒止的抽身和疏離:疏離有可能因動情而奮不顧身的自己,抽身于還來得及明哲保身的關頭。
現代人不承認控制欲是一種病,“投入”和“抽離”于多數人合該是一個人跳的心靈探戈:每一步都在與自己角力。帶著這種心理走進劇院,又怎會不是左右為難進退失據?以為是去看一個別人的故事,但真演起貌似與自己沒有相干的劇情時,立刻自覺疏離與不投入。只是若在舞臺上認出似曾相識的身影或輪廓,又會礙于那不是最想面對的“我”而第一時間疏離和作下沒有必要投入的定案。
也就是說,即便只是為了娛樂,今天的劇場也很難做到與當年的劇場爭長短:人心日趨復雜,頭腦反倒日趨簡單,大家都在逃避認識自我的后遺癥是,故事的重要性已不在于它是“說什么”,而是它被“怎么說”——橋段最好新穎,多變;但情感不宜復雜、細膩。
在這種環境下,劇評人真要一盡評論者的責任,首先應要明白過去一套標準的不合時宜。叫人遺憾的是,當一部有著現代視角的戲劇遇上堅持以適用于過去但無助于幫助觀眾明白現狀的角度寫劇評的“判官”時,無可避免地,因語境不同而產生的溝通失誤,就會造成“冤案”。
“冤案”是悲劇,“拉郎配”則是荒誕劇,一出戲劇之于某些劇評人,竟有“為何你不能是我的理想對象”的時候——既然具備符合需求的條件,偏又未致十全十美,于是洋洋灑灑的“如果我是你我會怎么做”。讀著讀著,突顯其中焦慮:比起劇評人,也許他更想當導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