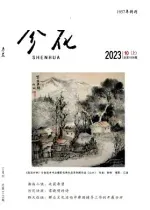王云鵬的油畫主義
跟云鵬做同事,將近三十春秋。漫漫歲月里,他好像只做了一件事——作畫;我好像也只做了一件事——作文。文畫雖為兄弟,我卻沒法與他相提并論。一謂甚高,一謂甚遠。他賣畫完全可以置房置地,我賣文無外乎添些油鹽醬醋。慚愧!
不過,從云鵬到油畫,我的心底確實私存了許多感想,相見的時候則另當別論。直到如今,碰了面,多半是戲言,未曾探討過油畫。呵呵,跟云鵬談油畫,尤其談云鵬的油畫,那我不是在“大巫”面前冒充“小巫”嗎?
何況“小巫”也冒充不了,冒傻氣而已。
喜歡云鵬的油畫,卻由此及彼,一幅又一幅。這回,云鵬將自己的得意之作匯成一集,曰《王云鵬:中國當代油畫藝術名家》,再度興奮了我。知天命的人,還會為朋友的油畫所興奮,實乃偏得。卻原來,里應外合,是云鵬潛入了我的記憶又迭出了我的記憶,讓我喜不自勝,又欲說還休,深怕誤讀了大師。
對,我經常叫他大師。我知道,這里面的感情成分居多。可是,當我再三再四地欣賞了云鵬的《山路》《山雨》《花蜻蜓飛走了》《秋日印象》《留住春天的風》《畢加索的鴿子》《香月嫂子》《紅蓋頭》以及《關東大姑娘·大身板》《關東大姑娘·大月亮》之后,我便情愿叫他大師了,算是舞文弄墨之人的一種由衷期望吧。我當然承認,大師至少應該具備三個條件,即雅俗共賞、承前啟后和一家之說。好在云鵬不斷地朝著這些方面努力,并且漸有長進,只是他不肯自吹自擂罷了。不肯,
僅僅是不肯嗎?早在十幾年前,油畫大師陳丹青來長春簽售《紐約瑣記》,席間便放言:“云鵬的油畫太他媽棒了,讓男爺們兒看了春心蕩漾!”
是不是“春心蕩漾”姑且不論,反正云鵬的油畫擺在眼前,什么人都不會無動于衷。譬如那幅《關東大姑娘·大身板》在北京中國美術館展出,一下子點亮了眾多來賓的目光,啟功先生更是喜出望外,欣欣然,執意要親手摸摸畫面上試牛仔褲的那個村姑的屁股,逗起周圍人的一片笑聲。我呢?有機會見證他一幅一幅油畫的誕生,卻沒機會領略他一個一個模特的真貌。想請他做個媒人結識二三,他總是嘻哈而過,年復一年,白費了我貪婪的眼癮。
所謂云鵬——“天邊云起,地上鵬飛。”
這是對畫家云鵬的解讀!
云鵬的油畫,走的是現實主義路線,亦即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無須避諱,這是藝術創作的老套子,往往費力而不討好。所幸,他的現實主義注入了浪漫主義,久而久之,形成了獨家的云鵬式的油畫主義,既“入世”又“超世”。梵高曾對弟弟說,沒有什么是不朽的,包括藝術本身。唯一不朽的,是藝術所傳遞出來的對人和世界的理解。云鵬成長在鄉村,成名在部隊,因而他的選材、手法、立意與取向,完全是純凈的詩意和詩意的純凈,透視著生活的小美與藝術的大美。美,或許是云鵬創作的最低綱領,又何嘗不是最高綱領?從云鵬到油畫,美是一把鑰匙。盡管他的作品被境內外的諸多收藏家一一收藏,但鑰匙始終存放在自己的心里。小美是入口,大美是出口,始始終終。
有入口和出口的畫家是幸運的,如云鵬。
相對而言,我比較喜歡西方油畫。近看一片疙瘩,適當退后,立即萬千氣象。當然,前蘇聯的油畫作品,對解放后的中國油畫家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直至形成了更加東方的“油畫語言”,比如劉春華的《毛主席去安源》和羅中立的《父親》一類代表作。而靳尚誼的精深和張曉剛的詭異,也傾力為中國油畫擴展了領域。我無意拿云鵬的作品硬往這些頂尖級人物身邊靠,靠也靠不近的。我只是以為,云鵬的作品之所以被圈里圈外的許多人喜愛,不是在于探索,而是在于守望。尤其是中國東北油畫的鄉土氣息和人物形象,分明是一種守望式的文化認知和實踐。從這個意義上講,云鵬的執著與進境,最核心也最根本的成因是傳統文化,而非現代藝術。
這些年來,云鵬弄墨“弄”出了名堂,而且是大名堂。油畫藝術節甚或當今藝術市場,多少行家和買家都在關注他、捕捉他。而同事和友人面前的云鵬,依舊是經常性的笑臉。云鵬的笑臉,比語言更殷勤。只要遇到對心思的,一律先哈腰,先點頭,進而笑臉盈盈。在這溫柔的背后,卻深藏著一個藝術家的堅定與冷靜。有道是:“富有常常溫柔。”那么,云鵬的溫柔,想必來自人生和藝術的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