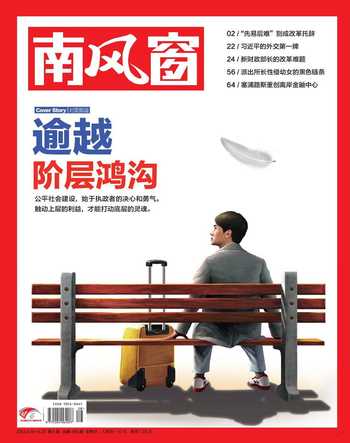地方“機場修建熱”的政經邏輯
李克誠
“江蘇9個機場7家虧損”,“地方政府為給機場‘輸血,甚至出文件強迫下屬單位包機出國”……今年年初,隨著媒體的曝光,“中小機場虧損”再次成為輿論的焦點。其實,不僅在江蘇,在全國范圍內,中小機場虧損已成為“公開的秘密”。
據中國民航局披露的數據顯示,我國現有182個民用機場中,有135家(約占74%)機場處于虧損。令外界不解的是,在此背景下,各地對修建機場的熱情卻有增無減、快馬揚鞭—“十二五”期間,我國將新建機場70個、改擴建101個—這幾乎是過去10年的總和。從地域分布上看,新一波“機場熱”正從東部沿海發達地區波及、擴展到中西部地區。
地方政府如此鐘情機場項目,背后隱藏著什么邏輯?
機場虧損難掩投資熱
中國民用航空局“掌門人”李家祥也許是最能感受到這股“機場修建熱”的人士之一。2010年,先后有29個省(區市)的53位省級領導前往中國民航局洽談合作事宜。據李披露,僅3月8日那一天,就有10個省份的省領導拜會民航局,“我們打開所有的辦公室進行接待”。
不過,在民航局“賓客盈門”盛況的背后,則難掩各地機場紛紛虧損的尷尬。李家祥披露,近年來我國機場每年虧損數約為20億元,平均每座機場虧1500萬~1600萬元。這些虧損的機場,需要依靠政府的持續補貼才能維持運營。
不僅如此,據政府部門人士向《南風窗》記者介紹,為了維持航線的運行,地方政府還會新開航線航班給予航空公司補貼,這也是各地通行做法。以江蘇為例,省里每年撥出8000萬元“國際航線培育專項資金”支持南京祿口國際機場,各地級市政府也紛紛效仿:最近3年常州市每年拿出5000萬元對航線航班實行保底補貼,連云港、南通、鹽城、徐州等地每年給予的航線補貼也均在2500萬~3300萬元左右。
據中國民航大學航空服務研究所所長李曉津的研究,在我國,一個機場要保證100萬左右的年客運量才能實現盈虧平衡。而這幾年新上馬的機場多屬于年吞吐量在20萬左右的小型機場,這也意味著,這些蜂擁上馬的項目,將會繼續步已有機場“連年虧損”的后塵。
那么,地方政府為何明知可能會虧損,仍愿意投資修建機場呢?對此,李家祥多次在不同場合給予回應,他認為,“絕不能簡單地從經濟效益上考慮中小機場建設投資、運營虧損等問題,而要從當地經濟社會發展角度來看待中小機場的綜合效用。”交通運輸專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經管學院教授張寧在接受《南風窗》記者采訪時也表示,在分析和評估機場的價值時,絕不應把機場僅僅簡單地看成一個普通的盈利的企業、單獨考量其財務成本。他說,事實上,機場作為重要的公共基礎設施,對地區發展的帶動往往是綜合性的。
最常被業內人士引證的論據是:按照國際權威機構測算,民航投入和產出比率是1︰8。國際機場協會(ACI)研究認為,機場每百萬旅客吞吐量,可以產生經濟效益總和1.3億美元,相關就業崗位2500個。
最近兩三年,中國民航局局長李家祥每年都受邀前往中央黨校,為多個省部級、司局級等中高級領導干部班講授“發揮民航業的戰略作用”,向地方大員們“灌輸”民航業如何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的理念。據介紹,一座支線機場的跑道約3公里、投資額三五億元,相當于3公里高鐵的投資。“一條3公里的高速鐵路,對一個地方的發展來說,它的作用極其有限。但一條3公里的飛機跑道,卻能把這個地區與整個世界聯系起來。”李家祥形象地說,“過去,人們常常講,‘要致富先修路!現在則是,‘要開放修機場,要想強上民航!”
目前,已有多個省份明確提出要把民航業作為新型戰略支撐產業來打造,宣稱要建設“民航大省”,并紛紛加快對機場的投資布局。
湖南稱,“十二五”期間,將完成邵東等4個機場建設,到2020年該省的機場將達到12個,“屆時將成為中南地區機場數量最多的省”。四川規劃,未來10年該省民用機場總數將達到17個。內蒙古也提出,“十二五”期間,將新增5個支線機場、7個通勤機場,到2015年末,全區的民航機場將達到20個……
地方經濟的“經濟賬”與“政治賬”
我國2003年機場屬地化改革后,機場的所有權和建設的決策權從民航局轉移到了地方政府。各地投資建設機場的積極性被調動起來。
特別是,最近幾年,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央和地方政府加大了對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投資力度。中央也開始從戰略層面重視并推動民用機場建設,2012年《國務院關于促進民航業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要“加大”機場建設力度,“適度超前”。這也是最新一波“機場修建熱”的背景所在。
而修建機場、開通航線對地方政府的好處也顯現出來。江蘇淮安機場自2010年通航以來,政府每年給予機場虧損的補貼約在1000萬元左右,但據淮安市提供的資料,2010年淮安機場建成的當年,淮安招商引資的實際到賬就突破了10億美元。目前,在淮安落戶的臺資企業已達到850家,這也使身處內陸地區的淮安成為繼深圳、東莞、蘇州之后全國第四大臺資聚集區。
江蘇鹽城,也成為利用機場和航線資源拉動區域經濟發展的典型。2003年,韓國現代起亞集團決定在鹽城投資建設“汽車城”,條件之一就是必須開通鹽城至韓國的航班。鹽城市政府財政補貼3000萬元開通了鹽城—首爾國際臨時包機航班。爾后,“汽車城”項目以及600多家與之配套的相關韓資企業也紛紛落戶鹽城。“政府每年補貼在航線和經營上的經費是3300萬,但企業每年繳給政府的稅收就是30多億,一本百利。”李家祥多次公開肯定鹽城機場。
修建機場,不僅有助于提升城市形象、招商引資、發展地方經濟,還是增加地方固定資產投資、GDP的“法寶”。這些都影響到地方主要領導人的政績和晉升。這也是地方領導“偏愛”建機場的另一原因。
在當前的政治語境中,通過經濟競賽來獲取政治提拔是地方政府官員晉升的主要途徑。而政治權力的金字塔結構決定了只有有限數目的官員可以獲得提升,這也意味著,同層級的地方政府主要官員之間,都處于一種政治晉升博弈中。因此,追求自身政績(GDP)的最大化,就成為不少地方主要官員不得不考量的“政治賬”。特別是最近幾年,在“穩增長”的大背景下,機場等大項目的投資建設,可用來抵消出口下滑和房地產調控對地方GDP增長的影響,因此,上馬機場等大項目,成為不少地方政府秘而不宣的操作“策略”。
“超前”建設的隱憂
盡管《國務院關于促進民航業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機場規劃建設既要“適度超前”,又要“量力而行”。但由于“適度超前”在操作層面缺乏清晰的界限,外界擔心,某些地方政府很可能會打著“適度超前”的旗號而行“過度超前”之實,或者盲目上馬機場項目,或者過于“超前”建設。
這已有前車之鑒。1992年,南方某市斥資40億元建設國際機場時,曾“大手筆”將該機場設計規劃成年旅客吞吐量為1200萬人次的大型機場。然而,該機場通航12年后,客運量才首次突破100萬。去年,該機場旅客吞吐量迎來了歷史上最好的成績—209萬人次,也僅相當于當初設計載客負荷的1/6。外界看來,該機場之所以常年陷入虧損,與其最初設計“過于超前”以及該地區過于密集、過度競爭的機場布局相關。
如今,相似的一幕仍在上演。以京津冀地區為例,按照發展規劃,在未來,該地區21.61萬平方公里的狹小空間內將存在11個機場,其中河北省內就有9個,上述任何兩個機場之間幾乎均在1.5~2小時車程內。在南北狹長的河北的東西兩側,又分布著太原機場和濟南機場等多個機場。如此眾多的機場布局在如此狹小的空間里,在外界看來,不免有重復建設之虞,也加劇了該地區機場間的過度競爭。而其帶來的消極后果,或許需要在未來多年后才能得以充分暴露和顯現。
就拿目前占據全國客運市場份額最大、經濟效益看起來最好的三大機場(北京首都、上海浦東、廣州白云)來說,其沉重的財務負擔已非外界所能想象。中國民航管理干部學院機場管理研究所所長譚惠卓向本刊記者介紹,三大機場的累計投資額均已超過400億元,近10年的投資中有40%靠銀行貸款,每年僅還本付息的資本成本高達20多億元。三大機場“除了在短暫的投資間歇期可能有較好的經濟效益之外,長期不可能產生良好經濟效益”。
對于那些熱衷于上馬機場項目的地方政府而言,這也許是一個最為清醒的警示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