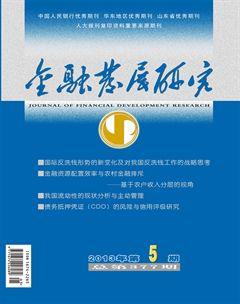金融資源配置效率與農村金融排斥
隋艷穎 夏曉平
摘 要:本文構建了不同收入層農戶的借貸違約風險結構模型,并利用該模型深入分析了不同收入層農戶的違約風險、對金融機構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和不同收入層農戶所遭受的金融排斥類型。研究結果表明:在農戶高、中、低三個收入層中,金融資源傾向于流入高收入層,高收入層最不容易受到金融排斥。中收入層金融資源的利用效率最高,卻最容易受到農村金融機構的供給排斥。低收入層對金融資源的有效需求不足,受到的金融排斥更多地表現為自我排斥。因此建立一個多元化格局、適合不同收入層農戶金融需求特點的農村金融體系是提高農村金融資源利用效率、緩解農村金融排斥的一個合理有效的途徑。
關鍵詞:農村金融;金融資源; 違約風險; 金融排斥;收入分層
中圖分類號: 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2265(2013)05-0008-06
一、引言
我國的農民承擔著自然、市場、政策等多重風險,貸款是農民抵御風險、緩解流動性約束和平滑消費波動的重要途徑,也是農民增加農業投入的重要支撐力量。但是,我國農村金融發展的現狀并不理想,金融資源錯配、信貸分配失效、金融資源利用效率低、金融排斥嚴重等問題使金融資源支持“三農”的功效大打折扣。我國農村金融供給采用的基本方式是政府主導帶補貼性質的指令性信貸方式。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農村金融機構以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導致農村金融供給主體在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之間難以權衡。從需求角度分析,不同收入層農戶的資本積累狀況、風險承受能力存在一定的差異性,對金融資源的需求強弱不一,但農村金融機構通常將其統一定義為高風險、低收益群體,從而在金融資源配置過程中排斥農村,割裂了農村金融需求與供給之間的聯系。
國內關于農村金融資源配置的研究多集中于農村金融資源配置是否有效,配置效率對農業經濟增長、農民收入提高的作用效果等方面,如鐘笑寒(2005)、朱喜(2006)、楊棟(2007)等人的研究。鮮見有人對不同收入層農戶的金融資源配置進行研究,而專門對農村金融資源配置過程中引發的金融排斥的研究更是一項空白。當前金融機構面向農村市場時,無視不同收入層農戶金融需求的差異,先驗地統一定義農戶“高風險、低收益”的信貸特征假設,可能恰恰是農村金融資源配置錯位、利用低效的癥結所在。基于此,本文擬從農村金融(本文研究中的農村金融僅指農村正規金融,并未涉及到農村非正規金融)的需求和供給兩方面出發,分析在農村金融資源配置過程中不同收入層農戶的違約風險和借貸收益,對不同收入層農戶的金融需求和金融機構的供給優先進行配對,并根據配對結果來揭示不同收入層農戶的金融排斥類型,進一步從提高農村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緩解農村金融排斥的角度提供政策建議。
二、文獻回顧
隨著我國農村金融改革的不斷推進和政府對“三農”問題的高度重視,學術界紛紛圍繞農村金融相關的問題展開研究。特別自農村金融機構商業化改革以來,農村金融資源配置效率更加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焦點。我國農村金融資源配置低效也已成為各界共識。相關的研究表明,一個功能完善的農村金融市場在提高農村資源配置效率過程中起到核心作用。但是,經濟轉型的國家由于缺乏有效的農村金融市場體系,國家的財政、金融部門對農村資源的配置效率是低下的。OECD(2001)通過對我國農村經濟體系進行研究進一步驗證了上述結論,他們認為我國農村金融的主要問題是農村信用和風險管理市場不完善,地方政府的趨利行為、尋租行為造成財政、金融資源低效配置和大量轉移。金融體系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資金配置功能,我國缺乏合適有效的農村金融機構,已經成為阻礙農民收入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我國,政府常常被賦予扶持農業信貸的重任,指令性的農村信貸模式導致他們為農民所提供的越來越低息的信貸對于刺激農業發展的效果微乎其微。在缺乏穩定的農業資本形成機制的大環境下,支農資金的增加不僅無助于農業經濟的增長和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還起到了抑制作用。農業對政策信貸依賴性強,金融機構的農村貸款投入在長期與農民收入、農村投資之間不存在均衡關系,在短期也未能有效地促進農村投資的增加和農民收入的增長,從而致使農村經濟發展存在資金投入不足和資金配置效率低的雙重瓶頸。另外,地方政府“政績至上”所引發的投資沖動和不規范行為往往使大量的農業信貸資金和財政支農資金從農業流向其他行業或者被揮霍浪費掉,造成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資金短缺的狀況一直難以得到有效緩解。特別是在農信社的改革中,當地方政府介入后,農信社的信貸資金供給出現明顯的“錯配”現象,“錯配”的程度也隨著地方保護主義的強化而加重。在農業信貸與農業經濟增長的關系中,二者之間的弱相關性、單向傳導性及農業弱質性與信貸資金逐利性之間的矛盾,導致了農業對信貸資金缺乏吸引力,阻礙了信貸資金流向農業。農村金融資源配置的低效率不僅阻礙了農業經濟的發展,而且加劇了農村受到金融排斥的程度。農村金融機構為了緩解資源配置低效率的壓力,大幅度地撤并其基層分支機構,導致了農村金融的空白。由于這一空白未能被其他農村金融機構填補,“撤并事件”對農村經濟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農村金融機構“脫農變異”、信貸配給不足現象普遍。據銀監會的統計顯示,截止到2007年末,獲得貸款支持的農戶數占到全國農戶總數的32.8%。但在真正有貸款需求的農戶中,仍有近40%農戶的貸款需求得不到滿足,大量農戶被農村金融機構排斥在外。
綜上所述,已有研究涉及我國農村金融資源配置的各個方面,也取得了較為豐碩的研究成果,這為本文研究的進一步開展提供了經驗和方法上的借鑒。但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外部環境和內部機制對農村資源配置的影響上,研究視角和切入點也大多集中于農村金融資源的整體配置效率,針對農村金融資源的直接配置對象農戶的影響分析較少,對不同收入層農戶金融資源配置分析也僅在為數不多的研究中出現過。因此,在現行的農村金融資源配置過程中,對不同收入層的農戶制度安排是否適當?哪一個收入層最容易在金融資源配置過程中受到排斥?回答清楚上述兩個問題,可能對重新設計農村金融的供給方式、提高農村金融資源的利用效率更有意義。所以,本文研究一個突出的特征就是從不同收入層農戶的信貸資金需求特征這一視角出發,探討農村金融資源配置對農戶金融需求的影響及其受到金融排斥的狀況。
三、不同收入層農戶借貸違約風險結構模型
(一)Black-Scholes-Merton違約風險結構模型
1973年美國金融學家布萊克和斯科爾斯(Black和Scholes)首次提出了后來被稱為B-S模型的期權定價公式。1974年默頓(Merton)提出了將期權定價理論應用于公司價值評估的方法,并利用期權理論進行了定價分析,形成了Black-Scholes-Merton股票期權定價模型的基礎。在該模型中,對違約風險的測度表述為:如果只存在單一的賬面價值為D、到期日為T的債券,假設在T時刻,當AT≤D時發生違約。其中,AT為公司總資產價值的買方期權。該模型認為,公司資產的市場價值符合對數正態分布。資產A的總價值大約等于股票市場價值和債務賬面價值之和。在時間t向T運動的過程,從資產價值在到期日T的概率分布中就可以得出違約概率(見圖1)。
(二)不同收入層農戶借貸違約風險結構模型
金融機構信貸決策是一項復雜的金融工程,金雪軍等(2008)通過研究違約風險與貸款定價的內在關聯、貸款定價中違約風險的理論、違約風險與貸款定價的實證分析等問題發現:違約風險通過降低信貸市場效率和信貸合同價值影響金融機構貸款定價決策。因此研究不同收入層農戶的違約風險,對分析農村金融機構信貸決策具有重要的意義。
構建不同收入層農戶借貸違約風險結構模型基于兩個基本假設:
假設1:農戶資產總值符合對數正態分布。
對數正態分布的機理是當某個隨機變量受到許多獨立的隨機變量“均勻”影響時,該變量是服從對數正態分布的。相關研究證明反映系統規模大小的社會經濟指標可以用對數正態分布來描述。其中,社會經濟指標是反映社會經濟系統狀態的特征量,其絕對量可以從總量上反映系統規模大小,如人員總數、產值、資產總值等。農戶資產總值可以作為描述農村社會經濟指標的絕對量。依據上述推理,可以認為農戶資產總值符合對數正態分布。
假設2:農戶是厭惡風險的。
2. 放寬假設條件,僅假設[μ1=μ2],由于[A1=A2],相同額度的生產投資,較低收入層的農戶需要借入更多的資金滿足生產,即[D1 四、不同收入層農戶金融需求與供給配對及金融排斥類型劃分 相對經濟效益而言,“三農”事業的社會效益更為明顯,但是金融機構作為理性的經濟人,追逐經濟效益也無可厚非,利益驅使農村金融機構在提供金融資源服務的過程中,明顯排斥低收益的農村地區。即使服務農村地區,金融資源也傾向于流入高收益低風險客戶群、排斥低收益高風險客戶群,重視商業化最優、忽視社會化最優。在初始資本、風險收益、信貸成本三大因素影響下,農村金融資源需求主體對金融資源需求差異化特征明顯。所以同質化的金融資源供給和差異化的金融資源需求無法達到合理匹配,需求與供給的嚴重錯位,使本來就遭受金融排斥之苦的廣大農村地區金融排斥程度愈發嚴重。 (一) 農村金融資源配置:供給方面 (二)農村金融資源配置:需求方面 假設農戶的借貸違約概率為[ρ(X,m)],其中[ρ(X,m)∈[0,1]]是[X]和[m]的函數,則農戶借貸者取得預期最大收益的概率為[1-ρ(X,m)],需要支付的利息成本為[i],交易成本和其他隱性成本為[z],收益為[R]。為了分析簡便,假設農戶借款數額為1。 農戶不同收入層的借貸需求決策為: (三)小結 從農村金融資源配置的供給和需求兩方面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 在農村金融交易市場上,最容易達成的交易組合為([E1,R1])。此時農村金融機構和農戶高收入層均達到了效用最大化,這也解釋了在農村金融信貸配給中,富裕農戶更容易獲得貸款的現象。在農村金融資源配置中,高收入層相對其他收入層顯然更不容易受到農村金融機構的排斥。 2. 最難達成的交易組合為([E3,R3])。由于最低收入層農戶違約風險最高,農村金融機構對其提供借貸也更為謹慎,申請條件也較為苛刻。比如提供抵押物,低收入層一般都無法提供有效的抵押物作擔保。對于低收入層,他們獲得信貸的目的可能更傾向于平滑消費,而當前農村金融機構主要服務于農戶的生產投資資金需求。從供給角度看,低收入層的金融資源供給明顯不足,受到了嚴重的信貸資源約束。農戶中的低收入層出于對借貸收益性和風險規避性的考慮,即使投資機會有利可圖,也不愿意向農村金融機構申請貸款,信貸資金的有效需求不足。這就在供給和需求之間形成了一個“真空地帶”。巴德漢和尤迪曾經提出,農村居民越是貧困,利用信貸平滑其波動收入流的動機就越強。但是,由于“真空地帶”中缺乏金融資源運動,這種平滑作用可能會無法實現,這也就大大降低了農戶中低收入層的借貸動力。在農村金融資源配置中,低收入層存在雙向金融排斥,一方面是農村金融機構的信貸機制排斥,另一方面是低收入層的自我排斥,自動放棄獲得金融資源的機會。 3. 介于中間的交易組合為([E2,R2]),主要體現了中收入層農戶在農村金融交易市場中的地位。這一收入層有借貸的動機,但是受到了違約風險和借貸收益的限制。農村金融機構在其有限的金融資源配給中優先考慮的是高收入層。因此,中收入層的借貸需求很難得到滿足。現實的情況是,在農村金融交易市場上,高收入層有借貸需求并能夠得到金融供給;低收入層沒有借貸需求或借貸需求不足,并且也得不到金融供給;中收入層是有借貸需求,但是難以獲得金融供給,成為當前農村金融供給排斥的主要對象。朱喜、李子奈(2007)的研究顯示,從借款的收入分布來看,可用資金的分配明顯偏向于富有的農戶。收入最低的15%的農戶得到的借款只占到總量的6.0%,而收入最高的30%的農戶得到總借款的48.3%,借款向富有農戶集中的趨勢十分明顯。借款對最貧困和最富有的農戶的收入作用不明顯,但是顯著促進了中低收入農戶產出的增加,其產出彈性約為0.08。以上表明,目前我國農村金融資源的這種配置方式,導致了最有活力的中收入層難以得到信貸支持,受到嚴重的金融供給排斥,這明顯降低了農村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農村金融機構的信貸配置機制導致農戶中占多數比例的中低收入層無法獲得資金支持,迫使其在需要資金支持時更多地轉向非正規金融。根據馬曉青(2010)對5省1412個農戶樣本融資偏好的調查,發現80%以上的樣本農戶在具有資金需求時首先選擇求助于非正式渠道,只有不到20%的農戶會優先考慮向正式機構融資。
五、結論及政策建議
基于農戶收入分層的視角,本文對農村金融資源配置與農村金融排斥特征進行了相關研究,并得出如下結論:(1)不同收入層的農戶信貸違約風險存在差異:高收入層農戶的違約風險最低,低收入層農戶的違約距離最短、違約速度最快、違約風險也最高。(2)在農村金融資源配置中,低收入層農戶并不是受到金融排斥最嚴重的階層。從金融供給方面看,低收入層農戶受到的金融排斥最嚴重,但從金融需求方面看,由于低收入層農戶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匱乏、風險承受力低、維持生活的意愿高于擴大生產的意愿,因此對農村金融市場的參與程度較低。低收入層農戶實質上不是受到了金融供給排斥,更多是源自于有效需求不足的金融需求自我排斥。(3)從風險收益性來看,中收入層農戶是農村金融市場上最具活力的一個階層,也是受到金融供給排斥最嚴重的一個階層。一方面他們信貸需求旺盛、信貸邊際效用顯著,另一方面由于風險高于高收入層而使他們受到嚴重的金融供給排斥。與高收入層相比,中收入層農戶主要從傳統的農業生產中取得收入,面臨的不確定性較大,他們只有很少的個人財產,幾乎無法提供正式的貸款抵押物。因此,信貸資源傾向于流向高收入層,中收入層信貸需求難以得到滿足。這種農村金融資源供給與需求的錯位,明顯降低了農村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
基于上述分析,我們認為農村金融資源配置取決于農村金融資源需求和供給之間的相互作用,農村金融排斥無論是信貸約束還是自我約束都離不開對金融資源需求主體的特征差異分析。在沒有明確不同收入層農戶金融資源需求特征的情況下,單純依靠增加農村信貸投入的數量,而不考慮信貸分配效率,不僅造成資源的極大浪費,而且對準確定位農村金融排斥主體、緩解金融排斥程度也是低效的。因此,建立多元化格局的農村金融體制、改變農村金融資源配置的基本模式、適應農戶多樣化的金融需求對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和緩解金融排斥可能更為有效。
具體而言,對于高收入層農戶,他們有一定的資本積累,能夠滿足信貸抵押要求,借貸資金多用于生產性投資,經營風險相對較小,更適用于現有商業性的農村金融模式。但是相對服務城市而言,服務農村的金融機構的比較收益仍然是較低的,這就需要政府按照農村金融服務“三農”的業績提供一定扶助和補貼,調動商業銀行服務“三農”的積極性。
對于中收入層農戶,他們資本積累不足,幾乎無法提供正式的信貸抵押物但又具有一定的償債能力,其借貸資金既要用來維持生產又需要平滑消費,不確定性較大,但是信貸的使用效率卻最高。目前,我國農村地區設立的中小金融機構,如村鎮銀行、農村資金互助社、小額貸款公司等的經營特點對這一階層更為有利。但是,為了降低借貸過程中的道德風險和避免逆向選擇問題,中小金融機構常發生“偏農脫農”行為。因此,需要通過給予政策性優惠,建立金融保險配套機制,降低中小金融機構的貸款風險,增強其服務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對于低收入層農戶,他們的資金需求主要是用來維持生存性消費。對這一階層,任何具有商業屬性的金融模式都不適應,他們一方面表現為信貸需求彈性為零,不接觸任何信貸資源,僅維持現有生存狀態,變動意愿不強,另一方面表現為信貸需求彈性為無限大。為了平滑突發性消費,他們可以接受高成本的信貸資金,并且多數情況以違約而告終。對于以營利為目的的金融機構而言,這一階層絕對不會是他們首選的目標客戶群,扶貧式的資金支持模式可能更為有效。但是也要防止產生過度依賴行為,扶貧資金支持模式要從“輸血模式”轉化為“造血模式”。綜合看來,只要理順了農村金融資源配置過程,明確農村金融排斥的主要群體和排斥類型,也就確定了不同收入層農戶受到金融排斥的程度和類型,從而可以通過構建多元化的農村金融體制、探索一對一的資源配置模式來有效緩解供需錯位所導致的農村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低的現實壓力。
參考文獻:
[1]陳雨露,馬勇.地方政府的介入與農信社信貸資源錯配[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0,(4).
[2]林毅夫.金融改革與農村經濟發展[J].北京大學中國經濟中心討論稿,2003,No.C2003026.
[3]張杰.中國農村金融制度:結構、變遷與政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4]吳恒煜,張仁壽.結構化模型中違約概率的比較靜態分析及實證[J].系統工程,2005,(5).
[5]杰弗瑞·A·杰里,菲利普·J·瑞尼.高級微觀經濟理論[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6]Koester,Ulrich.CAP is Something We Can be Pround of,Working Paper,University of Kiel,2000.
(特約編輯 齊稚平;校對 YJ,S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