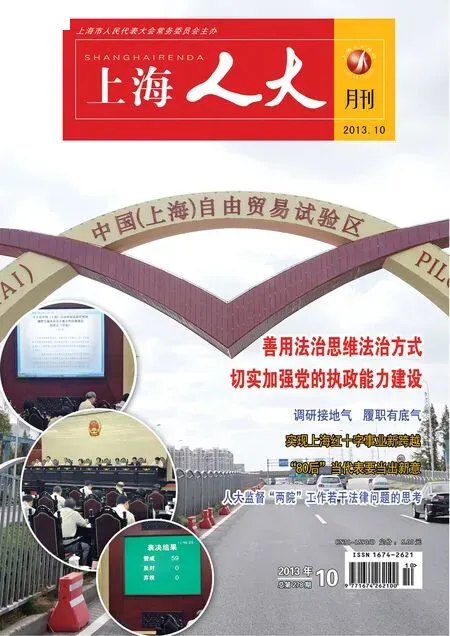用“法治紅線”守住“師德底線”
文/孫霄雋
用“法治紅線”守住“師德底線”
文/孫霄雋
教師,被譽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尊師重教歷來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近年來,從“最美女教師”張麗莉到“最美鄉村教師”的全國評選,來自教師群體的敬業奉獻故事不斷被媒體聚焦,每逢教師節,那些站在講臺上的“最美”也總能引起全社會的感動。
但是,從9月初湖北恩施某中學駭人聽聞的校園性侵事件,再到“幼兒園老師殘暴虐童”、“老師結婚給全班孩子發請帖”、“小學女生因答不出題遭受體罰”等一系列的報道,個別教師違背職業道德,逾越社會底線的違紀違法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損壞了教師的道德形象和社會認同。在教師節這個本該倡導師道尊嚴的節日里,師德問題,卻再次成為了公眾熱議的焦點。
學為人師,行為世范。作為一個“傳道、授業、解惑”的職業,教師的個人品德和舉止言行對孩子有著最直接和最深遠的影響。所以當涉“教”丑聞頻頻曝出之后,看似偶發的“師德問題”也必須引起全社會的重視和反思。
針對近期出現的一系列師德不端行為,在今年教師節前夕,教育部制定出臺了《關于建立健全中小學師德建設長效機制的意見》,其中規定“體罰學生、收受學生禮物、有償補課等都被列入師德禁行行為的‘紅線’,實行‘師德一票否決’評價機制……”希望通過劃出的這條“師德紅線”,守住全國1442萬名教師的“師德底線”。教育部這一做法是及時并值得肯定的。
就有效貫徹實施《關于建立健全中小學師德建設長效機制的意見》而言,也許如下問題是值得思考的:抽象的師德高低該如何評判?有違師德與違法間如何界定?采取“師德紅線”這種“高壓嚴打”的態勢能否管得住教師的“師德底線”?以考評師德表現的方式來約束和規范教師的職業行為,從操作的角度講,本身就是一種挑戰。
道德是一種約定俗成的習慣性規則,是在長期實踐過程中逐步形成的社會共識。師德問題更是屬于社會意識形態的范疇,評判教師的師德表現必須用事實說話。誰師德高尚,誰師德低下?誰來評判,怎樣評判?填表、打分、談話是必須的。但如果僅是以考評方式來衡量教師的師德,如果不能剔除其中諸多的人為因素,會使得制度的執行變形走樣,會使考評很難具有說服力,從而難以被廣大教師和全社會認可和接受。
在此之前,教育部門就曾多次出臺過中小學教師職業道德規范,規定教師應為人師表,堅守高尚情操,知榮明恥。但仔細回顧那些“師德淪喪”的案例,很多已經超出了道德規制的范疇。如果說收受禮品錢財、有償家教等還存在著“你情我愿”的道德因素的話,諸如強奸、猥褻、虐待學生,那已絕不是道德問題,更是法律問題,而且是涉及犯罪的問題。
我國的《教育法》、《義務教育法》、《教師法》、《未成年人保護法》中,早已明確規定了教師的職責,以及侵犯學生權益需承擔的法律責任。但對于校園中發生的侵權事件,一些地方的教育部門和學校從維護當地的教育形象、個人利益出發,往往實行內部處理,以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這無疑是對違法侵權事件的包庇和縱容。可以說,師德漸微的現狀與當下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法治環境有著密切的關系。法律的懲戒力和威懾力遠在道德規范之上,如果現有法律執行不到位,通過行政手段來規范師德的成效也會大打折扣。
毋庸置疑,教育部門會為加強《關于建立健全中小學師德建設長效機制的意見》的執行力作出不懈努力的。同時,筆者相信,教育部門也會意識到,遏制師德亂象、守住“師德底線”需要多管齊下,標本兼治,重在治本。從根本上講,要端正師德、阻止教師侵犯學生權益的事件再次發生,當務之急是要嚴格地、不折不扣地落實好《教師法》、《義務教育法》、《未成年人保護法》中關于保護學生權益的條款,而不是讓這些條款只是停留在文本上,同時積極推進相關立法,把當前的師德禁令法律化,如規定教師收受財物達到多少數額即為受賄等,明確法律認定、處罰界限以及申訴或救濟的渠道,用法律武器追究侵權人的法律責任,用法治思維來規范和約束廣大教師的職業行為,用“法治紅線”斬斷那些妄圖伸向學生的“黑手”,保護教師和學生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