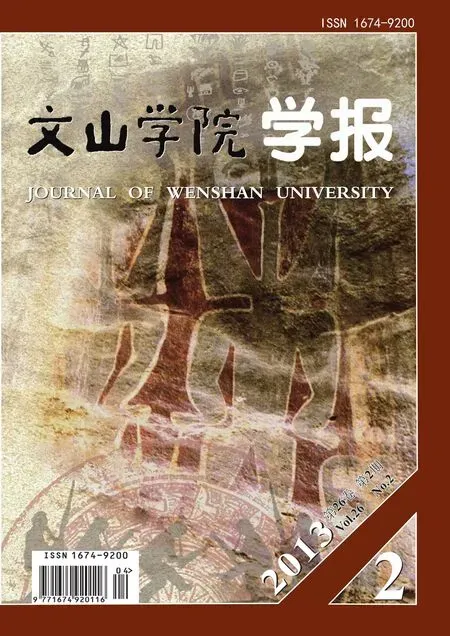網絡傳媒對公共權力的制約監督
梁耀東
(長沙學院 法學與公共管理系,湖南 長沙 410003)
2011年我國網民的搜索引擎使用率為79.4%,微博用戶環比增幅296%,用戶交互式信息配置方式已經取代了傳統信息配置方式[1]。隨著傳統的線性傳播方式轉變為“裂變式傳播”,網絡傳媒悄然成為制約和監督公共權力的強大輿論力量,如同懸在公權力掌握者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在網絡集群行為和群體極化現象發展的同時,網絡輿論和網絡輿論情緒都對現實社會和政府產生了強大的影響力。
一、網絡傳媒緣何對公共權力形成強大影響力
(一)科層制政府監管網絡傳媒的成本較高
究其深層原因,主要是它背后的經濟因素。媒體注重的是爆炸性新聞的效益,所以網絡媒體總試圖繞過監管發布轟動的消息而獲取更多的點擊率。網絡曝光后傳統新聞媒體的跟風也有類似的動因:既然當初不是自己爆料,就無需負擔發布者的責任,它們便爭先恐后地報道以爭取收視率。各種媒介競相互動的“第二媒介時代”網絡傳媒在傳播意義上超越了國家的控制[4](P10)。
傳統媒體擅長議程設置,它們告訴人們應該對哪些公共事務進行思考,從而組織和安排人們腦中的“擬態環境”[5](P16)。不同于電視和紙面媒體,在網絡中進行議程設置的效果更難預計,網絡傳媒中不僅新聞發布較少受控,而且信息受眾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會“選擇性接觸”與他們態度相一致的信息[6](P209-234)。管理部門要跟蹤調查網絡議程設置所取得的效果則更難,工作量也十分巨大,就更難說全面掌控網絡傳媒的議程了。
(二)傳統媒體未擔負起其應有的社會責任
威爾遜曾言:“公共輿論對于精英的冒險行為可以起到一個剎車的作用,使政策制定者由于害怕失去大眾支持而不去走極端。”[7](P184)公共輿論包含著對民生的關注、公眾對社會的價值判斷,以及對公共權力的道德評價。傳統媒體的輿論對于公共權力的制約監督作用已毋庸置疑,西方亦稱之為第四種權力。比如,在第一修正案的庇護下,美國記者對權力、暴力和腐敗的監督:佛羅斯特之于尼克松、穆羅之于麥卡錫、西摩赫什之于越戰和伊戰、斯蒂芬斯之于美國城市腐敗等都是經典的例子。從反戰到反迫害,從善款去向到國宴菜譜,從食品安全到公務員工資[8],傳統媒體幾乎無孔不入,相應的監督也接踵而來。且不說C-span對國會唇槍舌戰的全面直播和報刊雜志上對政府“吹毛求疵”的漫畫和時評,就連晚飯后的黃金時段都充斥著各類政治脫口秀。
有學者認為美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轟轟烈烈的“揭黑運動”源于新聞界的理念、制度和傳統[9],也有學者認為媒體揭丑的動力是基于“法—政治”邏輯的政治理念、信仰與法律文化[10]。而這兩種動力機制對中國傳統媒體的推動都較為有限,所以當西方傳統媒體像一個不懼艱險的巨人完全承擔起了沉重社會責任時,我國的傳統媒體卻把“燙手的山芋”都扔給了網絡,導致新聞不能由傳統媒體及時報道出去。“等到網上炒到沸沸揚揚且偏離事實真相時,才容許傳統媒體介入報道試圖后發制人,而此時局面已顯得十分被動了。”[11]
其實,我國輿論監督很早就有發展,20世紀50年代就頒布了《中共中央關于在報紙刊物上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當時的紙面媒體就擔負起了輿論監督的職責。盡管后來在反“右”和文革期間傳統媒體的監督先后經歷了收緊和畸變[11],但自改革開放以來,其發展一直在緩慢且謹慎地恢復當中。在社交網絡崛起的時代,這種緩慢的恢復已被新媒體的發展所超越。傳統媒體對某些潛在“敏感”事件的集體失聲,令社會的壓力無處釋放。由于缺乏正規、可控的減壓渠道,網民們不斷地用網絡語言對公共權力進行戲仿和暗諷。
許多由社會本身固有的問題都被訴諸網絡傳媒,如貧富差距的拉大、食品衛生監管、勞資矛盾、拆遷矛盾等。這些問題到了網上就都被認為是網絡傳媒帶來的問題,其實社會問題才是其背后的原因。然而傳統媒體卻不能宣泄這種壓力,當社會矛盾造成的壓力無處宣泄時,民眾便不約而同地選擇網絡傳媒作為唯一的減壓閥,因而中國的網絡傳媒獨自承擔了過重的社會責任。
(三)公眾表達意識的增強
在傳統的傳播模式中,社會公眾被置于金字塔結構的底層,對于公眾而言公共權力遙不可及,故公眾的心理權力距離較大。與其說公眾缺乏制約監督公共權力的能力,不如說公眾更缺乏制約監督公共權力的信心。
對于一些大型的住宅樓的建設更是由于暖通空調設備等所需要的材料的復雜性,就更需要管理人員注意這個問題了。暖通材料的質量是直接影響暖通設備的。購買的暖通材料必須符合國家的有關標準,在安裝之前必須要仔細的檢查和嚴格的規范。其中各種閥門和鍍鋅鋼板等輔料的質量情況更是需要注意的。因為這幾種在暖通管道的工程建設中直接影響著其質量。此外,還要加強對保溫材料進場的檢查,對施工前技術交底和施工中的檢查要嚴格監控,總而保證暖通空調設備材料質量。
“網絡傳媒可以讓公眾更多地了解世界,同時它也使得公眾能夠發表自己的觀點,聆聽、討論和及時獲取決策信息,所以它也是自古希臘雅典的市民辯論會場以來最為卓越的一項發明。”[12](P46-47)傳統媒體的傳播模式被扁平的、網絡式的網絡傳媒所取代,原先被置于傳播金字塔底層的公眾能夠與金字塔頂端的公共權力擁有者共同獲取新聞信息,也可以自由發表評論。
網絡打破了社會的僵局,打破了身份、財富和社會地位的藩籬,社會大眾能夠跨越不同的階層,直接以一個普通人的倫理道德標準來衡量公共人物及其行為(當然前提是沒有誹謗或誣陷)。雖然在現實生活中科層制的形式仍然存在,但是虛擬的網絡環境大幅縮短了民眾心理上的社會權力距離。現實中公共權力的不均衡配置在網絡中不被接受,民眾開始通過網絡傳媒來制約和監督公共權力。
二、網絡傳媒制約監督公共權力的模式
從制約與監督的維度來觀察,我們可以發現網絡傳媒制約監督公共權力的兩種基本模式,一種是包含了制約和監督的政府與社會良性互動制衡模式,另一種則是對公共權力進行網絡輿論監督的模式。我們觀察到網絡傳媒的制約監督能夠引起政府公信力的變化,其過程是在現實行政領域和網絡公共領域這兩個場域中完成的。見圖1。
(一)良性互動制衡模式
現實中行政權力的配置并不均衡,行政權力由行政部門及其官員享有。雖然在政治上有代表制度,但是民眾對于行政過程中的決策和執行缺乏制衡的手段。虛擬的網絡社會是現實公共生活在網絡中的映射,網絡公共領域為制約監督公共權力提供了新的場域。由于現實中有些政策不夠科學,以及有時在行政執行過程中忽視了民眾的利益,此時民眾便會通過網絡向社會和政府表達自身的利益訴求。倘使民眾的這種表達得到了政府的回應和意見征詢,那么就能夠進入一個政府和社會良性互動的模式。
這種互動的起點是民眾知情權在網絡中的部分實現,即民眾通過網絡知悉了政策的內容,并通過網絡共享了對政策可能導致結果的分析。當其切身利益被權力所忽視時,民眾更愿意通過網絡傳媒來發聲。當地方政府或行政部門愿意傾聽這種網絡民意,并就公共利益進行探討時,我們就可以說進入了參與式傳播過程。這種把公共利益要求轉變成重大政策選擇的功能,稱作利益綜合,是各類公共利益得到社會資源的政策選擇過程[13](P233)。在這一過程中政府與社會充分互動,這是一種典型的網絡媒體對公共權力的制約。經過參與和協商,地方政府知道了政策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以及執行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并對提案進行修改,進而又改變了自身的行為方式。由于考慮和平衡了各方面的因素,政策制定更加科學和行政執行更有效率。這樣,即使政策和執行的效果不盡如人意,民眾也能因曾經參與權力運作,而理解政府在公共事務管理中的難處。網民對公共權力運行做出正面積極的評價,最終政府公信力也能在這種互動中逐步增長。
(二)網絡輿論監督模式
在倫理事件和貪腐案件(與事件相比,案件已從倫理范疇進入了法律范疇)成為公共話題的時候,政府對網絡傳媒的回應性就變得十分關鍵,甚至不同的回應速度都會使事態朝不同方向發展。一種可能,政府通過網絡知曉了案件基本情況以后,及時回應并妥善處理,處理結果令網民基本滿意,那么政府公信力也基本不會有損失。另一種可能,政府沒有及時回應網絡輿論所關注的問題,緊接著事件背后深層的社會階層沖突讓該事件或案件在傳播過程中被符號化,從而引起更大規模的輿論情緒爆發。這個時候政府才回應,或者回應不得體,甚至繼續坐視不理,都將導致地方政府的公信力下降。
公信力對于地方政府或行政部門維持其公共形象至關重要,良好的公共形象能增加群眾對地方政府的信任感,也能在行政執行過程中有效地減少矛盾和社會沖突,有利于社會的和諧與發展。然而當政府公信力已經走低時,無論政府說什么、做什么都將不被公眾理解。如果地方政府或行政部門不在網絡傳媒中接受制衡,那么政府公信力就會一次次被蠶食,這恐怕會讓整個政府落入“塔西佗陷阱”。
三、規范與促進網絡傳媒制約監督公權力的途徑
公共行政學家、傳播學家拉斯韋爾指出大眾傳播的主要功能是傳輸、聯系和監督[14](P37)。如拉氏所言,由于大眾傳播往往引發對公共話題的討論,從而引發對公共權力的質疑,所以網絡輿論的矛頭頻頻指向公共權力。雖然作為低成本的輿情監測手段和權力監督工具,它的潛力巨大。但是倘若網絡缺乏規范,則必然會有負面效應產生,制約和監督都無從談起。如何揚長避短,更加規范地利用網絡傳媒監督和制約權利,都有待于從多方面推進。
(一)構筑網絡傳媒監督的法制秩序
法律是規范人類行為的工具,人們在網絡傳媒中的行為也需要規范,如果沒有法律的約束,這股強大的力量就會被人利用。“人肉搜索”和“網絡游街示眾”無疑嚴重侵犯了個人權利,而有些網絡事件中,在網民們“蒙面狂歡”的背后甚至有“網絡推手”影響網絡輿情的發展[15]。如果沒有法律來規范網絡力量,它所侵犯的可能不僅僅是公民個人的私權利,甚至有可能對社會穩定帶來負面影響。

圖1 網絡傳媒制約監督公共權力的模式示意圖
要規范網絡傳媒,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過法律。傳統的大陸法系國家(如:德國、法國、俄羅斯)均有《傳媒法》或《新聞法》。而我國至今沒有《新聞法》,也沒有《網絡法》和《誹謗法》。雖然我國有人大監督法,但并沒有針對網絡監督的有關內容。這不僅導致了傳統媒體無法可依,而且網絡傳媒亦不能依法來制約和監督。現今的網絡相關法規僅有對域名注冊的規定、網上銀行管理暫行辦法,以及知識產權法中關于侵犯著作權的若干條款及其司法解釋。前二者只是一些行政管理的技術,而知識產權法的司法解釋并不是針對網絡傳媒的特性制定的法律,這些零散的條款或規定無法滿足現下的法治需求,規定網絡傳媒有關各方權利與義務的法律亟待建立。
在法理層面,要明確輿論與司法的界限。輿論以普遍社會道德為標準,“輿論法則判別的是美德和惡行;而美德又完全是根據公眾的評價來衡量的”[16](P109)。雖說法律是道德的底線,但一曰道德,一曰法律,二者涇渭分明,絕對不能將道德作為審判的依據。網絡傳媒和司法部門由于視角的不同,網絡傳媒的視角是民生,以道德為原則,以輿論為武器;司法系統的視角是法律,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當然另一方面,行政權力也不能介入司法審判。如果輿論監督走的還是“輿論關注——領導批示——司法執行”的老路,那么影響司法公正的是這種錯位的權力分配。只有使網絡傳媒與法律和司法體系有效銜接才能真正規范網絡中的行為,使網絡傳媒制約監督的力量用在正途。
(二)防止輿論情緒影響政府公信力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權威的重要來源,良好的政府公信力能增強政府的組織能力和動員能力,降低政策執行成本[17]。網絡時代的政府公信力既可以通過網絡傳媒獲得增長,也可能因為對網絡監督的不妥應對而降低。在網絡輿論監督模式中,經過行政倫理事件或者貪污腐敗案件的符號化,讓網絡輿論轉化為更難處理的輿論情緒,進而使政府挽回公信力的努力失去效果。
社會階層沖突意識在網絡傳媒中的符號化是產生輿論情緒的核心步驟。比如2009年分別由當時的三個事件而引出的“富二代”“官二代”“農二代”這三個詞匯在網絡上迅速竄紅,次年兩會期間,這些符號就“轉正”為兩會代表們的用語。符號化的背后是社會階層沖突,社會階層之間的不平等,“是一種深藏在社會結構內部的社會群體之間的關系,政治分層與經濟分層只不過是它的不同表現形式”[18](P25)。不論中國的社會階層被分為十層(陸學藝,2002),還是“上層寡頭化,下層民粹化”的社會斷裂(孫立平,2006),總之今天財富與權力在階層之間的流動似乎難以尋覓,所以仇富和仇官心態在網絡公共場域中的表達日益強烈。
網絡中所折射的社會現象經過一次次的交互傳播與要素提煉,社會階層之間的沖突就逐漸地被符號化了。鮑德里亞闡明了從物到符號之間的發展分別經歷了符號對物的反應、歪曲、掩蓋和擺脫現實的過程。這些符號化了的“擬像”充斥著媒介,符號不再是指代,而是創造了我們所處的現實[19](P170)。“符號可以脫離于現實的根基而存在于對自身的演繹中,這使得社會的熵①在不斷增加,擬像在電子媒介中的仿真成為現實”[20](P78),以至于我們在接收信息的過程中直接對這些符號產生了條件反射——這樣的符號化是危險的,仇官和仇富心理可能會引起網民們對事件真相細節的選擇性忽略。更不容忽視的是,仇視的思維方式并不會引領人們冷靜地總結事件背后的教訓,以及審慎、長久地進行反思。
我國政府對網絡民意的回應可以被分為“無回應”“被動回應”和“主動回應”三種類型[21]。在網上民眾對政府和官員違背行政倫理的事件予以譴責,如果得到政府的及時回應和妥善處理,政府的公信力得以維持,但卻難以實現增長。這是因為輿論是以高于常人的道德標準來要求官員,當他們的行為越過常人的倫理標準時就很難被民眾所原諒。雖然民眾在網絡傳媒中對公共權力的監督,在腐敗案件的查處、甚至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方面都取得了許多標志性的成功,但是這一切如果沒有政府的回應與配合,單靠民眾是無能為力的。
在網絡輿論監督模式中,當政府及時回應并妥善處理網絡輿論關注的行政問題,可以勉強維持其公信力。若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還需要探索另一種模式。在良性互動模式中,政府的回應性被參與式傳播所取代。參與式傳播能促成地方政府、行政部門與社會的互動,在輿論情緒形成之前,甚至輿論事件發生之前發現和解決問題。
(三)通過參與式傳播完善公共利益表達機制
從學術概念而言,參與式傳播是在政府回應性的提法上更進了一步。俞可平教授認為,“公民參與又稱公共參與、公眾參與,就是公民試圖影響公共政策和公民生活的一切活動”[22](P1)。公眾參與是要實現民眾參與、表達和影響公共政策的權利,而網絡傳媒的興起就是民眾實現這些權利的一個契機。新聞宣傳工作應該“把堅持正確導向和通達社情民意統一起來,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人民首創精神,保證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23](P5)。可喜的是,在民眾參與式傳播的初步實踐中,一部分政府官員在微博中放下官架,以貼近生活的語言與網民交流,聽取意見與傾訴。其中最早一批建微博的官員現在已成網絡紅人,為政府公信力的提升做出了貢獻。
參與式傳播的基礎是公共理性與合理的治理結構。在網絡傳媒中,引起多媒體共鳴原因被解讀為網絡傳播中中性的意見或者互相抵消的網絡輿論占大多數,而有消極影響或起負面作用的網絡輿論比例則較小[24]。故而網絡傳媒有可能成為理性的載體,且已有一些政治哲學與公共行政學同仁開始著手研究如何培育網絡中的理性決策。參與式傳播“在公共治理結構上,重要的是將所有利害關系的公民都包括在內,形成公共問題共同治理的共同體”[25]。在治理結構上,形成黨委、政府、利益相關的民眾、監督機構良性互動的結構。“正如參與不是分散政府權力而是分擔政府責任一樣,網絡參與提升了政府治理的質量,而非分割政府的權力。”[26]因為“由政府管理者和公民共同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共同思考社會和民族的未來藍圖,遠遠比某一單方面的努力要重要得多”[26]。
參與式傳播的前提條件是民眾通過網絡傳媒行使知情權。如果公共權力自始至終都在黑箱中運作,那么坊間便會流傳各種猜測,這樣難免讓民眾對政府產生陌生感和不信任感。鑒于此,政府最科學的做法就是公開民眾知情權的客體。在知悉地方政府和行政部門的決策信息之后,民眾能有效地參與其中。參與式傳播不應只是救濟式的糾紛解決機制,還可以是積極參與政府決策的民主形式。“網絡傳播則創造了一種社會各個群體為了爭取自身的利益相互斗爭的傳播文化,并且出現了不受地點限制的新型公眾。這種變化凸顯了源自古希臘參與式民主傳統價值觀的重要性,參與式民主是文明禮儀和權力共享等(古希臘的)傳統價值觀相伴相生的。”[27](P337)其能否實現主要取決于政府的態度,只要政府主動吸納網絡傳媒中的民意,再弱小的聲音(只要是科學、理性、符合公共利益的)也可以影響政府的決策。
然而網絡的公民參與也應該有其界限。對于馬歇爾·麥克盧漢來說,媒介是人類思維的延伸,其形式會逐漸驅逐其內容[28](P19)。讓·鮑德里亞深受麥克盧漢“媒介即信息”論斷的影響,認為傳媒形式掏空了內容,媒介形式統治了社會。[20](P78)而與麥克盧漢不同的是鮑德里亞對媒介的日漸強大產生了戒心。盡管曼紐爾·卡斯特是網絡社會的推崇者,但實際上卡斯特的多部著作中都透露出,他對網絡在民主政治領域中的發展保持著警惕。他主張治理新媒體的原則包括“對政治保持必要的疏遠”[29](P371),并且指出網絡直接民主有明顯的局限性,網絡中大量低質量、極端的討論難以與現實中高效的精英決策相兼容[30](P403)。所以網絡中的參與式傳播更多地體現為一種非組織性的利益表達機制,民眾在網絡傳媒中的利益表達要成為有效的政策輸入則有賴于地方政府和行政部門的關注和吸納,進而形成“利益表達——利益整合——行為結果”的良性互動。
網絡傳媒不僅能督促公權力掌握者審慎地行使自己的權力,更可以是一座政府與社會溝通的橋梁。如果公共權力在決策之初和運行過程中都接受民眾通過網絡傳媒的制約監督(制衡),主動吸納民眾的利益訴求,那么參與式傳播將不斷提升政府的公信力(良性互動)。在網絡公共領域中實現開放式決策和對執行的監督,民眾就能更多地理解并配合地方政府和行政部門,從而有效減少行政過程中的摩擦,提高決策的科學性、平衡性,以及決策執行的效率。
注釋:
① 鮑德里亞借用了克勞修斯的物理學概念,“熵”用以形容社會與自然界一樣隨著時間而增長的無序狀態。
[1] CNNIC.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2011年度報告[EB/OL]. http://www.cnnic.net.cn/gywm/ndbg/201204/P020120507358937384891.pdf.
[2] 潘祥輝.去科層化:互聯網在中國政治傳播中的功能再考察[J].浙江社會科學,2011(1):36-43.
[3] Pool, I. de sola (1983) Technologies of Freedom[M].Harvard, MA: Belknap Press.
[4] Holmes. Communication theory: media, technology and society[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2005.
[5] Walter Lippmann. Public Opinion[M]. New York:Macmillan, 1922.
[6] Sears, David O., and Jonathan I. Freedman, “Selective Exposure to Information: A Critical Review.” In The Process and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 edited by William Schramm and D. F. Robert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1.
[7] Herbert G. Nicholas, “Building on the Wilsonian Heritage”,in Arthur Link, ed. ,Woodrow Wilson (New York: Hill&Wang, 1968).
[8] 歷年“普利策獎”獲獎名單[DB/OL].http://www.pulitzer.org/.
[9] 吳廷俊.理念·制度·傳統——論美國“揭黑運動”的歷史經驗[J].新聞大學,2010(4):42-47.
[10] 陳堂發.亦析美國新聞界“揭黑運動”[J].新聞大學,2011(7):33-36.
[11] 范似錦,楊凡.輿論監督與社會政治生態環境[J].現代傳播,2010(12):30-35.
[12] Jones, A.H.M. 1960. Athenian Democrac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3] 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小G·賓厄姆·鮑威爾.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14] Harold Laswell.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 1965.
[15] 王子文,馬靜.網絡輿情中的“網絡推手”問題研究[J].政治學研究,2011(2):52-56.
[16] 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M].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 P109. 引自洛克. 人類理解論的“后來版本”,原注為:Locke,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II, §11;參閱Koselleck, 同上 , S.41ff
[17] 高衛星.試論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流失與重塑[J].中國行政管理,2005(7):62-65.
[18] 李強.中國社會分層結構的新變化[A].李培林,李強,孫立平.中國社會分層[C].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19] Jean Baudrillad.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s[M]. Selected Writing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20] 張天勇.社會符號化——馬克思主義視閾中的鮑德里亞后期思想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1] 劉力銳.我國網絡民意的成長政治意蘊及政府回應[J].廣東行政學院學報,2009(5):22-26.
[22] 賈西津.中國公民參與——案例與模式[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23] 胡錦濤.在人民日報社考察工作時的講話(2008年6月20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4] 鐘瑛,余秀才.1998—2009重大網絡輿論事件及其傳播特征探析[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0(4):45-52.
[25] 黃顯中,何音. 公共治理的基本結構[J].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10(2):41-50.
[26] 顧麗梅.網絡參與與政府治理創新之思考[J].中國行政管理,2010(7):11-14.
[27] 斯蒂芬·李特約翰,凱倫·福斯著. 史安斌譯.人類傳播理論[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
[28] McLuhan & Fiore.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M].New-York: Bantham, 1967.
[29] (美)曼紐爾·卡斯特.認同的力量[M].夏鑄九,黃麗玲,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30] (美)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跨文化的視角[M].周凱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