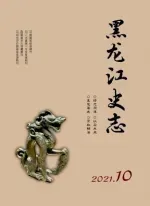江河文化的守護者——記當代作家、歷史文化學者范震威先生
柳成棟
50 多年來,我在松花江母親河的臂彎中長大,我深感母親河的體恤與溫暖。松花江母親的胸懷多么溫馨啊!我曾在母親河的草地上踏春、嬉戲,也曾在母親河柳叢繁茂的岸邊釣魚、撈蝦,我還曾在母親河的江汊子里游泳泛舟,唱一支歌兒,迎朝霞如火,送夕陽滿天,在蕩起雙槳的同時,也把我的愛,寄予給我們親愛的母親河——松花江。
——范震威
范震威,男,1941年生,著名詩人、作家、歷史文化學者。1962年畢業于哈爾濱業余藝術學院文學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曾任教師、技術員、出版社編輯。現任黑龍江省散文詩學會副會長。主要著作有《李白的身世、婚姻與家庭》、《燕園風雨40年——嚴家炎評傳》(合作)、《世紀才子蘇雪林傳》、《松花江傳》、《遼河傳》、《一個人的史詩——漂泊與圣化的歌者杜甫大傳》、《守望黑龍江》、《黑龍江傳》、《一個城市的記憶與夢想——哈爾濱百年過影》等10余部及論文、隨筆近百篇。
我與范震威先生相識已有20多年的歷史。1993年我的第一本詩詞集《長鋏歸來齋詩草》等三本詩詞集都承蒙他作序。
與范震威先生詩書往來,面聆謦欬,每次相晤,都有不同的收獲。然而收獲和啟發最多的是關于江河文化的交流。盡管范震威已出版了《李白的身世、婚姻與家庭》、《一個人的史詩——漂泊與圣化的歌者杜甫大傳》等多部詩人學者評傳,但他成績最大的是他為江河寫史,為江河立傳所成的《松花江傳》、《遼河傳》、《黑龍江傳》和江河文化隨筆集《守望黑龍江》的出版問世,使他成為江河文化的守護者。
一種緣分
早在1985年,范震威還是在省政府經濟研究中心工作的時候,正逢地理學家徐霞客誕辰400周年,每個省擬出一本反映各省自然地理、經濟社會發展的叢書。該書的編寫任務落在了經濟研究中心,范震威任常務副主編,開始對全省自然地理、經濟文化、風土民情進行調查。波瀾壯闊的黑龍江、波光瀲滟的松花江,清澈寧靜的烏蘇里江,波濤洶涌的興凱湖,連綿起伏的大小興安嶺、完達山,燃燒起了范震威心中的滾滾熱情,仿佛立刻要與這片神奇的土地擁抱、親吻,要做一名當代徐霞客的想法油然而生。在這次行走中,范震威進一步懂得了黑土文化主要是邊疆文化、各民族文化,當然最主要的是包括江河文化在內的地域文化。
此后,范震威回到編輯崗位上,又組織策劃了《話說黑龍江》、《話說烏蘇里江》的出版工作。這是對江河文化的第一次嘗試。斯時,范震威正在研究唐代有關詩人的傳記資料,準備為李白、杜甫等詩人寫傳。一個偶然的機會來到了身邊,河北大學出版社正在組織策劃大江大河文化傳記叢書編輯出版工作,《松花江傳》的編寫任務便落到了范震威的頭上。從此,范震威便和江河文化結下了不解之緣,仿佛如奔騰的江水,滾滾東去,一發而不可收拾。江河文化的寫作和研究也向前邁出了一大步。《松花江傳》出版之后,得到了河北大學出版社和社會各界的廣泛贊譽。正如著名學者伊永文所評價:《松花江傳》“那散文詩一樣優美的語言和筆調,使讀者在閱讀此傳時,獲得了極好的閱讀享受……對這條大河及水域周圍的名勝、特產、農田、人物、故事、神話、歷史的記述,其文筆時而清麗雋永,時而滄桑厚重,時而如澗奔流,時而波光如鏡,使人讀來如飲甘霖。”它如此優美、厚重、生動,像一曲悠長而耐聽的弦歌,永遠回響在松花江子民的耳畔。
此時,由于《遼河傳》沒有確定合適的撰稿人,范震威又承擔起了《遼河傳》的編寫工作。
一種情懷
江河是人類的母親。人類在江河的懷抱里繁衍生息,創造歷史。那奔騰不息的江河,充滿了生機活力,美麗而年輕。千萬年來,人類生于斯,長于斯,與江河的關系密不可分。江河哺育人類,也孕育了燦爛的文明和古老的文化。一條河流就是一部鮮活的歷史,一個動人的故事。江河伴隨我們走過了漫長的路程,她像一位歷史的老人,注視著朝代興衰,閱盡了歷史滄桑,它更像一位母親注視著身邊兒女的成長。這種江河與人結成的難以割舍的情懷,便是生命的動力,力量的源泉。
這種江河情懷首先就是故鄉情懷。1950年的春天,年僅9歲的范震威,隨著父母舉家來達到了松花江畔的哈爾濱。從此便喝松花江河水長大;成為松花江母親河兒女中的一員。雖然在松花江流域,來自山東、河北和遼寧的移民逐年增多,但在范震威的身上,在他的血管里,匯聚著東三省移民的影子,但他只承認自己是松花江的子民。正如范震威自己所說“50多年來,我在松花江母親河的臂彎中長大,我深感母親河的體恤與溫暖。松花江母親的胸懷多么溫馨啊!我曾在母親河的草地上踏春、嬉戲,也曾在母親河柳叢繁茂的岸邊釣魚、撈蝦,我還曾在母親河的江汊子里游泳泛舟,唱一支歌兒,迎朝霞如火,送夕陽滿天,在蕩起雙槳的同時,也把我的愛,寄予給我們親愛的母親河——松花江。”
這種對于母親河的故鄉情懷使得范震威對母親河松花江的熱愛與日俱增。這也正是范震威寫作《松花江傳》的動力。于是登長白,探江源;奔吉林,訪江神廟和長白山神廟;走松原,下前郭,赴德惠,北流松花江留下了范震威的足跡。
說到北流松花江,淪陷時期偽滿當局曾稱其為第二松花江。為了清洗殖民色彩,吉林省人民政府1988年專門下發了文件,將松花江南源天池至三岔河兩江相會之河口的江段亦稱松花江。為了避免含混或歧義,史家稱之為北流松花江。2002年8月,我陪同范震威專程到長白山進行考察,不但拍攝了一組珍貴的照片,而且獲得了松花江發源地長白的地質地貌、物產資源、江河源流走向等一手資料,我則寫下了近20首詩詞。
當我們一起登上長白山天池的時候,眼睛一亮,心中豁然開朗,一池藍湛湛的湖水,伴隨湖光升起的縷縷霧氣和天上漂浮的團團白云,真的仿佛進入仙境一般。一首七律脫口而出:“結伴同游長白山,佳期幸遇孟秋天。晴空初照池如鏡,幽谷凝觀水似藍。九域同根連萬里,三江一脈納千川。我臨崖頂神思久,云海風飄醉欲仙。”
當我們沿著乘槎河——松花江的本源下行的時候,河水匆匆地奔往瀑布口V型谷口,跌下68米的V型谷的峭崖,驚起一天白浪,飄出一片霧氣,這便是長白瀑布:“天河跌落掛前川,疑是珠簾百丈懸。玉帶閃光穹宇系,銀龍奪路谷中穿。煙云籠罩風飄雪,霧雨騰空袖裹寒。滾滾松江從此始,諸流匯合涌狂瀾。”在震耳欲聾的水聲中,河水經過沖躍的洗禮,翻卷著雪白的浪花沖出,沿著山坡,貼著樹林,穿過一片溫泉泊,向下迅跑。站在瀑布邊,那咆哮不止的跌落的水聲,令人驚嘆而有敬畏。瀑布從巖石上翻起浪花和白霧,從石隙間聚匯流出,這就是二道白河,也就是松花江的正源,此時我激動得眼睛濕潤了,那河里流淌著的不正是母親潔白的乳汁嗎?“千里尋源白河頭,噴銀瀉玉總無休。柔聲恰似母親喚,晶液猶如乳汁流。但使神池澤三省,好將圣水庇千秋。掬來一捧身心醉,熱淚盈眶喜淚流。”
一種守望
守望即堅守和瞭望。一個人有一個人的堅守的陣地,一個人有一個人瞭望的星空。范震威守望的是黑龍江的家園、黑龍江的土地、黑龍江的母親河,瞭望的是連綿不斷的江河文化、地域文化的發展變化。出于對家園沃土的酷愛,對山林、土地、江河的敬畏、拜謁和守望,范震威在撰寫《松花江傳》、《遼河傳》的空隙時間,又用他的殷殷之情、拳拳之心、貞貞之愛,將家園、黑土地、母親河的文化思考串聯在一起,形成了一部獨具文化特色的江河文化隨筆《守望黑龍江》。正如范震威所說《守望黑龍江》是生與斯、長于斯的黑龍江人或稱黑龍江老鄉所義不容辭的書寫。“當我用筆寫我心,也寫我的家園,寫我的黑土地和寫我的眺望、思忖和懷想的時候,我是在實現一個黑龍江人光榮而神圣的夢想。”
這種守望,是對江河歷史文化的一次梳理。是第一次用歷史滄桑的手來撫慰那夢中的河流與土地,從而再現滄海變桑田的歷史。這種守望是對江河和自然的敬畏。正如范震威所說:“敬畏不是軟弱,也不是畏縮,而是一種尊重。”當人們走進了江河,走進了自然,大自然的壯美,江河的浩渺,便會使人更加敬畏江河,更加敬畏山水,更加敬畏自然。從而更加熱愛江河,更加熱愛山水,更加熱愛自然。這種守望更是一種付出。為了了解松遼大平原的土地,以及這片土地上的山水風情,范震威帶著地圖,背著相機與行囊,從松花江源頭天池出發,跋山涉水,用腳和車輪一步一步地去丈量松嫩平原、松遼大地,去丈量山之巔、水之源、河之流。
為了慶祝《松花江傳》的出版、感謝文友、影友的支持,范震威請有關朋友小酌,我當場將書寫好的一首七律條幅獻給范震威:“如椽巨筆寫天河,信是豪情比墨多。長白登巔增壯志,松江成傳響高歌。東珠盡采三年血,藝苑精凝萬頃波。欲向母親交答卷,池中云影共婆娑。”
一種思想
人是有思想的。同樣,無論學術研究,還是文學創作都是要有思想作為動力,同時體現作者的思想。范震威為松花江作傳,為遼河作傳,特別是能為黑龍江作傳,就是愛國主義思想的集中體現。愛國主義思想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是比金子還重的一種品格。范震威的愛國主義思想首先表現在強烈的領土意識。河北大學出版社在策劃大江大河文化傳記叢書編輯出版時對于界江都未列入選題,黑龍江更是如此。對于生活在黑龍江土地上的龍江兒女,對于江河文化的守護者、研究者,對于世界第九條大河,中國第三條大河不為其作傳不能不是一種缺憾,也是對中國人特別是黑龍江人的一種絕大的嘲諷。在如今它既是政治家諱莫如深的“禁區”,也是史學家、文學家不便研究和探索的“禁區”,同時又是鮮有人探索的難區。是知難而進,還是知難而退,擺在了范震威的面前。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愛國主義思想、領土意識,堅定了為黑龍江作傳的決心。
其次是創新意識。光有決心和熱情是不行的。黑龍江傳如何撰寫是一個大問題。對于為江河作史傳在符合出版要求的前提下,必須在尊重歷史并有所創新,而創新最主要的是體例的創新,這是寫作前必須要解決的問題。困難總是難不倒有心人。范震威抓住了黑龍江的歷史的四個重要支點。一是公元前2231年息慎(肅慎)向中原進貢朝見帝舜開始,也就是黑龍江最早有史可稽查的時間。第二個支點是公元1077年,即遼道宗太康三年,道宗泛舟黑龍江、駐蹕黑龍江,黑龍江有了今天的名字。在影友的支持下,開始了對于黑龍江的探源之旅。第三個支點是1689年,也就是康熙二十八年,《俄尼布楚條約》中的簽訂,此時黑龍江仍是中國的內江。第四個支點為1858年《中俄璦琿條約》的簽訂,中國被迫割讓出了黑龍江以北6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黑龍江變成了界江。兩年以后,名之曰“兩國共管”的烏蘇里江以東、興凱湖以南,以及庫頁島30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再次被割去。黑龍江的內河時代開始了。“碧玉一條偏割半,誰把內河當界江?”有了這樣幾個支點,編寫《黑龍江傳》的難題迎刃而解。于是全書分為三大板塊,即黑龍江執掌水系、內江時代的黑龍江母親河、界江時代的黑龍江。思路清晰了,體例也就確定了。在三名影友的協助下,范震威開始了黑龍江的探源和對整個黑龍江流域的踏查。為此,2009年6月4日我專門為范震威壯行賦詩一首:“滾滾烏桓水,綿綿赤子情。江河追日月,云嶺探縱橫。尋脈呼倫走,溯源洛古行。滿懷憂患灑,一路憫憐生。好友欣相伴,長車樂為盟。”
其三是憂患意識。由于歷史的原因和人為的破壞,加之環境污染、過度開發,母親河已不堪重負,頻繁報警。范震威正在對故國山河壯麗景色所感染的同時,更加憂心忡忡。特別是當范震威看到三江濕地已缺少了昔日草叢、塔頭墩子雜陳其間,白云在藍天漂浮、水鳥水中嬉戲的情景,心中只有無奈的苦笑。痛失領土的傷痛未曾拂去,濕地被破壞的憂慮又浮上心頭。
《黑龍江傳》的編撰出版,不僅僅是第一人、第一次為母親河所立的江河自然史傳、文化史傳、開發史傳,同時也是一部沙俄侵華史傳。書中披露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無一不流淌著愛國主義的思想光輝。對于現在一些人已經忘掉歷史,特別是早已忘掉沙俄侵華史的當今,甚至連只字都不敢提的情況下把它能夠如實地寫進《黑龍江傳》中是最為難能可貴的。
一種毅力
荀子云:“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為了編纂《松花江傳》、《遼河傳》、《黑龍江傳》,范震威付出了巨大的艱辛的勞動。他以百折不撓、鍥而不舍、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和頑強的毅力,或單槍匹馬,或結伴而行,去踏查松花江源、追溯遼河源、探訪黑龍江源。除考察黑龍江以外,在考察中范震威一直沿襲著以公共汽車為主的交通方式。因為坐公共客車,方便中途下車考察。沒有汽車,就搭農用車、拖拉機、馬車,實在不行就步行。在松花江上,范震威幾乎坐遍了江上的大船、小船。10年來,櫛風沐雨,可以說是行萬里路,涉千重水,踏百座山,累計路程已達25000多公里,鞋子不知磨壞了幾雙。為了考察某一重要歷史人物、重大歷史事件,核對歷史的真實記錄、對照古今的變遷,范震威常常是步行幾十里,直到沒有人煙、無人問津的地方才罷休。宣傳部、史志辦、博物館,是他必去的地方,鄉村野老、漁樵、耕夫都是采訪的對象。有時無招待所便睡在老鄉家,或睡在網房子里。每天都要克服旅途的疲勞,堅持寫采訪日記采訪筆記,記滿了一冊又一冊。
一般來說,無論是采訪,還是寫作,除非有極特殊情況,范震威都是一鼓作氣,一氣呵成的。在踏訪遼河源的時候,范震威鑲嵌的牙不慎弄壞,這才將要修復的牙放在北京重新制作,自己回到哈爾濱休息了半個月,待修好了牙之后,又重新踏上了探訪遼河源的征程。在寫《松花江傳》時,因踏查松嫩兩江匯合處不慎將右手腕在船板上摔傷,才不得不休息一個月,但時間是不能浪費的,于是便到嫩江右岸地區走訪了嫩江、訥河等11個縣市。踏訪了尼爾基水庫、訥謨爾河。對于嫩江流域的地貌、自然經濟地理,農牧業生產都進行了考察。
嗣后,范震威又沿松花江干流,踏查了拉林河、呼蘭河、阿什河、牡丹江、倭肯河、湯旺河等河流,考察了三江平原,并沿松花江追尋三仙女的傳說、尋訪依蘭馬大屯金肇祖布庫里雍順登岸之地,直至到通江同三公路的起點同三廣場。為了進一步搞好北流松花江的探源,范震威特別注意松花江中上游地區的考古發掘,特意買了一本《吉林考古地圖冊》,親自考察遼代出河店戰爭遺址、大金得勝陀碑,核對古跡的記載。
正因為范震威有這種堅忍不拔的毅力,獲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才使得三部江河傳、一部守望寫得活靈活現、有聲有色。
在使用電腦寫作基本普及的今天,已經很少有人再用筆寫作了。據我所知作家賈平凹、梁曉聲是仍然用筆來寫作的作家之一,而范震威也是這樣的一位作家。他不但不用電腦寫作,而且連鋼筆和稿紙也不用,書寫工具是青一色的鉛筆,所用的紙張是A4紙,資料卡片是A4紙一裁4瓣。《松花江傳》、《遼河傳》、《黑龍江傳》和《守望黑龍江》4本書的寫作一共用了100多支鉛筆,A4紙用了數千張。最驚人的是范震威每寫一本書都是一次成稿,直接拿到出版社排版。因此,在作家手稿已經消失的情況下,范震威則留下了一部部寶貴的作家手稿,并已被有關部門所珍藏。
一種閱讀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是結合的。沒有讀萬卷書的基礎,行萬里路是不會有大收獲的。古人云:“讀破萬卷書,下筆如有神”,強調的就是讀書的作用。范震威是一個愛書成癖的人,家中到處都是圖書,一面墻被幾個大書柜占滿,各種古今中外圖書陳列其中。從1985年到1995年,整整十年的時間,范震威將《二十五史》通讀一遍,從此眼界大開,他也從單一的文學研究擴充到歷史文化研究的領域,邁進了歷史文化的大門,給退休后跋山涉水,為江河立傳、為城市立傳,為詩人、作家、學者立傳打下了基礎。其中《新唐書》、《舊唐書》幾乎都翻散花了,只好重新用繩子裝訂或用膠布貼上再用。舉凡正史、方志、歷史地理、傳記以及有關政治、經濟、文化的圖書,相關論文都在必讀之列。三部江河傳每部征引的書目都在百種以上,其中《黑龍江傳》、《松花江傳》征引書目各達160種以上。正因為有了這么豐富的歷史文化積淀,創作起來才得心應手,思如泉涌,下筆如神,妙筆生花;才能一氣呵成,一揮而就,一錘定音,一稿成書。
令人敬佩的是范震威4年的獨身生活,既無紅袖添香,又無伴侶斟茶,唯一伴隨的是閱讀與寫作。這是一種怎樣的毅力,怎樣的堅守。閱讀與寫作驅逐了孤獨,驅逐了寂寞。換來的是讀書的快樂、寫作的怡悅、出書的歡喜。
一種協作
范震威退休后之所以能夠順利地完成《松花江傳》、《遼河傳》、《黑龍江傳》、《守望黑龍江》、《一個城市的記憶與夢想——百年哈爾濱過影》等江河文化、地域文化等多部歷史文化著作,除了他個人懷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理想,為成就“三不朽”事業而“立言”的信念,以及一種歷史機遇和他本人的江河情懷、愛國思想、頑強毅力、苦讀精神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些影友和文友對他寫作的大力支持。在考察黑龍江的漫長征程中,是影友王冰、李顯國、王慶春開車陪同范震威自帶行囊、照相器材,一路風餐露宿、星夜兼程,沿著黑龍江走訪、考察、拍攝,總計路程可達13 000公里,拍攝了近萬幅照片,選入《黑龍江傳》中的就有近300幅。王毅敏則為《松花江傳》拍攝了大量照片。另外還有好多影友、文友或陪同考察長白山,或考察松花江,或考察黑瞎子島、烏蘇里江等地,給予范震威大力支持。另外李述笑、劉延年、張會群等人為《一個城市的記憶與夢想》無私地提供了好多哈爾濱珍貴的歷史老照片。這些都為這幾部書的出版增添了亮麗。
另外,寫作所需資料,文友也是有求必應,大力支持。這主要取決于范震威的人格魅力,范震威守信譽,講誠信,對于借取朋友的圖書資料從來都是一本不少、完整無損地送還書主,出書時對有所幫助的人一一在后記中鳴謝。出書之后,一一贈書。
正因為有了這種協作精神,促使范震威的著述一部接連一部的出版。
如今范震威雖然年屆古稀,但依然精神矍鑠,豪情不減。10年除完成10部著作的編寫出版之外,即將出版問世的還有《長城傳》,準備編寫的還有《大興安嶺傳》、《長白山傳》、《烏蘇里江傳》等等,我們期待著這些著作早日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