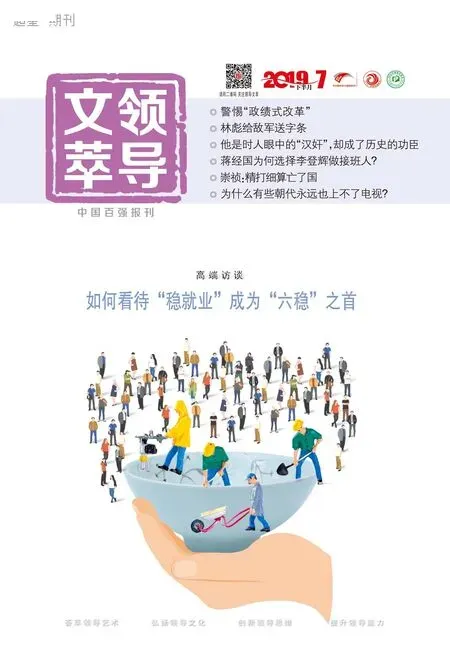范仲淹,句句是猛藥
晏建懷
北宋名臣范仲淹一生奔波仕途,屢次被貶,與同僚發生過沖突,甚至他的朋友、同窗、老師對他也頗多苛評。他的仕途推薦人、宰相晏殊就曾責備他 “好奇邀名”;另一位宰相呂夷簡也說他“務名無實”。但是,在他死后,南宋朱熹評論他是“天地間第一流人物”;明代方孝孺說他“時屯道難合,謗息名愈全”。在這些人眼中,范仲淹擁有一種勇敢直言,毫不退縮的品格。
為自立而讀書
范仲淹出生在成德軍(河北藩鎮,治所在今河北正定)節度掌書記官舍。其父范墉,曾任成德軍、武信軍(治所在今四川遂寧)、武寧軍(治所在今江蘇徐州)掌書記。所謂節度掌書記,是藩鎮里的高級文官職位,相當于現在的機要秘書。范仲淹兩歲喪父,家道中落,當時母親謝氏還十分年輕,貧無所依,便帶著兒子改嫁淄州長山(今山東鄒平)朱文翰,范仲淹也被改名為朱說,并在朱家長大成人。
在安鄉(今湖南安鄉)時,范仲淹曾在當地的太平興國觀讀書,寒暑不倦。清朝翰林張明先在詩里寫道:“荒臺夜夜芭蕉雨,野沼年年翰墨香”,以“書臺夜雨”的詩意,概括了范仲淹這段苦讀生活。1009年前后,范仲淹隨父母回到淄州長山,讀書于長白山醴泉寺,每天的飲食僅僅是一碗稀粥。他把粥放涼,待其凝固后分成4塊,早晚各吃兩塊,配著鹽拌韭菜末下飯。
如果說長白山醴泉寺讀書是范仲淹自覺讀書的表現,那么數年后,他到南京(今河南商丘)應天書院求學,則是為自立而讀書了。讓他自立的原因有點悲愴——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朱氏兄弟浪費而不知節儉,范仲淹曾多次勸阻,有一天朱氏兄弟被說得不勝其煩了,脫口而出:“我們用朱家的錢,與你何干?”范仲淹聽完十分不解,自己不就是朱家子孫嗎?驚疑之下,他四處打聽自己的身世,最后才知道朱文翰并非生父,自己是姑蘇范氏之子。范仲淹是個烈性漢子,他毅然決定自立門戶,并立即離開朱家,負琴攜劍,求學南京,唯一的目的就是發奮讀書、學成迎母。這一年,他23歲。
由于與朱姓決裂,范仲淹在應天書院求學時,生活一度沒有著落。《范文正公年譜》上說他晝夜苦學,夜里倦怠時就用涼水澆臉,饑餓時以稀粥為食。南京留守的兒子與范仲淹同窗,十分同情他,把他的情況告訴了父親。留守很感動,從自己的飯菜中節省出一份來送給范仲淹,但范仲淹婉然拒絕了,說:“不是不感謝您的深情厚意,但我喝粥習慣了,也不覺得苦,一旦享受豐盛的飲食,以后喝粥就索然無味了。”
還有一次,宋真宗幸臨南京,南京萬人空巷,應天書院師生傾巢而出,爭睹圣顏,只有范仲淹巋然不動,繼續讀書。有人回來后問他為什么不去一睹皇帝風采,范仲淹說:“將來覲見也不晚。”
戰場上以守為攻
范仲淹所生活的時代,正處在宋朝由盛而衰的轉折時期。吏治腐敗,財政虧空,農民與士兵不斷揭竿而起。邊境上,北方的遼國與西邊的西夏結成掎角之勢,不斷擾犯。
在范仲淹的仕宦生涯中,有兩件事在當時影響甚大:一是御邊,二是新政。1040年,宋與西夏的戰事復燃,范仲淹臨危受命,被派去御邊。在戰略上,他主張:“嚴邊城,使之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修固邊城、精練士卒、招撫屬羌、孤立西夏,想通過以守為攻的方式爭取勝利。但這一方針為許多朝臣所不理解,被譏為怯懦。當朝皇帝宋仁宗急于求成,要求主動出擊,結果和西夏打了兩次,損兵折將。痛定思痛,宋仁宗決定改而采取范仲淹的守策。在韓琦和范仲淹的主持下,邊城日固、士氣日盛、軍備日精,攻防體系初步建立起來,戰局開始有了變化,西夏再也不敢小覷宋軍,當時民謠可以為證:“軍中有一韓(韓琦),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范仲淹),西賊聞之驚破膽。”1043年,宋夏議和。
與西夏的戰爭僵持3年,不能速勝,使宋仁宗認為國力太弱,強內才能安外。他又犯了急于求成的毛病。戰事剛穩,就不顧功虧一簣的危險,于1043年4月緊急調范仲淹和韓琦為樞密副使,不久又升范仲淹為參知政事(相當于副宰相),命他拿出改革措施。范仲淹上書《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厚農桑、修武備”等10項改革措施,拉開了“慶歷新政”的序幕。這些措施中,除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3項外,其余都為改革吏治的措施,下的方倒是對癥,但影響了官員群體的既得利益,受到多方攻擊,再加上宋仁宗瞻前顧后,不夠堅定,10項改革措施只實行了6項就半途夭折,“慶歷新政”以失敗告終。
早在1021年,范仲淹還在泰州(今江蘇泰州)當地方官,海堤年久失修,每到海潮泛濫,農田就被洗蕩,百姓不堪其苦。范仲淹不斷上書建議修復海堤,一番周折后,最終爭取了朝廷的支持。經過3年艱苦卓絕的奮戰,一條150里的捍海大堤終于修成。通州(今江蘇南通)、泰州、楚州(今江蘇淮安)一帶從此水患無憂,當地百姓深深感念范仲淹的功績,將此堤取名為 “范公堤”。
1025年,范仲淹當上了大理寺丞,他不顧位卑言輕,立刻給垂簾聽政的章獻太后和宋仁宗上書,提出“救文弊以厚風俗,整武備以御外患,重館選以養人才,賞臺諫以開言路”等建議;1027年,在丁母憂期間,他也“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給朝廷上了一份萬言書——《上執政書》,針對貧病交加的時弊,他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備戎狄”等6條改革主張。據說,宰相王曾收到萬言書后,大為賞識,立即授意晏殊推薦范仲淹應學士院試。
被貶3次也不“收斂”
1030年,范仲淹上疏《乞太后還政奏》,請當時還在垂簾聽政的章獻太后“卷收大權,還上真主”,要求21歲的宋仁宗親政。章獻太后被觸怒,把范仲淹貶為河中府(今山西永濟)通判。曾推薦他的晏殊擔心連累到自己,把范仲淹叫去嚴加責備。為此,范仲淹給晏殊寫了封長信,說:“事君有犯無隱,有諫無訕。殺其身,有益于君則為之。”一副死倔死倔的樣子。
1033年,章獻太后駕鶴歸西,親政后的宋仁宗希望有所作為,找來一批太后垂簾時受壓制的官員。范仲淹也被召還,擔任了諫官。當時,宋仁宗因為寵幸尚氏、楊氏二妃,準備廢掉郭皇后,范仲淹卻率官到垂拱殿門,奏郭皇后不可廢,結果被押解出京城,貶睦州(今浙江建德)。
1035年冬,范仲淹因政績突出被提拔進京,歸來后的他論事愈急。當時,呂夷簡任宰相,頗為專權。范仲淹便把一些要員的晉升情況繪成《百官圖》上呈宋仁宗,指著上面開列的百官晉升順序說,“如是為公,如是為私,意在丞相”,直言宰相以權謀私,任人唯親。呂夷簡氣得七竅生煙,狀告范仲淹越職言事搞朋黨,離間君臣。這次,范仲淹又被貶職饒州(今江西鄱陽)。
歷經三度謫貶,范仲淹絲毫不見“收斂”,他那近似固執的堅持,源于憂國憂民的情懷,只是,真正理解他的有幾人?在當時的名流眼中,他是個不懂回旋的迂闊之人,王安石甚至指責他“好廣名譽,甚壞風俗”。
1052年,64歲的范仲淹舊疾纏身,感覺大限將至,便向宋仁宗呈上《遺表》,說的仍是邦國興衰。他以將死之言規勸仁宗要體恤民情,賞罰公正;他還對朝廷上上下下固守弊病、不愿變革的心態深感憂慮。至于身后事,只字未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