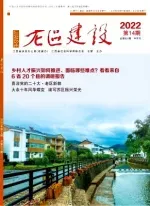試論晚清使臣議會書寫之傳播
余冬林 任群英
同治年間中外隔膜較深,早期使臣如斌椿、志剛、張德彝等對西方議會的認識大都失之于膚淺。1875年至甲午中日戰爭期間,晚清使臣郭嵩燾、劉錫鴻和薛福成等對西方文化都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考察。他們的道德優越感依然較為強烈,他們都不否定“三綱五常”和等級制度,都站在傳統的民本主義立場,強調議會的“通上下之情”的功能,企圖借鑒西方議會制度以“民本”制約“君權”或者說兩者互相制約。甲午戰爭至清朝覆亡期間,歷經戊戌變法、列國瓜分中國狂潮、八國聯軍侵華、義和團運動和清末新政等重大歷史事件,資產階級維新思想和革命思想風行其間,“自由”、“平等”、“民權”術語以及“進化論”和“民權說”等社會政治學說逐漸廣泛傳播。載振、戴鴻慈和載澤等使臣感受到時代潮流之趨向,雖然他們對上述觀念和理論有所認識,但是他們往往不自覺用固有的觀念消解“自由”、“平等”、“民權”等術語的底蘊,同時受到現實功利目的的影響,導致他們雖然認同或主張西方的憲政制度,但是實際上他們依然并未認識到西方議會制度的本質。
晚清使臣的議會書寫主要保存在其使西日記中。因此有必要將其使西日記的刊刻、收錄以及引述等情況作一必要的梳理,以勾勒出其傳播的大致輪廓。他們的使西日記多被收入王錫祺所輯的《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系列中。這部叢書共36帙,64卷,收書1348種。王錫祺從光緒三年(1877年)起,轉為研究輿地、洋務、時政。后來,他在沈蝶庵、龔壽秋、丁衡甫、王錫淲等親友的幫助下,經過15個寒暑的努力,收集輿地游覽書稿數千種,于光緒十七年(1891年)編成《叢鈔》。以后,于二十年(1894年)輯成《補編》、二十三年(1897年)輯成《再補編》。光緒時,“海內識字者,莫不知有小方壺齋。小方壺齋之名,與知不足齋、粵雅堂埒”。《知不足齋叢書》、《粵雅堂叢書》皆清代著名輿地叢書,小方壺齋叢書能與其相提并論,可見這部叢書流播之廣,影響之大。《申報》于1898年1月1日推出“《小方壺齋書籍》(即《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六十四本及其續編四本、再補編十六本”的新書廣告,且這一廣告竟然連續刊登4年,足見當時此套叢書應是非常暢銷的。晚清使臣的議會書寫亦藉此之力而廣為流傳。
除此之外,晚清使臣使西日記的流傳還有其他渠道,斌春的《乘槎筆記》除小方壺齋本外,尚有二酉堂刊本、醉六堂刊本、各國日記匯編本以及鐵香室叢刻本等多種版本。此外,《乘槎筆記》還曾連載于《中國教會新報》(《萬國公報》的前身),曾引起不少文人注意。在金武祥的《粟香隨筆》、李圭的《環游地球新錄》、毛祥麟的《墨余錄》、林昌彝《海天琴思錄續刻》、王仁俊的《格致古微》、金永森的《西被考略》、震鈞的《天咫偶聞》以及薛福成的《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等書籍中均見對《乘槎筆記》的引述。王韜在《甕牖余談》中評論曰:“有《乘槎筆記》一書已刊板于京師,一時通國傳觀,鈔襄陽播若之詞者,頓為紙貴。”至于志剛及其《初使泰西記》,震鈞的《天咫偶聞》亦有評述,“克庵先生沉潛理學,宗陸、王而不漸其流弊,以經濟自期。初以部郎使西洋,作《初使泰西記》。時使事肇端,人不愿往,先生毅然請行,卒以不肯事當道,竟不得大其用,遂出為庫倫辦事大臣,以風節著。”
張德彝的《航海述奇》除小方壺齋本外,還有《申報》本。光緒六年(1880年)上海《申報》館刊印了他初次隨使泰西的《航海述奇》。此外,《申報》在1894年1月18日《新印各種書籍出售價目》中,開列了《航海述奇》等數種海外游記。張德彝生前已刊行了《四述奇》,共三個版本:其一為光緒九年(1883年)京師同文館的鉛印刊行本;其二為光緒十七年(1891年)《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后者將《四述奇》中相關部分拆解成《隨使日記》、《使英雜記》、《使法雜記》、《使還日記》、《使俄日記》等5種;其三為清末安雅書局刊印本,具體年代待考,注明《總署官書鈔·使俄日記》,系以張德彝按照晚清外交制度按時寄回總署的“匯報”為據,采使俄部分而成,內容為《四述奇》中隨崇厚赴俄談判中俄邊界使事,可稱“使俄雜記”。至于他記述其駐英公使生涯的《八述奇》,宣統年間也曾刊行過石印本,錢鐘書《七綴集》(修訂本)多次引用。以上三種述奇在張德彝生前曾刊印過。張德彝的使西日記在金永森的《西被考略》、朱一新的《無邪堂答問》以及杞廬主人的《時務通考》等書籍中亦見引述。
如果說斌椿的《乘槎筆記》、志剛的《初使泰西記》以及張德彝《航海述奇》等,雖也流傳士林,但不過是旗人使臣的觀光之作,文筆粗拙,且對各國歷史地理政制沿革等西方文化,或語焉不詳,或鮮有觸及,只能是文人士大夫茶余飯后的談資佐料。當時引發晚清帝國朝野極大的心靈震撼的使西日記,則非郭嵩燾的《使西紀程》莫屬。郭嵩燾在《使西紀程》中比照西洋政治體制、外交軍事、商業活動、以及宗教法律等西洋文明,直言無忌地評論清廷之洋務得失,指斥士林虛驕風尚,對現實政治和傳統文化特別是“華夷之辨”等進行了強烈的質疑和批判。《使西紀程》因而遭遇“奉旨毀板”之厄運。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記載了當時士林洶洶朝野憤怒之情形:
《使西紀程》記道里所見,極意夸飾,大率謂其法度嚴明,仁義兼至,富強未艾,寰海歸心。……迨此書出,而通商衙門為之刊行,凡有血氣者,無不切齒,于是湖北人何金壽以編修為日講官,出疏嚴劾之,有詔毀板,而流布已廣矣。嵩燾之為此言,誠不知是何肺肝,而為之刻者又何心也。
面對洶涌而至的毀謗,郭嵩燾毅然向朝廷申辯和反擊,但得到的上諭卻是嚴斥和訓誡。平時而論,《使西紀程》褒揚西洋文化的態度和觀念,實在超越了時人所能接受的限度。當然,至少象李鴻章、薛福成、丁日昌、沈葆楨、文廷式等洋務派與郭嵩燾互相推重引為知己。《使西紀程》雖然沒有得到士大夫階層的普遍信服,但影響之深遠震憾力之持久實不可低估。其書雖毀,但新聞紙繼續刊刻,中外傳播依然如故。如《萬國公報》于光緒三年(1877年)6月2日—8月4日連日刊載之,坊間亦不斷私自翻刻,“既說明《使西紀程》有相當的閱讀購買市場,也顯示此日記的強大文化影響力。安徽蕪湖市阿英藏書室藏有阿英先生收藏的光緒四年的《使西紀程》刻印本,北大圖書館藏有光緒十七年和二十三年等數種刻本,就說明此日記當年毀而不絕的市場翻刻狀況。”由此可知,奉旨毀板反而更促進了其流布士林。由于《萬國公報》、《申報》以及《泰晤士報》等報紙的介入,郭嵩燾的日記得到廣泛傳播,其中有關西方政治制度的詳細記載,對十幾年后出現的維新變法運動也起到了一定鋪墊作用。
劉錫鴻的《英軺私記》,最初題作《星軺日記》,初刻于光緒四年(1878年)。據王立誠先生查考,它有光緒年間的鉛印本、袖珍石印本,均分為上下兩卷,也均無印行時間和出版者可考;又有光緒十七年刊行的《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這三種本子都題作《英軺日記》。另一種題作《英軺私記》,有光緒乙未(1895年)三月江標于長沙刊行的“寫錄正本”。此本即收錄江標輯《靈鶼閣叢書》第三集的同一版本,它是《英軺私記》的摘編。《英軺日記》在朱一新的《無邪堂答問》、鄭觀應的《盛世危言新編》等著作中均見引述。
薛福成的《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除小方壺齋本外,還有上海圖書集成印書局、上海醉六堂庸庵全集石印本以及上海積山書局中外時務經濟文編石印本等不同版本。1898年2月14日,《申報》以《薛星使日記》為名加以推介。此書將薛福成出使日記及續刻合刊結集,彌補了有志之士未窺全豹之憾。在載振的《英軺日記》等著作中亦見對其之稱引。載振的《英軺日記》則有1903年的上海文明書局鉛印本。此外,李伯元等的《繡像小說》還自從第1期開始以《京話演說英軺日記》加以登載,連續刊登了38期。
此外,從清人所編撰的西學書目表,亦可窺見晚清使臣使西日記之流播情況。如梁啟超于1896年出版的《西學書目表》中,開列了斌椿的《乘槎筆記》、志剛的《初使泰西記》、郭嵩燾的《使西紀程》、劉錫鴻的《英軺日記》、張德彝的《航海述奇》、《使英雜記》、《使法雜記》、《使俄日記》、《隨使日記》、《使還日記》、陳蘭彬的《使美紀略》、何如璋的《使東述略》、曾紀澤的《出使英法日記》、孫家谷的《使西書略》、李鳳苞的《使德日記》、蔡鈞的《出使瑣記》、薛福成的《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以及崔國因的《出使美日秘國日記》等10多種使西日記。光緒辛丑年(1901年)趙惟熙所輯的《西學書目答問》中,依然將斌椿、張德彝、志剛、郭嵩燾、孫家谷、劉錫鴻、陳蘭彬、何如璋、李鳳苞、曾紀澤(題名為《使西日記》)、薛福成、崔國因等的使西日記收入。可見,晚清使臣的使西日記在19世紀末受到知識界的普遍重視。當然,其中所蘊含的議會記述亦由此得到較為廣泛的傳播。
[1](清)王韜.甕牖余談[M].臺北:新興書局,1978.
[2](清)震鈞.天咫偶聞[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3]錢鐘書.七綴集(修訂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4]王川.從新近刊布的史料看晚清、民國藏政要員的洋務背景 [J].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3).
[5](清)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廿七冊)[M].揚州:廣陵書社,2004.
[6]吳微.西學的輸入與晚清古文的新變[J].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2).
[7]于翠玲.日記風波與〈申報〉糾紛——郭嵩燾毀譽的西方媒介因素分析 [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006,(2).
[8]朱維錚.郭嵩燾等使西記六種[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
[9](清)梁啟超.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