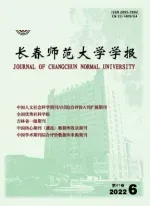消費社會視野中的身份認同教育
黃健毅,陳 良
(廣西民族師范學院,廣西 崇左 532200)
一、消費社會的興起及特征
(一)消費社會興起的過程
在資本主義生產中,消費能力的降低和消費需要的擴大這一矛盾的積累造就了巨大的危機。20世紀初,福特主義的出現極大地緩解了上述危機,它通過采用規模化、標準化的新型生產制度,使大生產和大市場得到完美結合。隨著福特主義的擴大,消費社會悄然形成。
進入60年代以后,福特主義生產制度本身固有的大規模與標準化結構性危機逐漸暴露出來。70年代后期起,具有更大靈活性設備的運用、更節省勞動力生產模式的出現、更具個性商品的生產、更有效引導消費方式的使用,使得消費社會走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此時,商品演變成為一種具有特殊意義的“符號”,一種能讓消費者得到精神滿足的符號。人們面對的不再是“物”,而是整個符號體系。20世紀初,自由主義者提出了消費者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動力。后現代社會理論的發展更是“消費社會”發展的催化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為鮑曼與布希亞。鮑曼認為“消費”在建構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起核心作用,它強調符號性消費;布希亞將消費物品系統和以廣告為基礎的溝通系統看作一種正在形成的“意義符碼”,這種意義符碼將自己的控制施加于社會中的物品和個體二者之上,人們在消費物品時,其實是在消費物品背后的意義,并在此意義中界定社會中的自我[1]110。此后,消費社會正式形成。
(二)消費社會的特征
第一,消費欲望的膨化。消費社會以不斷為大眾制造新的欲望為手段,攫取巨大財富。消費社會里,人們的欲望被無限激發,人人都變成了拜物機器,生活的目標就是購置市場上所有種類的商品,消費能給他們帶來快感。消費的本質不在于滿足生理的需要,而在于不斷追求難以徹底滿足的欲望。人們已經生活在非常豐裕的環境里,卻因受到商品生產者的煽動而無法感到滿足。第二,消費品符號化的意指。體現個人風格和獨特品味的符號化消費品代替了以使用功能為主的耐用消費品。物品已經成為一種其價值由學科性符碼所決定的符號。人們消費時,關注的不是商品的實際用途,而是商品的意義。第三,消費躍為社會再生產環節的主角。社會再生產的過程包括生產、消費、分配和交換四個環節,在生產社會中,生產起著主導作用,它決定著消費內容以及消費的方式。消費社會里,消費決定生產,決定其它環節。商品已能夠滿足人們的需要,甚至已過剩。為此,大眾傳媒和“新的文化傳媒人”通過意義聯想與時尚制造,引領生活風尚,刺激消費,以期維持生產。消費能力降低,便會出現巨大的經濟危機。
二、消費社會中的身份認同
從本質上講,“身份認同”是具有選擇性的,它在強調對象——人屬于某一個群體,而不是其他的群體。在消費社會里,人是具有消費能力的符號。人們在消費中界定自己,在自己消費的商品中認出自己,他們在自己的豪華汽車、豪華別墅、名牌服裝中發現自己屬于“上流社會”的群體,而非“貧窮”群體。
吉恩·布希亞指出,一切物品在社會意義上只是一個符碼,人們在消費物品的時候其實就是在消費符號。人們消費什么以及怎么消費實際上體現和貫徹了對自己身份的一個認同。因此,對自己身份的認同決定了個人在進行消費活動時的選擇,人們的消費活動是圍繞著自我身份認同進行的。在現實社會中,人們消費的物品其實別人也在消費,但是消費者自身無意識地說服和強化自己:“我與那些消費著類似物品的人是不同的”。同時人們在消費時強化自己:“這種商品是階級地位的象征,只有像我這樣的人才能消費得起它”,從而建立自我與商品符號的身份價值關系,進而表明他們與消費這一物品的人是類似的,而與不消費該物品的人是不一樣的。消費物品系統和以廣告為基礎的溝通系統形成的“意義符碼”將自己的控制施加于社會中的個體上,決定著個體的需要,人便失去了自由,成為具消費能力的符號。
三、消費社會中的教育
(一)教育的目的:身份賦予
教育身份賦予指的是受教育者通過接受教育,完成一段學習經歷,獲得一張“證書”,其在社會學意義上就獲得了一種教育身份。特別是學歷社會中,重視學歷的含金量,導致學生在學習上的片面發展和考試戰爭的激化,教育文憑的身份象征便成了眾者所趨之的。此外,用人單位在“買方市場”的優良環境中,過分挑剔地“消費”著教育產品,強化了“擁有高學歷者便擁有高收入,便獲致高質量的生活”的教育身份“效應”。
(二)教育的場域:充滿“符號”
教育場域,即教育中各種元素與矛盾之間存在的多元關系的網絡,是影響教育活動中有形與無形的各種元素與矛盾整合的一個范疇,包含的簡單元素有物理意義上的物質、人員、無形的意識形態及教育活動等。在消費社會里,教育場域就是一個小型消費社會。在教育場域中起關鍵作用的是各種強勢符號。顯然,有形的物質進入教育之前就已經成為了符號。教育中,意識形態往往通過教育政策控制整個教育過程,而掌握教育“話語權”的教育者是其順利實施的保障。同窗成了競爭有限教育資源的對手,教育場域成為一個“符號暴力”彌漫的世界。新生從一入學進入教育場域,就注定要歸訓于教育規則。符合標準的才是常態,順從的學生才是“好學生”,那些具有獨立性、創造性、個性突出的學生則被視為“思想混亂、令人頭疼”[2]92。所以,學生在教育場域中被貼上一個個帶著某種“色彩”的標簽符號,就像琳瑯滿目的商品。
(三)教育的結果:沒有靈魂的機器
消費社會在根本意義上是一個無限紛繁的世界,也是一個無比虛空的世界;是一個充斥著現象的世界,也是一個毫無內在意義的世界。人們在教育場域中棲居,卻又將面對這個世界的無限性和無根基性。因為這個直接的面對,個體的存在滲透了“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都是無依據的”的悖論感。這種根本性的悖論感不斷被強化,并且形成了個體自我認同的基本障礙。一方面,教育讓人們得到更完美“武裝”,但近乎完美的“武裝”使人們忘記了自己是誰;另一方面,在教育中,沒有留下任何能夠給學習生活以深刻而有目的感的東西,學生要做的只是吸收符號,把自己塑造成機器。“總而言之,學生們感到自己不過是一些在沿著供應信息和授予學位的教育裝配線上行進過程中被灌注知識的物件而已”[3]224。
四、結語
消費社會中,消費主體的人異化為具有消費能力符號的附屬,人被規約和訓制于一個個身份的場域中,漸忘了人本的追求和生活之意,淪為了攀附與對比的符號。因此,在消費社會中開展身份認同教育顯得尤其重要。人們需要通過適當的身份認同教育確定適合自己的身份,避免消費不良符號帶來的身份認同困難或者錯誤問題。
[1][美]瑞澤爾.后現代社會理論[M].謝立中,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
[2]楊廣軍.符號的批判——消費社會“課堂場域”的“形上”分析[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06:92.
[3][美]里茨爾.社會的麥當勞化[M].顧建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