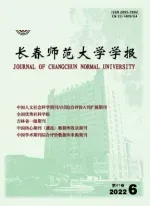日本明治時期北京官話課本中的兒化詞
楊杏紅
(1.閩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福建 漳州 363000;2.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上海 200234)
六角恒廣《中國語教本類集成》[1]共收錄了日本明治時期的北京官話教科書329 本,因其課本語言具有實用性、可靠性、時效性,所以“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是研究清末民初北京官話口語的有利材料。”[2]本文以這些課本語言為研究材料,考察清末民初北京官話口語中兒化詞的基本面貌。
一、官話課本中“兒”化詞的類型
(一)名詞
由“兒”參與構成的名詞,這一類“兒”化詞是最多的,有單音節名詞,也有雙音節名詞。如:
a 今兒 明兒 后兒 昨兒 前兒
b 數兒人兒 本兒 座兒 門兒 畫兒 項兒 面兒 鶴兒 鍋兒
c 草帽兒 連襟兒 碎花兒 秀穗兒 雞子兒 馬褂兒 相片兒 煙卷兒
d 地方兒 門口兒 路口兒 河沿兒 山頂兒 學堂兒 熱河兒
e人緣兒 俗話兒 工夫兒 景致兒 相聲兒 山音兒 存主兒年成兒
其中,a類是表示時間的兒化名詞,太田辰夫認為“今兒”“明兒”等,因在方言里“日”與“二”發音相同,結果變為“兒”[3],從清初可以找到這類現象。
b、c類中前面的名詞都表示的是細小的或者比較親近的事物,這類兒化詞數量比較多。
d類是表示地點的兒化名詞。值得注意的是“熱河兒”這個詞,“熱河”是一個實際的地名,它的后面出現兒化在其他的文獻中很少發現,可能跟“熱河”在當時處于休閑的圣地,讓人倍感舒適,因此才會出現兒化現象。
e類的兒化詞來源沒有固定的說法,大概是習慣說法。
官話課本中有部分三音節兒化詞。如:
銀滴珠兒 紫棠色兒 小意思兒 寶蓋頭兒 小胡同兒 大團龍兒 長方形兒
如果切分的話,三音節兒化詞也可以看成是單音節或者雙音節兒化詞,如上面的三音節兒化詞可以讀為“珠兒、色兒、意思兒、頭兒、胡同兒”。
在清末文獻《兒女英雄傳》中,多次出現“名1 +兒+名2”的結構,如:餡兒餅、緊箍兒咒、紅眼兒魚、熱湯兒面、雙臉兒鞋等等。這類“兒”化詞在日本明治時期的北京官話課本中很少見到,只發現三例:
黃花兒魚 花兒洞子 花兒匠
以上的例子,“兒”綴一般是先和前面的名詞構成兒化修飾后面的名詞,是一種偏正式的構詞方式,因此這種組合的兒化詞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中綴。官話課本中少見此類兒化詞,但今天的北京話中還保留了許多,如“花兒牌樓、豆面兒糕、棗兒檳榔、獨眼兒龍”等等[4]。
(二)量詞
明治時期的北京官話課本中帶“兒”的量詞主要有以下一些,如:
點兒 段兒 半兒 股兒 塊兒篇兒 絲兒 丁兒 條兒個兒 片兒 層兒
這些“兒”化量詞去掉后綴后都可以單獨作量詞使用,它們大部分都保留在今天的北京話口語中。
(三)方位詞
表示方位的兒化詞主要有以下一些:
中間兒 起頭兒 對過兒 雙臉兒 這邊兒 這溜兒 門口兒 西邊兒
官話課本中表示方位的兒化詞和《兒女英雄傳》中表示方位的兒化詞情況基本一致。
(四)代詞
北京官話課本中代詞后加“兒”尾的主要有:
多兒(錢) 幾兒 那兒 這兒
“多兒”“幾兒”是疑問代詞,同“今兒”“明兒”一樣,在“兒”化的過程中后一個詞根發生音變。“多兒”“幾兒”在《兒女英雄傳》中沒有發現,官話課本中卻大量使用。
(五)動詞
在日本明治時期的北京官話課本中,由一個動詞詞根語素加“兒”構成“兒化詞”的現象并不多,如:
開兒(好幾個開兒了,熟了。) 送兒(雇一送兒啊還是雇來回兒呢?) 等兒(等兒今兒晚上連夜時分。)
單音節動詞后面出現“兒”后綴,主要的語法功能是使動詞變成體詞性成分,如“蓋兒、扣兒”等,但在日本明治時期的北京官話課本中,有的單音節動詞附加“兒”后,其詞性并沒有發生變化,如上面的“開兒”“等兒”較為典型,在句中作謂語,“等兒”后還帶有賓語“今兒晚上”。
動賓結構的動詞中,后一個詞根經常“兒”化,以致整個動賓結構變成兒化詞。兒化詞的詞根均為動賓式的后一詞根,因最后一個詞根作為名詞通常可以兒化,習慣性地類推到了這些動賓結構中,這是兒化詞不斷增加的一種方式。如:
撒種兒 有錯兒 沒錯兒 領道兒 起名兒 解悶兒 作伴兒 聽歌戲兒 喝個酒兒 立個字兒 繞著灣兒 就手兒 取笑兒 耽誤兒 拐彎兒 跑堂兒
動詞重疊式帶上“兒”,有的是單個動詞的重疊,有的是動賓式前一詞根的重疊,如:
畫畫兒 坐坐兒 解解悶兒
“V 一(不)V”結構的“兒”化詞,如:
歇一歇兒 等一等兒 候一候兒 聽一聽兒 動不動兒
一些離合動詞,中間加入“著”,如:
盡著力兒 挨著次兒
和我們上面談到的動賓結構兒化不一樣,離合詞的后一個詞根一般不能單獨和“兒”組成兒化詞,如上面的“力兒”“次兒”就沒有發現相應的用例。
(六)形容詞
帶“兒”的形容詞數量不多,主要是雙音節語素帶“兒”的詞,如:
遠兒中路兒 就手兒 好看兒 現成兒 有趣兒 沒味兒 有空兒 出圈兒
重疊形式的雙音節形容詞常“兒”化,如:
涼涼兒 慢慢兒 快快兒 好好兒 遠遠兒 活活兒 爛爛兒
不過,上面這些重疊形式的“兒”化詞,后面一般都要有“的”,如:“偷偷兒的送他走了。”“我們就好好兒的養活他罷。”“您每天飯后總是出去遠遠兒的溜達一趟。”官話課本中有1 例沒有雙音節形容詞兒化不加“的”的句子,“你得好好兒記著。”(《官話篇》)這種情況在《兒女英雄傳》是沒有的。另外,和《兒》相比,官話課本中的重疊式形容詞的類型也少了許多。
(七)副詞
兒化的副詞主要有兩類:一類是因為雙音副詞的后一個詞根經常“兒”化,使得具有這些詞根的副詞也“兒”化,如:
趁早兒 早晚兒 使勁兒 到底兒 工夫兒 大前兒 一起兒
另一類是重疊式的副詞兒化的現象,如:
偏偏兒 準準兒 漸漸兒 偷偷兒 常常兒 天天兒 細細兒
(八)官話課本中出現一些較為特殊的“兒“化現象,這些兒化詞再《兒女英雄傳》中未見。如:
幾兒(今兒幾兒了?)
多兒(一共多兒錢?)
東兒(“您瞧著天氣怎么樣?不礙,決下不起來。若下雨怎么樣?若下,我輸給你一個東兒”)
“兒”出現在助詞“了”后面的現象,如:
可惜了兒(那一把傘是我心愛的,丟了實在是可惜了兒。)
髻了兒(髻了兒一呌,所是夏天了。)
末末了兒(到末末了兒那一回。)
從上面的例句可以看出,“兒”并不附加在前面的助詞“了”上,而是一個單獨的個體。通常我們在說明兒化詞中“兒”的音節時,一般并沒有將其看作一個獨立的音節,但上面幾例中的“兒”,從我們現在的語感來看,念成自成音節更為上口一些,因此我們認為這里的“兒”更像是一個表達語氣的詞語。這樣的用法在《兒女英雄傳》中也未發現。
二、官話課本中兒化詞的特點
上面我們描寫了日本明治時期北京官話課本中“兒化詞”的使用情況,跟同時期國內的文獻相比,基本類型雖然一致,但具體的內容有一定的差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兒化詞總數量相對減少
據汪大昌的統計,清末文獻《兒女英雄傳》全書59.6 萬字,各類帶“兒”的詞總計約5412個,重復出現只記一次的兒化詞有1150個。而早于《兒女英雄傳》約一個世紀的《紅樓夢》前80 回共76.9 萬字,各類帶有“兒”的詞總計不足500,因此,作者認為18世紀到19世紀中后期“兒”尾的使用呈明顯的上升態勢[5]。那么,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北京官話課本中兒化詞的使用情況是怎樣的呢?據我們的統計,《北京官話談論新篇》共5 萬字,兒化詞出現567 詞,不重復的兒化詞有81個;《官話篇》共4.5 萬字,兒化詞出現811 詞,其中不重復的兒化詞有151個。雖然以兒化詞出現的頻率來看,清末的北京官話口語課本中兒化詞出現的頻率更高,但不重復兒化詞的數量少了很多。我們在對比語料的時候,明顯感到《兒女英雄傳》中的許多兒化詞不見于北京官話課本中,如擬聲詞兒化“忒兒嘍婁的、不瞪兒不瞪兒的、嗚兒嗚兒”;重疊式形容詞兒化,如“大大方方兒、婆婆媽媽兒、老老實實兒”;數詞兒化,如“四五六兒、零兒”;還有一些由動詞構成的名詞兒化,如“吃兒、串兒、呈兒、釘兒”。這些帶有濃烈的土語色彩的兒化詞并沒有進入北京官話的課本中。
(二)兒化詞構成趨于規律,詞根相同的雙音節詞已經批量產生。比如:
這兒 那兒
人數兒 家數兒 件數兒 里數兒 天數兒 歲數兒 樣數兒
帳房兒 下房兒 住房兒 柜房兒
一樣兒 幾樣兒 兩樣兒 雜樣兒 各樣兒 照樣兒 這樣兒
浮面兒 當面兒 外面兒
一點兒 好點兒 半點兒
一季兒 四季兒
北邊兒 南邊兒 這邊兒 那邊兒
從統計的數據看,明治時期的北京官話課本兒化詞的出現頻率較高,但如果計算不重復的兒化詞,數量并不多,造成這一現象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詞根相同的雙音節詞大量產生。以“房兒”為例,《兒女英雄傳》中只有“茶房兒”,“住房、下房、柜房”都沒有兒化,而這些詞在官話課本中都已經兒化了。一方面是帶有土語色彩的兒化詞的減少,但一方面是詞根相同的兒化詞的增加,因此我們認為明治時期的北京官話課本中兒化詞的構成更為系統。
(三)語義功能的明晰
日本明治時期的北京官話課本中的兒化詞通常表示細小的事物,有喜愛之意。如:
鳥兒 花兒 盒兒 球兒 桃兒 猴兒 東兒 項兒(脖子) 面兒(粉) 鶴兒 鍋兒
雞子兒 馬褂兒 相片兒 煙卷兒 翅膀兒 信封兒 眼珠兒 碎花兒 官帽兒
另外,兒化詞還能表示親切的語義功能,如:
妞兒 女孩兒 娘兒倆 小孩兒 老頭兒 哥兒們 媳婦兒 老婆兒
盧小群在談到老北京兒化詞的語義時指出:在北京土語中,有時候兒化詞可以帶“大”,這種帶“大”的兒化詞并沒有表示“小”的意思,如“大奶奶兒、大鍋兒、大氣兒、大不點兒”等等;有的兒化詞還表示嘲諷、輕視、嫌棄的感情色彩意義,如“小偷兒、破貨兒、混混兒、鬼門關兒、鄉下佬兒”等等[4]。值得注意的是,這兩類語義功能我們在明治北京官話課本中都沒有發現,這種用法很可能是近一個世紀才產生的。
(四)個別兒化詞的使用跟當時的其他文獻存在著差異
在清中后期的文獻《紅樓夢》《兒女英雄傳》中,表示時間時都使用“今兒、明兒、后兒、昨兒、前兒”,均未發現使用對應的非兒化詞“今天、明天、后天、昨天、前天”。而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北京官話中,我們已經能夠發現一些對應的非兒化詞在使用著,如:《官話指南》中“今兒”24 例,“今兒個”24 例,有3 例“今天”;《北京官話談論新篇》中有4 例“今兒”,14 例“今兒個”,5 例“今天”;《官話急救篇》中有47 例“今兒”,3 例“今兒個”,1 例“今天”。從上面提到的這些材料所反映出來的情況看,大致可以推測,在18世紀中期之后的100 多年時間里表示時間的兒化詞“今兒、明兒、后兒、昨兒、前兒”曾在北京話口語中占有絕對的優勢;而在19世紀末,“今天、明天、后天、昨天、前天”等時間名詞開始在北京官話口語中出現,并逐漸占據主要地位。
指示代詞兒化主要是“這兒”“那兒”,在清代文獻中的使用情況見下表:

從上面圖表中可見,《紅樓夢》里用“這里”不使用“這兒”,到了《兒女英雄傳》中,“這兒”已經開始使用,但是和“這里”相比,使用的頻率并不高。而在日本北京官話課本中,“這兒”使用的比例明顯高于“這里”,有些教材如《日英漢語言合璧》通篇都出現“這兒”。“那兒”“那里”的情況也基本相同。太田辰夫指出:“‘這兒’‘那兒’等的‘兒’則是由‘里’變化形成的,是清代后期出現的變化。”[3]我們從這一系列語料中也證實了這一點。
三、結語
汪大昌在分析了《兒女英雄傳》的兒化詞后認為:無論和100 多年前的《紅樓夢》,還是與百余年后(1950年左右)的北京話相比,19世紀中期的兒化詞具有高度的能產性[5]。而通過對20世紀初北京官話課本中的兒化詞使用狀況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兒化詞在清末民初的北京官話中有明顯的簡化趨勢,一些缺乏規律性、土語色彩較濃的兒化詞并沒有出現在北京官話的課本中,而一些有規律、有特定語義的兒化詞卻數量有增加的趨勢,而且重復率較高,那么是不是說明在20世紀初兒化詞的發展已經趨于簡單化了呢?如果僅憑明治時期的北京官話課本所反映出現的情況下此判斷有些不妥,因為今天的北京話土語中還保留豐富的“兒”化用法,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見盧小群[4]、彭宗平[6]、齊如山[7]等學者的研究成果,具體的例子如“賣嚷嚷兒、媽媽頭兒、曬陽陽兒、四五六兒、針兒針兒、迭兒忙兒”等等。有些例子在《兒女英雄傳》中已見,但清末的北京官話課本中沒有,但在今天的北京話還經常說,如“四五六兒”。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清末北京官話課本中的“兒”話詞數量變少、趨于規律化這一特點呢?我們認為這應該跟北京官話的性質有一定關系。
清代余正燮(1775-1840)《癸巳存稿·官話》“雍正六年,奉旨以廣東、福建人多不諳官話,著地方官訓導,延臣議以八年為限,舉人、生員、貢、監、童生,不諳官話者,不準送試。”[8]為了使方言地區的官員朝見皇帝時消除語言上的障礙,于清朝雍正年間(1728)設立正音館,確立以“北京官話”為國語正音,并刊行了《官音匯解》、《正音撮要》、《正音咀華》等書來推廣北京官話標準音。清政府推行北京官話并不順利,大概經歷了兩百來年,直到清末北京官話才成為全國的共同語。“那些想說帝國宮廷語言的人一定要學習北京話,而凈化了它的土音的北京話,就是公認的帝國官話。”[9]而據《清末北京志資料》記載:“在官話之外,北京另有土語。雖同在北京,但因地之東西,處之南北,其語言多少都有些不同,音調亦不相同。”清人夏仁虎在《舊京瑣記》中就說到京師“言龐語雜,然亦各有界限。旗下話、土語、官話,久習者一聞而辨之。”日本明治時期(清末)的北京官話課本《官話指南》在凡例中也寫道:“京話有二,一為俗語,一為京話,其詞氣之不容相混,尤涇渭之不容并流。”從這些記載來看,清末北京官話是一種不同于當時北京土語的官方用語,如同今天的北京話和普通話的差別一樣。
清末的北京官話已經基本發展成為當時的民族共同語,和當時的北京土語存在著一定的差異,這種差異從兒化詞的基本情況即可窺見。北京官話作為一種“國語”為了適合非這一地區的人的學習,會很自然地過濾掉一些土語色彩濃郁的用法,而另一方面必須注重語言的規律性特點,因為有規律的語言現象更易掌握(這里的規律性包括兒化構成的系統性和語義表現的清晰性),只有這樣才更容易讓非這一地區的人學習。北京官話和北京土語存在差異,土語中有的兒化詞官話中不一定有,而官話中使用的兒化詞土語中也不一定都存在,因為兩者有不同的演化過程[10]。另外,日本明治時期的北京官話課本是外國人編寫的漢語教材,就如同今天南方人在學習普通話的過程中“兒化”“輕聲”始終是難以掌握的內容,在課本中避開一些不常見的兒化詞也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說,是在多方面原因的作用下,才導致了日本明治時期北京官話課本中的兒化詞有別于同時期國內文獻中的兒化詞。
最后要指出的是,使用域外的北京官話課本語言來研究北京話,可以為北京話的歷時研究提供有益的材料,但在使用這些材料時更應該注意到,北京官話的歷史可能并不等于北京話的歷史,北京官話只是北京話的一部分,北京話還包括北京土語,官話和土語相互影響,但又各有特點。只有認真區分材料的特點,才能把漢語史的問題談得更為清楚。
[1]六角恒廣.中國教本類集成[M].日本:不二出版社,1998.
[2]李無未.日本明治時期北京官話課本研究的基本問題[J].吉林師范大學學報,2007(1).
[3]太田辰夫.中國語歷史文法(修訂譯本)[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4]盧小群.老北京土語的語綴“兒”[J].賀州學院學報,2012(2).
[5]汪大昌.《兒女英雄傳》中“兒”尾的使用情況及相關問題[J].語言文字學,2003(2).
[6]彭宗平.北京話兒化詞研究[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5.
[7]齊如山.北京土語[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8.
[8]徐時儀.漢語白話發展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9]威妥瑪.語言自邇集[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10]李無未,楊杏紅.清末北京官話語氣詞例釋[J].漢語學習,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