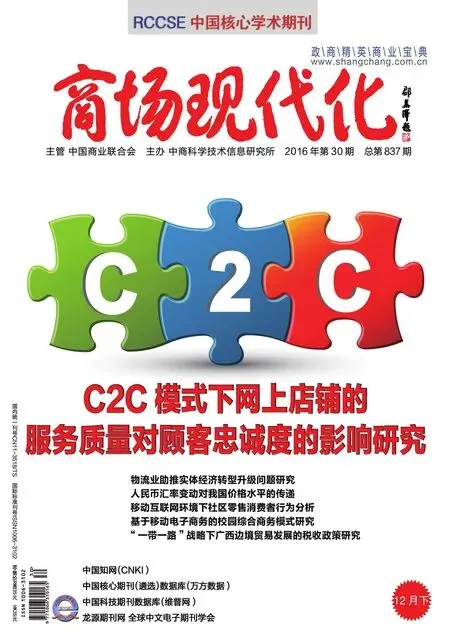中國國有企業所有權分享安排的思考
■馬 嵐 國網安陽供電公司
一、中國國有企業所有權的演變
1.所有權的演變。二十多年來國有企業的改革之路,經歷了放權讓利、利稅分流、兩權分離、承包租賃等一系列的嘗試,后來又經歷了從放權讓利到實行股份制,基本上是沿著“股東利益至上”的邏輯進行的。在這一過程中,過分突出了政府(所有者代表)在企業中的權益,忽視了經營者、生產者和債權人等其他企業契約參與者在企業中的權益和作用,其后果是:一方面,一旦政府強化所有權約束,便強化政企不分現象,一旦放松約束,就會出現經營者剩余控制權的濫用,造成國有資產流失,致使國有企業陷入“管”也難,不“管”也難得兩難困境。
2.全民所有制產權制度安排下的委托—代理關系。在全民所有制的產權制度安排下,如果由全民來行使生產資源的所有者職能,也就是說,采取集體行動投票解決,在不存在交易成本的情況下,顯然能更好的體現全民的意愿并且是可行的,但是也存在因為個體份額小會出現個體之間嚴重的機會主義行為。事實上,會出現集體決策成本,而且這種集體決策的成本是極其高昂的,從而使集體決策公有財產的使用變為不可行,也就是說,每個初始委托人均不能擁有國有企業的所有權(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因此,由國家來代理全民行使公有產權就成為必然選擇。
二、國有企業所有權安排
現代企業不能僅限于出資者利潤最大化,應同時考慮其他企業契約要素提供者,企業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分散對稱分布于企業契約要素提供者之中。因此,國有企業要優化所有權安排,就是要讓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和生產人員等其他企業契約參與者和作為出資者的全民一起成為國有企業的所有者,三者共同擁有企業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共同決策并分享剩余。
1.各級代理人的行為。對于國有企業的初始委托人來說,因為不是剩余的直接索取者,所以缺乏對國有代理的監督積極性,同時因為集體決策的不可行也沒有任何的剩余控制權。國有企業在委托代理關系上成為“沒有最終委托人”的企業,對于國有企業最終代理人來說,處于“非人力資本要素所有者缺位”狀態,這樣,政府就取得了當然代理人,對企業經營者來說就是委托人。在這種委托代理關系下,作為國有企業代理人的政府官員就自然擁有企業的剩余控制權,他們卻沒有剩余索取權。具體表現為剩余控制權由等級規則界定,與其承擔風險的能力及受控資產的經營效率并不直接相關,行政代理人努力的程度與其報酬無關。這樣的行政代理人作為理性的經濟人具有強烈的機會主義動機,因為缺乏約束其動機會導致行為的發生,當存在控制權損失的不可補償性時,就不排除作為國有企業監督者的政府代理人利用手中的“廉價投票權”為自己謀利,或者與同是政府官員,同樣沒有剩余索取權的下級代理人合謀共同瓜分國有資產。他們根本沒有積極性為國有企業挑選合格的經營者反而會通過機會主義行為實現自己效用最大化的目標。同樣,他們也沒有積極性監督經營者的行為,因為不能通過該行為實現自己的效用最大。
2.經營者的行為。國有企業的經營者不是像現代企業的初衷那樣是通過出資者依據經營才能選擇,而是通過行政代理人的行政考核來選擇。這樣國有企業經營者與行政組織、企業組織之間形成的是一種雙重博弈關系,即國有企業經營者與行政組織的重復性博弈、國有企業經營者與企業組織的一次性博弈。這種雙重博弈關系下行政組織將成為對國有企業經營者實行強激勵的主體,而企業組織是弱激勵的主體。這樣,國有企業經營者將主要考慮行政組織的行政目標而忽視現代企業的效率最大化目標。行政組織凌駕于企業組織之上與國有企業經營者發生關系,這樣經營者的選擇不用考慮企業效率,而只要考慮行政組織的目標能否實現的問題。顯然在這種所有權安排下,進入企業契約的經營者是否缺乏經營才能的,這必將導致企業效率的損失。在所有權由企業契約參與者共享安排下行政組織則通過企業組織與國有企業經營者發生關系。在經營者選擇問題上企業契約的其他參與者將一定程度的矯正政府代理人的行為。在這種所有權安排下,行政組織的強激勵主體地位將讓位于企業組織,對經營者行為將進行矯正,使其與企業效率目標相一致,抑制其機會主義主義動機。企業契約參與者共享企業所有權機制,這能夠有效激勵人力資本所有者的專用性人力資本投入。
3.國有企業所有權安排的缺點。企業所有權安排直接決定了各要素提供者在企業中的行為特征。改變企業所有權安排,將最終改變企業各要素提供者的行為。國有企業優化所有權安排后,能夠校正國有企業各契約參與者的行為,使其與企業效率最大化保持一致,由此將提高國有企業效率。
經營者和生產者等其他企業契約參與者相互監督并自我約束,同時也對一級代理人政府實行監督,這樣就解決了“誰來監督監督者”的難題,而國有產權主體則可以搭人力資本所有者的“便車”。這些監督者是企業的“內部人”,他們比國家代理人更了解企業的信息,具有信息優勢,減少信息的不對稱性,這種監督不僅節約監督費用,而且更有效率。因此,在這樣的所有權安排下,國有企業將大大減少來自政府的政治性目標的干預,企業經營者獲得了主要的剩余控制權,這樣能使他們在企業里進行有效的監督。同時,因為他們分享了部分剩余,大大減少了其自身的機會主義行為。另一方面,因為政府干預的減少,也就是說經營者剩余控制權增大,意味著經營者的能力和努力程度將主要體現為企業的效率信息,這樣也減少了其機會主義動機。
[1]袁慶明.新制度經濟學—高等院校經濟學教材.中國發展出版社,2005
[2]盧現祥.西方新制度經濟學.中國發展出版社,2003
[3]王國順,周勇,唐捷.交易、治理與效率.中國經濟出版社,2006
[4]張維迎.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5]科斯.企業的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