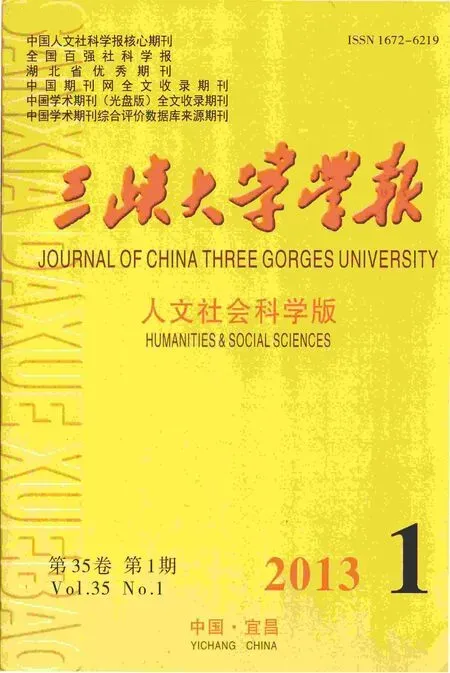明清時期土家族土司戲曲音樂生態生成與特征
熊曉輝
(湖南科技大學藝術學院,湖南湘潭 411201)
明清土司統治時期,是土家族戲曲藝術發展的興盛時期,尤其是戲曲音樂,最能體現土家族音樂文化特色。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土家族土司戲曲音樂對土家族歷史發展所起的作用,它伴隨著土家族人的民俗生活,成為了土家族精神生活的集中體現,有著重要的研究價值。土家族土司戲曲是一種集音樂、舞蹈、詩歌為一體的民間傳統戲劇藝術。它的創作素材來源于宗教祭祀、民間傳說、故事、民族習俗等,有故事情節和人物、角色。由于戲曲藝術來源于民間,故與當地的民歌、歌舞、器樂、曲藝音樂有著密切的聯系,而且有深厚的群眾基礎、濃郁的民族特色、獨特的表演形式。土家族土司戲曲在保留了本地區、本民族的特色以外,還引進和借鑒了漢族及鄰近地區其他民族的音樂特點加以融合與發展,形成了今天以漢族和其他民族文化為底蘊,保留和傳承了本地、本民族特色的戲曲藝術[1]197。土家族土司戲曲包括“儺堂戲”、“陽戲”、“花燈”、“酉戲”、“土地戲”、“木偶戲”、“南劇”、“柳子戲”、“高腔”等十多種。在土家族土司戲曲中,音樂與其他戲曲有著很大的區別,尤其在調式音階、旋律進行、曲式結構、唱腔等方面,有著自己的特色,有著土家族音樂固有的藝術風格,具有珍貴的民族文化價值和研究價值,同時對促進土家族社會發展、構建和諧社會有著積極的現實意義。
一、明清時期土家族土司戲曲音樂的生態生成與文化背景
1.土家族土司戲曲音樂的生態生成
土家族土司戲曲源遠流長,表演內容多與祭祀、民俗、傳說故事等有關。因受地理環境的制約和影響,土家族人相信神靈,崇拜祖先,在萬物有靈的信念下渴望風調雨順、人人平安。在這種現實生活條件下,土家族人從自己的民族戲曲中可以獲得一種精神寄托。所以,無論是儺堂戲、陽戲,還是花燈、酉戲、土地戲等戲曲,都受到土家族人的喜愛,并在土家族地區廣為流傳。同時,土家族戲曲在流傳過程中與當地民間音樂、戲曲融合,從而得到了新發展,也使土家族戲曲更貼近人們的欣賞習慣和生活情趣。
早在土家族社會的漁獵時代,土家族先民就創造了一種表現民俗生活的戲劇形式——毛古斯。毛古斯記敘了土家族先民的生產勞動與遠古時代的民俗生活方式。其中有的再現了古代的漁獵過程,有的反映了艱苦的農業勞動,這些內容都是通過比較輕松活潑的氣氛表現出來的,顯示了土家族先民樂觀向上、活潑開朗的性格和藝術才能[2]92。毛古斯在表演藝術上雖然原始粗糙,但其場次簡便、情節緊湊、語言明快、人物逼真,它與土家族歌舞融合起來表演,有一種原始古樸的藝術魅力,深受人們喜愛。仔細觀察,土家族毛古斯不僅與土家族民俗生活有關,而且與土家族宗教祭祀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后來,土家族地區產生了多種形式的祭祀儀式和儀式戲劇,比如儺堂戲、陽戲等,它對我們認識和研究土家族民間祭祀活動及土家族戲曲發展的關系有著重要意義。
土家族自古生活在湘鄂渝黔邊鄰地帶,這里山高林密,交通不便,生產落后,原始的生態環境神秘無比。由于歷史的原因,土家族人大都分散居在群山峻嶺和深山峽谷之中,這樣的居住環境,造成了土家族人思想意識的閉塞與狹隘,他們寄希望于神靈,“信仰神靈”成了土家族人的精神支柱。在“萬物有靈”的觀念下,土家族人相信神靈,崇拜祖先,把大自然的變化過程看作是無法克服、完全異己的過程,面對神奇的大自然,他們確立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建立了自己的精神對象。千百年來,土家族人一直生活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他們在惡劣的自然條件下,與環境抗爭,與外來勢力拼搏,但對文化、藝術的追求仍然保持著本民族固有的生活激情和娛樂傳統。我們發現,土家族先民在與惡劣的自然環境抗爭過程中,始終沒有停止對人性本能的釋放,積極尋求對樂觀生活的藝術表達。平時,人們交往與交流是通過歌樂的形式來完成的,由于土家族沒有文字,他們的文化傳承只有通過歌樂形式來實現。因此,歌樂成了土家族人極為重要的一種文化交流手段。當然,土家族戲曲藝術也是如此,土家族戲曲是在土家族生態歷史中,在民族與生態環境和諧相處中產生并傳承下來,具有自然選擇的必然性。土家族戲曲與人們所處的生態環境密切相關,土家族先民在“萬物有靈”概念的驅使下,臆造出一個個超自然的神靈,諸如山神、河神、獵神、土地神等等,這些超自然的神靈能夠管理自然,只要對它們尊崇,這些超自然的神靈便能以一種神秘勢力遏制各種自然災害的發生[3]188。可見,自然崇拜不僅是土家族至今保留的古老習俗,也為土家族戲曲藝術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資料來源。
明清時期是土家族戲曲發展的興盛時期,土家族人在傳承與保存自己傳統戲曲的同時,一些民間傳說、神話故事融入到戲曲之中,而且不斷地吸收和改編他民族戲曲,有意無意地吸收著其它戲曲的精華。尤其在音樂方面,不斷吸收湖湘音樂、巴蜀音樂、佛道音樂等營養,增加了一些簡單的伴奏樂,唱腔也逐漸形成了一定的板腔雛形,最明顯的變化就是,土家族原始戲曲音樂由地域性很強的土家原生型音樂形態衍變為跨本土的多種風格的音樂形態。例如辰河高腔、湘劇、陽戲等就是對土家族戲曲影響較大的外來戲曲。據資料記載,明朝嘉靖、清朝乾隆年間,辰河高腔戲班就開始出現職業班社,有高臺班、矮臺班、坐唱三種形式,一直在土家族地區流行[4]143。川劇對土家族戲曲影響較大,明代以后,川劇戲班在四川、貴州等土家族地區流行;至清雍正乾隆年間,土家族部分地區開始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川昆”、“高腔”、“胡琴”、“彈戲”、“燈戲”等五種聲腔。土家族“南劇”原是土家族于清代時期吸納由湖南南部傳入的漢劇改編而成,此劇種后來發展成為糅合川劇及土家族地方方言風格的地方戲。湖南“湘劇”對土家族“南戲”也產生影響,至今土家族的“南戲”中仍有不少“湘劇”的曲牌,如【四平調】、【北路二流】、【吹腔】、【北路】等。“南劇”吸納了地方民間音樂的一些成分,深受土家族人喜愛。“南劇”雖然不是土家族人原創的劇種,但因經過土家族人的再度創作與提煉,演變成為富有南方民族特色的戲曲,可以說是民族文化交流的產物[5]89。對土家族來說,戲曲及音樂已經滲透到他們生產、生活、宗教等各個領域,他們對音樂的喜愛,對戲曲的熱情和追求仿佛與生俱來,在戲曲中能找到生命的意義,能找到自然與樸實的美感,能找到自己的價值。明清以來,土家族土司戲曲藝術及其音樂形式既是土家族人生活的反映,又是其原始民俗生活的真實寫照,也是土家族人適應生存環境的歷史產物,從它的音樂結構與形式中可以感觸到土家族生態歷史的痕跡。
2.土家族土司戲曲音樂的文化背景
在土家族地區,很早就存在著歌舞演故事的戲劇活動,土家族先民巴人曾以巫為中心展開歌舞演故事,在民俗生活、戰爭、圖騰崇拜等形式中,用歌、舞、樂形式表達了自己的愿望與情感。史料與民間傳說都記載了“武王伐紂,前歌后舞”的故事,故事除了敘述土家先民歌舞藝術以外,同時還強調歌、舞、樂在民俗生活、戰爭、圖騰崇拜中的重要意義。秦漢時期,歌、舞、樂演故事已經有了語言對白,動作表演、故事情節等比歌、舞、樂更進一步。據晉代常璩《華陽國志·巴志》記載,《巴渝舞》主要由四部分構成,一曰《予渝本歌曲》,二曰《安臺本歌曲》,三曰《弩渝本歌曲》,四曰《行辭本歌曲》[6]14。《巴渝舞》中安臺、行辭部分就是設壇祭祀、講演祝詞,期間含有歌唱、對白、表演等戲劇成分,這說明《巴渝舞》是屬于有故事情節的歌舞,它具備了“伐紂”故事內容,有“武王”、“紂王”等戲劇人物。這種早期的歌、舞、樂表演故事形式對土家族戲曲形成、發展起著巨大作用。東晉時期,武陵郡也有過“演故事”的歌舞。武陵郡是秦昭王設置的郡,公元前202年漢高祖劉邦將它改為黔中郡,黔中郡曾是土家族先民生活的區域,居住在武陵郡的土家蠻夷被稱為“武陵蠻”或“五溪蠻”。《荊州記》記載:“縣南臨沅水,水源出牂牁且蘭縣,至郡界分為五溪,故五溪蠻。”《宋書·夷蠻》記載:“蠻民所在多險深,居武陵者有雄溪、滿溪、辰溪、酉溪、潕溪,謂之五溪蠻。”這都說明武陵蠻是土家族的先民。唐代,土家族地區不僅流行歌舞,而且民歌也特別流行,在歌、舞、樂表演故事中,人們運用歌舞、祭祀儀式、民俗生活等手法表演故事,使故事的內容和形式更復雜化。唐代中葉,土家族地區盛行《竹枝歌》,這種一人領唱眾人合的表現手法對土家族戲曲音樂的形成有一定的影響。土家族《竹枝歌》并非只是一人獨唱或集體合唱的歌唱形式,而且有時為多曲相聯,有人領唱,有人相和,用鼓和竹子作伴奏樂器。《竹枝歌》在土家族戲曲音樂發展中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諸如《竹枝歌》等類的土家族民間音樂,其在一定程度上對土家族戲曲及音樂形式、內容、體裁等的發展,尤其是戲曲唱腔的形成產生了一定的推動作用。據史料記載,宋朝時期,土家族先民生活的巴蜀地區就有“雜劇”活動,巴、蜀等地出現了召集各種民間藝人進行藝術交流的院壩廣場。在南宋寶慶、紹定年間,巴渝的土家族地區就有各種商品交易集會和戲曲活動場所,還舉辦各種廟會、花會、燈會等[7]35。元代,中央王朝為了加強對西南少數民族的統治,繼續實行了土司制度。早在五代時期,土家族地區各大姓酋長就已確立了對各自地域的統治,到了元代,中央王朝在此基礎上對土司官制、等級以及同中央王朝的關系作了補充和修改。此時,土家族戲曲已經初具規模,并顯示出自己獨特的個性特征。
土家族土司戲曲音樂的形成與發展,還有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那就是漢文化與其他民族文化對土家族文化的影響。明清時期,是土家族社會與外界交流頻繁時期,也是土家族戲曲興盛與發展時期,當時已經出現了具有一定規模的戲劇班子,如“儺戲班”、“木偶戲班”、“陽戲班”、“花燈戲班”等。我們發現,土家族戲曲也逐漸向傳統戲曲形態靠攏,在道白、唱腔、伴奏等形式上不斷漢化,同時又體現著土家族民間藝術的某種風格。土司統治時期的土家族戲曲在音樂調式、唱腔風格上顯示出了自身特點,仍然保持著土家族原始的音樂特征,而且沿著嚴格的師承關系代代相傳。明清土司統治時期,是土家族戲曲全面發展時期,土家族地區特定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環境為戲曲的產生和發展提供適宜的土壤,在受到其他民族戲曲音樂的影響下,其戲曲音樂逐漸多元化。土家族戲曲的產生、繁榮、發展與當時的主流文化息息相關,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據記載,明朝萬歷年間,昆山腔受到統治者和士大夫階層的喜愛,而其它地方戲曲則被看作是“雜調”。直到清代乾隆時期,以“昆山腔”為官腔的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各地方民間戲曲逐漸興起,各種復合聲腔已經形成。在民間,只有小生、小旦、小丑稱為“三小”的地方小戲開始萌芽,成為清中葉戲曲潮流中的一大景觀[8]28。土家族戲曲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發展、興盛的。比如土家族南戲,它的音樂聲腔是在南路聲腔(二黃)、北路聲腔(西皮)合流的基礎上吸收上路聲腔(秦腔、梆子)而形成的一系聲腔,又以南北雜為主,成為皮黃腔系中的重要劇種。根據我們考證,發現南、北路(二黃、西皮)聲腔源于荊河派漢劇,約在清乾隆年間傳入土家族地區;上路聲腔(秦腔、梆子)約在清嘉慶年間傳入土家族地區。高腔是流行于土家族地區的另一地方劇種,最初來源于江西的弋陽腔,后來與本地的佛教音樂、道教音樂、民間音樂等不斷融合,逐漸演變成土家族一大劇種。隨著土家族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宗教等與外界的不斷交流和發展,土家族戲曲在人們日常生活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位置,也為其戲曲音樂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社會背景和文化基礎,同時也給土家族戲曲音樂吸收其它民族戲曲音樂營養提供了契機。
二、土家族土司戲曲音樂特征
1.調式音階
土家族土司戲曲音樂調式大多數屬于不完全的五聲調式,在音階的構成上因地域、劇種的不同而形成各自的特點。

表1 土家族土司戲曲音樂調式音階結構表
比如土家族儺堂戲、陽戲、花燈等戲曲劇種的調式音階,一般多為三音列、四音列結構,少數劇種才表現出完全的五聲音列結構。土家族土司戲曲音樂調式主要以三、五度結構和四、五度結構為主,有的則是兩種調式形態的綜合。
以土家族儺堂戲為例,儺堂戲音樂大多數是不完全的調式音階,基本為三音列、四音列結構,其音階結構明顯地缺宮音或缺角音。如儺堂戲《安猖》唱段:

從上例旋律可看出,《安猖》雖然屬于羽調式,但實際上是一個不完全的調式骨架,因為缺少角音,又沒有大三度結構,因而調性游移,既可以看作是A羽,也可看著為A商,調式形態不明確。明清以來,土家族土司戲曲音樂調式音階逐漸發展為五聲性樂音組織,這種五聲性樂音組織是在三聲音列、四聲音列的基礎上發展為宮、商、角、徵、羽五種五聲性的調式,分別由不同的五種五聲音階組成,并運用于土家族戲曲音樂之中,如圖:
[宮調式]

[商調式]

[角調式]

[徵調式]

[羽調式]

從上圖可看出,五聲性并不等于五聲音階,而是指音調運行時以音組織的核心“大二度”、“小三度”構成三音組的運行規律[9]45。所以,土家族土司戲曲音樂調式音階不僅有三音列、四音列、五聲音階的組織形式,也有各種五聲性的六聲音階、七聲音階等樂音組織形式。
2.旋律進行
土家族土司戲曲音樂因為融入土家族民歌、鼓舞與宗教音樂,故具有強烈的五聲性音列特征,旋律進行以級進、三度小跳為主,間以四度或四度以上的大跳的旋法為主為多,同時出現同音反復或舒而不展,形成一種平穩、怡然自得的旋律走向[10]31。土家族土司戲曲音樂旋律進行有以下幾種特殊樣式。
(1)級進與連續級進。級進與連續級進在土家族土司戲曲音樂旋律進行中最為常見,無論是儺堂戲、陽戲、花燈戲、木偶戲,還是南戲、柳子戲、文琴戲等,級進的二度音程、三度音程比比皆是。土家族戲曲音樂吸收了本民族和他民族的民歌、歌舞音樂、宗教祭祀音樂、民俗音樂等,旋律音調除了同本民族語言有一定的聯系外,主要是由戲曲中角色需要來決定的。比如在儺堂戲中,二度級進和三度以上曲折級進最常見,二度級進為多,二度中又以大二度級進為主。在土家族戲曲音樂旋律發展過程中,旋律多呈下行運動趨勢,比較特殊的是,旋律在進行中一直保持著級進勢頭,乃至越入另一八度,這可能是由人聲或樂器的音域造成的一種意欲超越極限的結果。
(2)同音交替與重復。在儺堂戲、陽戲等土家族戲曲的旋律中,以級進式的“同音交替重復”最為普遍,其旋律往往在“同音重復”中得到引申。如土家族儺堂戲中《高儺·打路》旋律片段:

在上例旋律中,旋律發展是在三聲音列的結構上引申了一個大二度,而且隨著旋律的展開,每個音重復的次數也就越多,“6 6”、“11”、“22”、“33”這種同音連綴在一起的旋律結構形式,是連續交替出現的,先出現的音起著引申旋律向前推進作用,后出現的是對前面音的肯定,起到穩定音作用。土家族土司戲曲音樂旋律主要是靠唱腔中的相同音樂旋律的變化或重復,在戲曲音樂唱腔的內部突出交替和重復。在如儺堂戲等戲曲音樂中,以級進式的“同音交替重復”較為常見,一般在這類戲曲的前半部分唱腔中出現較多,這也正是因為整個戲曲表演中運用儀式音樂素材有所不同。有專家認為,儺戲唱腔音樂與土家族“擺手歌”一樣,重點強調調式主音,這就是它與本地區其它音樂在結構、色彩上的區別[11]473。土家族戲曲旋律的發展離不開“同音交替重復”這一重要表現手法,但土家族戲曲音樂旋律重復、變化手段又是多樣的,樂句變化重復、樂段變化重復都是發展旋律、擴充聲腔的手段[12]。
(3)二、三聲音列序進。二聲音列、三聲音列序進是土家族土司戲曲音樂旋律進行最基本的運行方式,它依次向高、向低的序進形態,以及回旋形態都較為常見。二、三聲音列序進是土家族戲曲音樂旋律發展的基本手法,在某種程度上表現出比較單純的形態特征。二聲音列、三聲音列旋律具有典型的生活化特點,表現土家族樂觀向上的生活情趣,它受到土家族語言的影響,是對土家族語言聲調的一種美化。如民間儺戲中《白旗》唱段:

從以上旋律可看出,《白旗》明顯具有“三音列”特征,其唱腔平穩,節奏起伏性較弱,在節奏上既有松、緊的對比變化,行腔時又有“級進”和“跳進”相互結合,聽起來平和自然。
3.曲式結構
土家族土司戲曲音樂曲式結構復雜多樣,可分為單曲體結構與聯曲體結構。單曲體,有時穩定,有時又比較自由。在聯曲體中,樂句經過重復變化而形成多句體樂段,且呈現多種形態。土家族土司戲曲音樂的單曲體結構形式有:單句體、雙句體、三句體、四句體、五句體和多句體,其中以雙句體為最多。聯曲體結構又是在單曲體的形式上發展起來的,單曲體通常是指由一個樂句組成的樂段,聯曲體以單曲體為基礎,不斷循環往復,而樂句與樂句之間都有樂器銜接,既起到伴奏作用,又起到過渡、充實、調節、幫腔等作用。如《陽戲》中《小姑賢》王氏(旦)唱的《金錢調》:

陽戲《小姑賢》中的金錢調,用鑼鼓作引子,前奏三小節就是第一樂句的變化重復,然后又有兩小節間奏;第二樂句有三小節,緊接著又是四小節間奏,間奏緊緊模仿著主題;第三句是轉句,有三小節,后跟有兩小節間奏,第四局結束。它是典型的一段體結構,起、承、轉、合分明,結構為:引子(鑼鼓2小節)……前奏(3小節)……起a(3小節)……間奏(2小節)……承b(3小節)……間奏(4小節)……轉c(3小節)……間奏(2小節)……合d(3小節)。
我們按習慣把單句體用A表示,那么雙句體、四句體、多句體結構可以表示如下:雙句體:A(領)+A(和);A(領)+A1(和);四句體:A(領)+A1(和)+A1(領)+A2(和);多句體:A(領)+A1(和)+A(領)+A2(和)+A(領)+A3(和)+A(領)+A4(和)+……
4.唱腔
土家族土司戲曲音樂很具有特點,各種戲曲種類相互影響,相互吸收,演出形式大多數與宗教祭祀活動有關,并且融入一體。土家族土司戲曲唱腔音樂比較豐富,它們融合了本民族和他民族的民間歌曲、民間歌舞音樂、民間宗教音樂、民間特色器樂,除了儺堂戲唱腔用嗩吶伴奏之外,其余大多數為鑼鼓伴奏的清唱一啟眾和,氣氛熱烈,民族特色濃厚。如湖北鶴峰地區流行的儺愿戲,是一套完整的祭儀,有24堂法事。鶴峰儺愿戲音樂無管弦只用鑼鼓間奏,也稱打鑼板。打鑼板唱腔分為三類:其一,法師腔。法師腔由掌壇師演唱,掌壇師主持祭壇儀式,演唱時不斷舞動司刀、令牌,吹響牛角,聲腔的高音區沉長,有一特殊腔韻貫穿,爆破音強烈。其二,祭戲腔。祭戲腔是祭祀儀式“正八出”中被請進儺壇的各位神仙的唱腔[13]173。表演時,這些“神”由人化裝扮演,分為生、旦、凈、丑。演唱時,由于受到當地語言的影響,真假聲結合成了一種特殊的韻味風格。其三,正戲腔。正戲腔是鶴峰儺愿戲的主要唱腔,是祭戲腔與當地民歌唱腔的融合,但又與祭戲腔有所區別。正戲腔按照角色行當分為生、旦、凈、丑,一般以上下句的反復構成段落,樂止音為“6”或“2”。音域約在五度至十一度之間,無管弦伴奏,無固定音高。表演時,演唱者用吶喊式發聲方式,在用嗓和潤腔上形成了聲音高亢、音量強大,富有穿透力的演唱特點。
在湘西土家族地區,儺戲唱腔最有特色,其唱腔有十三腔:桃花拜柳、慢三眼、滴水、四平調、辰河、三黃散、悲哀、二黃原、二黃、三黃快、喜樂、倒數、猛虎等。有九板式:雙鳳朝陽、三擊鼓、撲燈娥、單夾雙、豹子頭、鳳點頭、朝金殿、雙拍翅、三錘鑼等。湘西土家族儺戲唱腔突出的特點就是呼應,其“頭、腹、尾”的三部結構形式也就是在呼應原則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目戲有長有短,唱腔結構也有所不同,唱詞長短因唱腔和劇情而定,唱腔曲詞在結構上多有重復。
土家族陽戲的唱腔因流行地域不同也有不同特點,其唱腔體系結構還是屬于民歌體系,按唱腔結構特征分為正調和小調兩大類。正調是土家族陽戲運用最多的一個調群,主要包括正宮調、蛤蟆趕調、金錢調、悅調、陰調、潼關調、小丑調以及由正宮調繁衍出來的正宮二流、正宮三流、導板、叫喊、哀子等板式,正調一般由上下兩句唱腔和相應的兩個調門組成,依字行腔、反復演唱。小調在土家族陽戲唱腔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演唱方法保留了土家族民歌的特點,民風淳樸,生活氣息濃厚。小調唱腔音樂較為固定,但唱詞變化靈活。
土家族土司戲曲音樂中的唱腔手法比較單一,唱腔具有多元、兼容、獨特的藝術個性和民族特質,在演唱方式上有一些模式化特征,有自己唱腔結構組合原則。這樣,土家族土司戲曲唱腔結構既保留了原素材的風格和結構形式,又有創新的因素,它使土家族土司戲曲唱腔更富有嚴密的邏輯性和有規律的音樂組織形式。
[1]熊曉輝.湘西歷史與文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2]彭繼寬,姚紀彭.土家族文學史[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9.
[3]趙書峰,劉能樸.湘西土家族梯瑪神歌調查研究綜述[J].中國音樂,2007(1).
[4]思南縣政協.思南縣文史資料:第九輯[M].1985.
[5]熊曉輝.清代改土歸流時期漢文化對土家族音樂活動的影響[J].音樂探索,2011(6).
[6](晉)常 璩.華陽國志校注圖補[M].任乃強,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7]張永安.巴渝戲劇舞樂[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4.
[8]陳倫旺.土家族地區戲曲興盛的文化藝術背景[J].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3).
[9]田世高.土家族音樂形態論[J].天津音樂學院學報(天籟),2003(1).
[10]熊曉輝.湘西土家族民歌旋法探微[J].民族音樂,2009(1).
[11]張子偉.中國儺[M].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
[12]胡 萍,蔡清萬.武陵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其文獻集成[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13]劉冰清,彭林緒.土家擺手的地域性差異[J].中南民族大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