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空氣質量戰略”落地
◆叔 平 /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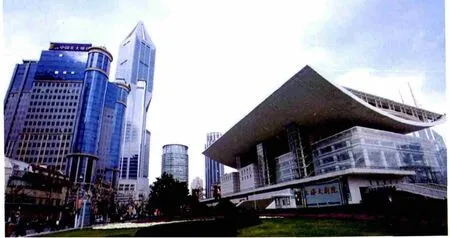
霧霾,2013年12月初開始肆虐十天后暫時離滬而去。人類歷史上沒有同時發生過這么大范圍的這么嚴重的霧霾。不只是上海,范圍有幾百萬平方公里,比當年倫敦霧霾區域大多了。
事實上,倫敦霧都的陰影從未真正遠去——在治理了20多年市民“重見天日”之后,倫敦又被汽車尾氣困擾。2003年,在一片質疑聲中倫敦采取了征收“交通擁堵費”措施。由此,政府公務用車大量減少,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公交車上下班,人們甚至在地鐵里能夠看到當時的倫敦市長肯?利文斯通的身影。6個月后,倫敦市中心區尾氣排放下降12%。但這遠未達到理想的境地,“倫敦仍是歐洲最不健康的城市之一”,為工業革命的“買單”完成了,為汽車革命的“買單”還在繼續中,新市長鮑里斯?約翰遜上任后推出了“市長的空氣質量戰略”,如今還在推行中。
回到上海,情況更趨復雜。因為第一輪燃煤排放引發的霧霾尚未治理完成,第二輪汽車尾氣為害的霧霾又夾擊過來,并有區域性的相互影響。從上空往下看,一大片破棉絮般的污云纏繞在上海的高樓大廈間,排遣不去……
此次霧霾,最兇狠的就是汽車尾氣。由汽車尾氣、燃煤等產生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在空氣中經過化學反應,會進一步轉化成的硫酸鹽、硝酸鹽等更小的顆粒。更可怕的是,濕度達到90%—92%,細顆粒會膨脹8倍,變成靜止不動的“破棉絮”,令人呼吸困難,醫院人滿為患也就不足為怪了。
倫敦的前車之鑒,我們還用多說嗎?當我們的政府官員篤定坐在那里論道“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時,想必憂心此事,會以此為焦點進行問題破解式的探討,拿出強有力的應對之策。
只可惜,治理空氣,并非如治理一條蘇州河那么簡單。空氣是無邊界的,今日的AQI指數還是20多,明天就有可能是200多乃至500。不過,霧霾也似乎是有“靈性”的,哪里GDP膨大,哪里就容易成為它的“家”。由此可見,我們要算大賬,不能因為汽車、房產以及凈化器、口罩等產業拉高了GDP而不以為然。因為發展經濟的目的,是為了讓人們過上更好的生活,絕不能本末倒置。
說起讓人們過上更好的生活,不由想起了令人懷念的上海世博會期間。那是一段藍天白云、陽光燦爛的日子——可見,辦法是有的,就是有堅決的措施下去!我們到底有沒有決心:寧可過粗茶淡飯的苦日子,也不要做霧霾中的“土豪”夢呢?!
措施也是有的。這次特大霧霾期間我們關注到兩個:一個是許多運動員帶面罩奔跑的上海國際馬拉松比賽結束后的第二天,上海發布了霧霾預警。另一個是“肆虐10天本輪污染終告一段落”后,上海發布了“滬大氣污染應急預案”。印象深刻的是“擬‘晚八點早六點’兩次發布”和“PM2.5五年降20%”,以及“下一步將削減煤炭消費總量”等。此前,我們還關注到上海碳排放交易正式啟動和提前實施了新車國V標準。
記得上海“兩會”期間,市環保局局長張全表示,以后遭遇空氣嚴重污染,將進一步加大應急措施,包括部分公車帶頭停駛等。還有委員提議要嚴控“黃標車”上路,并稱高污染的“黃標車”在上海市超過了23萬輛。這些都有措施了嗎?都執行了嗎?執行情況好嗎?未見削減數量信息公布。“PM2.5五年降20%”,與其說要的是措施,不如說要的是執行力!要的是信息公開的透明度!
鐘南山院士最近說:“霧霾的原因基本明確了,在大城市首先是汽車尾氣;第二是作為能源的煤;第三是建筑工地;第四是區域污染;第五是烹調引起。”
佐證此說,上海公布的數據是:目前上海PM2.5的來源25%來自工業,25%來自機動車排放,10%來自工地、堆場、道路揚塵等,7%來自電廠,10%來自秸稈燃燒、餐飲、干洗業等生活排放,另有20%來自區域相互影響。
更有揭示PM2.5來源和形成機制的復旦大學莊國順教授斷言:“煤的燃燒也是重要原因,但是我大膽斷定,這次大范圍霧霾的主要原因在于汽車尾氣排放。”
可見,限制城市的汽車數量,嚴格控制機動車排放,已刻不容緩。當然同時要調整結構,上海必須借助自貿試驗區建設,加快形成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還要以大城市承載力為限度,逐步降低人口密度。
改變能源結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短時間內扭轉困局,只有把“狠招”放在降低交通排放上。其一是降低機動車出行量;其二是降低機動車保有量;其三是提升尾氣質量。
科學發展是硬道理,將“狠招”落到實處,還得將環境治理作為考核領導政績的首要指標。中央批準中組部考核干部:“比發展質量;比發展方式;比發展后勁”,真是好得很。只有這樣,才能“區域聯攔”霧霾。
城市,是安全的保障。人們來到城市,是為了更美好的生活。當我們連呼吸都受阻的時候,什么更重要呢?
趕緊實施“空氣質量戰略”吧,從對車叫“停”做起。當大家安步當車,爭相告別公務車、私家車,以多乘地鐵、公交、多走路為榮時,我們的“空氣質量戰略”就落了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