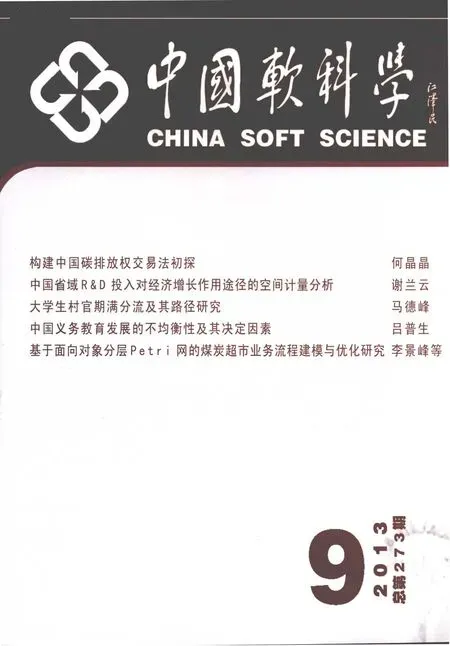收入結構和融資模式對商業銀行盈利和風險的影響
陸 靜,阿拉騰蘇道,尹宇明
(1.重慶大學 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重慶 400030;2.電子科技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四川成都 610054)
收入結構和融資模式
對商業銀行盈利和風險的影響
陸 靜1,阿拉騰蘇道1,尹宇明2
(1.重慶大學 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重慶 400030;2.電子科技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四川成都 610054)
以1997-2010年144家中國商業銀行為樣本,研究了非利息收入份額和非存款融資份額對銀行盈利能力及抗風險能力的影響。首先采用非平衡面板數據發現銀行規模、權益資本比、資產增長率對非利息收入和非存款融資有顯著作用。其次,采用廣義矩估計法考察了非利息收入和非存款融資對銀行盈利和風險的影響。研究表明,非利息收入和非存款融資對中國銀行業的盈利能力有顯著正相關,還能有效地分散風險;GDP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和存貸款基準利差等外部宏觀環境也顯著影響著銀行的盈利和風險水平。中國銀行業應在發展利息收入的同時,進一步開拓非利息收入業務和非存款融資渠道,提高經營水平構建多渠道盈利的模式。
商業銀行盈利;商業銀行風險;非利息收入份額;非存款融資份額
一、引言
2011年12月,中國某股份制銀行行長在接受境外媒體采訪時稱“銀行……利潤太高了,有時候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McMahon,2011)[1],由此引發了2012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關于商業銀行利潤是否過高的討論。重慶市長黃奇帆認為,這源于中國銀行業存貸款的息差達3個多百分點,憑空地比世界上其它銀行多了兩個點(蘇曼麗,2012)[2]。另一些專家則認為“銀行以息差收入為主、盈利靠規模和息差驅動,這種發展方式和盈利模式無法持續,必須加快轉型步伐”(劉詩評等,2012)[3]。所謂轉型,就是要大力拓展中間業務,提高非利息收入的份額。2012年6月9日,中國央行在降低存貸款基準利率的同時,把貸款下浮幅度增加到了20%,并首次允許存款利率上浮10%,這一舉措既加快了利率市場化的步伐,又從監管角度促進了商業銀行改變傳統盈利的模式。特別是對中小銀行而言,甚至面臨著存貸利率倒掛的局面。存貸利差的縮小迫使中國銀行業紛紛擴大非利息收入以保持盈利增長率、努力尋求非存款融資(批發融資)以減少存款成本上升帶來的壓力。那么銀行業收入結構和融資模式的轉變將會帶來正面影響還是負面影響呢?
事實上,自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以來,西方各國紛紛反思銀行業的不同經營模式對其抗風險能力的影響。在次貸危機中,從銀行負債資金來源的角度看,高度依賴批發融資的模式(如美國的投資銀行模式)可能招致較大的風險。從資產運用的角度看,危機也顯露出不同經營模式的缺陷。危機導致美國部分投資銀行破產倒閉(如貝爾斯登和雷曼兄弟等),“兩房”被美國政府接管,美林證券被收購,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轉為銀行控股公司,使美國銀行業完成了模式發展的循環過程:1930年代前實行混業經營制;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迫使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分離;1999年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重新引入混業經營模式;2008年大型獨立投資銀行消失。因此,金融危機后,混業經營的全能制銀行因其遭遇負面沖擊時的較強恢復力成為政府和監管部門青睞的金融機構,重新奪回了銀行業發展的主導地位。就中國銀行業而言,能否借鑒國際銀行業發展的先進經驗,吸取教訓,按照合理和穩健的方式實施收入結構轉型和融資模式調整,是中國銀行業化金融全球化挑戰為機遇的關鍵之舉。
本文立足于1997年中國銀行業實施系統改革之初,采用面板數據分析和GMM(廣義矩估計)方法,力求通過考察1997-2010年間144家中國銀行業的非利息收入及非存款融資(Nondeposit Funding)對銀行盈利和風險水平的影響,既可以解開實業界人士“銀行業盈利模式是否該大力向非利息收入方向扭轉”①參見趙洋.銀行業盈利模式需要怎樣的轉變.金融時報,2012年03月19日。的困惑,也可以警示銀行業對非存款融資渠道的審視、重視和管理,為銀行業進一步提高盈利水平、增強核心競爭能力和防范風險提供參考途徑,為監管部門維護金融穩定、促進經濟繁榮提供決策參考。
二、文獻回顧
現有關于銀行最優收入結構和融資模式的相關研究中,國外學者存在不太一致的觀點(Demirgue-Kunt和 Huizinga,2010)[4]。一種觀點認為銀行通過傳統存貸款業務可以獲取客戶的相關信息,而這些信息會幫助銀行更好地爭取同一客戶的中間業務,銀行開展非利息收入的業務可以增加銀行的盈利并在一定程度上分散銀行的風險,因此,這會促進銀行在未來獲得更好的表現(Diamond, 1991;Rajan, 1992;Saunders和 Walter, 1994;Stein,2002)[5-8]。但是也有學者認為,當銀行的業務或機構設置增加時,會引發額外與金融特質相關的技術問題和潛在的代理問題(Jensen和Meckling, 1976;Jensen,1986)[9-10],因此即便通過非利息收入業務能轉化風險,但轉化的風險與由它帶來的弊端孰大孰小是不確定的。Myers和Rajan(1998)[11]的研究認為,因銀行非利息收入擴大而增加的資產流動性甚至可能提高銀行經營者背離銀行利益的概率。Baele等(2007)[12]采用1989年至2004年間歐洲銀行的數據研究了非利息收入份額對銀行風險和股票收益率的影響,結果發現銀行非利息收入與股票市場的系統風險存在正相關,而與銀行的特質風險存在非線性關系——多數銀行的非利息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時,特質風險減小了。Laeven和 Levine(2007)[13]使用1998-2002年間43個國家的數據考察了銀行的托賓Q值與收入分散化程度(用非利息收入份額測度)之間的關系,他們發現在收入結構和數量上相近的樣本銀行中,收入分散化程度高的銀行一般托賓Q值較低,但是作者沒有詳細討論其中的因果關系,僅解釋這是因代理問題所致的。Stiroh(2004)[14]在研究美國銀行業的非利息收入份額對銀行收益和風險的影響機制中發現,美國銀行業中Z-scores值最高的銀行其非利息收入份額等于零,因此表明非傳統銀行業務可能增加了銀行的風險。
在銀行融資模式的研究中,Diamond(1984)[15]認為銀行的負債結構和它在資本市場獲得批發融資的能力向潛在存款人傳遞了該銀行信用等級的信號。Calomiris(1999)[16]認為如果銀行發行的次級債券超過了存款保險的信用等級,則這些次級債券的投資人實際上發揮了監督銀行經營的作用。因此,銀行的非存款性融資通過較好的監督功能而降低了銀行的脆弱性。然而存款融資和非存款融資將分別通過銀行擠兌或批發融資的突然中止而帶來不同的潛在流動性風險。Huang 和 Ratnovski(2008)[17]建立了一個說明批發融資負面影響的理論模型,他們認為當批發融資的提供者獲取了關于銀行資產質量的負面或噪音信息時,這些批發融資者將撤回資金,從而導致銀行因償付能力不足而破產。
Demirgue-Kunt 和 Huizinga(2010)[4]擴展了Stiroh(2004)[14]的研究,他們采用101個國家1334家銀行截至次貸危機爆發前的數據,分析了銀行收入結構和融資模式對風險和盈利的影響,研究發現當銀行極度依賴非利息收入或非存款融資時,銀行的風險都會很大;其次銀行的非利息收入雖然能增加銀行的盈利,但只能在很小的程度上起到分散銀行風險的作用;而非存款融資對銀行的盈利能力則有負面作用,但其在銀行非存款融資份額不高的情況下,可以有效地降低銀行風險。
與國外相比,國內的相關研究較少,且國內學者的研究視點主要集中在非利息收入這個指標上,鮮有文獻聚焦于銀行的融資模式。僅有的融資模式研究考察的是銀行流動性而非盈利性,如成文豪和王坤(2011)[18]利用工、中、建三大國有商業銀行2004年至2010年的面板數據研究了商業銀行融資模式對流動性的影響,他們得出了10%置信水平下兩者存在線性負相關的結論。在有關中國銀行業收入結構的研究中,學者們主要從三個方面展開。一是分析了中國商業銀行收入的影響因素,如王爽等(2011)[19]通過73家城市商業銀行2002-2009年的財務數據,探析了城市商業銀行收入結構變化的影響因素,他們認為,銀行經營成本、技術進步、資產管理水平、銀行規模和股東結構對凈利息收入有顯著性影響;經營成本和技術進步對非利息收入有顯著性影響。二是研究了非利息收入對銀行收入水平的作用。周好文和王菁(2008)[20]以投資組合理論為基礎,研究了1999-2006期間中國商業銀行非利息收入的波動性與營業收入波動性的關系,發現兩者的波動性呈負相關。在非利息收入對銀行盈利的影響研究中,婁迎春(2008)[21]使用國內 12家商業銀行2000-2005年的面板數據,以總資產收益率為被解釋變量,銀行的非利息收入份額為解釋變量,得出銀行非利息收入份額與資產收益率呈負相關關系,即非利息收入份額越高,銀行的贏利能力越差。不過,盛虎和王冰(2008)[22]采用相同的因變量和自變量,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即非利息收入份額和銀行總資產收益率之間呈顯著正相關。而邢學艷(2011)[23]通過對比分析國內不同規模銀行的非利息收入份額等指標,得出了我國不同類型商業銀行的收入結構存在差異,銀行的資產規模及國有股比率等是造成該差異的主要原因。第三則是從風險角度方面考量非利息收入對銀行風險的影響。但因我國非利息業務開展和發展較慢,直接研究二者關系的文獻較少。鄭榮和牛慕鴻(2007)[24]的研究發現,增加銀行非利息收入在提高銀行收益的同時,也會給銀行帶來風險。魯丹(2008)[25]則利用12家商業銀行1986-2005年的數據研究發現,非利息業務的拓展并不能降低我國商業銀行的經營風險。張慶君和張荔(2011)[26]通過對中國14家商業銀行的實證分析,考察了資產價格的波動對中國商業銀行收入結構及銀行系統風險的影響,得出資產價格波動與銀行系統風險指數間存在顯著的相關性關系,與非利息收入結構有明顯的正相關關系。
本文的研究動機在于以下四個方面。首先,縱觀國內的研究成果,不難發現,學術界受金融危機的啟示和影響的關注點主要局限在我國非利息收入的研究中,但本次金融危機的爆發,除了警示我們銀行風險控制的重要性和銀行盈利模式的重新回歸和定位外,也表明了銀行融資渠道和份額將直接影響到負債的風險性和經營的穩定性,但現有研究并未對銀行融資模式的影響機制給予足夠的重視,也未開展較深入的分析。其次,在探析我國銀行業非利息收入對盈利和風險的影響方面,多數文獻僅從收入角度研究,且主要針對中國四大行和股份商業銀行,樣本的代表性有限,致使研究結論出現較大分歧,我們的研究將涵蓋全國144家商業銀行連續14年的數據,提高了結論的穩健性。第三,國內針對非利息收入對商業銀行經營風險的研究還較少,且衡量銀行風險的指標比較單一,商業銀行是在承擔并管理風險的過程中獲得相應收入的,風險水平對銀行有重要的影響,因此我們擬在研究中納入銀行風險這一因素,特別是采用Z-Score指標測度銀行的風險水平,該指標在國內相關研究中很少被使用過。第四,考慮到傳統的最小二乘回歸在非利息收入對銀行盈利的影響研究中無法處理解釋變量的內生性問題,尤其當加入風險因素時,這種內生性更加突出,因為風險與收益始終是相伴而生的,為此,我們擬采用廣義矩估計方法(GMM方法,Arellano和Bover,1995)[27]來克服變量的內生性問題。
三、研究設計
本文的研究思路是先簡要分析樣本銀行非利息收入和非存款性融資的變化,以及它們與銀行盈利和風險水平的發展趨勢,同時使用相關性矩陣分析這些關鍵指標的聯系;其次分別以銀行的非利息收入份額和非存款融資份額為因變量,選擇銀行內部的特征變量值為自變量,進行面板數據回歸;第三,考察銀行非利息收入和非存款融資對盈利能力和風險水平的影響,在銀行盈利能力的指標上我們選擇了ROA,而銀行風險水平的測度方面,我們借鑒國外學者的做法,使用Z-Score值。為避免樣本異質性問題,解決回歸中的變量內生性問題,我們采用GMM回歸方法。
(一)模型設定
在銀行收入結構和融資模式的影響因素方面,我們設定的分析模型為:

(1)式中,i表示不同的銀行個體;yit是被解釋變量,代表非利息收入份額或非存款性融資份額;Ait為影響銀行非利息收入份額或非存款性融資份額的銀行特征指標,包括銀行規模、權益資產比、資產增長率、費用結構等;Ct為t時期的金融市場結構變量,包括資產的市場份額、存款市場總份額和市場集中度等;Dt為t時期的宏觀經濟變量,包括GDP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等,δit為誤差項。
在銀行的收入結構和融資模式對風險和盈利的影響方面,參考國內外已有研究,以及Demirguc-Kunt 和 Huizinga(2010)[4]、Jokipii 和 Milne(2011)[28]的模型,我們設定的回歸方程如下:

(2)式中①線性形式是分析銀行盈利能力的一種慣用的方程形式。Short等(1979)和Bourke(1989)曾嘗試運用幾種其它函數形式分析,但結論顯示線性模型與其它形式的結果幾乎沒有差異。,i表示不同的銀行個體;Yit是被解釋變量,表示t時期第i家銀行的風險或盈利指標,本文采用的盈利指標是資產收益率(ROA),風險指標使用 Z-score值;Yi,t-1為第 i家銀行風險或盈利指標的滯后項;Z1、Z2為分別非利息收入份額和非存款融資份額;Bit是t時期第i家銀行的內部特征變量,包括銀行規模、Z值、X效率等;Xt為t時期宏觀經濟變量,包括GPD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存款款基準利率、利率變動等,Ct為t時期的金融市場結構,主要是市場集中度;μit為誤差項。
(二)變量選擇
在銀行收入結構分析中,我們選取非利息收入開展研究;在銀行融資策略方面,我們將銀行負債分為存款融資和貨幣市場工具類的短期非存款性融資。我們使用銀行非利息收入占總收入的份額來衡量銀行非利息收入的情況,使用短期非存款融資占其總融資之和的份額度量非存款融資水平,在此基礎上,我們聚焦于銀行不同收入結構和融資模式中隱含的收益與風險的權衡。
在方程(1)的回歸中,我們從銀行特質變量、金融市場結構和宏觀變量的角度,考察它們對銀行非利息收入份額與非存款融資份額的影響。銀行的特征變量有:銀行規模,采用銀行資產的對數形式表示,銀行資產規模的不同,會直接影響到銀行戰略選擇的方向和銀行開展業務的側重點及定位,通常人們認為規模較大的銀行往往更具實力應對風險,掌握風險控制工具、技術及方法,因此我們希望得到銀行規模對銀行的非利息收入業務及銀行持有非存款融資的行為的影響作用力。權益資產比,用凈資產與資產的比值計算,衡量銀行的資本情況。資產增長率,隨著中國金融市場的改革和完善,銀行間業務開展的政策差異性在逐步縮小,銀行業的競爭程度也日趨激烈,因此,可以搶占先機有效運用銀行資源和資本的銀行往往資產增長率的速度也較高,因此不能單一考核銀行規模這一指標,還要結合增長率,看銀行的高資產增長率是否與非利息收入業務和非存款融資有關。費用結構率是銀行的經常費用/總資產之比,衡量商業銀行的開銷結構,體現銀行經營成本的高低,銀行在開展業務和吸收融資時,除了考慮給銀行帶來的收入,也要權衡相應的支出費用。

在方程(2)的銀行特征變量方面,除了本文要重點考察的非利息收入份額和非存款融資份額外,我們還保留了銀行規模變量,且當被解釋變量為銀行盈利指標ROA時,我們在解釋變量中加入了衡量銀行風險程度的Z值。由銀行危機理論可知,商業銀行追求盈利的可持續性時,其抗風險能力是最基本的前提。所以,在分析盈利能力的影響因素時,風險因素的考量不能忽略。與此同時,我們納入銀行效率指標。銀行效率能較好地體現銀行的運營情況,它是指銀行在業務活動中投入與產出(或成本與效益)之間的對比關系,反映銀行對資源有效配置的情況,是衡量銀行在同業競爭中投入產出能力、可持續發展能力及是否具備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指標。效率高的銀行能更好地、更有效地發揮貸款資源、獲得更可觀的收入。但縱觀國內研究銀行盈利決定因素的文獻中,鮮有將X效率作為解釋變量來探討銀行X效率與盈利能力之間的關系。因此本文運用成本X效率來衡量國內銀行的效率,避免了因使用成本收入比衡量成本效率導致的不精準問題,開可以解決采用經營費用與總資產之比作為銀行盈利解釋變量時,與ROA的共線性問題。本文采用Berger等(2009)[29]提出的超越對數函數,運用隨機前沿法測算了中國銀行業1997-2010的成本效率,并將效率結果變形為統一的排序后,作為盈利指標的解釋變量來探討銀行X效率對銀行盈利的影響程度。函數形式如下:

(3)式中,i、t分別代表銀行和年份,k=1,…,4表示4個產出變量,并且 δjk=δkj,C是銀行的費用成本,4個輸出變量y分別是:總貸款、總存款、流動資產、其他盈利性資產;2個投入變量w是:總存款的利息支出和固定資產的非利息支出;固定投入變量z是銀行盈利性資產值①(3)式中除以是為了標準化變形,這樣會降低估計效率的異方差,方便比較。。計算出樣本銀行各年份的成本效率值后,對它們進行升序排序,再采用統一的轉換公式(orderit-1)/(nt-1)使它們變成[0,1]之間的效率水平值,orderit表示銀行i在t年的效率值排序中的位置,其中nt是t年中參加排序的銀行數量。變形轉換后的數字可以反映出銀行i在t年的效率與其他銀行相比時處于整個行業的哪個水平。例如如果一個銀行在t年的效率值強于系統中70%的銀行,則它的效率水平即為0.7。第t年中效率最差的銀行效率水平為(1-1)/(nt-1),即效率水平為 0;第t年中效率最高的銀行效率水平為(nt-1)/(nt-1),效率水平即為1②在比較應用中,效率水平比單純效率排序更精準,因為它能直觀地反映出個體銀行在某年行業中所處的效率水平位置,并且當所有年份的效率值都使用統一標準轉換后,可以在時間跨度上將樣本銀行進行比較。。
方程(2)的宏觀變量除了延用方程(1)中的變量外,還加入了銀行利率波動率及存貸款基準利率差這兩個指標。在分析銀行業行為時,除了宏觀經濟變量外,整體金融市場的系統經濟指標對銀行的影響也尤為重要,所以與其它文獻相比,我們試圖衡量金融系統的經濟指標對銀行盈利和風險的影響程度。在計算存貸款基準利率差時,本文以一年中執行利率的時間為權重加權算出每年的存貸款利率值后再相減。我們參考Garcia-Herrero和Gavila(2009)[30]使用銀行拆借平均月利率的標準差測度利率波動率,但因為數據缺失原因,我們將該文中以7天為基準的銀行拆借平均月利率改為每月衡量的銀行拆借平均月利率,期望運用上述各指標能真實衡量測度出宏觀經濟變量對銀行業盈利能力及風險水平的影響狀況,從而提出合理有效的政策建議。
四、實證分析
(一)數據來源及描述性統計
本文從Bankscope數據庫中收集了1997-2010年末的208家銀行的年度數據,但由于部分銀行數據缺失情況嚴重,所以我們刪除了不足兩年的樣本;剩余的152家樣本銀行中還包括一些現已不存在的銀行如鹽業銀行、金城銀行等③這些銀行被其它銀行并購了。,故也將之刪除。最終獲得的樣本銀行共有144家④在銀行盈利能力及風險水平的回歸分析中,采用的廣義矩估計更適用于大樣本的回歸。。銀行的特征變量來自Bankscope數據庫,行業的相關數據主要取自中國金融年鑒,宏觀數據選自CEIC數據庫(表1)。
從表2可以看到,中國商業銀行的平均ROA為 0.83%,遠低于 Demirguc-Kunt和 Huizinga(2010)[4]1.8%的資產收益率,樣本期間中國商業銀行的ROA在2005年以后才有了較大的增長,在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整體上都低于0.5%,2007年以后才達到了1%左右。其中股份制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都經歷了一個U型發展過程,也就是在2001年中國加入WTO的最初幾年,受到了較大的負面沖擊,隨后又迎頭趕上來了。
我國商業銀行的非利息收入份額的均值為7.054%,雖然該指標在近幾年有大幅提升,但還是小于國際平均水準,并且個別樣本銀行出現了非利息收入份額為負值的情況,由于該值在樣本中的頻率僅為0.109%,故在實際回歸中我們剔除了這種異常值。

表1 主要變量及其含義
非存款融資份額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別為0%、99.11%,接近 Demirguc-Kunt和 Huizinga(2010)[4]的0%、100%,但我國商業銀行的非存款融資份額的平均值更高,因此這值得我們聚焦研究我國商業銀行的非存款融資份額是否處于合理的范圍內,對銀行的風險有無促進作用。而對比Z-score值的情況,我國商業銀行的Z-score值總體較高,說明相較金融危機爆發前國外銀行業的經營模式,我國現行的銀行模式具有更高的安全性,瀕臨破產的機率也較低。

表2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二)主要指標的分析
1.非利息收入份額和非存款融資份額

圖1 中國商業銀行非利息收入份額的頻率分布

圖2 按不同銀行類型劃分的平均非利息收入份額
圖1展示了樣本銀行非利息收入份額的頻率分布,可以發現我國商業銀行沒有任何一家銀行完全依賴于非利息收入業務,分布在0.05和0.10之間達到峰值,即在樣本期間,我國商業銀行的利息收入份額與國際市場股份制商業銀行平均10%~20%、國際性先進銀行40%~60%的非利息收入份額相比,還存在著比較大的差距。圖2可以看到中國商業銀行非利息收入份額平均值的變化趨勢。總體而言,非利息收入份額在逐漸增加,1998年的非利息收入份額處于一個谷底。圖2還表明,1998年,四大國有銀行的非利息收入份額最低,考慮到四大國有銀行的改革在該年剛起步不久,因此其對銀行整體系統的影響程度和能力還較高,所以明顯拉低了行業整體均值。隨著四大國有銀行改革成功和相繼上市,這些大型國有商業銀行憑借龐大的資產和客戶規模、廣泛的營銷網絡及商譽等優勢,非利息收入的提高明顯快于其他商業銀行,處于行業領先水平,到2010年超過了其它所有銀行,這與段玉琴(2010)[31]的研究結論相同。

圖3 商業銀行非存款性融資份額的頻率分布

圖4 按不同銀行類型劃分的平均非存款融資份額
圖3表示非存款性融資份額的分布情況。大多數銀行的非存款融資份額接近于0.05,但還是有少量銀行的非存款融資份額超過了0.5。圖4的非存款融資份額的變化幅度較大,但總體呈減少趨勢,且自2007年后下降幅度極明顯。Demirguc-Kunt和 Huizinga(2010)[4]認為非存款融資是在金融危機中可能造成銀行的不穩定,且經歷次貸危機后,各銀行的非存款融資勢必會有明顯降低。我國商業銀行的近年來的非存款融資份額恰好印證了 Demirguc-Kunt 和 Huizinga(2010)[4]的觀點。
2.非利息收入、非存款性融資、銀行利潤和風險水平
本文使用的銀行盈利指標是銀行資產收益率(ROA),我們采用 Demirguc-Kunt和 Huizinga(2010)[4]中衡量銀行破產概率的指標值——ZScore來衡量銀行的風險情況。Z-Score等于ROA與權益比率(Equity-to-AssetsRatio)之和除以ROA的標準差①與Demirguc-kunt和Huizinga(2010)的方法類似,本文ROA的標準差以近4年的數據為基礎來計算。。Z-Score越大,表明銀行破產的概率就越小。圖5和圖6表示非利息收入份額、非存款性融資份額與資產收益率(ROA)和Z-Score的關系。這兩個圖中,將非利息收入份額和非存款融資份額分別按升序排列后,將排列后的值均等分成20份,將與它們排序時相對應的ROA值和ZScore值取均值后刻畫在圖中。在圖5中,ROA與非利息收入份額、非存款性融資份額的關系趨勢不是很明顯,波動幅度沒有明顯的大起大落,但在整體的趨勢中ROA與非利息收入份額和非存款融資份額呈正相關關系。可以看到,在圖6中,隨著非利息收入份額和非存款融資份額的增加,銀行Z-Score也隨之增加。這與Demirguc-kunt和Huizinga(2010)[4]的結果不太一致,Demirguc-kunt和Huizinga(2010)[4]刻畫的100多個國家的非利息收入份額、非存款融資份額與銀行Z-Score值的關系線呈現倒U型。他們認為在一定程度內,非利息收入份額和非存款融資份額與銀行Z-Score值呈正相關關系,增加它們能分散銀行風險,但超過某一數值后,它們之間的關系會反向發展,呈負相關,增加它們反而會提高銀行的風險。本文認為相較 Demirguc-kunt和 Huizinga(2010)[4]研究的眾多國家的銀行而言,中國現階段的金融發達水平還較低下,且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剛剛起步,無論是非利息收入業務的開展還是非存款融資的擁有量都低于國際平均水平,因此,我國銀行業現階段的正相關關系正處于Demirguc-kunt和 Huizinga(2010)[4]文中倒U型的上升階段。非利息收入高的銀行一般更傾向于持有非存款融資,這與Kashyap 等(2002)[32]和 Song 和 Thakor(2007)[33]中驗證的同一金融機構中負債與收入關系中的非利息收入份額和非存款融資份額的正向共存性相一致。至于這兩個指標對銀行盈利和風險水平的影響研究,將在下文加以分析。

圖5 按非利息收入和非存款融資大小分組后的資產收益率及其擬合趨勢

圖6 按非利息收入和非存款融資大小分組后的 Z-score值及其擬合趨勢

表3 相關性矩陣分析
(三)非利息收入份額與非存款融資份額的影響因素
這里使用面板數據的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分析,回歸結果見表4。回歸(1)、(3)為只考量了銀行特征變量的情況。由回歸結果可知,規模大的銀行非利息收入份額更高,但非存款性融資份額更低。銀行規模與非利息收入之間的正向關系并不是偶然的,規模大的銀行確實在創造非利息收入的業務中更具競爭優勢,有能力提供更多種類的產品和服務,為專業化和產品交叉銷售提供更多的機會等。如圖2和圖4所示,資產規模龐大的四大國有銀行的非利息收入份額就較其他類別的銀行高,非存款性融資份額較低。資產增加快、發展速度快的銀行其非利息收入額也較高,非存款融資份額也高。非利息收入份額與費用率呈正相關的原因在于開展非利息收入業務,不僅需要銀行投入額外的人力、物力拓展銷售網絡,還需要投入額外的資金進行產品研發和配套硬件設施建設,如果銀行的發展相對不夠成熟,開展非利息業務需要的投入必然會引發營業成本的大幅上升。同時我國銀行業所處的經營壞境不足寬松,允許銀行混業經營的政策還未放開,這樣,勢必導致相關業務起步晚,業務關系不穩定,投入成本高的特性。當加入金融市場結構和宏觀經濟變量后,它們的作用影響較小,銀行非利息收入份額只與資產的市場份額顯著負相關,而在高通脹和GDP高增長時期銀行的非存款融資份額較低。

表4 非利息收入和非存款融資的影響因素
(四)銀行收入結構、融資模式對盈利和風險的影響
這部分研究中,我們不可避免地遇到變量的內生性問題。因為盈利高的銀行可能會通過增加權益資本來維持盈利局面,或盈利后通過擴大規模、增加廣告宣傳等手段對未來盈利產生積極影響;從另一個方面考慮,盈利高的銀行也可能會雇傭更多的員工,這會增加銀行支出、降低銀行效率對盈利產生負面影響,即變量之間因果的雙向性會導致內生性。其次,在樣本期內,政府對金融市場還存在一定程度的干預,所以樣本銀行間往往會因為政策差異導致相互間的異質性。這些問題也存在于過去的研究中,但沒有被重視和有效解決。本文采用廣義矩估計方法(GMM)進行回歸。廣義矩估計不要求擾動項的準確分布信息,允許隨機誤差項存在異方差和序列相關,能夠較好地解決解釋變量的內生性問題。GMM回歸采用被解釋變量的水平值和差分值的滯后項為工具變量,與此同時針對可能存在內生性的解釋變量,GMM將它們的滯后項作為工具變量,同時GMM估計能顧及到樣本異質性,因此得到的參數估計量比其它方法更合乎實際。
在表5和表6中,除了明顯的外生變量外,我們對其余變量都使用了工具變量,并將使用工具變量的變量在回歸結果中用斜體字表明①參照Garcia-Herrero和Gavila(2009)。。首先對工具變量的過度識別約束進行了Sargan檢驗,方程中的 Sargan檢驗值分別為:69%、58%、62.9%、45.28%、45.28%、33.92%,按照5%的顯著性水平,不能拒絕工具變量約束有效的原假設,即所采用工具變量的過度識別約束有效。
回歸系數的瓦爾德聯合檢驗表明,拒絕剩余顯著解釋變量系數等于零的假設②我們對初次估計結果使用瓦爾德系數聯合檢驗,假設不顯著變量的系數等于0,如果假設沒被拒絕,則去除不顯著的變量后對剩余變量再次回歸。直到剩余變量的系數等于0被拒絕時,才停止減除變量。,此處我們直接報告最終檢驗后的結果③表格中空白的變量表示在初始回歸中因不顯著,經過瓦爾德檢驗后沒有再繼續帶入下次回歸。。此外,為了便于與其它文獻比較,我們還對顯著的回歸變量進行了面板數據模型估計(固定效應)和OLS,所得到的結果基本一致④限于篇幅,這里沒有報告面板固定效應和OLS的估計結果,需要的讀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表5和表6顯示,中國商業銀行非利息收入份額的比重越大,銀行的盈利水平越高,且增加非利息收入份額可以降低分散銀行的經營風險,表現為非利息收入份額與銀行的Z-score值顯著正相關。目前我國商業銀行從事非利息業務主要是以收費為主的業務,這類業務資本要求低、不涉及銀行的資產與負債,有利于降低銀行的風險,并且所需風險撥備也較低,因此能在一定程度內平滑和緩沖各類沖擊,使商業銀行的非利息收入較為穩定。因此開展非利息業務不僅能幫助我國銀行業的服務呈現多樣化,分散銀行風險,更能在服務中創造收入、增加盈利。同樣地,銀行非存款融資份額也與銀行盈利水平和抗風險能力顯著正相關。非存款融資份額較高的銀行能很好地避免流動性危機,并增加銀行盈利水平。非存款融資份額高的銀行表明其在金融市場上更容易獲得投資者的青睞而籌集資金。通常地,銀行流動性越好,則抵御外界負面沖擊的能力越強,故在不完全的資本市場上,它的籌資成本也相對越低,因此可以提高銀行的盈利能力,但是中國商業銀行目前的盈利大部分來自于存貸款利差,如果銀行資產的流動性過高,勢必會影響銀行的預期收益率,因此在增加非存款融資份額時,有必要將其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

表5 收入結構和融資模式對盈利的影響

表6 收入結構和融資模式對風險的影響
在其它變量中,商業銀行的規模和效率對銀行盈利和抗風險能力有顯著的積極作用。規模較大的銀行,其分布地域往往更為廣泛,它們業務種類齊全,網點數量多,且資產價值高,可以憑借規模優勢降低成本、提高利潤,且規模較大的銀行通過上市后可以對自身風險管理水平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同時我國規模較大的銀行資產實力雄厚,在銀行風險管理中的整體監測、預防和控制水平更高。
宏觀變量中的GDP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的提高、銀行基準存貸款利率差的擴大都有助于提高中國商業銀行盈利水平,增加其抗風險的能力。但銀行系統利率的波動率卻相反。GDP增長率被視作經濟體制發展的一個總指標,經濟中投資機會與商業周期是正相關的,因此銀行商業機會和經濟增長率之間存在正相關性,在GDP增長率降低減緩時,經濟景象衰弱對銀行的抗風險能力是一個檢測機會。從銀行存貸款基準利率差的實證結果中,可以印證中國商業銀行的主要贏利模式仍然是獲取利息差,但隨著利率市場化的逐步發展,未來利率縮小的趨勢不可避免,這會影響銀行盈利能力的可持續性,因此要求中國銀行業應該努力實現盈利來源的多樣性,積極拓展非利息業務,增大非利息收入在經營收入結構中的比重。同時中國金融市場的市場化程度較低并且中國實行嚴格的利率管制,因此當銀行對貨幣政策的調整方向和工具運用沒有準確地預期并做出及時調整時,勢必會在政策轉向時使銀行經營活動受到負面干擾,影響其抗風險能力。
五、結論
本文采用面板數據的固定效應模型對影響中國銀行業非利息收入及非存款融資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在此基礎上,選取銀行的盈利指標ROA和銀行抗風險測度指標Z-score值作為被解釋變量,銀行規模、效率等特質變量和宏觀經濟指標作為控制變量,研究了非利息收入份額和非存款融資份額對銀行盈利能力和風險的影響。研究表明:
①銀行非利息收入主要受銀行內部特征變量影響,其中銀行規模大、權益資產比高的銀行,其非利息收入份額往往較高。同時因中國金融市場的分業經營環境,使銀行業在開展非利息業務中存在局限性,并且開展非利息業務需要銀行投入額外的資金拓展銷售網絡及配置設施等,因此會引發銀行的費用上升。四大國有銀行近年的非利息收入份額有明顯提高,遠高于其他銀行,說明這些銀行已經意識到傳統存貸業務帶來的利息收入增長空間的局限性,正在積極實施經營和戰略管理轉型。
②銀行非存款融資除了受銀行內部特征變量影響外,還與金融市場集中度和宏觀經濟中的GDP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情況有關。銀行規模大、權益資產比高的銀行,其非存款融資份額較低。資產增長速度較快的銀行更青睞于更大的非存款融資份額,體現了成長較快的銀行對資產流動性的需求比較高。當GDP增長率較高或高通脹時期,銀行往往不會大量吸納非存款融資。
③在考察銀行非利息收入份額和非存款融資份額對銀行風險、盈利水平的影響時,我們發現,銀行非利息收入份額、非存款融資份額對銀行的資產收益率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非利息收入業務可以分散銀行經營風險,與測度銀行風險的Z-score值顯著正相關(Z-score值越大,銀行越安全不易破產),而中國商業銀行持有的非存款融資情況仍舊處于較低風險的程度,及倒U型的上坡階段,因此,增加非存款融資份額會起到協調銀行流動性作用,對抗流動性風險。
④除了銀行非利息收入份額和非存款融資份額對銀行風險、盈利的影響外,我們也得到了其它變量的作用關系。規模大、效率高的銀行往往盈利水平更好,應對風險能力的更強;同時銀行的風險水平往往與銀行的盈利顯著負相關,因為銀行承受較高風險經營時,勢必要有更多收益回報才能彌補其承擔的風險。市場集中度對銀行盈利的結果表明,現階段我國銀行業的壟斷情況仍舊存在,占有壟斷地位的銀行因廣泛的網點分布和客戶中的信譽高,更易吸納存款和開展信貸及其它業務,因而更易增加收入,但集中度與銀行的風險水平顯著負相關,集中度的下降會表明競爭程度的上升,而往往激烈的競爭是促使銀行全方位加強自身經營的能力動力,提升綜合實力,這其中自然包括銀行的抗風險能力。就宏觀經濟變量而言,銀行處在經濟周期的繁榮時期時,往往盈利水平更好,中國經濟總體實力的持續走強為中國銀行業盈利能力的提升提供了良好的經濟環境,也為銀行提升抗風險的水平奠定了基礎平臺。此外,有關中國銀行業盈利的主要模式,央行制定的存貸款基準利率差越大,銀行獲得的利潤越多,破產倒閉的可能性越低。但考慮到中國的具體國情,銀行如不能對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方向進行準確預測和及時應對,就會對盈利產生負面影響,利率波動率對盈利和風險指標的負相關即是表現之一。
因此,在傳統業務競爭日益劇烈的情況下,商業銀行的非利息業務種類和創新,非存款融資的便捷和靈活性,在某種程度上為銀行增加了新的利潤增長點,但吸取金融危機的教訓和經驗,隨著這部分業務和非存款融資數量的大力擴展,它們也可能加大盈利的波動性和風險的不穩定性,所以商業銀行在大力拓展非利息收入業務、吸納非存款融資時,不僅要重視對它們成本的控制和縮減,更不容忽視它們的風險。
[1]McMahon,Dinny.民生銀行行長:利潤高得不好意思公布[N].華爾街日報,2011-12-05.
[2]蘇曼麗.兩會代表委員熱議銀行高利潤,銀行行長否認暴利說[N].新京報,2012-03-12.
[3]劉詩平,趙曉輝,顧瑞珍.代表委員剖析銀行“日進斗金”:利潤為何這么高?[EB].新華網,2012-03-03.
[4]Demirgue-Kunt A,Harry Huizinga H.Bank Activity and Funding Strategies:The Impact on Risk and Return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0,(98):626-650.
[5]Diamond D W.Monitoring and Reputation:the Choice Between Bank Loans and Directly Placed Debt[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9,1991.689-721.
[6]Rajan R G.Insiders and Outsiders:the Choice Between Informed and Arm'S-Length Debt[J].Journal of Finance,1992,(47):1367-1400.
[7]Saunders A,Walter I.Universal Ban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What Could We Gain?What Could We Lose?[M].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94.
[8]Stein J.Information Production and Capital Allocation:Decentralized Versus Hierarchical Firms[J].Journal of Finance,2002,(57):1891-1921.
[9]Jensen M C,Meckling W H.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3):305-360.
[10]Jensen M C.Agency Costs of Free Cash Flow,Corporate Finance,and Takeover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6,(76):323-329.
[11]Myers S C,Rajan R G.The Paradox of Liquidity.[J].Journal of Finance,1998,(113):733-771.
[12]Baele L,De Jonghe O,Vander Vennet R.Does the Stock Market Value Bank Diversification?[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2007,(31):1999-2023.
[13]Laeven L,Levine R.Is There A Diversification Discount in Financial Conglomerate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85,2007.331-367.
[14]Stiroh K J.Diversification in Banking:Is Noninterest Income the Answer?[J].Journal of Money,Credit,and Banking,2004,(36):853-882.
[15]Diamond D W.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Delegated Monitor-ing[R].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51,1984.393-414.
[16]Calomiris C W.Building An Incentive-Compatible Safety Net[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1999,(23):1499-1519.
[17]Huang R,Ratnovski L.The Dark Side of Bank Wholesale Funding[M].Mimeo,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Washington,DC,2008.
[18]成文豪,王坤.融資結構對國有商業銀行的流動性水平影響的實證分析[J].財政金融,2011(21):43-44.
[19]王爽,黃雅婷,鮑明明,陳鐘靈.我國城市商業銀行收入結構及其影響因素探析[J].中國外資,2011(22):63-77.
[20]周好文,王菁.從資產組合理論視角審視我國商業銀行非利息收入的波動性[J].經濟經緯,2008(4):155-158.
[21]婁迎春.我國商業銀行非利息收入對經營績效的影響研究[J].經濟師,2008(4):240-242.
[22]盛虎,王冰.非利息收入對我國上市商業銀行績效的影響研究[J].財務與金融,2005(5):8-11.v[23]邢學艷.我國商業銀行收入結構的實證分析[J].經濟師,2011(9):181-183.
[24]鄭榮年,牛慕鴻.中國銀行業非利息業務與銀行特征關系研究[J].金融研究,2007(9):129-137.
[25]魯丹.多元化經營能降低銀行風險嗎?[D].復旦大學,2008.
[26]張慶君,張荔.資產價格波動對商業銀行風險的影響[J].金融論壇,2011(5):25-30.
[27]Arellano M,Bover O.Another Look at the Instrumentalvariable Estimation of Error-components Models[J].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5(68):29-52.
[28]Jokipii T,Milne A Bank Capital Buffer and Risk Adjustment Decisions[J].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2011,(7):165-178.
[29]Berger A N,Hasan I,Zhou M.Bank Ownership and Efficiency in China:What will Happen in the World's Largest Nation[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2009 ,(33):113-130.
[30]Garcia-Herrero A,Gavila S,Santabárbara.What Explains the Lower Profitability of Chinese Banks?[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2009,(1):2080-2092.
[31]段玉琴.我國商業銀行贏利模式轉型研究[J].中國市場,,2010(40):56-58.
[32]Kashyap A K,Rajan R,Stein J C.Banks As Liquidity Providers:An Explanation for the Coexistence of Lending and Deposit-Taking[J].Journal of Finance,2002,(57):33-73.
[33]Song F,Thakor A V.Relationship Banking,Fragility,and the Asset-Liability Matching Problem[J].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07,(20):2129-2177.
[34]利明獻.利率市場化下的銀行盈利模式[J].中國金融,2011(20):28-29.
[35]趙洋,李文龍,楊洋.銀行業盈利模式需要怎樣的轉變[N].金融時報,2012-03-19.
[36]Bourke P.Concentration and other Determinants of Bank Profitability in Europe,North America and Australia[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1989(13):65-79.
[37]Caprio Jr.G.,Demirgue-Kunt A,Kane E J.The 2007 Meltdown in Structured Securitization:Searching for Lessons Not Scapegoats.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WPS4756,World Bank,Washington,DC,2008.
[38]Short R E,Bellows R A,Staihmiller R B,Carr J B.Multiple Linear and Nonlinear Regression Analyses of Factors Causing Calving Difficulty[J].The Riogenology,1979,(12):121-130.
[39]Taylor J B,Williams J C.A Black Swan in the Money Market[R].Working Paper 13943,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Cambridge,MA,unpublished,2008.
The Impact of Banks'Activity and Funding Strategies on Risk and Returns
LU Jing1,Alatengsudao1,YIN Yu - ming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30,China;2.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Chengdu 610054,China)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lications of bank activity and short-term funding strategies for bank risk and return using a sample of 144 banks in China from 1997 to 2010.First,this paper uses unbalance panel data with fixed effects to analyze what explains banks'noninterest income and nondeposit funding.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noninterest income and nondeposit funding of these banks is not only determined by asset scale,but also concerned with the ratio of equity to assets and growth rate of real bank assets.Besides,we use panel data GMM method to analyze empirically how noninterest income and nondeposit funding affect the profitability and risk of sample banks.We find that both of them increase the return on assets,and also could offer some risk diversification.Moreover,real GDP growth,inflation and standard interest margins have also been found to affect commercial banks profitability and risk.While getting much more interest income,the Chinese banking should further explore the non-interest income and nondeposit funding business,improve operational level and build profits of multi-channel mode.
commercial bank profitability;commercial bank risk;noninterest income share;nondeposit funding share
F832.33
A
1002-9753(2013)09-0023-14
2012-12-04
2013-06-18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71373296,71232004,71272085)、國家社會科學基金(09BJL024)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金(12YJA630135)資助項目。
陸靜(1966-),男,四川樂山人,重慶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金融系副主任、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美國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訪問學者,研究方向:金融風險計量與管理。
(本文責編:瑞 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