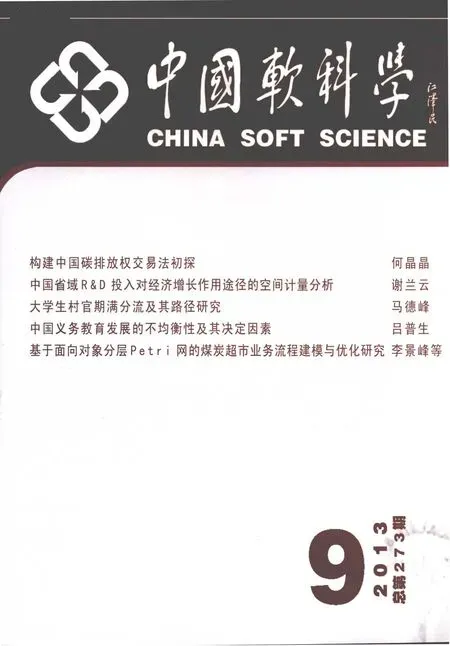中國義務教育發展的不均衡性及其決定因素——基于2000-2008年數據的實證分析
呂普生
(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湖北武漢 430072)
中國義務教育發展的不均衡性及其決定因素
——基于2000-2008年數據的實證分析
呂普生
(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湖北武漢 430072)
中國義務教育發展的不均衡性主要體現在區域差異、城鄉差異、校際差異和群體差異等方面。2000-2008年相關數據資料顯示,4個方面的差異情況總體上要么呈現出擴大趨勢,要么穩定在高位水平,目前尚未得到顯著緩解,而且校際差異遠甚于其它方面。這種不均衡性的根源在于供給模式的不合理性,即在傳統精英主義路線下,以政府單一供給為取向的重點導向型供給模式。
中國義務教育;不均衡性;區域差異;城鄉差異;校際差異;群體差異
一、問題、方法與目標
優先發展教育是我國國家發展的基本戰略,而義務教育是整個教育體系中可塑性最強的階段。然而,當前我國義務教育卻面臨著十分嚴峻的問題,其中最為突出的是發展的不均衡性,這種不均衡性從入學機會、資源分享機會和教育成就機會等方面直接引致教育的不公平性,進而再生產社會的不公平性。
我國義務教育發展的不均衡性究竟體現在哪些方面,達到了何種程度?什么因素從根本上導致了這種不均衡性?如何應對這種不均衡性?本文著力探討前兩個問題,同時也對第三個問題進行初步討論。
本文主要運用2000-2008年可得的官方統計數據和可靠的實證研究資料,從4個方面來分析我國義務教育發展的不均衡性:即區域差異、城鄉差異、校際差異和群體差異,其中每一個方面都從教育機會、教育投入和教育成效3個維度中選擇最能體現其差異的“個別維度”進行分析,而所選維度又采用“最為直觀的指標項”加以佐證。其中(1)教育機會的指標項涉及入學率、特殊教育學生入學率、男女童入學率差異;(2)教育投入的指標項涉及經費投入、辦學條件、教師資源等方面;(3)教育成效的指標項則涉及普及率、學生輟學率和鞏固率、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1]、教育基尼系數、不同經濟文化背景學生的入學率和升學率差異,等等。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本文不打算也沒必要討論所有維度和所有指標項,而只是選取其中反映直觀且數據易得的維度和指標項加以論證。
本文所運用的官方統計數據主要來自歷年《中國教育統計年鑒》、《中國教育經費統計年鑒》和中央及地方政府網站所公布的官方統計數據,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以及計算與繪圖的方便性,有些指標項選取2000-2007年數據,有些選取2000-2008年數據。其他實證研究資料一方面來自筆者的實地考察,另一方面取自具有較高可信度的學術研究文獻。
本文使用的測度指標項差異情況(或離散程度)的具體方法包括極差、標準差、極差率、差異系數和教育基尼系數等。其中極差和標準差主要反映數據離散程度的絕對差異,數值越大,表明絕對差異越大;而極差率、差異系數和教育基尼系數主要反映數據離散程度的相對差異,數值越大,相對差異也越大。
通過該研究,本文試圖在以下兩方面作出推進:(1)學界對中國義務教育發展的不均衡性已有共識,但從實證層面證明這種不均衡性的數據資料相對陳舊,本文則運用新近的數據資料,對中國義務教育發展的不均衡性重新作出論證,揭示這種不均衡性至今尚未得到有效緩解,在有些方面甚至存在擴大趨勢。(2)從供給模式選擇角度對導致中國義務教育發展不均衡性的根源作出全新解釋。既有研究傾向于從經濟發展的區域差異和城鄉分化的二元結構角度解釋義務教育發展的不均衡性,但這尚未觸及根本,因而解釋力相當有限。本文認為,導致中國義務教育發展不均衡性的根本原因是不合理的供給模式,即在精英主義路線下,以政府單一供給為取向的重點導向型供給模式。因此,破解中國義務教育發展不均衡性的根本出路在于變革供給模式,從精英主義轉向“全納主義”,從重點導向戰略轉向優質均衡發展戰略,從政府單一供給轉向政府主導型復合供給。
二、義務教育發展不均衡性實證分析
中國義務教育發展的不均衡性主要體現在區域差異、城鄉差異、校際差異、群體差異、民族差異和結構差異等方面,本文集中考察前面4種差異。
(一)區域差異:省際間差異與縣市間差異
義務教育發展的區域差異可以從4種不同角度加以衡量:一是省際間區域差異;二是省域內差異,主要包括一個省域之內市州之間的差異和縣際差異(即縣市間差異);三是按一般的地理和行政特征所劃分的,以東、中、西部地區為分析單位的區域差異;四是按照全國教育發展指數所劃分的不同教育發展水平地區之間的區域差異①有學者仿照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有關人類發展指數(HDI)的計算公式,構建出教育發展指數(EDI),用來全面反映和比較中國各省區市的教育發展水平。[2]。本文采用前面兩種角度。
1.省際間區域差異
義務教育發展的省際間區域差異可以從教育經費投入上得到直觀反映,具體包括省際間的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差異、財政預算內教育經費差異②需要說明的是,這里的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和財政預算內教育經費是針對一個省份各級各類教育的總體投入而言的,但它也能大致反映義務教育的投入情況。、義務教育階段生均教育經費差異和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差異等方面。
(1)從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看,2007年最高的3個省份依次是廣東、江蘇和北京,分別為681.1億元、567億元和502.1億元;最低的3個省份依次是青海、西藏和寧夏,分別為40.5億元、40.6億元和54.8億元。[3]經費最高省份是最低省份的16.8倍。如表 1、圖 1、圖 2所示,從 2000年到2007年之間,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的標準差數值一直處于上升趨勢,差異系數雖然趨于下降,但仍處于較高水平。這表明省際間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的絕對差異依然在擴大,而相對差異有所減小,但相對差異的水平仍然較高。

表1 2000-2007年各地區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的標準差和差異系數

圖1 2000-2007年各地區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標準差的時序變化

圖2 2000-2007年各地區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差異系數的時序變化
(2)從財政預算內教育經費看,2007年最高的3個省份依次是廣東、江蘇和北京,分別為641.6億元、506.1億元和417.9億元;最低的3個省份依次是青海、西藏和海南,分別為39.1億元、40.4億元和48.6億元。最高省份是最低省份的16.4倍。[3]2000到2007年間財政預算內教育經費與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的變化趨勢基本相同(表2,與之相關的圖與上述圖1、圖2相似,在此省略)。

表2 2000-2007年各地區財政預算內教育經費的標準差和差異系數
(3)從義務教育階段生均教育經費來看,2007年普通初中生均教育經費最高的3個省份依次是北京、上海和浙江,分別為16946元、15729元和7106元;最低的3個省份依次是貴州、河南和安徽,分別為 1962 元、2268 元和 2292 元(圖 3)[3]。最高省份是最低省份的8.6倍。從表3、圖4和圖5可以看出,2000到2007年之間各省份普通初中生均教育經費的標準差隨時序變化而以較大幅度在不斷拉大,差異系數先是擴大然后趨于穩定并維持在較高水平。這表明省際間初中生均教育經費的絕對差異在持續擴大,而且擴大速度比較快,相對差異同樣也在擴大,并且相對差異的水平非常高。這也意味著省際間生均投入差異的形勢非常嚴峻,不同地區間學生所能享受的教育資源有非常大的差異,資源分享機會存在顯著的不公平性。

圖3 2007年各地區普通初中生均教育經費排序
①這里的平均數是指各地區生均教育經費的算術平均值,而不是全國生均教育經費。以下各表中涉及生均投入的平均數含義與此相似。

表3 2000-2007年各地區普通初中生均教育經費的標準差和差異系數

圖4 2000-2007年各地區初中生均教育經費標準差的時序變化

圖5 2000-2007年各地區初中生均教育經費差異系數的時序變化
2007年小學生均教育經費最高的3個省份依次是上海、北京和天津,分別為13592元、10684元和5703元;最低的3個省份依次是貴州、河南和江西,分別為 1574 元、1628 元和 1906 元(圖 6)[3]。最高省份是最低省份的8.6倍。表4、圖7和圖8顯示,省際間小學生均教育經費的標準差隨時序變化不斷拉大,與初中生均教育經費變化趨勢相同,但其差異系數呈現出先擴大后縮小的趨勢。需要注意的是,小學生均教育經費的差異系數雖然有縮小趨勢,但它是在達到一個極高值0.810之后才有所減緩并依然維持在接近0.7以上的高水平。這表明省際間小學生均教育經費的絕對差異和相對差異都還非常大。
(4)從義務教育階段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來看,可以得到與生均教育經費基本相同的結論,在此不贅述。
2.縣市間區域差異
省域內市州間和縣際間區域差異的實證數據鮮有權威且公開的統計文獻可循,因而本文主要參考了既有學術文獻中的一些數據。就市州間義務教育發展的區域差異而言,有學者研究了2005年湖北省公共教育經費的分配狀況:
從省內區域差異來看,2005年,湖北全省小學“預算內生均公用經費”的基尼系數分析結果顯示,17個市(州)中小于或等于全省數值(0.34)的市(州)占67%;普通初中“預算內生均公用經費”的基尼系數小于全省數值(0.35)的市(州)占75%。這一現象說明,大部分市(州)之間義務教育發展水平差異大于市(州)內部差異[4]。
這份資料顯示,2005年湖北省義務教育階段生均預算內公用經費的基尼系數介于0.34~0.35之間,七成左右的市州小于全省數值,三成左右的市州大于全省數值。這表明全省的差異更大程度上是由各市州之間的差異造成的,而且市州間差異大于市州內部差異。由此可以證明:省域內市州之間義務教育的區域發展是極不均衡的。

圖6 2007年各地區普通小學生均教育經費排序

表4 2000-2007年各地區小學生均教育經費的標準差和差異系數

圖7 2000-2007年各地區小學生均教育經費標準差的時序變化

圖8 2000-2007年各地區小學生均教育經費差異系數的時序變化
從縣域間差異同樣可以佐證省域內義務教育發展的區域差異。有學者以縣為單位,按經濟發展水平從東到西把山東省劃分成五類地區,并相應地選擇代表各地區平均水平的5個縣,研究了2002年義務教育的發展狀況。分析結果顯示,2002年山東省東部縣人均教育投入水平、教師工資水平、農村中小學生均教育經費等各指標是西部縣的3.25~4.68倍。該研究對比了全國東中西部地區的差異情況,認為全國范圍內東部地區基礎教育各項經費指標是中西部地區的1~2倍,因而得出了“省內教育差距大于省際教育差距”的結論[5]19-24。這里的數據至少證實了省域內義務教育發展中不容忽視的縣際差異。如果把城鄉差異和校際差異也納入到省域內差異,可以確信,義務教育發展的省域內差異應該會大于省際區域差異。因此,省域內義務教育發展不均衡是一個更為突出的問題。
(二)城鄉差異
一般意義上的城鄉差異可以有兩種理解:一是指城市(大中城市)與農村的差異;二是指城鎮(包括城市和縣鎮)與農村的差異。統計學意義上的城鄉差異通常是指后者。此處有關生均教育經費的分析主要采取統計學意義上的“城鎮與農村差異”①由于統計年鑒對一些數據并沒有作出統計,在計算各指標的城鄉差異,尤其是生均教育經費和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的城鄉差異時,即使按這種統計學意義去計算,也將遇到非常大的計算量。必須指出的是,統計學方式(城鎮與農村差異)實際上會大大縮小大中城市與農村的真實差別,因而城市與農村的差異通常是大于城鎮與農村差異的。,不過這種統計方式所顯示的城鄉差異會大大小于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差異;有關教師質量的分析主要考察城市與農村的差異。
最能直觀反映中國義務教育城鄉差異的統計指標是生均教育投入和師資水平。從生均教育經費來看,2003年城鎮和農村地區小學生均教育經費分別是1751元和1058元,城鎮大約是農村的1.66倍②按表中數據的嚴格計算是1.65倍。文字表述中取整數的地方,按文字表述中所取數據計算。下同。;普通初中分別是2086元和1211元,城鎮是農村的1.72倍。到2007年,城鎮和農村地區小學生均教育經費分別是3157元和2464元,城鎮是農村的1.28倍;普通初中分別是3845元和2927元,城鎮是農村的1.31倍(表5)。
從2000-2007年生均教育經費城鄉之比的時序變化來看,小學生均教育經費的城鄉差異先是不斷擴大,然后趨于縮小;初中生均教育經費的城鄉差異盡管有所波動,但呈現出縮小的趨勢(圖9)。這說明義務教育階段生均教育經費的城鄉差異總體上在不斷縮小。2007年的城鄉差異都縮小到1.3倍左右,這與近幾年實行的城鄉統籌的免費義務教育和國家加大對農村地區的教育投入有關。盡管如此,城鄉差異卻一直存在,而且從生均教育經費的絕對差值來看,城鄉差異還比較大:其中2003-2007年間小學生均教育經費城鄉差值都在700元左右,初中城鄉差值都在800元以上。

圖9 2000-2007年義務教育階段生均教育經費城鄉之比

表5 義務教育階段中小學生均教育經費城鄉之比 單位:元,%
與生均教育經費城鄉之間的絕對差異保持穩定而相對差異不斷縮小的情況有所不同的是,義務教育階段教師資源的城鄉差異呈現出另外一些特點。從教師學歷合格率②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第十一條的規定,“取得小學教師資格,應當具備中等師范學校畢業及其以上學歷”;“取得初級中學教師、初級職業學校文化、專業課教師資格,應當具備高等師范專科學校或者其他大學專科畢業及其以上學歷”。據此,小學教師中師以上、初中教師專科以上為合格學歷。學界把“小學教師專科以上學歷”和“初中教師本科以上學歷”分別看作小學和初中相對高水平的教師學歷。來看,即使直接對比城市與農村的情況,2003-2008年小學教師合格率只有微弱的差異,而且這種差異在不斷縮小;初中教師合格率由相差8個百分點迅速降低到相差2個百分點。縣鎮與農村之間的差異則更小。2008年城鄉教師合格率總體上已比較接近(圖10)。

圖10 2008年義務教育階段教師質量城鄉差異
可是,教師合格率的微弱差異并不意味著城鄉教師的質量水平是大體相當的。表6和圖10充分表明,義務教育階段中小學實際的教師質量在城鄉之間還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從城市和農村的“小學教師專科以上學歷”來看,2003年城市的比例為64.4%,農村為31.77%;2008年城市的比例為87.96%,農村為62.82%;2003-2008年間城市與農村相差大約25!32個百分點。從城市和農村的“初中教師本科以上學歷”來看,2003年城市的比例為48.65%,農村為14.28%;2008年城市的比例為75.93%,農村為42.33%;2003-2008年間城市與農村相差大約33~39個百分點。這種相對差異的程度是十分驚人的,而且,更為嚴峻的是,2003-2008年間義務教育階段教師質量,尤其是初中教師質量,一直維持著高度的差距,并沒有很明顯的縮小趨勢(圖11,圖12)。這必須引起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嚴正關切。

表6 2003-2008年義務教育階段中小學教師質量城鄉差異 單位:%

圖11 2003-2008年小學教師專科以上學歷城鄉差異

圖12 2003-2008年初中教師本科以上學歷城鄉差異
(三)校際差異
校際差異是民眾最能直觀感受到并且直接影響公民受教育權的一種教育差異。義務教育階段的校際差異表現為各種形式:既有優質學校與薄弱學校的差異、言明或不言明的示范校與普通校的差異,又有城鎮學校與農村學校的差異,還有公辦學校和民辦學校的差異,等等。
校際差異的內容可以概括為如下方面:一是教育投入方面的差異,包括教育政策傾斜、教育經費投入、師資水平、教育設施設備和校舍條件等方面。享受教育政策傾斜的學校(如示范校或優質公立學校),不僅能獲得較大的經常性經費投入,而且還能獲得名目多樣的巨額專項教育基金。同時,這類學校還擁有較高質量水平的教師隊伍,教師待遇和發展空間也明顯優越于薄弱學校中的教師。二是教育管理制度、教育理念和方法的差異。基于教育投入優勢而獲得的優秀的學校管理者和師資隊伍,通常擁有較好的辦學理念、可以設計正確合理的教育目標和制度安排,形成良好的教學方式和學校文化,這為學生成長提供了寶貴的教學環境。三是教育成效的差異。良好的教育資源、管理制度、教學方法和學校環境更易于產生較好的教育成效,而顯著的教育成效則可以為學校贏得良好的社會聲譽。正是這種“名牌效應”產生了第四種校際差異,即潛在教育影響的差異:包括進一步獲得政策傾斜和各種專項經費,穩定和發展師資隊伍,以及吸引社會捐資助學和良好的生源,等等。
如何來證實這種校際差異呢?一種方法是對全國范圍中小學校的典型樣本進行校際比較;另一種方法是比較某一行政區域內中小學校之間的差異。根據第一種方法,有學者進行了全國范圍的分層抽樣調查,得出了2004年的一些數據,從不同類型中小學的教育經費、教師學歷層次和教學儀器設備等方面證實了義務教育發展的校際差距[7]221-226。筆者在此采納其中的關鍵數據作為分析的基礎。

表7 2004年全國范圍分層抽樣中小學校際差異① 該表格根據《教育均衡論》(翟博,2008)第221頁表6-14和第226頁表6-18、表6-19三個表格整理而成。本文表格只采用了原有表格中的主要數據項。[6] 單位:元,%
從表7可知,2004年全國范圍內一類小學生均教育經費和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分別是三類小學的2.3倍和2.6倍,絕對差值分別高達1753元和1395元;一類中學生均教育經費和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分別是三類中學的2.6倍和2倍,絕對差值更是分別高達2639元和1396元。這教育經費的差異是相當顯著的。從教師質量來看,一類小學和三類小學專科以上學歷的教師分別占90.0%和78.6%,相差11個百分點;一類中學和三類中學本科以上學歷的教師分別占82.1%和34.0%,竟然相差了48個百分點。這表明中小學尤其是中學教師質量存在著十分驚人而嚴重的校際差異。再者,從生均儀器設備金額來看,一類小學是三類小學的2.6倍,一類中學是三類中學的3.1倍,說明中小學在辦學設施條件方面還存在極其不均等的校際差異。
根據第二種方法,有學者考察了湖北省17個市州內義務教育階段中小學之間的校際差異:
以2005年為例,同一市(州)普通初中校際間的“生均公用經費總支出”差距已達到3.4~37.3倍,其中超過10倍以上的市(州)多達11個;而普通小學校際間的差異更是高達14.3~429.2倍,超過100倍以上的市(州)有6個,超過50倍以上的市(州)有8 個之多[4]。
雖然此處只統計了“生均公用經費”一項指標,但它所反映的同一行政區域內的校際差異是異常突出的。需要強調的是,公共義務教育資源在城市示范學校和農村薄弱學校之間的分配差異尤為明顯。校際間教育資源的巨大差異必然深深地影響著不同學校師生的生存狀態、教學質量和教育成效。
(四)群體差異
由校際差異分析可知,義務教育發展的校際差異總體上是優質學校與薄弱學校之間的差異,本質上則是優質教育資源在不同學校間的分配差異。與此相對應,義務教育發展的群體差異總體上是不同社會群體,尤其表現為優勢群體和弱勢群體之間受教育機會的差異,本質上則是不同社會群體分享優質教育資源的機會差異。
第一,優勢群體更易于占據優質教育資源。
在優質教育資源短缺的情況下,能否獲得良好的受教育機會、分享優質教育資源,往往與適齡兒童少年的家庭背景緊密相關。影響受教育機會的家庭因素主要包括父母職業背景、父母受教育水平和家庭經濟能力三個方面。這三個因素在區分維度上是相互獨立的,但所指涉對象在理論上和現實中都有相互疊加的可能性。一般而言,職業、文化和經濟上的優勢群體更容易占據優質教育資源,這種情形在許多國家的教育實踐中都存在,但在中國則有明顯加劇的趨勢。
有研究顯示,在優質中學里,“干部、知識分子和高收入家庭子女占學生總數的70%以上”。在受高等教育機會(意味著義務教育階段的教育成功機會)的差距方面:從父親職業來考察,“農民子女與工人、干部、企業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子女進入高等學校的可能性之比為1:2.5:17.8:12.8:9.4”;從父親受教育程度來考察,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者,其子女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是小學及其以下者的38.1倍,是初中文化者的26.4倍,是高中(包括中專)文化者的6.3倍。這種受高等教育機會的差距“在相當程度上是基礎教育階段機會不平等累積的結果”[5]29,31,269。
據此可以判斷,在義務教育階段,黨政機關干部、知識分子和高收入家庭子女在獲取優質教育資源和獲得教育成功的機會方面具有明顯的優勢,而農民和農民工、低文化水平和低收入家庭子女則處于顯著的劣勢地位。受教育機會的代際差異十分明顯。
造成這種群體差異的原因是多維的,其中比較突出的有兩個:一是優質教育資源主要分布在優勢群體居住地。城鄉二元結構使得社會階層分化也有城鄉二元性,優勢群體大都居住在城鎮,而農村地區①這里指狹義的農村,把縣鎮歸入到城鎮當中。基本上都是農業人口。與此同時,優質教育資源主要分布在城鎮學校,農村學校則極為稀缺。按照義務教育階段就近入學的原則,大部分農村地區學生,尤其是中西部貧困落后地區的弱勢群體,其分享優質教育的機會相對于城市優勢群體而言是極不均等的。二是優勢群體在獲取優質教育資源上具有更強的競爭力。雖然優質教育資源主要分布在城鎮,但城鎮校際間差異也非常大。同時,隨著人口流動加速,城鎮階層分化加劇,城鎮中弱勢群體的比例也相當可觀。在競爭有限的城鎮優質教育資源(“擇校熱”)過程中,面對著戶籍限制、高額贊助費、人情網絡等障礙,城鎮弱勢群體依然處于劣勢。
第二,擇校競爭加重了各階層尤其是弱勢群體的教育負擔。
優質教育資源幾乎是所有社會群體渴望爭奪的對象,“擇校熱”并沒有明顯的減緩趨勢。擇校競爭不僅發生在優勢群體與弱勢群體之間,還發生在各階層內部;不僅發生在城鎮內部,還發生在農村內部和城鄉之間,家住農村和縣鎮的學生選擇大中城市優質學校就讀的比比皆是。盡管優勢群體在擇校競爭中更有實力,但值得關注的是,真正參與擇校競爭的更多的是弱勢群體。因為無論是城鎮中的流動民工群體還是家住農村的農民群體,在城鎮中參與擇校競爭都受到戶籍制度的強烈約束。相關調查研究證實了這種情況:
對擇校影響最大的因素是戶籍。第一,由于農民子女的戶籍不在城市或縣鎮,到城市和縣鎮讀書就要擇校……第二,從父母職業也顯示出,農業戶口的子女擇校比例較高;第三,從父母的學歷顯示,學生父母學歷為初中者擇校比例較高,也指向農民和打工者;第四,從學生家庭經濟收入看,無論是城市中小學,還是農村中小學,擇校或借讀的學生大多是家庭年收入在3萬元以下的低等收入家庭;第五,重男輕女現象普遍存在,男孩擇校比例高于女孩[7]241-242。
無論對優勢群體還是弱勢群體,擇校競爭都會加重家長的教育負擔,但教育負擔的內容和程度是有所區別的。對優勢群體而言,擇校競爭導致的經濟負擔相對較低,但不能忽視的是,他們承受著較大的心理負擔,這主要來自以考試成績為升學標準的篩選機制。對弱勢群體而言,經濟負擔和心理負擔是雙重的:他們需要花費大部分家庭收入用于擇校競爭和其它教育支出,因而經濟負擔遠遠超過優勢群體;同時,他們不僅有來自于升學的心理負擔,而且還承受著來自其他群體排斥和歧視的心理壓力,尤其是當這種排斥和歧視首先是由子女承受進而傳遞到父母身上時,其心理負擔的程度會成倍地增加。這種情形在流動民工群體當中更為普遍。
第三,流動兒童與留守兒童教育問題亟待解決。
在戶籍等因素限制下,城鎮擇校競爭的主要人群之所以是流動民工子女,還與該群體的龐大規模有關。流動民工子女既包括隨遷的流動兒童,也包括留守兒童。據2008年統計,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中,流動兒童達884.7萬人,50% ~60%集中在東部地區;留守兒童達2140.3萬人,80%以上集中在中西部地區。[8]兩者合計多達3025萬人,占當年義務教育階段總在校生數(15905.7萬)的19%。這里的統計數據尚不包括適齡但未入學以及中途輟學的流動民工子女。
如此龐大的民工子女群體使得流動兒童與留守兒童教育問題特別突出。由于流入地教育資源短缺、戶籍限制、一定的社會排斥與歧視、民工經濟承受能力有限、留守兒童缺乏家庭親子教育等原因,流動民工子女的教育狀況普遍不如一般適齡兒童,在入學率、升學率、留級率、輟學率、識字率等方面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都處于劣勢。
不僅流動民工子女與普通兒童在教育狀況上存在差異,即使在流動兒童與留守兒童之間,在受教育機會和社會化程度上也存在一定的差異。有研究發現:流動兒童在教育社會化、家庭生活社會化、身心健康社會化等方面優于留守兒童,但在人際交往社會化和獨立性程度等方面不如留守兒童。就總體的社會化結果而言,流動兒童優于留守兒童,但選擇流動還是留守受到居住條件、收入水平和閑暇時間等各種客觀條件的約束[9]。
第四,受教育機會的性別差異依然存在,女童處于劣勢。
義務教育階段受教育機會的性別差異表現在如下方面:在擇校競爭中,男童擇校率相對較高;在流動還是留守的兩難選擇中,男童有更多的機會隨父母流動到城鎮入學;在流動民工子女難以承受教育負擔的情況下,首先失學和輟學的情況女童相對較多。因此,雖然義務教育階段全國入學率統計顯示女童入學率與男童相當,但女童受教育機會在實際情形中處于劣勢,女童受教育權需加大保護力度。
三、義務教育發展不均衡的決定因素:新的解釋
一般認為,區域差異和城鄉差異與中國經濟發展的地區差異和城鄉二元分化的社會結構緊密相關,而群體差異則在任何社會都普遍存在,它多少與階層差異具有高度相關性,因而縮小義務教育發展不均衡性的出路也相應地在于:縮小社會經濟發展的區域差異,打破城鄉二元結構,以及縮小階層差距。
筆者承認這3個因素對中國義務教育發展不均衡性的影響,而且也相信在這3個方面的改進有助于縮小不均衡性。然而,這種解釋尚未觸及根本,因為它難以解釋為何有些經濟發達地區的義務教育也存在發展不均衡問題,而有些經濟相對不那么發達的地區,其義務教育發展反而較為均衡(如安徽省銅陵市)①2009年11月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作出了《關于表彰全國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工作先進地區的決定》,表彰了全國92個縣市區,安徽省銅陵市名列其中。。
實際上,無論是區域差異、城鄉差異,還是群體差異,歸根結底都體現為校際差異。上文對各種差異的實證分析也表明,校際差異往往比其它各類差異更為突出、更為尖銳。若能實質性地解決校際不均衡問題,其它三種不均衡也將迎刃而解。當然,校際不均衡問題的解決應當循序漸進,當前的首要任務是實現縣域內的校際(優質)均衡,接著是省域內校際均衡,隨后才是省際間的校際均衡。把握住校際不均衡這個關鍵問題,也為應對義務教育發展的不均衡性找到了突破口。
義務教育發展的校際不均衡主要表現在兩個相互關聯的方面:一是校際間的資源配置不均衡,二是“非優質學校”普遍存在。非優質學校包括普通學校和薄弱學校,其中薄弱學校既可能是資源不足導致的資源薄弱學校,也可能是管理不善導致的治學薄弱學校。一般來講,資源充足學校未必是治學優良學校,但資源薄弱學校通常也是治學薄弱學校。
如果把義務教育的整個供給過程區分為提供環節、生產環節以及提供與生產的連結環節,那么校際間資源配置問題屬于提供層面的問題,而學校治理問題則更多地屬于生產層面的問題,連結提供與生產的則是政府管理問題。
(1)在提供層面,決定校際間資源配置是否均衡的關鍵因素有兩個:一是教育提供主體(舉辦者)的教育期望(提供意愿);二是提供主體的提供能力。如果提供主體的教育期望不高,缺乏提供意愿,或者教育期望有不合理的偏向,或者即使有良善的提供意愿,但提供能力不足,那就會有選擇地把資源投入個別學校,從而導致校際間資源配置不均衡。
(2)在生產層面,決定一個學校能否成為優質學校的關鍵因素要區分兩種不同的情形,一種情形是資源充足,另一種情形是資源不足。在資源充足的情形下,能否成為優質學校取決于學校的治理狀況,或者說它的生產效力,它至少取決于3個關鍵因素:一是學校與政府的關系,即學校自主性程度;二是學校內部關系,即學校組織形式;三是學校與家長、社區的關系,可稱為學校的社區環境。這3個因素的任何一個出現問題,都會導致治學薄弱學校的出現。在資源不足的情形下,缺乏資源支持的學校治理通常很難成為優質學校,這很大程度上是由提供層面的問題所引發的,而決定生產效力的3個因素的好壞,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改善或加劇學校治理層面的薄弱程度。
(3)在政府管理層面,政府資源配置能力的強弱、學校生產效力的好壞,都與政府的管理能力息息相關。政府管理能力是連結提供過程和生產過程的中樞。在與提供過程的連結上,政府既是提供主體,也是管理主體。盡管政府管理能力的核心是資源配置能力,但它包含更廣泛的內容,如教育規劃、政策制定、力量整合等等。在與生產過程的連結上,政府的管理能力體現在對資源利用的監督、學校運行的管理、教育績效的評估等方面,這涉及政府與學校的關系。
概括地講,包括義務教育提供、生產與管理在內的整個供給過程,構成了義務教育供給模式。義務教育供給模式的不同選擇,將決定提供主體②提供主體不局限于政府,也包括非政府提供主體。是否具有良善的提供意愿和充足的提供能力,決定學校是否具有高效的生產效力(教育績效),并且決定政府是否具有良好的管理協調能力。因此,義務教育供給模式的不同選擇從根本上決定了義務教育發展的校際均衡程度,進而決定了整個義務教育發展的均衡程度。
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我國義務教育在供給實踐中秉持精英主義路線,采取的是重點導向型供給模式,而且傾向于政府單一供給和全面控制型管理。
在這種供給模式下,地方政府的提供意愿具有明確的偏向性和選擇性,而且不乏塑造教育政績的沖動,因此,縣域內教育資源大都被集中投入到政府著力打造的幾所“重點”學校(“中心”學校或“示范”學校)上,造成強校愈強、弱校愈弱的校際不均衡格局。
地方政府普遍存在的提供能力不足問題進一步加劇了義務教育發展的不均衡性。受經濟發展水平和資源稟賦所限,許多地方政府公共財政不足,公共教育資源匱乏,尤其是優質教育資源極度短缺。在教育政績的驅動下,地方政府同樣會把有限的教育資源投入到少數幾所學校,其它大部分學校尤其是傳統薄弱學校和農村學校往往難以獲得應有的教育資源。再加上過度依賴政府單一供給模式,社會和市場教育資源鮮有得到合理開發和有效應用,提供能力不足至今依然是大多數地方政府(尤其是中西部縣市政府)面臨的共同問題,這導致一個結果是教育亂收費。
學校治理不善也是義務教育發展不均衡的另一個重要成因,其結果是大規模的“非優質學校”。學校治理不善是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提供層面資源不足是大部分“非優質學校”的共同成因,上文提到的決定學校生產效力的3個因素——學校自主性、學校組織形式、學校的社區環境——也至關重要。就學校自主性而言,目前地方政府對義務教育學校大都采取全面控制型管理模式,學校缺乏自主性,難以按照學校領導者的教育理念和特色追求辦學,這導致“千校一面”與“校際不均衡”共存。在政府控制之下,學校組織形式也缺乏民主性、開放性和激勵性,教師參與度低,積極性和創造性被遏制。另外,政府在社區環境治理方面的乏力和滯后也影響著學校治理績效。
在連結提供與生產的環節上,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協調機制,不少地方政府無論在資源配置能力還是在學校管理能力方面都顯得比較乏力。一方面,資源配置效率低與提供能力不足的相互疊加擴大了資源配置的不均衡性;另一方面,政府直接控制學校與學校自身治理不良的相互疊加則惡化了學校治理績效。
由此可見,徹底扭轉精英主義教育戰略,變革政府威權控制下的重點導向型供給模式和單一供給取向,是應對義務教育發展不均衡問題,實現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的根本出路。
四、結論與討論
根據以上實證分析和理論解釋,我們得出如下結論:
(1)中國義務教育發展的不均衡性主要體現在區域差異、城鄉差異、校際差異和群體差異等方面。總體上講,四個方面的差異情況要么呈現出擴大趨勢,要么穩定在高位水平,這意味著中國義務教育發展呈現出相當嚴峻的不均衡性;除個別指標項外,暫時缺乏足夠有力的證據表明這種不均衡性得到了顯著緩解。
(2)在區域差異方面,省際間國家教育投入①指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國家財政預算內教育經費,這是針對整個教育體系而言的。的絕對差異在擴大,而相對差異有所減小,但相對差距值仍處于高位水平;省際間義務教育生均教育投入的絕對差異和相對差異都在高位水平上持續、快速擴大,這表明省際間資源分享機會差距顯著;另外,省域內縣市間區域差異有超過省際間區域差異的跡象。
(3)在城鄉差異方面,義務教育生均教育經費的城鄉差異雖有波動,但總體上呈現出縮小趨勢,這是國家實行城鄉統籌的免費義務教育和加大農村地區教育投入的結果;不過,生均教育經費的城鄉差異一直存在,且絕對差值依然相當大;城鄉之間的教師合格率差異微弱,但教師質量卻一直維持著巨大差距,教師質量的城鄉差距并沒有明顯的縮小趨勢。
(4)在校際差異方面,無論是全國層面還是縣市層面,校際差異都相當顯著,縣市范圍內生均公用經費的校際差異甚至達到上百倍。公共教育資源在城市示范學校和農村薄弱學校之間的分配差異尤為顯著,校際差異與城鄉差異的疊加加劇了義務教育發展的不均衡性。校際間教育資源的巨大差異直接影響著不同學校師生的生存狀態、教學質量和教育成效。
(5)在群體差異方面,優勢群體與弱勢群體在入學機會、資源分享機會和成功機會方面都存在顯著差異,受教育機會的代際差異十分明顯。在優質教育資源短缺的情況下,優勢群體更易于占據優質教育資源;為爭奪優質教育資源,真正參與擇校競爭的更多的是弱勢群體,而擇校競爭加重了各階層尤其是弱勢群體的教育負擔。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規模龐大,其教育狀況普遍不如一般適齡兒童。受教育機會的性別差異依然存在,女童處于劣勢。
(6)無論是區域差異、城鄉差異,還是群體差異,歸根結底都體現為校際差異,校際發展的不均衡程度遠甚于其它方面。實質性地縮小校際差異是應對義務教育發展不均衡問題的突破口。盡管社會經濟發展的區域差異、城鄉二元結構和社會階層差距都是義務教育發展不均衡的影響因素,但并非決定性和根本性因素。我國義務教育發展不均衡的根源在于供給模式的不合理性,即在傳統精英主義路線下,以政府單一供給和全面控制型管理為特征的重點導向型供給模式,這種供給模式從根本上導致了巨大的校際差距和整個義務教育發展的不均衡性。
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之本,是實現社會公平最偉大的工具[10]。然而,義務教育發展的不均衡性導致了兒童入學機會、資源分享機會和教育成功機會的不公平性,教育的不公平性則再生產了社會的不公平性。切實縮小義務教育發展的區域差異、城鄉差異、校際差距和群體差異,實現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通過促進教育公平增進社會公平,是當前我國義務教育發展的緊迫任務。
為此,在義務教育治理中,我們首先要在教育理念上從精英主義轉向“全納主義”,要致力于確保每一位兒童的平等教育權利和均等教育機會,促進每一位兒童全面發展,不讓任何一個孩子掉隊。其次,我們要從重點導向戰略轉向優質均衡發展戰略,一方面要確保教育資源的均衡配置,另一方面則要改善所有學校的治理,尤其是改善農村學校和薄弱學校的治理績效。在優質均衡發展戰略目標下,至關重要的幾個方面是:明確義務教育學校建設基準,推進義務教育標準化建設;結合各地經濟社會生態確立義務教育生均經費標準,確保經費落實到位;建立義務教育中小學預算制度,將資源配置納入法制化、規范化渠道;鼓勵學校自主、多元、優質發展。再者,為有效推進均衡發展戰略,我們需要變革義務教育供給模式,從政府單一供給轉向政府主導型復合供給。所謂“政府主導”,是指政府是義務教育供給的核心主體、唯一的權力中心和最終責任主體,政府機制是各種組合模式的中心機制;所謂“復合供給”,是指通過政府機制與非政府機制的有效組合實現互補與合作,進而激發提供主體良善的提供意愿,擴充提供主體的提供能力,改善政府的管理協調能力和學校的教育績效,最終促進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最后,在把握供給模式變革這一根本出路的同時,我們也需要重視相關外部因素的改善,如縮小社會經濟發展的區域差異,打破城鄉二元結構,以及縮小階層差距等等。
[1]張 力.關于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J].科學決策,1999(3):19-21.
[2]岳昌君,丁小浩,等.中國教育發展現狀[R]∥閔維方,王 蓉.中國教育與人力資源發展報告:2005-200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18-20.
[3]教育部財務司,國家統計局社會和科技統計司.中國教育經費統計年鑒 2008[Z].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9.
[4]葉 平,張傳萍.對教育公平與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思考[J].政策,2007(4):40-42.
[5]轉型期中國重大教育政策案例研究課題組.縮小差距:中國教育政策的重大命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6]教育部發展規劃司.中國教育統計年鑒:2000-2008[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2009.
[7]翟 博.教育均衡論:中國基礎教育均衡發展實證分析[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
[8]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編著.2009年中國教育綠皮書:中國教育政策分析年度報告[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9:10.
[9]劉成斌,吳新慧.留守與流動——農民工子女的教育選擇[M].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8.
[10]薛建強.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之本[J].科學決策,2005(12):21-23.
The Im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mpulsory Education and Its Determining Factor: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Data 2000-2008
LV Pu-sheng
(Wuhan University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Wuhan 430072,China)
The im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mpulsory education is mainly embodied in regional differences,urban-rural differences,interscholastic differences and group differences,etc.Relevant data among 2000-2008 shows that in general those four differences either present a expand trend,or stable at a high level;the differences not be reduced observably till now.The interscholastic differences outdistance others.The root of the imbalanced development is that the supply model of Chinese compulsory is unreasonable.The supply model of Chinese compulsory is key school-oriented which guided by traditional elitism and depends on government singly supply.
Chinese compulsory education;imbalanced development;regional differences;urban-rural differences;interscholastic differences;group differences
P76
A
1002-9753(2013)09-0082-15
2012-09-14
2013-04-23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04&ZD015)
呂普生(1982-),男,湖南宜章人,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講師,博士后。研究方向:教育政治學。
(本文責編:海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