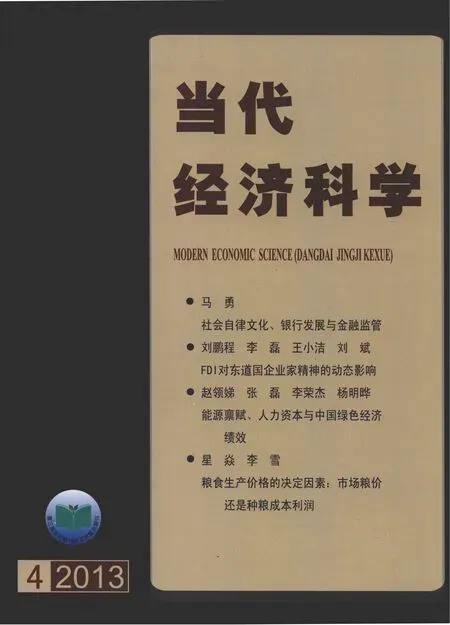貿易開放、產出增長與收入結構優化——來自國家級高新區的經驗證據
楊 暢,白雪潔
(1.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天津 300071;2.南開大學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天津 300071)
貿易開放、產出增長與收入結構優化
——來自國家級高新區的經驗證據
楊 暢1,白雪潔2
(1.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天津 300071;2.南開大學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天津 300071)
本文重點考察了貿易開放對我國國家級高新區產出增長與收入結構的影響,運用2007-2010年我國54個國家級高新區的面板數據,采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表明:與FDI的作用不同,在控制了其他影響因素后,貿易開放加劇了市場競爭,不利于高新區的產出增長;技術收入隨著貿易開放度的提高而下降,高新區收入結構差距被拉大,穩健性檢驗結果表明該結論是可靠的。通過進一步的理論闡述,本文認為貿易的競爭擠占效應對高新區技術收入的影響較為顯著,而在開放環境下高新區的收益轉化作用并不明顯,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并不利于高新區的發展與轉型。這一結論對進一步明確我國高新區功能定位,培育企業在國際競爭下的的生存與適應能力具有尤為重要的政策含義。
貿易開放;國家級高新區;產出;收入結構;發展轉型
一、問題的提出
科技對于國家或地區發展具有長期的推動作用,為了促進高新技術企業的發展,自從上世紀50年代美國高科技園區崛起以來,加拿大、英國、法國、日本、韓國、以色列、巴西等很多國家和地區紛紛建立起符合當地特點的高科技園區(Science Park)。產業集群理論成為了指導高新區實踐發展的主要理論基礎,政府通過政策優惠、人才引進和技術吸收等方式促進高新區集群效應的發揮。根據國情和區域發展特點,我國自1988年批準了第一個國家級科學工業園區(北京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以來,截至2011年底,我國的國家級高新技術開發區的數量已達到88個,對促進我國技術成果的轉化和產學研互動,發揮高技術企業對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周元、王維才[1]認為高新區的發展經歷“要素群集”、“產業主導”、“創新突破”和“財富凝聚”四個階段,并認為我國高新區大部分都已由“要素群集”階段轉換至“產業主導”階段,基本完成了“一次創業”。進入新世紀以來,為了使高新區的產業發展跨上新臺階,2001年9月科技部提出國家級高新區“二次創業”的構想,基本內涵為依托一次創業所積累的條件,使高新區從粗放的外延式發展向以自主創新為主的內涵式發展轉變,注重優化配置科技資源和提供優質服務的軟環境,拓展國際市場,發展特色和主導產業,建立新體制和新機制等“五個轉變”[2]。也就是說,使高新區由“重量”向“重質”的發展方式轉型。
2001年11月,正值高新區“二次創業”的背景下,我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貿易范圍更為廣泛,結構更為復雜,其影響逐漸滲透于國內各個經濟主體間。高新區作為我國經濟與科技發展的一個重要載體也受到觸及:城市貿易開放水平會直接影響到當地高新區的出口創匯、技術外溢與吸收、市場結構以及高技術產品競爭程度等,因此,考察城市貿易水平與高新區內生因素的交互作用是進一步研究高新區技術吸收水平、研發創新能力、國際市場競爭力等轉型發展問題的基礎和前提,這也是分析開放條件下高新區“二次創業”路徑的重要內容。
我們認為,分析貿易開放對高新區的影響首先應從創新能力入手,而現有的文獻在研究國際貿易與創新的關系時大多是從技術溢出和擴散的角度切入:學者們通常認為,技術擴散途徑主要由進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資構成。20世紀增長理論的發展使得大量的經濟學者對衡量技術進步的重要指標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測算和影響因素的研究有了濃厚的興趣,較早具有開拓性的實證研究方法有CH模型[3]和對其改進的LP法[4],國內學者在研究國際貿易技術外溢方面也常常使用此類方法進行測度,李小平和朱鐘棣[5]選取1998-2003年的工業行業數據,總結6種R&D存量計算方法,對貿易、研發溢出和生產率增長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國際貿易渠道的R&D溢出促進了我國工業的技術進步率、技術效率和TFP增長的結論。毛其淋和盛斌[6]考察了對外經濟開放、區域市場整合與中國省際全要素生產率的關系。葛小寒和陳凌[7]從國際技術外溢吸收的角度考察了我國不同類型吸收變量的能力,得到國內研發強度、人力資本和制度變量都對技術溢出利用和吸收起到了關鍵作用,技術差距變量的影響雖不顯著但結果為正。另外,李平,崔喜君和劉建[8]根據不同專利的創新程度研究了國內資本存量、FDI、進口貿易和國外專利申請四大變量對自主創新的影響,得到進口溢出的國外研發對我國自主創新的總體產出彈性顯著為負,但這種影響隨著自主創新層次的提高而逐漸降低。
很多學者也對不同國家和地區的高新區的發展和企業創新效率進行了研究,比如Zhang&Sonobe[9]通過考察高新區內外部的高技術企業的相關數據,研究我國高新區的有效性,并著重分析其聚集和擁擠效應,得到高新區內部的高技術企業對于生產率的擁擠負效應大于其聚集正效應的觀點。Squicciarini[10]認為科學園扮演了創新苗床的角色,并以1970—2002年芬蘭科學園相關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另外,Link&scott11則對高新區的增長進行了分析。
由上述可知,現有的文獻很多是從技術創新與企業生產效率的角度分析高新區的發展問題,研究國際貿易的技術溢出也大多是從全要素生產率和吸收能力的角度進行考察。而就高新區的特殊性而言,單從國際貿易的技術溢出角度考察其對高新區的影響并不全面,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也很難充分解釋貿易開放對研發投入、人力資本和優惠政策更加密集的高新區的影響。 將貿易開放納入到高新區發展的分析框架后,其與高新區的內生增長變量會產生交互影響,那么城市貿易開放度的變化會怎樣影響處在轉型期的我國高新區的產出與收入結構?此時高新區內生因素對其自身的發展又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其背后的機制又是如何?目前從國內外的對高新區的研究來看,鮮有文獻專門就這些問題進行研究,這正是本文的研究價值所在。本文把高新區內生特征、城市環境與高新區的產出和收入結構共同納入到分析框架中,實證考察城市貿易開放度對高新區發展的影響,在此基礎上對高新區產出與收入的影響因素以及貿易結構也做了相應的分析。
二、研究設計和數據說明
(一)模型
本文研究的重點是考察貿易開放對我國高新區產出增長與收入結構的影響,因此在上文分析的基礎上建立計量模型如下:

其中,下標i表示各高新區,t表示年份,I是本文主要的考察對象,包括高新區的產出與收入;open表示貿易開放度指標;G表示高新區特征變量,主要包括高新區人力資本、科技投入強度、資產充裕度和規模等可能影響高新區產出與收入的內部因素;city表示城市控制變量,主要包括城市人均GDP、人力資本稟賦、FDI和財政支出水平等可能影響高新區產出與收入的其他地區因素;u表示隨機誤差項。
(二)主要指標的解釋和度量
(1)被解釋變量的度量。對高新區而言,獲得更高的產出和收入是尋求發展的根本動力,要想弄清開放條件下高新區的發展變化,就要同時考慮其所處的貿易開放環境與內生因素對高新區產出和收入的綜合影響。因此,鑒于數據所限,本文選取高新區的產出,即年末工業增加值來衡量城市貿易開放度對高新區總體發展的影響。另外,高新區收入主要包括技術收入、產品銷售收入和商品銷售收入三種,三類收入所代表的技術含量和創新能力是不同的①技術收入的技術含量最高,其收入可以代表企業技術發展水平;商品銷售收入技術含量最低,其基本不含有企業技術創新或技術加工。,為了評價高新區內涵式的收入增長,我們將三類收入分別除以高新區年末從業人員數得到人均科技收入、人均產品銷售收入和人均商品銷售收入作為考察高新區收入結構影響的衡量指標。
(2)貿易開放度指標與城市控制變量。學者們通常用國際貿易額同GDP比率來衡量貿易開放度[12-13],因此,我們采用各城市對外貿易總量/各城市GDP總量來衡量城市貿易開放度;另外在考察高新區內部出口強度時,我們采用高新區出口創匯額與當年工業總產值的比值表示高新區出口強度,以上進出口額均用當年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折合成人民幣。我們認為,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影響著高新區產品需求、勞動力資源和原材料供給等各方面因素,是高新區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土壤;城市的人力資本稟賦可以代表高新區所處的科技人文環境,對其產出和科技創新具有一定的作用;而外商直接投資可能會通過類似的機制影響高新區的發展水平,如果不控制FDI可能會高估貿易開放對高新區發展的影響;財政支出水平反映了政府對當地經濟的干預力度,可以近似反映出地方的市場化進展程度[14]。其中,我們選取城市人均GDP作為衡量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采用普通高等學校在校學生數占城市人口比重表示;外資進入程度采用高新區所在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資額占GDP的比重來衡量;城市財政支出水平用當年各地地方財政一般預算內支出與當地GDP比值表示。
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實施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精品工程,建設一批設施完備、功能多樣的休閑觀光園區、森林人家、康養基地、鄉村民宿、特色小鎮”。通過互聯網平臺,提升鄉村形象,發展鄉村共享經濟、創意農業、特色文化產業。“互聯網+休閑農業”模式全面整合移動智能終端、云服務平臺和大數據分析技術,使休閑農產品、服務項目和品牌等信息通過微博等多種互聯網營銷方式進入公眾視野。提供以農民和從業者為主導的APP營銷和休閑農業網站平臺等,為消費者提供全面、準確、便捷、時尚的休閑農業信息和服務。
(3)高新區控制變量。本文加入上述高新區特征變量的原因在于:通常,人力資本作為重要的技術吸收和創新變量影響著高新區的發展;科技投入強度越高其技術進步越快;高新區資產越充裕增長越迅速;高新區的發展規模也會通過基礎設施建設、配套服務等條件影響其科技研發決策和轉型發展速度。其中,選取各高新區大專以上人員與從業人員的比值表示高新區人力資本水平;高新區資產充裕度取高新區年末資產與從業人員的比值來表示;科技投入強度采用高新區科技活動經費支出與科技活動人員比值表示,因為科技活經費支出反映了高新區開展科學研究與試驗發展應用以及教育與培訓等全部科技活動的支出情況,科技活動人員的人均科技活動經費支出可以直接作為衡量高新區科技投入強度的指標;另外我們選取高新區年末從業人員數的對數值作為高新區規模的衡量指標。
(三)估計中的問題及處理
內生性會導致最小二乘估計有偏且不一致,由于本模型存在變量遺漏或雙向因果帶來解釋變量內生的可能性,比如,在這里城市貿易進出口額與高新區某些發展的評價指標可能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即高新區產出或收入的增加也可能會提高當地貿易額。因此,為了盡量降低由此帶來的估計偏誤,我們使用工具變量克服內生性問題。參考之前學者們的做法,本文采用各高新區所在城市到海岸線的最短距離倒數(乘以100)作為貿易開放度的工具變量[15]。另外,本文還選取2000年的貿易開放度作為另一個工具變量以增加估計的有效性[16]。
另外,盡管加入了地區控制變量,但為了減少高新區政策和經濟環境隨時間的變化和未觀測到的動態差異對估計結果的影響,我們選取面板數據的時間固定效應。由于可能存在無法識別的異方差,本文所報告的估計系數均經過了懷特(White)異方差修正;為了使數據更加平穩以及避免各變量不同單位對回歸結果的影響,我們對各變量均取對數處理。
(四)數據來源與說明
由于統計數據的限制,本文選取2007-2010年54家國家級高新區的相關數據作為分析樣本②火炬年鑒中54家高新區所處地區名稱為:北京、天津、石家莊、保定、太原、包頭、沈陽、大連、鞍山、長春、吉林、哈爾濱、大慶、上海、南京、常州、無錫、蘇州、杭州、寧波、合肥、福州、廈門、南昌、濟南、青島、淄博、濰坊、威海、鄭州、洛陽、武漢、襄樊、長沙、株洲、廣州、深圳、珠海、惠州、中山、佛山、南寧、桂林、海南、成都、重慶、綿陽、貴陽、昆明、西安、寶雞、楊凌、蘭州、烏魯木齊。其中海南高新區城市控制變量采用海口市數據,2008-2010年吉林高新區商品銷售收入以及惠州高新區2007年技術收入和2008年商品銷售收入數據缺失,其他缺失數據均來自楊凌示范區。,所在地包括4個直轄市、5個計劃單列市、23個省會城市和其他的21個地級市(含珠海)以及楊凌示范區。本文所涉及的高新區被解釋變量(工業增加值、技術收入、產品銷售收入、商品銷售收入)以及高新區其他相關變量均取自2008-2011年的《中國火炬統計年鑒》。城市貿易數據取自于各城市當年的統計公報;距海岸線最短距離是通過電子地圖測算得到的;城市控制變量均取自《新中國60年統計資料匯編》和相應年份的《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以及各地統計公報。表1報告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量,通過檢驗方差膨脹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發現其取值均在可接受范圍內①根據經驗法則,如果最大的方差膨脹因子vif≤10或1/vif≥0.1,則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因此我們不考慮多重共線性問題。

表1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量
三、計量結果及分析
在計量模型建立的基礎上,本節對貿易開放與高新區產出和收入結構的關系進行實證檢驗,首先考察其對高新區產出的作用,并逐步加入城市控制變量,以檢驗其穩健性;然后考察其對不同類型收入的影響,并對影響高新區產出與收入的因素進行了分析。
(一)貿易開放度與高新區產出
貿易開放對高新區的影響并不像一些學者認為的僅存在貿易技術溢出的促進作用,以高新區產出作為考察對象,分析貿易開放對高新區的影響,結果如表2所示,方程(1)報告了高新區產出的基本影響因素,研究結果大部分與以往文獻研究類似,高新區人力資本、科技投入強度和規模以及城市經濟發展水平成為影響高新區產出的四大主要因素,而資產充裕度對于高新區的產出作用并不顯著,值得注意的是,此時城市貿易開放度對于高新區產出具有顯著的負效應。為了控制城市其他影響因素可能導致的誤差,我們通過逐步加入變量的方法來考察其系數與顯著性的變化,在加入城市人力資本稟賦變量后,如方程(2)所示,貿易開放系數仍顯著為負,而城市人力資本稟賦系數也為負,從側面說明高新區產出中高技術產品比例較低,并未很好的依托城市人力資本環境,城市與高新區之間尚未形成融洽的產學研對接機制,一些人才被吸引到高校、研究所等其他部門。為了進一步控制外商直接投資對高新區的影響,我們發現在方程(3)加入城市FDI變量后,貿易開放的負系數顯著性反而增強,這說明貿易開放對于高新區確有一定的影響作用,而外資的進入促進了高新區產出的增加,二者作用力相反。通過方程(4)我們發現,在控制了政府財政支出因素后,貿易開放系數仍為負。為了克服內生性,我們使用上文分析得到的兩個工具變量進行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計,方程(5)報告了兩階段最小二乘法估計的結果,相對于方程(4),貿易開放系數仍顯著為負,且絕對值提高將近5個百分點,這表明如果不考慮內生性的話,會較大程度低估貿易開放對高新區產出的影響,而我們發現政府財政支出對高新區產出的影響并不顯著。另外,為了降低國家傳統的地區政策(城市行政級別)對估計結果可能產生的影響,我們對高新區所在城市按照行政級別予以賦權[17],作為政策虛擬變量對結果進行控制②參考姜彩樓和徐康寧[17]的方法,本文將直轄市和經濟特區權重設為3,副省級市和計劃單列市設為2,一般地級市和其他城市設為1。。從方程(6)中看到,貿易開放系數仍顯著為負,而城市的行政級別對高新區也具有顯著的負作用,也就是說,國家政策的優勢反而降低了高新區的產出,這說明地方行政級別所帶來的傳統政策優勢并沒有惠及高新區,而地區競爭環境的加劇卻對高新區產出構成了一定的擠占。最后,為了保證工具變量是有效的,我們采用多種統計指標進行考察:Kleibergen-Paap rk LM統計量用來檢驗未被包含的工具變量是否與內生變量相關,結論在1%的水平上拒絕了原假設,說明不存在工具變量識別不足的情況;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的統計量大于Stock-Yogo檢驗10%水平上的臨界值19.93,因此拒絕工具變量弱識別假設;Hansen J檢驗的相伴隨概率為0.4125和0.7991,接受原假設,所使用工具變量的外生性得以檢驗,因此所選取的兩個工具變量具有合理性,我們得到貿易開放對高新區總體產出影響為負的結論是可靠的。
(二)貿易開放與高新區收入結構
雖然貿易開放度對于高新區產出總體估計結果為負,但由于貿易對經濟主體可能存在的雙重影響作用,我們并不能一概而論,本節將考察貿易開放對高新區收入結構的影響。我們按照火炬統計年鑒的收入分類對高新區收入進行逐項分析,通過高新區企業不同技術含量收入(技術收入①火炬年鑒對技術收入解釋為:指企業全年用于技術轉讓、技術承包、技術咨詢與服務、技術入股、中試產品收人以及接受外單位委托的科研收人等。、產品收入②火炬年鑒對產品銷售收入解釋為:指企業全年銷售全部產成品、自制半成品和提供勞務等所取得的收人。和商品收入③火炬年鑒對商品銷售收入解釋為:指企業銷售以出售為目的而購入的非本企業生產產品的銷售收人。)的估計來分析貿易開放度對高新區收入結構的影響。
表3報告了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的估計結果,從前三列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到,在控制了高新區其他影響因素后,貿易開放對于技術收入同樣具有負影響,并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而其對于產品收入的影響并不顯著;從第三列可以看到貿易開放度的提升對于企業技術投入量最低的商品收入來說得到了一定的提高 ;方程(4)、(5)和(6)中加入了城市控制變量和政策虛擬變量后,商品收入的貿易開放系數變得不再顯著,但對于技術收入的影響仍顯著為負,其系數進一步擴大,工具變量也檢驗合格,說明貿易開放確實會拉大高新區收入結構差距,降低了技術收入,該結論是穩健可靠的。這就表明城市貿易開放度的提升對于技術投入含量較低的產品收入以及幾乎不含有技術投入的商品收入影響并不明顯,而技術收入對貿易的敏感度較強,那么,為
什么貿易開放對高新區不同的收入類型有著不一樣的影響呢?關于該問題本文將在第四章對其嘗試性地進行理論闡述與分析。在此之前,我們先對影響高新區收入結構的其他相關因素進行簡要的分析。
(三)貿易開放條件下高新區收入結構的影響因素分析
現在我們知道,一個城市的貿易開放度會拉大高新區的收入結構,而且技術收入的下降從某種意義上有悖于高新區發展轉型,特別是“二次創業”的基本初衷與要求。下面,我們可以通過其他解釋變量對高新區三類收入的影響來分析開放條件下決定高新區發展的幾類因素。在此,我們僅對加入城市變量后的模型進行考察,如表3中的方程(4)-(6)所示,高新區人力資本對于技術含量較低的產品和商品收入來說并不顯著,這是因為高新區人力資本主要用于研發和產品技術的咨詢和服務上,而人力資本對于技術收入的顯著促進作用證實了其對高新區發展與轉型的重要性。
我們注意到,高新區科技投入對技術收入的促進作用并不顯著,這與謝建國、周露昭[18],張海洋[19]以及李小平、朱鐘棣[5]對于技術效率和技術進步的分析結論類似,李小平、朱鐘棣[5]認為本行業R&D資本阻礙了本行業的技術進步增長的原因可能與行業本身使用的R&D資本的投入結構不恰當、使用效率不高等因素有關;另外,這還與制度以及研發成果沒有進入生產領域轉化成現實生產力有關[18],這些可能也是科技投入對高新區技術收入作用不明顯的原因。而其對于產品收入顯著的促進作用也說明高新區科技投入大部分用來加工、自制半成品或提供勞務上,很少用于高科技產品的研發和生產領域,這也是有悖于高新區轉型發展要求的一個表現。同樣的情況發生在資產變量上,高新區資產主要對技術含量不高的產品收入和沒有技術投入的商品收入顯著,這從側面說明高新區資產主要投入在回報周期短、利潤率較高的半成品銷售、勞務和商品買賣的商業活動上,而真正投入在科技研發領域的資金較少,甚至擠占了部分科技研發投入。對于技術收入有促進作用的是高新區規模,在高新區形成了一定規模后,軟硬環境均有了一定的積累,企業不再追求短期利益,而更注重長遠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此時技術創新與研發顯得格外重要,這正體現了我國高新區“二次創業”的意義,高新區規模越大其在技術領域的投入可能越大,相應的收益也就越多,而其他方面的投入則相對下降。

表2 貿易開放度與高新區產出
城市經濟發展水平(人均GDP)對于技術收入的影響顯著為正,越發達的城市其人力資本質量越高,科技環境越優越,基礎設施越完善,城市發展程度和經濟規模直接構成了對于高新區企業半成品和勞務的需求,因此城市人均GDP對產品收入的影響也很顯著,而發達的城市最終商品來源較廣,替代品較豐富,激烈的競爭導致城市發展水平對于商品收入的影響并不顯著。因此,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對高新區的轉型發展會起到促進作用。另外,外商直接投資對商品收入的競爭擠占比較顯著,對于較低技術含量的產品收入具有一定的溢出效應,但核心技術卻沒有溢出和擴散,因此對于技術收入的促進作用并不顯著。城市較高的行政級別雖然對產出有抑制作用,但其對于資金、人力的吸引以及聚集和技術擴散作用推動了高新區技術交易與轉化,這種對技術收入的顯著促進作用說明行政級別高的城市有利于高新區向創新發展方向轉型。下文將對貿易開放與高新區產出以及收入結構的作用關系進行探討。

表3 貿易開放與高新區收入結構
四、進一步理論闡釋
由前文的實證研究發現城市貿易開放度對高新區的產出具有負效應,且拉大了收入結構差距。由于數據所限,我們無法對貿易開放與高新區發展的潛在作用機制進行更為微觀的定量分析。但相對于貿易的技術擴散和溢出的正向作用,國內一些學者在研究貿易與創新的關系時也提出了質疑,本節試圖通過對以往文獻的梳理,結合本文的實證研究,對估計結果進行理論上的解釋。
關于進出口對企業技術創新的負面影響,謝建國、周露昭[18]認為進口產品也可能侵蝕國內企業的市場份額,降低企業創新的預期收益,從而抑制了企業創新的動力,不利于進口國技術的提升。王慶石[18]等認為出口貿易的技術外溢效應在經濟發展水平、開放程度、基礎設施和地區經濟結構等方面都存在門限特征。對于科技和研發功能更為顯著的高新區來講,結論更值得探討:因為簡單的貿易加工仍是我國貿易的主要模式,其對當地技術進步的影響可能并不顯著,甚至擠占了部分研發型產品的生產研發資源和國外市場份額;謝子遠、梁丹陽[21]通過研究高新區研發投入發現出口規模與高新區研發投入強度有反向關系,并認為這是由于高新區出口產品技術含量不高以及以加工貿易為主的出口方式造成的。
從高新區企業收益方面考慮,貿易會使高新區市場競爭加劇,收入下降;另外,技術溢出對于初級產品和非高新技術工業品來說吸收較快,可以迅速被模仿和轉化,而對于高新技術產品則不易快速利用吸收并大規模投入生產,因為高技術企業具有的資本、設備、技術人員和管理模式不可能迅速通過簡單的模仿而改變。且高技術產品或專利一般會受到國外企業較強的技術保護[8];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西方國家對技術出口的控制日趨苛刻,真正的核心技術很難從正常貿易中得到[22]。而在我國勞動力成本上升的背景下,粗放型的增長方式的矛盾凸現,高新區在貿易開放下的競爭優勢并不明顯,配套的科技服務業發展亦不完善,國際競爭的加劇會抑制高新區企業研發和生產的積極性。因此,在考慮了其他要素和變量后,我們有理由相信城市貿易開放對高新區技術和加工品的生產可能會出現負面影響。
下面我們對前文的實證分析進行擴展,貿易開放對高新區企業收入的影響有利又有弊,那么究竟利大還是弊大要看高新區的主要產品結構、性質和規模等多方面特征。綜合考慮以上文獻,在不考慮高新區企業直接貿易獲利的情況下,可以簡單的將貿易下的高新區企業損益效應影響變量總結為一個函數:

其中,πi代表第i個高新區企業的貿易收益;Gi(·)代表高新區企業通過貿易帶來的技術外溢函數,貿易規模或開放度s和貿易產品的技術結構t直接影響了國際貿易的技術擴散;Bi(·)表示企業因貿易所帶來的市場份額丟失或資源擠占函數,其主要取決于貿易規模s和貿易產品相對價格p等因素的影響;ηi代表第i個企業技術進步的收益轉換因子.ηi>0,它受到人力資本等吸收與創新變量h,企業獲得的收入中技術投入量的占比θ,企業規模f以及貿易競爭下企業激勵性創新度q①本文的貿易競爭下企業激勵性創新度q主要指在開放條件下,國內企業面臨貿易競爭壓力而更新技術、加強競爭力的反應速度和努力程度。的影響;而以μi代表的擠占損失參數受到貿易品與企業產品結構的相似度λ和企業產品市場份額m的影響。

那么,貿易開放程度對高新區企業貿易收益的影響可以表示為:

因此,不考慮其他變量,我們假設對于高新區企業i來講,在技術外溢函數Gi和擠占損失給定的情況下,企業能否從國際貿易中得到收益主要取決于參數ηi,而根據前文的梳理和實證分析我們大體可以得到:由于現有的科技型資本、設備、人力資源和管理模式等因素不可能通過模仿而迅速改變,企業技術投入量占比越高的產品,在開放經濟體中遇到類似產品時,其轉換成本越高,模仿難度就越大,技術外溢的接收就越困難,貿易的收益轉換因子ηi也就越小,即

因此,結合式(2)和式(3)我們有:

由此我們得到命題:高新區通過研發和生產得到的收入中技術投入量越高,其從貿易開放的進程中所得收益越小,即可能存在貿易收入的“負技術投入門檻效應”。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表3的估計結果。從某種意義上說,貿易開放下技術收入額的下降會抑制自主創新的積極性,擠占了高新區的創新資源,減緩了高新區轉型發展的速度。也從另一個側面暴露了我國高新區貿易創匯主要集中在商品領域,而并非企業所擁有的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和較高附加值的技術品,這也是當前高新區“二次創業”的意義所在,當然這一結論有待于下文的進一步驗證。
五、穩健性檢驗:高新區出口強度與收入結構

表4 穩健性檢驗:高新區出口強度與收入結構
前文的實證分析是從貿易開放的角度考察其對高新區產出與收入結構的影響,結論說明高新區的產出及技術收入對于城市貿易開放水平敏感度很高。但城市貿易開放度不能完全代表高新區的貿易強度,為了進一步驗證上述理論分析以及表3估計結果的穩健性,考察內部貿易變量對高新區收入結構帶來的影響。如前文所述,在本節我們采用高新區出口創匯額與高新區總產值的比值作為高新區出口強度來考察高新區內部貿易因素對于高新區技術收入、產品收入以及商品收入的影響。為了克服內生性,采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的估計結果如表4所示,我們發現,該結論與表3的分析結果一致,隨著高新區出口貿易強度的提升,技術收入在1%水平上顯著下降,并且在加入了城市控制變量后(如方程4所示),該系數的絕對值進一步擴大,而其對高新區產品收入和商品收入的影響卻變得不再顯著。說明即使高新區自身出口強度的提高,企業也很難從中得到“技術福利”,企業對于技術溢出的吸收能力較弱,效益的轉化機制不足。
這進一步表明了高新區企業在對短期利潤的追逐下,由于技術品的研發與生產周期較長,自身貿易強度的上升反而擠占了部分高技術品的生產研發資源,高新區的技術收入相應下降,這與謝子遠、梁丹陽[21]得到的高新區企業出口規模與研發投入強度成反比的實證結果在某種意義上是一致的。表3的結論得到再次驗證,也為上一章的理論闡釋提供了一定的依據,從另一個角度反映出高新區粗放式增長下出口品技術附加值較低的特點,貿易開放下對技術收入的帶動作用并沒有顯現。
需要說明的是,為了進一步增加結論的穩健性與信服力,避免因可能存在的異方差或者工具變量的相關識別性問題帶來的估計偏誤,本文仍選取上述工具變量采用有限信息極大似然估計(LIML)以及廣義矩估計(GMM)的方法對模型進行了重新估計。通過對回歸系數以及顯著性的觀察,我們發現無論是采用有限信息極大似然估計(LIML)還是廣義矩估計(GMM),所得結論并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且工具變量經檢驗均合格,表明上文的結論是非常穩健的。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并沒有報告詳細的估計結果,如有需要可以向作者索取。
六、結 論
本文從國家級高新區的角度考察了貿易開放對其產出增長與收入結構的影響,運用2007-2010年我國54個國家級高新區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得到的結果主要有:與FDI的作用不同,在控制了其他影響因素之后,城市的貿易開放顯著地抑制了高新區的產出,穩健性檢驗結果表明該結論是可靠的。而且,無論從城市貿易環境還是高新區出口強度變量入手,都顯示出貿易開放會導致高新區技術收入的下降,不利于高新區收入結構的優化,此時競爭擠占效應占主導地位,技術外溢很難被快速消化吸收轉化為收益,對于追求自主創新和科技進步的高新區來說,這一結論令人擔憂。
我國高新區經歷了二十多年的發展,高技術企業發展和孵化環境以及基礎設施日趨完善,高新區規模增長迅速。從表面上看,本文得到的結論似乎不符合人們的預期,但對于處在轉型期的我國高新區來說并不奇怪,數量過多、發展功能與目標不明確、結構趨同等原因導致目前我國高新區依靠粗放式增長的問題仍很嚴重。高新區的多數產品處于產業鏈的中下游,融資渠道窄、科研投入不足導致自主創新能力提升緩慢,且高技術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不強。近年來,雖然國家級高新區的出口創匯額不斷攀升,但主要以商品銷售和產品加工為主,技術附加值低,很難在國際高技術產品市場占有一席之地。此外,我國高新區的技術吸收與收益轉化能力較弱,除技術壁壘因素外,高新區企業人才儲備不足與技術轉化機制不完善也是原因之一。
我們發現無論是產出還是收入結構上,高新區對于城市貿易開放環境具有相當高的敏感度,在今后分析高新區發展方向和影響因素的同時,應該統籌考慮城市貿易開放和高新區內生因素的影響。鑒于貿易開放與高新區發展的雙重作用,第一,要明確我國高新區的功能目標,使其與我國其他類型開發區(如經濟技術開發區等)的發展定位區分開來,突出科技研發優勢,進一步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第二,要大力提升高新區人力資本水平,優化鼓勵創新的體制機制,促進產學研融合發展,提供和諧可持續的創新土壤,發揮高新區的區域輻射功能;第三,面對復雜的國際市場環境,高新區應培育和孵化潛力企業,根據所在地區經濟特點發展特色科技服務,增加出口品的技術附加值,提升國際競爭力。
本文的研究為今后分析開放條件下我國高新區發展路徑和影響因素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以往高新區旨在積極吸引外資和技術,卻忽略了高新區內生變量同貿易開放的交互影響,較少考慮其對產出和收入結構上的不利因素,未來的研究有必要擴展考慮這種貿易開放的擠占效應對于企業或部門發展的影響,將這種負面效應與企業或部門增長因素的交互作用納入到現有的研究框架當中,探索貿易開放對不同部門和個體發展的綜合影響。
[1]周元,王維才.我國高新區階段發展的理論框架——兼論高新區“二次創業”的能力評價[J].經濟地理,2003(4):451-456.
[2]韓伯棠,等.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園區的現狀及二次創業研究[M].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07.
[3]Coe D T,Helpman E.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5,39(5):859 -887.
[4]Lichtenberg F R ,Pottelsberghe de la Potterie B .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A comment[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8,42(8):1483 -1491.
[5]李小平,朱鐘棣.國際貿易、R&D溢出和生產率增長[J].經濟研究,2006(2):31 -43
[6]毛其淋,盛斌.對外經濟開放、區域市場整合與全要素生產率[J].經濟學(季刊),2011(1):181-210.
[7]葛小寒,陳凌.國際R&D溢出的技術進步效應——基于吸收能力的實證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9(7):86-98.
[8]李平,崔喜君,劉建.中國自主創新中研發資本投入產出績效分析—兼論人力資本和知識產權保護的影響[J].中國社會科學,2007(2):32 -42.
[9]Zhang Haiyang,Sonobe T.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s in China,1988 -2008[J].Economics:The Open-Access,Open-Assessment E-Journal,2011,5(6):1-25.
[10]Squicciarini M.Science parks,knowledge spillovers,
and firms innovative performance:evidence from Finland[R].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s,2009,No.2009-32.
[11]Link A N,Scott J T.The growth of research Triangle Park[J].Small Business Economics,2003,20(2):167-175.
[12]Levine R,Renelt D.A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cross-country growth regression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2,82(4):942 -63.
[13]劉斌,李磊.貿易開放與性別工資差距[J].經濟學(季刊),2012(2):429-460.
[14]樊綱,王小魯,張立文,朱恒鵬.中國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報告[J].經濟研究,2003(3):9-18.
[15]黃玖立,李坤望.出口開放、地區市場規模和經濟增長[J].經濟研究,2006(6):27-38.
[16]Wooldridge J.Econometric analysis of cross section and panel data[M].Cambridge,MA:The MIT Press,2002.
[17]姜彩樓,徐康寧.區位條件、中央政策與高新區績效的經驗研究[J].世界經濟,2009(5):56-64.
[18]謝建國,周露昭.進口貿易、吸收能力與國際R&D技術溢出:中國省區面板數據的研究[J].世界經濟,2009(9):68-81.
[19]張海洋.R&D兩面性、外資活動與中國工業生產率增長[J].經濟研究,2005(5):107-117.
[20]王慶石,張國富,吳寶峰.出口貿易技術外溢效應的地區差異與吸收能力的門限特征——基于非線性面板數據模型的實證分析[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9(11):94-103.
[21]謝子遠,梁丹陽.國家高新區研發投入影響因素研究[J].科學管理研究,2010(5):27 -30.
[22]騰堂偉,曾剛,等.集群創新與高新區轉型[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
Trade Openness,Output Growth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Income Structure:Evidence from National Hi-tech Zones in China
YANG Chang1,BAI Xue-jie2
(1.School of Economics,Nankai University,Tianjin300071,China;
2.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Nankai University,Tianjin300071,China)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s of trade openness on the output growth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income structure for National Hi-tech Zones.Using the panel data of54 Chinese National Hi-tech Zones from2007 to2010 to conduct empirical analysis,the paper finds that trade openness is unfavorable to the output growth of hi-tech zones and widens the gaps of the income structure,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roles of FDI.Furthermore,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trade effects of competition to the technical revenue for hi-tech zones is obvious ,while the effect of revenue conversion is insignificant in the open economy .To some extent,it is contrary to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of hi-tech zones.Therefore,there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to get a clear functional orient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tech zones and cultivate the abilities of survival and adaptation for enterprises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Trade Openness;Output;Income Structure;National Hi-tech Zones;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A
1002-2848-2013(04)-0091-11
2013-03-20
天津市教委社會科學重大項目“天津八大優勢支柱產業鏈發展現狀調查及對策研究”
楊暢(1986-),天津市人,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城市與區域經濟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制度環境與產業發展;白雪潔(1971-),女,蒙古族,內蒙古自治區通遼市人,南開大學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產業經濟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產業發展與產業政策。
責任編輯、校對:鄭雅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