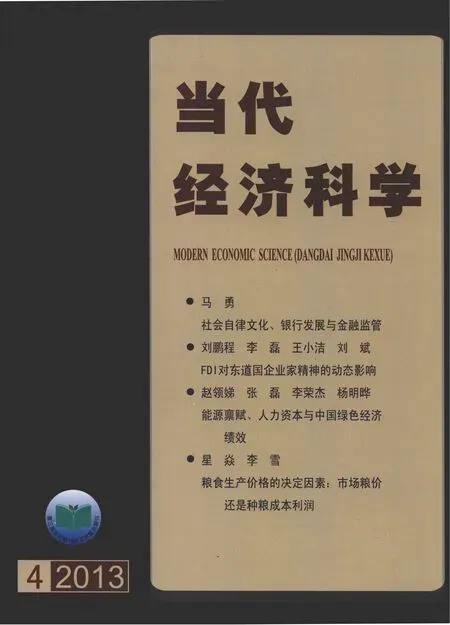中國省會城市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全要素生產(chǎn)率增長及收斂性分析
王美霞,樊秀峰,宋 爽
(西安交通大學經(jīng)濟與金融學院,陜西西安 710061)
中國省會城市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全要素生產(chǎn)率增長及收斂性分析
王美霞,樊秀峰,宋 爽
(西安交通大學經(jīng)濟與金融學院,陜西西安 710061)
省會城市;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全要素生產(chǎn)率;趨勢與特征;收斂性
省會城市是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集聚重地,以此為樣本進行深入研究,將有助于更客觀的分析中國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的發(fā)展水平與特征。本文通過對中國30個省會城市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全要素生產(chǎn)率(TFP)增長變化及收斂性分析發(fā)現(xiàn),1995-2009年,省會城市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TFP呈快速增長趨勢,且其增速明顯高于全國以及31個省市區(qū)的平均水平,技術進步水平的提高是其主要原因,技術效率則出現(xiàn)少許負增長,說明產(chǎn)業(yè)粗放型特征仍然明顯;TFP增長雖存在顯著區(qū)域差異,但呈現(xiàn)收斂趨勢,且部分城市已顯現(xiàn)明顯的“追趕效應”。
一、引 言
從世界范圍來看,20世紀80年代開始,在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發(fā)達國家產(chǎn)業(yè)結構由“工業(yè)經(jīng)濟”向“服務經(jīng)濟”轉(zhuǎn)型的趨勢不斷深入,城市作為服務經(jīng)濟發(fā)展的集聚地和源頭,日益發(fā)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作為各地區(qū)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中心的省會城市,城市化水平顯著提高,不僅制造業(yè)發(fā)達,而且也集聚了大量的以制造業(yè)需求為中心的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例如信息、金融、物流、租賃與商務服務等。在省會城市,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與制造業(yè)的融合不僅使制造業(yè)的價值越來越多地體現(xiàn)在服務上,同時服務業(yè)的大量集聚與發(fā)展也強有力地推動了城市經(jīng)濟的增長和城市功能的提升。2009年,中國服務業(yè)增加值比重和就業(yè)比重分別為40.5%、34.1%,其中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增加值比重和就業(yè)比重分別為19.8%、9.6%;30個省會城市服務業(yè)增加值比重和就業(yè)比重分別為58.2%、57.9%,其中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增加值比重和就業(yè)比重分別為32.3%、29.9%。這說明,省會城市服務業(yè)、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的發(fā)展水平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省會城市集聚的大量資本、信息、知識、技術和人才等因素更能真實反映和滿足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發(fā)展的需求。國家“十二五”規(guī)劃中更是明確提出,要加快服務產(chǎn)品和服務模式創(chuàng)新,促進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與先進制造業(yè)融合,推動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加快發(fā)展。因此,對于正處于工業(yè)化中期與后期交替階段的中國,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快速發(fā)展的同時,增長質(zhì)量更應引起關注,因為主要依靠資源、要素投入而非效率提升所引發(fā)的經(jīng)濟增長是難以長期維持的,技術進步和效率提升才是經(jīng)濟長期持續(xù)增長的重要源泉[1]。鑒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礎上,嘗試使用 Malmquist-DEA指數(shù)法,分時期、分區(qū)域測算中國30個省會城市1995-2009年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的全要素生產(chǎn)率(TFP)變化情況,并對TFP進行分解和收斂性檢驗,以期為加速提升中國省會城市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效率提供對策借鑒。
二、文獻綜述
目前,國內(nèi)外不少學者都對服務業(yè)效率進行了研究。Klassen與Russell等分析總結了服務業(yè)效率、生產(chǎn)率和有效性的不同內(nèi)涵及其測度指標差異,并在考慮高接觸服務業(yè)的同質(zhì)性和異質(zhì)性特征的前提下,提出改進服務業(yè)效率和生產(chǎn)力水平的建議[2]。Kankana等選取1984-1990年美國201家大型商業(yè)銀行相關數(shù)據(jù),測算了美國解除金融管制初期銀行業(yè)的TFP增長情況,結果說明技術進步、純技術效率和規(guī)模效率的提高是主要原因[3]。Hirofumi和Fukuyama通過對1992-1996年日本銀行業(yè)TFP的測算,發(fā)現(xiàn)TFP以年均2%的速度下降,主要原因是技術效率下降引起的[4]。Vivek和Ashok研究了南非銀行業(yè)在種族隔離之后的全要素生產(chǎn)率增長情況[5]。Chiu與Jan等人使用DEA模型評價了臺灣銀行業(yè)的技術效率[6]。Shang與 Hung等人運用DEA模型測度了電子商務產(chǎn)業(yè)和酒店業(yè)的績效[7]。
程大中運用規(guī)模報酬不變的總量生產(chǎn)函數(shù)分析得出,中國服務業(yè)增長的驅(qū)動力在20世紀90年代后發(fā)生轉(zhuǎn)換,資本—產(chǎn)出比對服務業(yè)的貢獻開始超過TFP增長[8]。顧乃華研究發(fā)現(xiàn),1992-2002年間中國服務業(yè)的發(fā)展遠未能挖掘出現(xiàn)有資源和技術的潛力,服務業(yè)增長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推動,TFP貢獻非常小。楊向陽和徐翔研究發(fā)現(xiàn),1990-2003年中國服務業(yè)TFP的平均增長率為0.12%,主要原因是技術進步水平的提高,但技術效率下降產(chǎn)生的負面影響也不容忽視[10]。楊勇認為,TFP對服務業(yè)產(chǎn)出的貢獻率在1980年前波動較大,1980年后漸趨平穩(wěn),1981-1991年TFP年均增長率為3.26%,1992-2006年為0.11%[11]。原毅軍和劉浩等人認為,中國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TFP出現(xiàn)負增長,前期原因是技術進步,后期為技術效率,且東部地區(qū)TFP下降的速度要遠低于中西部地區(qū)[12]。劉興凱和張誠分析發(fā)現(xiàn),中國服務業(yè)技術效率和技術進步增長率分別為0.7%和1.8%,TFP增長及其分解指數(shù)存在區(qū)域性差異,但收斂檢驗表明,各省區(qū)市的TFP增長呈現(xiàn)出長期的收斂趨勢[13]。黃莉芳與黃良文等認為,中國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技術效率水平較低,且區(qū)域差異主要表現(xiàn)在東部和中西部之間[14]。陳艷瑩與黃翯認為中國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TFP逐步上升,主要得力于技術進步,而技術效率在有些年份呈小幅下降趨勢,說明未能充分挖掘現(xiàn)有資源和技術的潛力[15]。王恕立和胡宗彪認為,1990-2010年中國服務業(yè)及細分行業(yè)的TFP處于上升通道,90年代以前主要依靠技術效率改進,21世紀后則依靠技術進步[16]。
綜上可見,現(xiàn)有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現(xiàn)有文獻缺乏對城市化程度高、服務經(jīng)濟發(fā)達的大城市尤其是省會城市的研究;第二,現(xiàn)有文獻鮮有對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TFP增長趨勢與特征進行研究。而如上所述,大城市尤其省會城市實際是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發(fā)展的集聚地,對省會城市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全要素生產(chǎn)率及其發(fā)展趨勢與特征的研究,可以更真實、更客觀的反映中國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的發(fā)展狀況,據(jù)此提出的對策性建議也將更具針對性,本文選題即源于此。
三、評價方法、模型和數(shù)據(jù)處理
(一)評價方法
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是一個涉及多要素投入、多項關聯(lián)產(chǎn)出的復雜系統(tǒng),要對這樣一個復雜系統(tǒng)進行合理、科學的效率評價,所選取的評價方法,必須既要滿足產(chǎn)業(yè)經(jīng)濟學關于效率評價指標選取的基本要求,又要充分體現(xiàn)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的產(chǎn)業(yè)特性。只有這樣,才能得出符合客觀實際的科學結論。因此,本文擬采用Malmquist-DEA指數(shù)模型來進行分析評價。首先,數(shù)據(jù)包絡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即DEA)是由著名的美國運籌學家Charnes和Cooper等學者在“相對效率評價”概念上發(fā)展起來的一種新的效率評價方法[17]。DEA方法用于評價多個決策單元的相對有效性,是一種非參數(shù)線性規(guī)劃技術,特別適用于多投入、多產(chǎn)出的復雜系統(tǒng)的效率評價,應用范圍較廣。它通過對投入和產(chǎn)出比率的綜合分析,計算投入產(chǎn)出效率,由于不需要考慮投入與產(chǎn)出之間的函數(shù)關系,也不需要預先估計參數(shù)及任何權重假設,特別適用于復雜系統(tǒng)的效率評價。其次,Malmquist生產(chǎn)率指數(shù)法相對于其他效率測度方法具有以下優(yōu)點:第一,它適用于多個國家或地區(qū)的跨時期的樣本分析;第二,不需要投入與產(chǎn)出變量的相關價格信息,這對實證分析非常重要,因為,一般情況下,相關投入和產(chǎn)出變量數(shù)據(jù)比較容易得到,而要素價格等相關信息的獲取通常較困難,有時甚至根本不可能;第三,它能夠被進一步分解為技術效率變化指數(shù)和技術進步變化指數(shù)兩個部分,且也不必事先對研究主體的生產(chǎn)函數(shù)模型進行假設等。因此,本文選用Malmquist-DEA指數(shù)模型進行評價,既可以彌補傳統(tǒng)評價方法的不足,又能夠客觀、全面地反映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的產(chǎn)業(yè)特征,是可行而恰當?shù)摹?/p>
(二)模型簡介
1.Malmquist生產(chǎn)率指數(shù)
Malmquist指數(shù)最初由瑞典經(jīng)濟學家和統(tǒng)計學家 Malmquist[18]提出,Caves[19]首先將該指數(shù)應用于生產(chǎn)率變化的測算,此后逐漸與Charnes等建立DEA理論相結合,演化成了Malmquist-DEA指數(shù)模型,被廣泛應用到技術效率和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測算中。研究者普遍采用Fare等[20]構建的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數(shù)。
從時期t到時期t+1,度量全要素生產(chǎn)率增長的Malmquist指數(shù)可以表示為:

其中,(xt,yt)、(xt+1,yt+1)分別表示時期 t和 t+1的投入與產(chǎn)出向量,Dti、Dti+1分別表示以時期t的技術為參照,時期t和t+1的距離函數(shù)。
根據(jù)上述處理得到的Malmquist指數(shù)具有良好的性質(zhì),它可以分解為不變規(guī)模報酬條件下的技術效率變化指數(shù)(EC)和技術進步指數(shù)(TP),過程如下:

式中,EC是指從時期t到時期t+1的技術效率變化;TP是指時期t到時期t+1的技術進步。其中,技術效率變化指數(shù)(EC)還可以進一步分解為純技術效率指數(shù)(PC)和規(guī)模效率指數(shù)(SC)。當Mi大于1時,說明從t時期到t+1時期全要素生產(chǎn)率是增長的;反之則是衰退的。
計算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的第i個行業(yè)在t時期與t+1時期的Malmquist生產(chǎn)率指數(shù),需要解決四個不同的線性規(guī)劃問題,它們分別是Dti(xt,yt)、Dti(xt+1,yt+1)、Dti+1(xt,yt)、Dti+1(xt+1,yt+1),運用數(shù)據(jù)包絡分析(DEA)的非參數(shù)分析法,即可求解以上四個距離函數(shù)。
2.DEA基本模型
DEA方法主要包括兩個基本模型,即規(guī)模報酬不變的CCR模型和規(guī)模報酬可變的BCC模型。以下將分別進行簡要介紹。
(1)CCR模型
首先假設某系統(tǒng)中有n個決策單元(DMU),每個決策單元都有m種類型的輸入和r種類型的輸出,則某決策單元的輸入向量為X=(X1,X2,……,Xm),輸出向量為 Y=(Y1,Y2,……,Yr),通過引入具有非阿基米德無窮小量ε,建立的CCR模型為:

式中,ε為非阿基米德無窮小量,一般取10-6,s+、s-為松弛變量。上式中主要的經(jīng)濟學含義是:λj將各個有效點連接起來,形成有效生產(chǎn)前沿面。非零的松弛變量即過剩量s+或不足量s-使得有效面可以沿著水平或者垂直的方向延伸,從而形成包絡面。θ則表示DMU距離包絡面的投影。
(2)BCC模型
CCR模式是假設在固定規(guī)模報酬前提下來衡量整體效率,但由于并不是每一個DMU的生產(chǎn)過程都是處在固定規(guī)模報酬之下,于是去除CCR模型中規(guī)模報酬不變的假設,而以規(guī)模報酬變動取代,發(fā)展成BCC模型。

利用CCR模型可計算出綜合效率,而在BCC模型下,可計算出純技術效率,且系統(tǒng)的綜合效率(技術效率)等于純技術效率和規(guī)模效率的乘積。
根據(jù)投入或產(chǎn)出距離函數(shù),DEA可以相應分為基于投入或產(chǎn)出兩種不同方法。基于投入的DEA方法目的是為了測算生產(chǎn)單元相對于給定產(chǎn)出水平下最小可能投入的效率,而基于產(chǎn)出的DEA方法則是為了度量實際產(chǎn)出與給定投入水平的最大可能產(chǎn)出差距。
(三)樣本選取、數(shù)據(jù)來源和處理
本文參考國內(nèi)外有關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的定義,依據(jù)我國國民經(jīng)濟行業(yè)分類的國家標準,并基于研究需要及數(shù)據(jù)的可獲得性對本文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的外延進行選取。由于2003年國家統(tǒng)計局對服務業(yè)進行重新分類,本文1995-2002年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的外延包括:地質(zhì)勘查水利管理業(yè)、交通運輸倉儲和郵電通信業(yè)、金融保險業(yè)、房地產(chǎn)業(yè)、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yè),2003-2009年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的外延包括: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yè)、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yè)、金融業(yè)、房地產(chǎn)業(yè)、租賃和商務服務業(yè)以及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zhì)勘查業(yè),歷年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的數(shù)據(jù)由上述行業(yè)數(shù)據(jù)加總得出。
由于拉薩市的相關統(tǒng)計數(shù)據(jù)缺失,本文樣本為除拉薩市外的30個省會城市。數(shù)據(jù)主要來源于歷年各省、直轄市、自治區(qū)統(tǒng)計年鑒和《中國城市統(tǒng)計年鑒》。估算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TFP涉及到的三個變量為: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產(chǎn)出、資本投入和勞動力投入。三個指標的選取、數(shù)據(jù)來源及處理介紹如下:
1.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產(chǎn)出。根據(jù)Mahadevan的研究[21],用各省會城市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增加值來衡量,為保證可比性,并按照1995年不變價指數(shù)進行縮減。
2.資本投入。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資本密集,因此對其資本投入的準確估算至關重要。估算物質(zhì)資本存量通常采用兩種方法:Hedonic評估法(Hedonic Valuation,簡稱HV法)和永續(xù)盤存法(Perpetual Inventory Method,簡稱PIM)。由于HV法所需條件極其復雜,所以大多數(shù)國家和地區(qū)都采用PIM法。目前,永續(xù)盤存法已成為國際上較為通行的估算資本存量的方法。近年來,國內(nèi)外大量文獻運用PIM法對我國的物質(zhì)資本存量進行估算,在已有的研究中主要從估算全國的、分省區(qū)的以及某個產(chǎn)業(yè)(行業(yè))的資本存量三個層面展開,如:Chow采用物質(zhì)產(chǎn)品平衡體系中的積累指標估算我國1952-1985年農(nóng)業(yè)、工業(yè)、建筑業(yè)、運輸業(yè)和商業(yè)等五個產(chǎn)業(yè)部門的資本存量[22]。薛俊波和王錚依據(jù)投入產(chǎn)出表的數(shù)據(jù),進一步細分估算了全國包含農(nóng)業(yè)、建筑業(yè)、食品制造業(yè)、金融保險業(yè)、商業(yè)飲食業(yè)等17個行業(yè)部門1990-2000年的資本存量[23],徐現(xiàn)祥等則從產(chǎn)業(yè)細分和省區(qū)細分結合起來考察的角度,系統(tǒng)估算了全國1978-2002年31個省市區(qū)三次產(chǎn)業(yè)的物質(zhì)資本存量[24]。
值得指出的是,多數(shù)文獻研究雖然從分地區(qū)或分產(chǎn)業(yè)對我國固定資本存量的測算方面作過一些嘗試,但多數(shù)研究表現(xiàn)相對粗獷,要么沒有深入考慮細分產(chǎn)業(yè)固定資本形成的差異,要么沒有深入考慮地區(qū)固定資本形成差異。徐現(xiàn)祥等人結合考慮了產(chǎn)業(yè)與地區(qū)的差異,用分產(chǎn)業(yè)GDP縮減指數(shù)和固定資本形成總額指數(shù)構造了分產(chǎn)業(yè)固定資本形成價格指數(shù)比較合理。因此,本文按照徐現(xiàn)祥等的做法,將基年(1995年)各城市的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資本存量通過下式求得:K1995=I1995/(0.05+gy),式中gy為1995 -2009年的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年均增長率。現(xiàn)有文獻對折舊率的選取缺乏一致,但多數(shù)選取5%作為資產(chǎn)折舊率,本文也采用5%這一數(shù)值。
3.勞動力投入。嚴格地說,勞動力投入應該考慮數(shù)量和質(zhì)量兩個方面,但考慮到數(shù)據(jù)的可獲得性,本文選用各省會城市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年末從業(yè)人數(shù)來表示。
四、實證結果分析
基于上述三個變量數(shù)據(jù),筆者使用DEAP2.1軟件,測算了中國30個省會城市1995-2009年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TFP及其分解的指數(shù)變動情況。本文主要基于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總體時序的階段性和三大類省會城市的區(qū)域性兩個方面進行分析。對于TFP總體時序的階段性分析,我們以中國入世后的伊始年2002年為界,主要劃分為1995-2002年和2003-2009年兩個階段進行分析。具體結果如下:
(一)1995-2009年30個省會城市TFP變動的階段性結果
由表1可知,1995-2009年間,30個省會城市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TFP平均增長率為9.9%,這主要得益于技術進步水平的提高,其平均增長率為10.8%,而技術效率卻有少許的下降,為-0.8%,對TFP的增長起到負面影響。從TFP變化的階段性結果來看,1995-2002年間,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TFP平均增長率為11.3%,主要得益于技術進步,為14.7%,而技術效率的增長出現(xiàn)下降趨勢,為-2.2%,且主要原因為純技術效率和規(guī)模效率均呈現(xiàn)出負增長;2003-2009年間,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TFP平均增長率為9.3%,其中技術進步貢獻率為7.8%,技術效率為1.7%,這說明該期間TFP的增長源于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的共同作用。
從TFP分解結果來看,1995-2009年間,純技術效率指數(shù)平均增長-1%,規(guī)模效率指數(shù)平均增長0.3%,這說明純技術效率下降是導致技術效率總體下降的主要原因,從而反映中國省會城市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發(fā)展中存在現(xiàn)有的資源和技術潛力沒有得到充分利用的問題;另一導致TFP下降的可能原因是由于體制性約束,交通運輸、金融、房地產(chǎn)等行業(yè)存在一定程度的壟斷和行政干預;第三,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主要為制造業(yè)部門的生產(chǎn)提供中間服務產(chǎn)品,制造業(yè)部門結構、技術需求的變遷對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總產(chǎn)出增長的貢獻以及技術效率增長影響起絕對主導作用。盡管,TFP指數(shù)在研究期內(nèi)以年均9.9%的速度增長,增長較為明顯,但卻低于技術進步年均10.8%的增長速度。為了更加清晰地分析中國省會城市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TFP指數(shù)的增長變化原因及趨勢,下面將從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表1 1995-2009年中國30個省會城市TFP指數(shù)及其分解
1.技術進步。1995-2002年間,所有年份的技術進步指數(shù)都保持快速增長,平均增長率為14.7%,尤其是2002年達到最高值34.7%。這表明1992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發(fā)展第三產(chǎn)業(yè)的決定》等相關政策的實施已經(jīng)取得了顯著的效果,隨著市場逐步開放,國外先進的管理經(jīng)驗和技術進入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技術外溢效應明顯;另一方面,中國工業(yè)勞動生產(chǎn)率增長的主要驅(qū)動因素的轉(zhuǎn)變,即由轉(zhuǎn)軌初期的單一資本深化驅(qū)動轉(zhuǎn)變?yōu)楫斍暗募夹g進步為主和資本深化為輔的多引擎共同推動,導致對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的技術進步產(chǎn)生顯著的外溢效應。2003-2009年間,技術進步指數(shù)為7.8%,其中2003年技術進步指數(shù)出現(xiàn)負增長,為 -12.2%,2004-2009年間,技術進步指數(shù)又保持平均11.1%的增長速度。這可能有兩個原因,第一,入世初期我國生產(chǎn)性服務企業(yè)對于外資的先進技術的學習和效仿能力較差,隨著過渡期的深入,生產(chǎn)性服務企業(yè)的消化、吸收能力增強;第二,20世紀90年代以來,計算機互聯(lián)網(wǎng)等信息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迅速提高了與制造業(yè)密切相關的交通運輸、金融、商務服務等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技術水平,從而成為推動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TFP指數(shù)增長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在省會城市,該作用更加凸顯。
2.技術效率。1995-2002年間,技術效率都處于震蕩波動的過程,2003-2006年間,技術效率一直處于增長狀態(tài),平均增長率為8.1%,其中純技術效率平均增長率為2.1%,規(guī)模效率平均增長率6.2%,尤其在2004年達到技術效率增長的峰值18.7%,但是在2007后,技術效率又出現(xiàn)了連續(xù)三年的負增長,平均為-6.8%,純技術效率增長率-3.1%,規(guī)模效率增長率為-3.8%。究其原因,這可能與該期間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的國際與國內(nèi)成長環(huán)境密切相關。1995-2001年間,由于我國還未正式加入WTO,生產(chǎn)性服務企業(yè)還未切身體會到“狼來了”的真實壓力,雖然該期間技術進步明顯,但對新技術的消化吸收的動力及能力不足,導致了技術效率的低下與波動;2003-2006年間,由于中國服務市場對外資的持續(xù)、深入開放,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對技術進步的消化吸收能力不斷增強,對在華外資企業(yè)的管理和技術溢出的學習效應顯著,因此,促進了我國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效率的持續(xù)提升;2007-2009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經(jīng)濟和對外貿(mào)易均受到不同程度影響,實體經(jīng)濟增長放緩,在華外資企業(yè)頻頻裁員,珠三角很多中小制造企業(yè)倒閉,金融業(yè)、房地產(chǎn)業(yè)、物流等主要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遭受重大打擊,因此技術效率連續(xù)三年處于負增長。
(二)三大類省會城市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TFP變動結果
本文根據(jù)中國社會科學院最新發(fā)布的《2011年中國城市競爭力藍皮書: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中公布的各城市綜合競爭力指數(shù)[25],將中國31個省會城市分為三大類,經(jīng)筆者整理如表2所示。
根據(jù)表2的分類,三大類省會城市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TFP變動情況如表3所示。

表2 中國31個省會城市綜合競爭力分類情況
由表3可知,1995-2009年間,從整體來看,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TFP平均增長率為3.6%,其中技術進步平均增長4.8%,技術效率平均增長-1.3%,且技術效率的下降受到規(guī)模效率和純技術效率雙重因素下降的影響;分類來看,第一、二、三類城市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TFP均處于增長狀態(tài),其平均增長率分別為10.7%、8.1% 和3.7%;從每一類省會城市的內(nèi)部構成來看,城市之間的TFP存在顯著差異,且影響TFP差異的因素也各不相同,具體分析如下:
1.第一類城市。四個城市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TFP平均增長率為10.7%,比整體水平高7.4個百分點,技術進步是主要原因,平均增長11.4%;從全國范圍來看,TFP速度增長位于前三位的都在第一類城市,依次分別為天津、廣州、上海,其TFP平均增長率為12.9%,12.4%和11.8%,并且技術進步都是推動TFP增長的主要原因。四個城市中,只有北京TFP增長是技術效率和技術進步共同作用的結果,平均增長率分別為1.4%和4.1%,從其分解結果來看,規(guī)模效率負增長,為-4.6%,是影響北京TFP未達到一線城市平均水平的主要原因。天津、廣州、上海三個城市技術效率均出現(xiàn)負增長,分別為-1.1%,-0.9%和 -1.7%,其中,天津的純技術效率和規(guī)模效率均下降,后兩個城市則只有規(guī)模效率下降。
2.第二類城市。十八個城市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TFP平均增長率為8.1%,比整體水平高4.5個百分點,技術進步指數(shù)平均增長9.5%,是推動TFP增長的主要原因。TFP平均增速位列前三甲的是合肥、成都和杭州,分別為8.9%、7.8%、7.4%,其中合肥得益于技術效率和技術進步共同提高,分別增長為6.9%和1.9%,成都和杭州兩市則歸功于技術效率的提高,分別增長9.1%和14.3%;TFP出現(xiàn)負增長的有六個城市,為沈陽、武漢、福州、石家莊、南寧和南昌,平均增長率分別為-1%、-4%、-1.5%、-2.2%、-3.5%、-1.5%,六個城市的技術進步均為正值,故技術效率下降是導致TFP下降的主要原因,分別為-3.3%、-1.7%、-4.2%、-2.7%、-3.8%、-3.4%。

表3 各省會城市1995-2009年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TFP及其分解
3.第三類城市。八個城市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TFP平均增長率為3.7%,技術進步指數(shù)平均增長5%,是推動TFP增長的主要原因,而技術效率出現(xiàn)負增長,為-1.6%。TFP增長最快的是烏魯木齊,為9.5%,在全國30個省會城市中位列第四,其中技術進步增長10.7%,是促進TFP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太原和海口兩市TFP出現(xiàn)負增長,分別為-3.3%和-3.5%,前者是由于技術進步下降引起,為-4.4%,后者是由于技術效率下降引起,為-5.3%;除太原市外,其他各市技術進步均為正。
綜上所述,省會城市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TFP增長存在顯著差異,第一類城市增長較快,第二類城市次之,第三類城市增長較慢。 這也說明,第一類城市其主要動力來源于技術進步的推動,平均增長為11.4%,高于全國省會城市平均水平,一定程度上說明了一類城市由于經(jīng)濟基礎好,對外開放程度高,吸引了大量的外資、先進技術和優(yōu)秀人才,尤其是電子信息、計算機、金融、商務服務等行業(yè)的快速發(fā)展,帶動技術進步水平不斷提高,從而推動TFP快速增長。在第二、三類城市中,也有部分城市TFP增長較快,如合肥、烏魯木齊等,前者可能是由于城市內(nèi)聚集了中國科技大學等一大批高校科研院所,在改善技術效率和技術進步方面效果顯著,后者則由于新疆地區(qū)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國家的大力支持,以及原本基數(shù)較低,提升空間較大,TFP的“追趕效應”較為明顯。1995年以來,各省會城市技術效率基本沒有提高,甚至出現(xiàn)下降,技術進步是導致TFP增長乃至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地區(qū)差異的重要原因,這也從另一方面說明,提高技術效率是今后促進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發(fā)展的關鍵所在。
五、收斂性檢驗
中國省會城市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的TFP有較大差異,部分二、三類省會城市對一類城市的“追趕效應”已比較明顯,那么,TFP差異是如何演化的?是否會呈現(xiàn)出逐步縮小的態(tài)勢?要回答這些問題,必須對其增長變化趨勢進行收斂性檢驗。收斂理論是新古典增長模型中基于資本邊際報酬遞減和規(guī)模報酬不變條件下得出的推論,是研究國家或地區(qū)間經(jīng)濟差距動態(tài)變化趨勢的理論。根據(jù)Barro和Sala-i-Martin的研究成果,收斂包括δ收斂和β收斂,β收斂又分為絕對β收斂和條件β收斂[26]。δ收斂是指各經(jīng)濟體發(fā)展水平差距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縮小,一般用標準差來衡量。絕對β收斂是指落后經(jīng)濟體發(fā)展速度快于發(fā)達經(jīng)濟體,最終能達到相同的穩(wěn)態(tài)水平。如果每個經(jīng)濟體的發(fā)展趨近自身穩(wěn)態(tài)水平,那就是條件β收斂。本文將討論δ收斂和絕對β收斂。
δ收斂一般通過國家或地區(qū)水平指標的標準差或變異系數(shù)來反映其差距的變化趨勢,筆者在圖1中給出了1996-2009年中國各省會城市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TFP逐年標準差。
從圖1可以看出,1996-2009年間,TFP增長的標準差δ值呈現(xiàn)逐漸波動的減小趨勢,說明呈現(xiàn)δ收斂,城市間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的TFP增長差距逐漸縮小。2003年之前δ值波動幅度較大,之后逐漸趨于平緩,說明TFP的差距保持相對穩(wěn)定。下面將進行絕對β收斂檢驗。

圖1 1996-2009年各省會城市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TFP增長標準差
根據(jù)Bernard等的分析[27],本文將采用如下的檢驗β收斂性的回歸模型:

式中,ΔlnTFPiT為各城市0到T期間TFP平均增長率,lnTFPi0為0期TFP增長率,ε為隨機干擾項,β為0期全要素生產(chǎn)率lnTFPi0的系數(shù),收斂速度λ可以通過公式β=-(1-e-λT)/T求得。若β為負,則表明存在絕對β收斂。根據(jù)前文分析得到的1996-2009年各省會城市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TFP的數(shù)據(jù),利用上述回歸模型,使用Eview6.0軟件進行分析,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第一類省會城市三個時期的β值均為負,TFP增長呈收斂趨勢,且1996-2003年間和2004-2009年間的收斂速度分別為2.8%和3.4%,說明北京、上海、廣州和天津的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TFP增長差距在逐漸減小;第二類省會城市在1996-2003年β值為正,不存在絕對β收斂,但在2004-2009以及1996-2009年間,呈收斂狀態(tài),收斂速度分別為5.1% 和2.6%;第三類省會城市在三個時期內(nèi)β值多數(shù)為負,存在絕對β值收斂,但β值均不顯著,說明收斂趨勢弱化。

表4 中國三大類省會城市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TFP收斂性檢驗
六、結論與建議
綜上,本文運用Malmquist-DEA指數(shù)方法,測算并分析了中國30個省會城市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增長和變化情況,并對其增長趨勢進行了收斂性檢驗,得出以下結論:
1.省會城市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增速明顯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也明顯高于31個省市區(qū)的平均水平,由此可見,省會城市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的發(fā)展水平與變化特征是影響全國水平的重要因素。重視省會城市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效率問題應是今后一個時期理論研究與實際工作的重心。
2.技術水平的持續(xù)提升是推動省會城市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全要素生產(chǎn)率增長的主要原因。隨著1992年國家有關大力發(fā)展服務業(yè)政策的出臺和市場逐步開放,國外先進的管理經(jīng)驗和技術進入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領域,技術外溢效應明顯。與此同時,20世紀90年代以來,計算機互聯(lián)網(wǎng)等信息產(chǎn)業(yè)的迅速發(fā)展,提高了與制造業(yè)密切相關的交通運輸、金融、商務服務等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技術水平,這一推動作用在省會城市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
3.技術效率相對低下在整體上牽制了省會城市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增速。技術效率的下降主要受到規(guī)模效率和純技術效率雙重因素下降的影響。這說明省會城市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現(xiàn)有的資源和技術潛力尚未得到充分利用。其原因既可能有制度因素,如金融、通信等行業(yè)的壟斷因素可能使效率受損;也可能是企業(yè)自身的管理因素,比如,由于現(xiàn)代物流人才、金融人才的缺乏而使效率低下,等等。總之,提高技術效率應是今后促進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發(fā)展的關鍵所在。
4.中國省會城市間的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全要素生產(chǎn)率有較大差異,但部分二、三類省會城市對一類城市的“追趕效應”已較明顯。上述三類省會城市之所以出現(xiàn)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全要素生產(chǎn)率增速縮小之勢,其可能的原因是2004年底之后中國服務業(yè)市場對外的全面開放、城市化進程的全面加速等因素,從而促進了二、三類城市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生產(chǎn)效率的提升。
基于以上討論,本文提出如下對策性建議:
1.各省會城市應進一步加大教育和科技投入,提高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技術進步水平。政府要通過財政、稅收等途徑,加大教育投入,建立起完備的人才培養(yǎng)機制,制定合理的人才計劃,建立健全技術創(chuàng)新機制,重視技術創(chuàng)新環(huán)境建設,鼓勵企業(yè)建立各類研發(fā)機構和增加研發(fā)投入,使企業(yè)成為創(chuàng)新主體,積極推動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技術進步。
2.各省會城市要充分利用自身的資源、技術等優(yōu)勢,堅持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與先進制造業(yè)的融合發(fā)展,以全球金融危機引發(fā)的產(chǎn)業(yè)結構調(diào)整為契機,進一步推動我國制造業(yè)從過去片面注重生產(chǎn)環(huán)節(jié)向“研發(fā)”與“生產(chǎn)”相結合的戰(zhàn)略轉(zhuǎn)變,尤其是高新技術(先進)制造產(chǎn)業(yè)專業(yè)化分工的深化與細化,強化專業(yè)化服務企業(yè)的分工優(yōu)勢,重點扶持與本市城市功能定位匹配的具有比較優(yōu)勢的生產(chǎn)性服務產(chǎn)業(yè),強化先進制造業(yè)對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的拉動作用。
3.應逐步消除行業(yè)壟斷,加大開放力度,強化市場競爭。目前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普遍存在管制和進入壁壘,如金融業(yè)、電信業(yè)、鐵路運輸、信息媒體等行業(yè)。長期以來,這些行業(yè)競爭不足,效率低下。要加快對壟斷行業(yè)的改革步伐,合理引導民間資本和外商投資參與國有企業(yè)改革,推動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資源配置由政府向市場主導的轉(zhuǎn)變,加強監(jiān)管,規(guī)范管理。
4.各省會城市要加大與周邊地區(qū)及鄰省的信息、技術、人才聯(lián)動,大力拓展服務外包業(yè)務,尤其是第二、三類省會城市要進一步加大與第一類城市的交流與合作,學習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積極承接發(fā)達地區(qū)的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由于二、三類城市內(nèi)在自身的經(jīng)濟發(fā)展會產(chǎn)生強大的需求動力,故自身要重視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效率的提升,進一步縮小城市以及區(qū)域之間的差距,盡快實踐其“追趕效應”。
[1]Krugman P.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J].Foreign Affairs,1994(6):62 -78.
[2]Klassen K J,Russell R M,Chrisman J J.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measures for high contact services[J].The Services Industries Journal,1998(4):1 -18.
[3]Mukeherje K,Ray S C.Productivity growth in large USA commercial banks:The initial post-deregulation experience[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2001(5):913-939.
[4]Fukuyama H,William L W.Estimating output allocative and productivity change:Application to Japanese banks[J].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2002(1):177-190.
[5]Arora V,Bhundia A.Potential output and tota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R].IMF Working Paper,2003,No.3.
[6]Chiu Y H,Jan C,Shen D B,Wang P C.Efficiency and capital adequacy in Taiwan banking:BCC and Super-DEA estimation[J].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2008,4:479-496.
[7]Shang J K,Hung W T,Lo C F,Wang F C.Ecommerce and hotel performance:Three - stage DEA analysis[J].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2008(4):529 -540.
[8]程大中.中國服務業(yè)的增長與技術進步[J].世界經(jīng)濟,2003(7):35-42.
[9]顧乃華.1992-2002年我國服務業(yè)增長效率的實證分析[J].財貿(mào)經(jīng)濟,2005(4):85-90.
[10]楊向陽,徐翔.中國服務業(yè)全要素生產(chǎn)率增長的實證分析[J].經(jīng)濟學家,2006,(3):68-76.
[11]楊勇.中國服務業(yè)全要素生產(chǎn)率再測算[J].世界經(jīng)濟,2008(10):46-55.
[12]原毅軍,劉浩,白楠.中國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全要素生產(chǎn)率測度—基于非參數(shù) Malmquist指數(shù)方法的研究[J].中國軟科學,2009(1):159 -167.
[13]劉興凱,張誠.中國服務業(yè)全要素生產(chǎn)率增長及其收斂分析[J].數(shù)量經(jīng)濟與技術經(jīng)濟研究,2010(3):55-67.
[14]黃莉芳,黃良文,洪琳琳.基于隨機前沿模型的中國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技術效率測算及影響因素探討[J].數(shù)量經(jīng)濟與技術經(jīng)濟研究,2011(6):120-132.
[15]陳艷瑩,黃翯.我國生產(chǎn)性服務業(yè)增長的效率特征—基于2004-2009年省際面板數(shù)據(jù)的研究[J].工業(yè)技術經(jīng)濟,2011(5):42-49.
[16]王恕立,胡宗彪.中國服務業(yè)分行業(yè)生產(chǎn)率變遷及異質(zhì)性考察[J].經(jīng)濟研究,2012(4):15-27.
[17]Charnes A,Cooper W,Seiford L M.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Theory,methodology,and application[M].Dordrecht:Kluwer Academic,1994.
[18]Malmquist S.Index numbers and indifference curves[J].Trabajos de Estatistica(S0081 -4539),1953,4:209-242.
[19]Caves D W,Christensen L R,Diewert W E.The economic theory of index numbers and the measurement of input and output,and productivity[J].Econometrica,1982,50:1393-1414.
[20]Fare R,Grosskopf S,Norris M,Zhang Z Y.Productivity growth,technical progress,and efficiency change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4(1):66 -83.
[21]Mahadevan R.Sources of output growth in Singapore`s service sector[J].Empirical Economics,2000(3):495-506.
[22]Chow G C.Capital 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3(3):809-842.
[23]薛俊波,王錚.中國17部門資本存量的核算研究[J].統(tǒng)計研究,2007(7):49 -54.
[24]徐現(xiàn)祥,周吉梅,舒元,等.中國省區(qū)三次產(chǎn)業(yè)資本存量估計[J].統(tǒng)計研究,2007(5):7-13.
[25]倪鵬飛,侯慶虎,梁華,陳小龍.2011年中國城市競爭力藍皮書: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26]Barro R J,Sala-i-Martin X.Convergenc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2(2):223 -251.
[27]Andrew B B,Charles I J.Comparing apples to oranges:Productivity convergence and measurement across industries and countri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6(5):1216-1238.
The Growth and Convergence Analysis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Provincial Capitals'Productive Service in China
WANG Mei-xia,F(xiàn)AN Xiu-feng,SONG Shu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710061,China)
Productive service is mainly amassed in the provincial capitals.It is more objective to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level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productive service by deeply studying its productivity,growth trend and features of provincial capitals'productive service.This paper measures the growth changes i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of the thirty provincial capitals'productive service in China and makes the convergence analysis of it.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FP of the thirty provincial capitals'productive service presents a quick growth trend from1995 to2009 and the average growth rate of its TFP per year is higher than that of overall China's and thirty provinces'productive service.The dominant factor leading to TFP growth is technical progress.Technical efficiency is on the negative increase and the extensive features of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ies development are still evident.The TFP increases apparently differs among the three types of provincial capitals,but presents a convergent tendency.And some cities obviously show a catch-up effect.
Provincial Capital;Productive Service;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endency and Feature;Convergence
A
1002-2848-2013(04)-0102-10
2012-06-25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中國產(chǎn)業(yè)安全問題研究——零售企業(yè)國際化影響與我國零售產(chǎn)業(yè)安全相關性的實證研究”(立項號:08B JY087)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王美霞(1981-),女,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鄂爾多斯市人,西安交通大學經(jīng)濟與金融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零售企業(yè)國際化、服務業(yè)效率評價;樊秀峰(1955-),女,陜西省鎮(zhèn)安縣人,西安交通大學經(jīng)濟與金融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跨國公司理論與國際直接投資。
責任編輯、校對:李再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