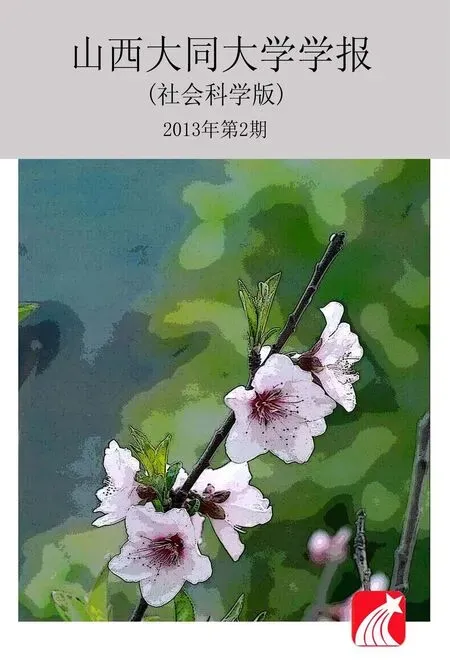清康熙年間黑龍江地區達斡爾人編旗駐防考實
闞 凱
(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北京 100081)
清康熙年間黑龍江地區達斡爾人編旗駐防考實
闞 凱
(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北京 100081)
清代黑龍江地區的達斡爾人在康熙、雍正年間經過了兩次大規模的編旗駐防活動,極大地補充了黑龍江地區的兵員,在黑龍江八旗駐防體系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其中從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至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黑龍江地區的達斡爾人在清政府的安排下,先后6次編旗設佐。這一過程中的族屬、駐防地、佐領數也在不斷變化之中。
索倫;達斡爾;康熙朝
清軍攻占北京后,原居于東北的滿族人眾,大多“從龍入關”,當時的情景是:“沈陽農民,皆令移居北京,自關內至廣寧十余日程,男女抉攜,車轂相擊。”[1](P3756)據有學者考證,順治元年(1644年)至二年(1645年)間,滿族入關人數多達百萬之眾。[2](P8)特別是作為其軍隊精銳的滿蒙漢軍八旗,更是往返征戰于關內各地,這就造成了東北防務的空虛。作為滿族的龍興之地,東北地區的重要性對清王朝來說不言而喻,為解決兵源不足的問題,將當地各土著居民編入八旗成為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手段。康熙年間,清政府在黑龍江地區開始大規模地從達斡爾等部族中抽調成丁,開啟了從康熙朝到雍正朝約50多年編旗駐防的帷幕。學界以往對清代黑龍江地區的八旗駐防研究成果頗多,但關注的重點多為八旗駐防的內部體制與機構設置以及兵額與餉額等,具體到編旗過程,則有不盡詳實之處,且編設旗佐的數量也多相互抵牾。本文擬對康熙年間黑龍江地區達斡爾族編旗駐防的脈絡加以厘清,以期還原此段史實。
一、康熙朝以前索倫達斡爾人編佐的狀況
明末清初,居于黑龍江地區的土著居民主要包括鄂倫春、鄂溫克、達斡爾等族,統稱索倫部。康熙六年(1667年)的史書記有“查打虎兒有一千一百余口,未編佐領,應照例酌量編為十一佐領,設頭目管理”,[3](卷22,P310)這是最早單獨出現達斡爾(打虎兒)之族名。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又有“俄人誘索倫、打虎兒、俄羅春之打貂人”[3](卷112,P147)之語。由此可見,最遲至康熙年間,達斡爾、鄂倫春已開始單獨冠名,而索倫則開始專指鄂溫克人。
早在天聰年間,黑龍江地區達斡爾人便與后金政權發生了聯系。天聰八年(1634年),達斡爾族著名首領巴爾達齊“率四十四人來朝,貢貂皮一千八百一十八張”。[4](卷18,P239)此后,有關達斡爾與后金(清)之間的交往史不絕書,但雙方之間的交流多限于貢貂、朝覲、賞賜等事,直至崇德四年(1639年),皇太極命令索海、薩穆什喀出征索倫部落。此次出征,收降了大量索倫人眾,崇德五年(1640年)五月,將其中歸降的男子481人編設牛錄,皇太極諭曰:“爾等可令索倫來歸之眾,同我國外藩蒙古郭爾羅斯部落,于吳庫馬爾、格倫額蘇勒、昂阿插喀地方駐剳耕種,任其擇便安居,其中有能約束眾人堪為首領者,即授為牛錄章京,分編牛錄。”[4](卷51,P687)這481人后來被編為了8個牛錄。同年,又將薩穆什喀等往征索倫所獲之“二千七百五十一名,婦女三千九百八十九口,編入八旗,至是,均賞衣服布匹,復令較射,分別等第。一等者,視甲喇章京;二等者,視牛錄章京;三等者,視半個牛錄章京。”[4](卷53,P71)隨著對黑龍江地區的征服,大量的索倫人眾開始歸附清朝。崇德六年(1641年)五月,“索倫部落一千四百七十一人來降”,“以都勒古爾、達大密、綽庫尼、阿濟布為牛錄章京,管理索倫部落新降人戶”,并“賜索倫部落牛錄章京都勒古爾、達大密、阿濟布、訥努克、竇特、布克塔、充內堪代、俄爾噶齊、吳葉、勒木白德、烏陽阿、章庫、車格德、拜察庫、撓庫、訥墨庫等蟒緞朝衣……”。[4](卷56,P751)如此眾多的索倫人眾被編旗設佐,是否意味著他們就此都納入了八旗序列中了呢?顯然并不都是如此,因為在崇德七年(1642年)和順治五年(1648年)又出現了賜“索倫部落牛錄章京訥耨克等二十二人宴”,[4](卷59,P807)“索倫部落牛錄章京阿濟布等貢貂皮,賞賚如例”[5](卷39,P313)等語,此處的訥耨克即為前面提到的訥努克。可見,此時編設的索倫牛錄仍是以貢貂為主要任務,并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一種地域性的組織結構。[6](P229)又查閱乾隆朝頒定的《八旗通志》可發現,在鑲黃旗滿洲第五參領下的第一佐領,為崇德五年(1640年)由索倫人丁編為半個牛錄,命布克沙管理,后來因為人丁滋生,遂編為一整牛錄。[7](卷,P38)此處的布克沙,似應即前文所提到的16佐領中的布克塔。由于史料的殘缺,究竟有多少索倫牛錄被納入八旗滿洲序列尚不能明確,但可以確知的是,這一時期編設的索倫牛錄被分為了兩個部分,一部分仍于原居住地為清政府貢貂,而另一部分則成為新編滿洲八旗的一部分。
二、康熙年間索倫達斡爾人的六次編旗駐防
從十七世紀四十年代開始,沙俄勢力開始向黑龍江流域滲透,這就迫使原居于黑龍江、精奇里江一帶的達斡爾人逐漸向南遷移至嫩江流域。康熙二十一年 (1682年),寧古塔將軍巴海、副都統薩布素率“烏喇、寧古塔兵一千五百名,并置船艦,發紅衣炮、鳥槍及演習之人,于黑龍江、呼瑪爾二處建立木城”,[3](卷106,P82)驅俄戰爭由此開始。但由于兵源不足,清政府開始在黑龍江當地征調達斡爾人參與此次戰爭。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薩布素奏:“應于來春,就近移打虎兒兵五百人,先赴額蘇里耕種,量其秋收,再遷家口,以烏喇、寧古塔兵三千,分為三班,將軍、副都統等更番統領駐防。”[3](卷112,P162)關于這些達斡爾兵丁是否就此駐防黑龍江,《實錄》中并無明確記載,但查閱檔案,卻可發現此五百人之蹤跡。據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正月十五日《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等為曉諭達斡爾官兵攜帶口米事致欽差輕車都尉的咨文》稱:“駐防本處達斡爾八牛錄五百兵丁前來之時,應從各自家里攜帶充足行軍口米,今年耕種所需牛只夫役,請曉諭各自攜帶。”[8](P2)另據雍正六年(1728年)黑龍江將軍那蘇圖的咨文:“正藍旗達斡爾佐領額扎爾根病故。經案額扎爾根承襲佐領厚案,康熙二十二年出征雅克薩五百牲丁與二十三年初編佐……”,[8](P263)可以確知,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這500達斡爾人被編為8個佐領,開始駐防黑龍江城。
勾檢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及二十七年(1688年)檔案,不難發現此8佐領之姓名與旗色。其中,鑲黃旗佐領額勒珀車、正黃旗佐領塔爾呼蘭、正白旗佐領綏伯 (后病故,由其子依哈圖補放)、正紅旗佐領畢勒聰額、鑲白旗佐領圖揚圖、鑲紅旗佐領格吉格哩、鑲藍旗佐領提帕尼,而正藍旗佐領并未提及。但查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六月初一日《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等為補發兵丁孀婦錢糧事致寧古塔將軍等的咨文》中有“達斡爾孫特依牛錄”的記錄,核對康熙二十九年有關黑龍江城墨爾根駐防兵丁的檔案,其中駐防黑龍江城正藍旗達斡爾佐領為蘇特依(孫特依),可知前述檔案中未注旗色之達斡爾孫特依牛錄當屬正藍旗。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清政府第二次在索倫人中編旗設佐駐防。由于此次編旗原因主要是因為索倫人生活貧困,無以為生,故此次所編八旗索倫人被稱作“貧窮索倫”。此次編旗活動始于康熙二十七年一月,當時的索倫總管瑪布岱致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的咨文中稱:“為報送貧窮索倫達斡爾中情愿披甲人等數目事,輕車都尉瑪拉、郎中依道會同查問,情愿披甲者,貧窮索倫三百三十二人,貧窮達斡爾八十四人,此外尚有外出打牲之人等未及查問,俟伊等返回之時再行查問,若有情愿披甲者,另文咨報。”[8](P24)由于當時索倫部的打牲牲丁尚有一部分未歸,故此次編旗活動直至年底才告完成。有關檔案中關于這次編旗的詳細情況記錄如下:
應披甲之貧窮索倫達斡爾人等到達后即行編設牛錄。索倫之達達克圖為佐領,此牛錄以卓克希勒圖為驍騎校,披甲六十二人;賽圖為佐領,此牛錄以納密岱為驍騎校,披甲六十二人;霍倫岱為佐領,此牛錄以噶日勒圖為驍騎校,披甲六十二人;雅奇岱為佐領,此牛錄以希勒慶額為驍騎校,披甲六十二人;恩格爾為佐領,此牛錄以色爾特赫依為驍騎校,披甲六十三人;色勒布為佐領,此牛錄以希納岱為驍騎校,披甲六十三人。已咨兵部,議以達答克圖、透訥依、依策勒圖牛錄隸鑲黃旗;霍鸞岱、雅奇岱牛錄隸正黃旗;賽圖、鞥額、色勒布牛錄隸正白旗。所編八個牛錄共計佐領八員、驍騎校八員,每牛錄算上小領催各六名,則披甲為五百人。[8](P78)
那么,這8個貧窮索倫牛錄最后駐于何處,據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給索倫總管的咨文稱:
速行查驗可披甲之索倫達斡爾,遇有收撫即速咨報我等。現以天寒,爾等咨行我等,再至我等咨復,則漸趨寒冷,俟收攏完畢,以爾等人力護送。此番前來,若情愿將各自子女一同攜來,令其攜來,不能前來者,若欲暫留索倫達斡爾地方,即可留下。此項人等到達我處后即編牛錄,我處駐防與墨爾根駐防需分別編佐。[8](P50)
可見,最初薩布素原想將此次編設的索倫達斡爾人于黑龍江城和墨爾根兩處駐防。但查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及三十四年(1695年)黑龍江城駐防八旗佐領名錄,并未見此八佐領,而在墨爾根城的名單中則可見此八人。由此可知,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所編的貧窮索倫八佐領最后的駐防地為墨爾根。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仍然是為了解決索倫達斡爾人的生計問題,清政府再次從他們中間抽丁設佐。據康熙二十九年的檔案:“撥補披甲之(索倫)二百零七丁,達斡爾十八丁,加上佐領一員,已于康熙二十八年八月初五日送往爾處。彼等均于本月初十日起到達墨爾根地方。”[8](P83)可見,這次編佐活動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即以開始。關于此次編旗設佐的具體情況,康熙二十九年薩布素呈送康熙帝的題本中有較詳細的敘述:
查得,索倫達斡爾內無以為生應撥補披甲之索倫,加上索倫佐領一員,二百七丁;無以為生應撥補披甲之達斡爾二百丁。依照先前編設八牛錄貧窮索倫之例編設牛錄,由其中揀選干練之人,將曾任佐領之薩姆巴庫補放佐領,塔勒達尼補放該牛錄驍騎校,設披甲六十二名。將索倫固耶克補放佐領,齊岱補放該牛錄驍騎校,設披甲六十二名。將索倫多倫綽補放佐領,霍莫爾多補放該牛錄驍騎校,設披甲六十二名。再以達斡爾十八丁、索倫十二丁,會同先前編設牛錄之貧窮索倫各牛錄所余之丁,設一牛錄,然無干練之人可補放佐領驍騎校。鑲黃旗陳達斡爾格吉格爾牛錄驍騎校霍羅耐精干,堪以管理,將其補放佐領,因罪革職留任陳達斡爾驍騎校溫杜拉哈精干,堪以管理,將其補放此牛錄驍騎校,設披甲六十三名。薩姆巴庫隸鑲黃旗,固耶克、多倫綽牛錄隸正黃旗,霍羅耐牛錄隸正白旗。[8](P92)
此次共編設4個佐領,分別為索倫佐領薩姆庫巴、固耶克、多倫綽,達斡爾佐領霍羅耐(因霍羅耐原為達斡爾格吉格爾牛錄之驍騎校,故將此佐列為達斡爾)。同年,在《索倫總管等為商議遷移索倫達斡爾人事致黑龍江將軍的咨文》中又有:
爾等所屬住在墨爾根周圍達斡爾人等移居何地至今尚未確定,且今年房屋未拆,農田仍應種植。欽差大臣查勘墨爾根地方,若確定可建城駐兵則建城。此地達斡爾人等應盡早遷移。現今官兵移來建房耕地,若爾等達斡爾今年仍不遷移,則貧窮索倫十二牛錄無居處無耕地。于我等圣主之民,無誰得利,眾皆受損。惟盡快議定達斡爾遷移之地。既然本年遷移,在所移之地開墾,請將此處原有農田分撥耕種,將一半農田發給貧窮索倫十二牛錄耕種。[8](P88)
此咨文中所提到的“貧窮索倫十二牛錄”應即是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所編的8個索倫牛錄及此次所編之薩姆庫巴等4個牛錄。由此也可確知,康熙二十七年所編的8個索倫牛錄應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隨薩布素由黑龍江城遷至墨爾根駐防。參照康熙二十九年黑龍江城和墨爾根兩處八旗佐領名錄,我們又發現,在墨爾根城只有11個貧窮索倫牛錄,此外還有隸屬于正黃旗的達斡爾塔爾呼蘭牛錄,而此牛錄為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最初編設的8個達斡爾牛錄之一,前次所編應駐防于墨爾根的正黃旗多羅綽牛錄則出現在黑龍江城駐防中。此兩牛錄當為相互對調,其具體原因史料并未具體說明,但查康熙四十年(1701年)黑龍江將軍沙納海的題本,當時原任索倫總管的卜魁因病休致,命正黃旗達斡爾佐領塔爾呼蘭補放為索倫總管。據吳雪娟考證,卜魁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卸任,所以塔爾呼蘭當于康熙三十或三十一年升為索倫總管,并率所屬牛錄遷至墨爾根。為保持各城的旗色之完整,故將原駐于墨爾根同樣為正黃旗的多羅綽牛錄對調至黑龍江城。
康熙三十年(1691年),清政府第四次在索倫達斡爾人中編旗披甲。披甲兵丁主要從科洛爾、喀爾塔爾奚、庫瑪爾、額雨爾、黑龍江等5個驛站中揀選,共抽丁150名,編為了3個牛錄。其中“以正白旗浩勞納依牛錄溫都爾罕補放佐領,達斡爾哈魯尼補放驍騎校,編入鑲黃旗;以正黃旗索倫霍羅岱牛錄驍騎校噶喇勒圖補放佐領,索倫浩丹楚補放驍騎校,編入正黃旗;以正白旗達斡爾依哈圖牛錄驍騎校道喇喀依補放佐領,達斡爾布勒塔納依補放驍騎校,編入正白旗”。[8](P110)隨后,又將溫都爾罕牛錄改撥入鑲白旗,噶爾勒圖牛錄改撥入正紅旗,多爾凱牛錄(道喇喀依)改撥入正藍旗。對于這3個牛錄的駐防地,最初原計劃駐于黑龍江城,以調換當地的達斡爾牛錄,后因達斡爾人已在當地建房耕種,所以此3個牛錄最后改為移駐墨爾根城。
同年八月,清政府將齊齊哈爾附近的達斡爾人又一次進行編佐。這次編佐的原因,據當時齊齊哈爾等村的達斡爾佐領稱:“厄魯特、喀爾喀相互征伐,若眾巴爾呼等窮寇得知我等諸村散居而肆意侵擾,則欲保妻孥,亦非一時之所能收,且皇上之事,亦將難以適量采獲。據此,我等情愿披甲,于我等住地附近,擇一形勢之地筑城聚居。”[9](P26)可見,這次編佐主要是因為當時準噶爾部進攻喀爾喀蒙古,屬于喀爾喀車臣部的巴爾虎人舉族內遷,但在內遷過程中,與原居于嫩江流域的索倫達斡爾人發生了沖突,為避免雙方矛盾的激化,清政府遂將達斡爾人編旗設佐,更移駐地。另據《兵部為照準給達斡爾總管瑪布岱副都統銜事給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的咨文》稱:“由齊齊哈爾等各村達斡爾人中挑選一千丁披甲,駐于卜魁驛站地方新筑之城,由管理索倫總管瑪布岱統領。”[8](P182)此處所提到的“卜魁驛站地方新筑之城”即是齊齊哈爾城。這次編設的佐領數目,在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發給兵部的咨文中有如下記載:“現齊齊哈爾周圍村屯達斡爾等新編牛錄,阿爾濱等十六佐,佐領十六人,驍騎校十六人,一千名兵丁,伊等亦多用硬弓。故阿爾濱等十六佐官兵弓,依照先前編設牛錄貧窮索倫達達克圖等八佐官兵發行之例,請發給七力以上、十力以下之弓。”[8](P189)這里提到當時這部分達斡爾人共編設了16個牛錄。但查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的齊齊哈爾駐防佐領名錄,我們只發現有12個人的名字,那么是否是檔案記錄有誤?又見同一年博爾德城駐防官兵名單,又可發現有鑲黃旗達斡爾佐領郭爾必岱、正黃旗達斡爾佐領庫特內、正紅旗達斡爾佐領必勒格德依、鑲白旗達斡爾佐領波哩堪等4人之名。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戶部給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的咨文中曾提到遷移齊齊哈爾兩個牛錄的達斡爾人,前往墨爾根教習火槍。對于調派鳥槍兵赴墨爾根一事,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即以準備實行,當時計劃調錫伯和達斡爾500官兵前往,但由于此時錫伯人正在遷移途中,所以議定一年后再行調撥。關于此事,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的檔案中有如下記載:
為據墨爾根城稍近計,應將鑲黃旗波哩喀牛錄、正黃旗庫特內牛錄遷來,惟將鑲黃旗果爾比岱、波哩喀二牛錄皆往這邊遷移,則致波哩喀牛錄調換盔甲。據此,停波哩喀牛錄,將昆都勒德依牛錄移至墨爾根,或波哩喀、庫勒德勒特依皆系鑲黃旗,相應將昆都勒德依牛錄由鑲白旗退為鑲黃旗,互換波哩喀、昆都勒德依二牛錄盔甲,而后將波哩喀牛錄派來此處之處。[9](P53)
據此檔案,計劃將波哩喀或昆都勒德依牛錄調至墨爾根。但查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黑龍江將軍沙納海給奉天將軍的咨文,又可發現有“駐齊齊哈爾所屬博爾德城之鑲白旗波哩喀佐領”一語,[9](P151)既然博爾德城隸屬于齊齊哈爾,則無波哩喀牛錄遷移墨爾根,再移博爾德之事,可能的情況是此4牛錄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直接調駐博爾德城。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蒙古科爾沁部將所屬之錫伯、卦爾察、達斡爾人丁共計一萬四千四百五十八名全部“進獻”給清朝,其中可披甲之丁為一萬一千八百一十二名。這些錫伯等族人眾,最后被編為84個牛錄,分別駐防于齊齊哈爾、吉林烏喇、伯都訥三地,其中齊齊哈爾駐防共編設了24個牛錄。此次“進獻”的達斡爾人究竟有多少人,史料中并未明確記載,但可以確知的是,有一部分達斡爾人在齊齊哈爾城被編入了八旗駐防。當時,“將錫伯丁二千二百五十名,編為十五牛錄,達斡爾丁七百五十名,編為五牛錄”。[9](P54)但自從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以后,檔案中卻不見此5牛錄之蹤跡。趙志強和吳元豐先生認為,“當時,科爾沁所獻錫伯人官員較多,而達斡爾人內只有佐領2員,且年老不能勝任。因此,除錫伯牛錄外,達斡爾5個牛錄、以錫伯達斡爾丁合編的2個牛錄,其佐領均以錫伯人委任,統稱錫伯24牛錄。齊齊哈爾的錫伯族遷入盛京時,這部分達斡爾人也在其中,成為錫伯人了。”[10]然而,從檔案的記錄情況來看,事實卻并非如此。在齊齊哈爾所編20個牛錄中:
原先為官之錫伯副都統一員,參領三員,佐領二十一員,驍騎校十三員,典儀一員,三等侍衛三員。達斡爾僅有佐領二員,驍騎校五員,典儀一員,三等侍衛一員。察錫伯章京、驍騎校等榮華富貴之人,雖然丁少,但一族之中補放許多官員。窮族無體面之人,雖有丁六十、七十至百余名,但一官半職尚未補放。今若照部文,以其先為官,將一族之官四、五員悉數委用,則無官丁之族人實感不公。且于另族之牛錄,僅起用另族之官員,俾其管束,則難以管束。據此,計族人之多寡,視技藝諳練,善于管束,揀選議補者:原參領奇塔特、阿玉西、音達,原佐領孔揆、扎木素、們篤、鄂齊爾、巴爾呼勒岱、那彌岱、烏爾圖納斯圖、霍勒慧、布顏圖、德勒登、阿布喇勒、阿裕錫、巴扎爾,原驍騎校鄂欒岱,原侍衛額布根,原委章京格玫、閑散阿穆呼朗,請補放佐領。原佐領布延圖、扎嚕、納薩爾圖、阿爾善、正古特依,原驍騎校烏爾圖納蘇圖、鄂哩喀、阿哩渾、特古德依、巴尼、鄂磊、謨奇塔特、索倫泰,原侍衛阿蘭善、顧曼,閑散愛松阿、濟喇、必里格、查圖、巴西圖,請補放驍騎校。因丁少官浮而留之佐領戴吞、驍騎校納木西等人,請準注冊,嗣其族牛錄出缺,隨出隨用。[9](P54)
通過這份名單可以看出,達斡爾5個牛錄并未因原任佐領數目少而改以錫伯人委任,而是將原為佐領的布延圖等5人降為了驍騎校,將原為驍騎校的鄂欒岱等4人補放為佐領,以期達到以本族之官治本族之人的目地,而此鄂欒岱等4人可能即為達斡爾佐領。另外,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科爾沁“進獻”錫伯等族人之時,曾有部分人丁漏查,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這些人相繼被編入其親族所屬之牛錄。其中有郭爾羅斯扎薩克四等臺吉烏爾圖納蘇圖、鄂齊爾所屬阿哈泰佐領下的莽色家達斡爾丁濟蘭泰、霍濟泰及哈濟噶爾家達斡爾丁齊哷泰,因其三人之兄弟在巴札爾佐領下,故將此三人歸入巴札爾牛錄,前文所提的巴札爾牛錄未注明為何族。據此,巴札爾牛錄也應為齊齊哈爾達斡爾5個牛錄之一。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之后的檔案中將達斡爾5牛錄都歸入錫伯人當中。對此,日本學者楠木賢道認為,“這應該是當時清朝大大改變了‘錫伯’這一稱呼原有的含意,為了進行統治,將其作為民族的范疇重新進行了設定。”[11](P291)
三、余論
綜上,從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至康熙三十一年 (1692),清政府在黑龍江地區的達斡爾人中共編設牛錄44個,其中索倫牛錄12個,達斡爾牛錄32個,具體情況見下表:

時 間 駐防 地 牛錄 數康熙二十三年 黑龍江城 達斡爾牛錄8個康熙二十七年 墨爾根 索倫牛錄8個康熙二十九年 墨爾根 索倫牛錄3個,達斡爾牛錄1個康熙三十年 墨爾根 索倫牛錄1個。達斡爾牛錄2個康熙三十年 齊齊哈爾、博爾德 達斡爾牛錄16個 (駐防齊齊哈爾12,駐防博爾德4)康熙三十一年 齊齊哈爾 達斡爾牛錄5個
這里還有兩點需要說明,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黑龍江城的一個達斡爾牛錄與墨爾根的一個索倫牛錄曾互調駐防。從康熙三十八年 (1699年)開始,齊齊哈爾的5個達斡爾牛錄隨錫伯人一同遷至盛京地區。
這一時期,黑龍江城、墨爾根、齊齊哈爾三城的設置初步實現了清政府在黑龍江地區邊防體系的構建,索倫、達斡爾人陸續被編入八旗駐防,若按每牛錄50人計,大約有2200多人披甲當兵,極大地緩解了黑龍江地區兵源不足的狀況,也解決了部分貧窮索倫達斡爾人的生計問題,史稱“三城兵籍,達呼里居數之半”,[12](P204)便是這一情況的反映。同時,也為雍正十年(1732年)清政府在黑龍江地區再次編旗設佐提供了有效的經驗。
[1]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9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0.
[2]張 杰,張丹卉.清代東北邊疆的滿族[M].沈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5.
[3](清)馬 齊等.清圣祖實錄(卷22)[M].北京:中華書局,1986.
[4](清)鄂爾泰等.清太宗實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6.
[5](清)巴 泰等.清世祖實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6.
[6]劉小萌.清前期東北邊疆“徒民編旗”考查[A],滿族的社會與生活[C].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88.
[7](清)鄂爾泰等.八旗通志(初集)[M].長春: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85.
[8]達斡爾史料集編委會.達斡爾資料集(第九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9]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錫伯族檔案史料[M].沈陽:遼寧民族出版社,1989.
[10]趙志強,吳元豐.錫伯家廟碑文考[J].社會科學輯刊,1984(4):98-105.
[11](日)楠木賢道.駐防齊齊哈爾的錫伯佐領的編立過程[A].清代中國的若干問題[C].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1.
[12]方式濟.龍沙紀略[A].龍江三紀[C].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5.
〔責任編輯 趙立人〕
On the Dawoer Garrison in Heilongjiang Area during the Kangxi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KAN Kai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081)
In Kangxi period and Yongzheng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Dawoer,an ethnic group,was incorporated into the" Eight Banners"as garrison for twice,which greatly supplemented the forces in Heilongjiang area and exerted enormous influence to the defence system.From the year 1684 to 1692,the goverment arranged six movements in which ethnic groups,defence areas and officials changed a lot.
Suolun;Dawoer;the Kangxi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K249.2
A
1674-0882(2013)02-0011-06
2013-01-28
闞 凱(1978-),男,遼寧阜新人,在讀博士生,研究方向:清史及北方民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