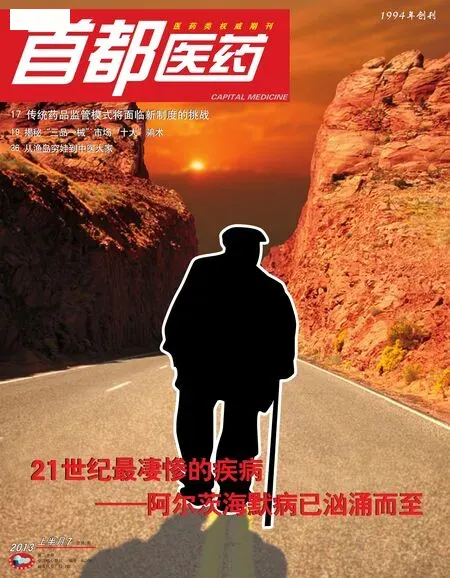走近阿爾茨海默病患者的世界

據不完全統計,我國的阿爾茨海默病患者已占到全世界患者的四分之一以上。在這樣一個沉重的比例下,龐大的患者群體以及他們的家人子女都在如何生活?阿爾茨海默病給患者自身以及他們的家屬,乃至整個社會都造成了哪些影響?為此,記者走訪了相關醫生、護士以及部分患者家屬,希望在與他們的交流中,將一個更直觀的阿爾茨海默病呈現給廣大讀者。
患者 令人心酸的“幸福”
在北京某知名三甲醫院,一位從事阿爾茨海默病治療多年的醫生向記者簡單描述了阿爾茨海默病患者的內心世界。“患者一旦出現了阿爾茨海默病的相關癥狀,他就不再有完整的自我了,隨著病情的發展,患者會慢慢失去部分記憶和意識。阿爾茨海默病也可以說是一個逐漸的‘自我喪失’的過程,有點像我們常說的‘返老還童’。在某種意義上講,患者本身是沒有什么痛苦的,甚至可以說是‘幸福’的。”這位醫生說道。“與阿爾茨海默病打了這么多年交道,眼看著病魔一點點‘抹去’患者的記憶,使他們或快或慢地走向木訥,與家人彼此陌生,而自己卻全然不知,作為醫生的我,也曾為此唏噓不已……”
在談及阿爾茨海默病對患者自身造成的影響時,這位醫生說起了他的一些親身經歷和體會:“在我收治的患者當中,有些人見到異性就脫褲子,甚至當眾手淫,這是一種本能的表現,與倫理道德無關。遇到這種情況,我覺得最好的辦法還是把患者領到無人的場合,任由他去做吧,癡呆患者本來就沒有什么生活樂趣了,對于他而言,這也許就是生命中的最后一點快樂了,我們又何必去剝奪它呢?只要不影響別人,就沒必要橫加干涉,更沒必要以‘品德敗壞’等言語刺激患者,這樣做毫無意義。”
家屬 撐著堅強的“無助”
“大概是從兩年前開始,我愛人出現了健忘、抑郁、情緒不穩等一系列癥狀,最開始也沒覺得不妥,以為只是更年期的問題,直到幾個月前,她開始不認人了,我才發現問題的嚴重。”一位來自武漢的患者家屬在北京天壇醫院神經內科病房的走廊上與記者聊了起來。“聽說北京治這個病效果好,我們就過來了。目前已經住院兩個星期了,每天就是固定的打針吃藥,也沒見有什么好轉。我也在網上查了,癡呆癥只能通過藥物盡量減緩病情的發展速度,并沒有什么藥可以有效治療,如果還是這樣,這周我可能就要辦出院手續回武漢了。”這位家屬說道。通過了解記者得知,患者剛滿60 歲,在阿爾茨海默病發病人群中算年齡偏低的。“我愛人出現輕微癡呆癥狀時,主要是變得不愛說話了,她常站在窗前望向大街發呆,像是在等著我和兒子回家,我們在家陪她時,她卻總是發脾氣。她以前是個非常開朗又要強的人,家務活從來都不讓我們父子倆做,在工作單位也是業務骨干,沒想到兩年時間就徹底變了一個人……”說到這里,這位身材魁梧的湖北漢子把頭轉向了另一側,避開了記者的目光。
在另外一位女性癡呆患者的床前,一位兩鬢斑白的老者正在為平躺著的老伴按摩。當記者說明來意后,老人向記者不停地搖擺著手臂,表示不愿意接受采訪。巧合的是,老兩口的兒子正好走進了病房,在看了一眼表情呆滯的母親后,他表示可以給記者五分鐘時間。
在簡短的采訪中,記者得知小伙子一家是山西人,孤身一人在北京打拼,父母在老家務農。作為家中惟一的孩子,當得知母親發病后,他就將父母一起接來北京,并為母親聯系醫院治療。今天也是下班后趕到醫院,準備接替陪護了母親一天一夜的父親。“其實真沒什么好說的。母親得了病,我這當兒子的就是責無旁貸的事,趕上這么個治不好的病,我跟父親只能坦然面對,積極治療。”當被問及目前母親的治療情況時,小伙子有些動容地說道:“住院后,病情好像發展得更快了,剛住了一個星期,母親就從一個還能有簡單交流,生活基本能自理的狀態變成了一個無法交流且生活完全依賴別人的人,我覺得并不是醫院的治療有什么問題,而是當初不應該把母親送到北京來。”小伙子接著說道:“突然換了環境,母親恐怕很難適應,如果這樣,還真不如我們父子回老家照顧她呢,老家的醫療條件比北京也差不了多少的,只是我的工作剛有些起色,就這樣放棄,有些可惜了……”
說起家屬與患者的關系,一位醫生向記者講起了她經歷的故事:“記得幾年前,我應患者家屬要求,參加了一次‘家庭會議’,會議的主題就是‘是否要將癡呆多年的老母親送到養老院’。患者家屬之所以希望我參加,一是因為我作為老人的主治醫生多年,對老人的病情非常了解;二是希望我從醫學的角度提出一些專業的建議,綜合評估一下老人目前的情況,送到養老院是否可行。本來是個挺好的事,可真到兒女們開始商量之時,這個會議就慢慢‘變了味’,大家從 ‘該不該送養老院’的討論,演變成了‘孝順與忤逆’的大辯論,爭得面紅耳赤。”醫生向記者介紹說,老人有三男一女,四個孩子,自從老人得了病,一直都是由小女兒照顧,其他兄弟三人按月交給妹妹一定數額的撫養費,直到半年前,長期腰疼的小妹查出了腰椎間盤突出,才找來哥哥們,提出輪流照顧老人的要求。當時,三兄弟還沒有什么照顧癡呆老人的經驗和思想準備,對于阿爾茨海默病須全天候看護,發病之后會打人罵人摔東西等情況始料不及,沒過幾個月,就開始叫苦連天,趕緊找來小妹和醫生,商量送養老院的事情。“我記得當時小妹說‘媽媽她三兒一女,最后卻被送進了養老院,你們不嫌丟人我還嫌丟人呢,這么多年我是怎么照顧過來的,怎么到你們那就不行了呢?!’說到此處,小妹泣不成聲。三個哥哥則表示在家照顧多有不便,養老院照顧老人比家人更有經驗等等,這事最后也沒有達成共識,反而讓兄妹之間傷了和氣。”
“在我收治的患者中,還有相當一部分曾受到過家庭暴力,老人身上都是一塊塊的淤青,非常可憐。”這位醫生分析說:“之所以這種情況比較典型,是因為阿爾茨海默病在初期階段的一些表象往往會被人所忽視,患者的種種反常行為會引發家庭矛盾,而作為家人,卻還沒有認識到這是病,導致與患者發生爭執,甚至家庭暴力。除此之外,還有一些長期照料癡呆患者的家屬或保姆,自己全心全意的付出往往得不到患者的認可與感激,反而會遭到猜忌甚至打罵,造成家庭氣氛緊張,自身精神壓力大,從而引發家庭暴力。”
“其實我認為,將癡呆病患者送到專門的治療及養老機構,并非是件壞事。這樣做不但可以讓患者得到更科學的治療,也同時拆除了家里的‘定時炸彈’,使家人的生活質量大幅提高,只是人們還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此外,中國人傳統的‘孝道’也在其中起了反作用,把老人送到養老院就是不孝嗎?我覺得不盡然,久病床前無孝子,在阿爾茨海默病患者的家庭中不是個例,而是通病。與其這樣,又何必苦守著所謂的‘孝’字不放呢?把老人‘囚’在家里,滿身青紫,你們又是在‘孝’給誰看呢?”
社會 無法卸下的“負擔”
關于癡呆患者對于社會的影響,在采訪中,很多醫生都認為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容易發生的問題就是走失,一旦發現不及時,后果往往很嚴重。一位醫生回憶道:“記得去年在貴州發生過一起老人離家走失事件,四個兒子找遍了老人可能去的任何地方,也發動了警察、親友,甚至在網絡上一起尋找。從他們調取的小區監控錄像上看,老人是向郊區方向走的,錄像也只記錄到了老人進入郊區之前。在最后一處錄下老人身影的地方及周邊,大家苦苦尋找無果。三天后,老人被發現凍死在了離市區幾十公里外的一處建筑工地的基坑內……”
天壇醫院神經內科的護士也提到了患者容易走失的問題:“那天早上有個護士帶著患者去做常規檢查,護士就是去趟洗手間的工夫,患者就消失了。當時那個護士一再叮囑患者站在原地別動,等她回來,前后最多兩分鐘,人就丟了。“當時我們找遍了醫院,也看了監控錄像,發現患者自行走出了醫院大門,我們一路追下去,卻沒發現任何線索,直到第二天凌晨兩點多,東單派出所的民警聯系到了醫院,才知道老人找到了。” 這位護士繼續說道:“患者當天其實是穿著病號服的,走了那么遠的路,也沒人注意到他,要不是深夜被好奇的路人發現,又正好趕上當時是夏天,氣溫還不算低,恐怕就真出大事了。”
“如果按照業內普遍認同的我國60歲組老年期癡呆患病率約為5%,一個癡呆癥患者平均每周的治療及用藥花費1000 元左右計算,每年全社會將為此增加4600 多億元的負擔。”一位醫生給記者算了這樣一筆賬。“有‘醫保’或工作單位,能報銷的患者還好一些,對于一些外地來京治療以及工薪收入的家庭來說,確實是一筆不小的開支。當然,醫保基金每年也在為這類患者及家庭分擔著巨大的壓力,占用著大量的醫療資源,政府還要投入大量的經費建設養老機構等等。這個病不同于其他疾病,雖不會直接危及生命,但卻無法治愈。如果把病情的發展比作一條向下延伸的坡路,各種治療手段也只是能將這個向下的坡度盡量減緩些而已。可是家屬卻往往不能理解,總認為花了那么多錢,結果還是看著老人每況愈下,感覺這錢花得冤啊。”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醫生表示,癡呆患者無法表達自己的想法,無法與家人溝通,生活需要有人照顧,家庭條件好些的可以請保姆,不然就要有人全天候陪在患者身邊,更何況還有好多家庭信不過保姆,認為只有家人照顧才放心,這無形之中就形成了“一拖一”甚至“一拖全家”的局面,為此,他也希望通過本刊呼吁盡快完善社會支持性服務體系,在政府的支持下,建立更多專業機構,培養更多專業護理人才,在給患者提供專業照顧的同時,“解救”患者家屬,讓他們重返工作崗位,為家庭增加收入,為社會創造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