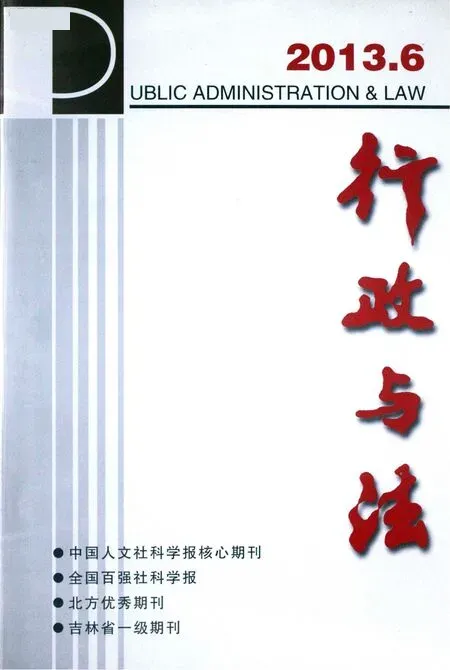鄉村治理模式變革與農村社會發展——以浙東DT村為例
□ 陳開炳
(中共浙江省臨海市委黨校,浙江 臨海 317000)
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至今,我國的鄉村治理模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即以改革開放為界,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開放以前主要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時期;80年代后是以村民自治為核心的“鄉政村治”時期。本文采用田野調查的方式,以農村為視角,探討了新中國成立后鄉村治理模式變革對農村社會發展的影響,并從中得到一些經驗和啟示。
DT村是浙東臨海所轄的一個自然村,2012年,DT村全村608戶,總人口1876人,黨員42人。村里有大小企業46家,2011年集體經濟收入1185.3萬元,人均收入13076萬元。該村近年來先后被評為臨海市經濟發展強村、臺州市級示范村、省級文明村等。DT村是一個主姓宗族村,劉氏占總戶數的70%以上,其他柯、陶、杜等姓氏接近30%,這些姓氏的戶數比較平均。從1949年至2011年換屆選舉完成,DT村先后產生過6位村書記,5位村主任(以前是生產大隊隊長)。
一
改革開放前,我國的鄉村治理主要采取的是以人民公社體制為載體的控制型治理模式。
農村的人民公社治理體制于1958年開始確立,此前有一個過渡時期,當時國家對農村實行的是區鄉制的管理模式,這一管理模式是在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后,在摧毀國民黨的鄉村保甲制度,對原有的農村基層政權組織進行改造的基礎上建立的。從1950年開始,新政權逐步建立起區鄉(行政村)制度。1950年12月頒布《鄉(行政村)人民代表會議組織通則》與《鄉(行政村)人民政府組織通則》后,鄉(行政村)政權組織很快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來。此時,全國有的省在縣以下設區、行政村、自然村三級,行政村相當于鄉,由若干個自然村組成;有的省在縣以下設區公所、鄉、村三級,區公所作為縣的派出機關,代表縣政府監督所屬的鄉、村。1954年9月,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頒布了《憲法》并制定了《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委員會組織法》,從法理上確認了我國農村的基層政權體制,由此縣鄉基層政權架構初步構建。
新政權成立后,立即對傳統的治理方式進行革命性的變革,以現代性的政黨組織作為鄉村治理的主要力量,以行政命令體制作為鄉村治理的主要手段,極力排除傳統文化在鄉村治理中的影響。將傳統的國家政權對鄉村的某種放任態度轉變為全面控制、全面滲透,這在鄉村治理上是千古未有之事。這種對傳統治理方式的革命性改造,有利于國家意志直接達至鄉村,但對執政者來說,因為要組建基層治理體制,需付出巨大的治理成本;對廣大的農民來說,壓制了他們作為小生產者自由經營的天性,使其創造力無從發揮。
由于我國新建立的政權是黨領導國家的政治體制,在各級行政機關中都建立了相應的黨組織,幾乎在每一個鄉村也都建立了附屬鄉鎮黨委的黨支部,開啟了中國特色的“政黨下鄉,黨組織進村”的歷史時代。所以,這時的中國鄉村治理實行的是雙重控制:以政府權力為載體的行政控制與以黨組織為載體的組織控制,基于我國實行的是黨政合一的一元化領導,故行政控制與組織控制能夠緊密地結合起來,實施對鄉村的治理。DT村在1949年解放后,立即進行了土地改革,按家庭土地財產狀況,劃分地主、富農、中農、貧農諸種成份。按土地占有多少劃分,當時DT村有11位地主,2位富農,村里對他們的土地重新進行了分配,使少地無地的貧農無償獲得了土地和其它生產資料。20世紀50年代后半期,國民經濟恢復后,我國進行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改造。在農村進行合作化運動,農民開展互助合作,成立互助組,合作化運動的最后結果是在農村建立了人民公社體制。1958年7月,中共中央發布《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對人民公社的建設進行了全面的規劃、設計,9月底基本實現了農村的集體化、公社化,全國共70多萬個高級農業合作社被合并成的2萬多個人民公社所取代。
隨著全國人民公社運動的不斷發展,1958年,DT村在建立高級社后迅速向集體化生產轉變,成立了生產大隊,受當時的大田人民公社領導,在生產大隊之下成立13個生產隊。人民公社的建立進一步強化了國家對農村的控制,農村生產完全服從于政府的安排,農村的自主經營被徹底消除。國家對農村經濟及諸種社會資源實行了全面的壟斷,社隊成了農民經濟生活的直接控制者。農民種植什么、種植的糧食如何分配由生產隊決定,人民公社的農民社員成了整個嚴密體系中的一個細胞,個人對社隊形成了嚴重的依賴關系,基層政權組織也成為人們唯一可以依賴的組織。人民公社確立的嚴密體制,使國家權力向農村社會得以全面滲透。農村社會自治空間極為狹小,上級黨政組織能以自己的意志安排村里的權力結構,用單一的行政手段實施對村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管理。此時的DT村書記、生產大隊長都由上級任命,這一現象一直延續到改革開放初期。人民公社體制增強了國家的動員能力,使其能夠很容易地組織村民進行集體性的工程建設,如在20世紀50年代末DT村民與其它村村民一道參與了修建大型水庫的工程。農戶個體的生產、生活也深受社隊的影響,如糧食的種植只能由社隊安排,家里的日用品如食鹽、白糖等也由生產隊分配,村民副業與手工業活動(如穿棕床)則被禁止。
據調研獲取的資料顯示,在村教育方面,村里有一所小學,學生讀書需交一定的學費,“文革”時學校停辦,“文革”結束恢復。在衛生保健方面,村設保健室,對工傷等簡單疾病可以醫治,一般的疾病需上醫院診治。在文化生活方面,由于當時沒有電燈、電視,在年底才有文藝表演;有時還要接受意識形態方面的教育,如學習毛澤東思想。偶爾也有電影放映,基本上是以革命題材為主。
總而言之,在人民公社體制時期,農村社會是國家權力直接控制下的一個組織單元,農村干部的組成、農業生產、教育文化等都受上級安排、指揮,農戶對社隊組織具有很大的依附性;村民的生產生活缺乏獨立性、自主性,精神文化生活簡單,這一代人所受的教育普遍較低,物質貧乏,人們普遍過著貧困的生活。
二
人民公社體制雖然強化了國家對農村的控制,保證了國家向農村汲取工業化所需的糧食等經濟資源,但人民公社體制混淆了政府組織與經濟組織的職能,將經濟組織運行政治化,侵犯了經濟組織的經營自主權,違反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同時又導致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問題的出現,權力集中的體制嚴重阻礙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人民公社體制使農村社會發展保持在封閉式的運行狀態上,但這是以強制性的制度規范來維持的,并未得到廣大農民的普遍認可,因而難以激發他們的生產積極性,國家為此付出了巨大的管理成本,但農村的生產效率并沒有得到明顯提高,廣大農民仍然生活在赤貧狀態。不少農村暗地里對集體化的生產方式進行調整,如私下承包、劃出自留地等。DT村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私下留出一點機動地,每戶約0.1畝,允許種些蔬菜。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改革開放的方針政策,我國開始了對農村治理方式的改革,這種改革始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即所謂 “承包到戶”。在不改變農村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改革農業生產方式,將土地承包給家庭耕種,變集體化的生產為以家庭為單位的個體生產,以家庭的自由經營取代整齊劃一的計劃生產。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從根本上動搖了原有的人民公社管理體制,原來的生產隊作為組織安排農村生產事務的功能不再必要,以集中控制為特點的鄉村治理模式失去了賴以存在的基礎,新的治理模式逐漸產生。
新型鄉村治理模式的確立需要有一個過程。首先是在經濟層面進行的調整,允許農民自由經營,除農業外還可經商辦廠。其次是村里的公共事務由村民自行組織,村民自治活動因之產生。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發出了《關于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通知要求將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鄉的規模一般以原有公社的管轄范圍為基礎,可以適當調整。同時要求按鄉建立鄉黨委,并根據生產的實際需要與群眾的意愿逐步建立經濟組織。到1983年底,全國超過12700個人民公社宣布解體。到1985年,全國剩下的249個人民公社自行解體,由91590個鄉鎮取而代之。至此,延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體制終于退出了鄉村治理的歷史舞臺。同時,為改變因原有的公社、大隊、生產隊體制解體而引起的農村公共事務管理真空的局面,以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為主要內容,農民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村民自治應運而生,村民自治在廣西自誕生后迅速在全國推開。截至1984年底,全國共建立了948628個村民委員會。至此,我國鄉村治理從改革開放前的集中控制模式轉變為相對寬松的“鄉政村治”模式。“鄉政”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具有高度的行政性和一定的集權性;“村治”則以村規民約、村民輿論為基礎,具有一定的自治性和民主性。“村治”相對于“鄉政”而言,“村治”是“鄉政”的基石。“鄉政村治”是現階段中國特色的農村政治。鄉政村治的治理方式,變原來黨政的雙重控制為“黨組織+村委會”的雙重治理,黨組織仍然受上級領導,村委會則越來越脫離上級意志的安排。在20世紀80年代乃至90年代初,許多農村的村主任由鄉鎮安排,新世紀以來,鄉鎮不再安排村委人選,完全由村民選舉產生。因為農村生產已不再像人民公社時期那樣由上級決定。
DT村在20世紀80年代建立村民委員會后,該村的村民自治經歷了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在1997年以前,村主任的人選由上級指派,從該年開始由村民投票選舉,村里事務由黨支部與村委會一道管理。因為農村種植水稻收入有限,村民大多外出打工經商,農民收入渠道的增多使農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新世紀以來,隨著大田撤鎮設為街道,被納入城區規劃,再加上經過大田的甬臺高速公路、34省道、75省道的建成,使DT村的區位優勢日益凸顯,該村迎來了新的發展良機。村兩委決定以出租標準廠房引進企業的形式發展集體經濟。目前,已建設出租標準廠房面積10.5萬平方米,引進中小企業40余家,村內餐飲、娛樂、運輸等輔助性服務行業隨之興起,村固定資產已達到1.5億元,村民人均收入由原來的千余元變為上萬元,許多村民住上套房、別墅。在文化生活方面,傳統宗族文化、民間信仰得到恢復。該村在1994年對劉姓宗族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修譜活動,并建立了劉姓祠堂。村里自行投資500萬元,興建了文化廣場、籃球場、文昌閣、文化長廊等設施;村里還組建了18支文藝隊伍,成立了骨牌鑼鼓傳習基地、大田板龍傳習基地,傳承板龍、骨牌鑼鼓、舞蹈等傳統民間文化。骨牌鑼鼓與大田板龍分別列入臺州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浙江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在民間道德方面,該村成立了孝敬文化教育會、社會公德推進會和新村民文化促進會等組織,開展促進家庭和睦、鄰里團結、知法守法的評比活動,倡導講科學、重文明的新風尚,使DT村成為當前臨海市新農村建設的一個范本。

DT村不同時期社會發展狀況對照
三
DT村半個多世紀的發展折射出我國鄉村治理模式變革給農村社會帶來的巨大變化。DT村從一個貧窮之村轉變為一個經濟富裕之村,農民生活從普遍貧困到共同富裕,從一個文化生活貧乏的農村到民間文藝組織興盛的現代新農村,從根本上說,是源于現代鄉村治理體制的變革。反思鄉村治理模式變革對農村社會發展的影響,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啟示:
第一,鄉村治理須以經濟社會的現實發展為基礎。國家實行鄉村治理的目的是為了使農村經濟社會走上有序發展的軌道,與國家其它方面的發展相協調,實現國家的發展戰略。但鄉村治理不能脫離鄉村經濟社會的現實發展,片面地采取強制性手段進行治理,這既違背現代民主政治的發展要求,也不符合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目標。在改革開放前的20多年,國家沒有正視農村生產力落后的社會實際情況,不尊重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將鄉村治理納入建設新制度、新社會的國家戰略之中,而這種新制度超越了我國作為農業國家的發展水平。在農村,政府以國家權力為后盾,以行政命令為手段,組織農村的社會生產,安排農村的社會生活,使農村社會的各個方面都在國家政權的操控之下,農村的文化生活、公共事務只能由上級組織的行政意志來決定,農民只能機械地執行上級意志,因而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得不到發揮,農村社會面貌長期得不到改變。
20世紀80年代農村土地承包到戶,國家在鄉村治理上根據農村社會的現實需要進行調整,并逐漸摸索出以村民自治為核心的新型治理模式。這種治理模式立足于人民公社解體后農村自主經營的實際狀況,從原來的以國家意志為中心轉向以農村的自我發展為中心,政權減少對農村社會的行政控制,使農村的自主發展得以展開,過去那種不適合農村發展實際的做法被徹底拋棄。這種治理方式得到了廣大農民的認同,適應并促進了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DT村村民的生活能夠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就得益于這種新型鄉村治理模式的確立。
第二,鄉村治理須在尊重農民意愿的基礎上發揮其創造力。改革前,鄉村治理主要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進行,單純從國家發展戰略的角度來確定鄉村治理的模式,忽視了農民的意愿與要求。在無法抗拒強大的國家權力的情況下,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無法得到發揮。這時的鄉村治理內容就是落實黨和政府的政策、計劃,實現國家意志。這種鄉村治理的后果是,將農村經濟社會發展限定在特定的狀態上,而這種狀態是停滯的,不是線性的上升運動。所以,在人民公社治理體制時期,我們看到的只是國家權力的空前膨脹,行政權威的急劇擴張。在這種體制下,農民不需要思考個人生產生活如何展開,因為這種體制已事先為他們作出了安排,他們只需服從、執行上級的命令,機械地實現國家的意志;在這種體制下,農民個人的創造精神沒有發揮的空間,農村社會缺乏活力,因而更談不上發展。改革開放后,鄉村治理模式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國家改變了原來集中控制的治理模式,取消人民公社體制,國家權力不斷地從農村領域退出,使農民的積極性、創造性有了發揮的可能。農民不再是被國家意志支配的機械的、被動力量,而是投身社會建設的有生力量,社會活力由此得到空前迸發,農民有了發揮創造力的機會,也使社會涌現出許多新生事物。從包產到戶,到村民自治,到鄉鎮企業……30多年改革進程中的許多成就都離不開農民創造力的發揮,可以說,農民成了現代改革的巨大推動力量,這一切都源于鄉村治理模式改變后所提供的廣闊社會空間。
第三,鄉村治理不應割裂歷史文化傳統。歷史的、文化的因素是鄉村治理最深刻的因素,尤其是幾千年歷史沉淀下來的習慣、傳統是確定鄉村治理模式的前提條件。我國歷史傳統是“王權止于縣政”。國家權力一般到達縣一級,在縣以下,由政府引導、組織鄉村賢達、士紳進行鄉村治理,對農村經濟社會的治理基本上采取一種放任的態度,這既可以減少因政府直接管理所帶來的巨大治理成本,也可以激發農村內部力量進行自我管理,實現國家治理的目標。歷史發展到20世紀,盡管我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傳統的農業文明被現代工業文明所滲透,以儒家精神主導的中華文明被西方文明所侵蝕,然而,現代中國向工業社會轉變是不可避免的歷史趨勢,在鄉村治理上也必然要求進行某種轉變,但歷史傳統的某些積極因素 (如重視儒家道德、民間自治)不應拋棄,某些有雙重影響因素的如民間宗教、宗族文化等應加以適當引導,發揮它們在鄉村治理中的作用。
DT村的經濟社會發展,在人民公社體制時期,也是在國家意志的壓力下維持在特定的狀態之中,歷經20多年沒有多大改變。同時,傳統的宗祠、信仰文化都受到了沖擊,村民被動接受意識形態方面的灌輸。黨組織與社隊組織是影響村民生活的最重要因素。20世紀80年代改革后,國家權力開始逐步退出,農村走向有限度的自治,歷史文化中的某些傳統因素也開始復蘇,比如宗族文化重新興起,該村在上個世紀90年代重建祠堂,進行了修譜。TD村占主導的劉姓宗族中的精英,彼此團結合作,繼承、發揚了宗族文化中鄰里互助、共振村落的良好傳統,該村的領頭人也頗有過去熱心公益的鄉賢作風。在該村,黨組織在一定程度上被宗族文化所溶解,它在村莊管理中更多的是具象征性的意義。值得反思的是,在村民自治的實踐中,我們更多的只是學習西方普遍選舉、民主競爭等形式上的東西,所謂的組團選舉被認為具有西方黨派競爭的色彩而被一些人津津樂道,而在實際上二者相差甚遠。在熟人社會的農村,競爭性選舉會使人將自己或家庭利益作為明目張膽的追求,完備的制度設計因熟人社會的制約而流于形式,一個弱勢的村民如何去監督強勢的村干部?雖有法律的途徑但不鬧到人命關天,一般村民都不會采用。當前,鄉村治理中的村民自治雖有積極的意義,但也必須看到,這種治理手段還沒有很好地將傳統文化中重視道德的因素發掘出來。DT村因有良好的宗族文化氛圍,加上村的領頭人懷有造福鄉民的情結,使得當前自治架構帶來的負面因素得以克服。在筆者看來,DT村的成功,更多地是在于當前鄉村治理轉為寬松之后,農民個人的創造力、傳統文化中某些積極因素得以發揚的結果。從中也可以看出,鄉村治理的完善、優化有賴于深入發掘傳統歷史文化中的積極因素。
[1]徐勇.鄉村治理與中國政治[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2]于建嶸.鄉鎮自治:根據和路徑——以20世紀鄉鎮體制變遷為視野[J].戰略與管理,2002,(06).
[3]賀雪峰.鄉村治理研究與村莊治理研究[J].地方財政研究,2007,(03).
[4]尹冬華.從管理到治理——中國地方治理現狀[M].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