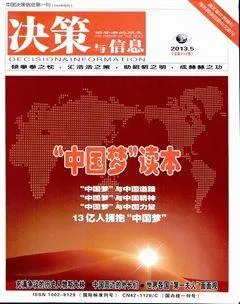誰為中國人未來養老?
張 銳
中國巨大的養老金“窟窿”被國內外媒體和研究機構不斷地抖落出來,外加人口老齡化所拉大的養老金缺口,國人未來養老難題一次又一次成為焦點。
巨大的養老金缺口
英國著名金融機構巴克萊集團最新研究報告指出,中國政府負債最高達50.44萬億元人民幣,最少也有32.24萬億元,而結合2012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為51.9萬億元計算,中國的政府性債務占GDP比重為62%至97%不等。同時巴克萊強調,由于中國養老金缺口的不明,未來將顯著影響中國的政府性債務水平。作為對巴克萊集團聲音的策應,《紐約時報》援引某研究機構的預測稱,未來20年內,中國的養老金缺口將累計至10.9萬億美元,這將導致未來中國老無所依。
稍早于巴克萊集團,世界銀行在一份研究報告中指出,如按照目前的制度及模式,到2075年間,中國養老保險的收支缺口將高達9.15萬億美元。與此同時,德意志銀行與中國銀行也分別獨立完成了對中國養老金財務風險的分析和估算。德銀的結論是,與GDP的規模比較,在不改革的情況下,養老金缺口到2020年將占GDP的0.2%,到2050年占GDP的5.5%;今后38年累積,養老金總缺口的現值(用名義GDP增長率作為折現率來計算)相當于目前GDP的75%;中銀則稱,到2013年,中國養老金的缺口將達到18.3萬億元。在目前養老制度不變的情況下,假設GDP年增長率為6%,到2033年時養老金缺口將達到68.2萬億元,占當年GDP的38.7%。
官方的判斷與研究機構的結論似乎存在著出入。據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公布的數據,中國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總收入為1.7萬億元,總支出為1.3萬億元,累計結存達1.9萬億元。因此,人社部認為,總體上說養老保險基金收入大于支出,不存在基金缺口問題。同一個命題,出現完全相反的判斷,主要在于研究機構所強調的是養老金的中長期缺口,而中國官方則著眼于當期的收支平衡以及目前財政條件下養老金發放所具備的足夠支撐力。
的確,算總賬,我國養老金整體上結余兩萬億元左右,由于我國養老金繳存實行地方政府統籌,因此,不排除部分省份出現支付缺口。據人社部公布的信息表明,目前我國有14個省份的養老金收不抵支,收支缺口達到了767億元新高,而且缺口規模還將擴大。同時,人保部預測,到2025年,僅中國城市養老金的缺口就達6萬億元,如果加上農村人口的養老金需求,其缺口無疑會更大。由此不難判斷,官方對養老金缺口未來的預期在方向上與民間機構的判斷是完全吻合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養老金存在地區性缺口的同時,我國養老金目前的整體儲備量還非常之低。以養老金占GDP之比比較,全球最高的是挪威,為83%左右,日本為25%,美國為15%,而中國僅約占2%左右。正是如此,據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國情調研項目報告披露的調查結果顯示,只有17%的人認為養老保險能夠完全滿足生活需要,而認為不能滿足的達到39.1%。
支付模式之痛
始于1990年代之初的中國城市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帶有著明顯的糾錯與還賬色彩。在社保制度推出之前,企業職工創造的大部分財富并未以基金形式積累,而是以資本的形式進入到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投資與生產過程,正是因為當年拿走了他們的“必要扣除”,而且這些被“扣除”的部分也沒有辦法返還,因此這一時期的員工退休后就不再單獨繳納養老金,而其所領取的養老金則由后來參保的新人所繳資金來補充。由此就產生了中國特有的養老金“現收現付”模式,也產生了現有企業員工養老金賬戶“空賬”的別致現象。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將這種現象譏諷為“最大的龐氏騙局”。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養老金發展2012》的報告顯示,中國城鎮基礎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空賬額已經突破2萬億元大關,達2.2156萬億元;而且近年來國家連續以每年10%左右的幅度提高養老金,使得國家財政只能優先為退休者發放養老金,而無法在短期內對“空賬”進行補充。現有在職職工在為體制轉軌和改革承擔了巨大歷史成本的同時,也使得未來自己的養老充滿了很大的不確定風險。
問題的關鍵在于,“現收現付”的養老金模式有效運轉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假設基礎之上的:勞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大大超過退休人員,繳納的社保收入超過需要支付的養老金。因此,“人口贍養比”即勞動年齡人口需要贍養的老年人數量的比率就成為決定一個國家養老金支付力量強弱的關鍵因子。從目前來看,我國人口贍養比穩定在3:1,即三個勞動者撫養一個老年人,因此可以勉強維持現有老年人養老金的正常支取。但是,伴隨著老齡化的逐步提高和退休職工的迅速增加,在生育率日漸下降的前提下,贍養比將出現降低甚至惡化趨勢,“現收現支”的模式必然難以為繼。
據國家人口計生委的研究報告,目前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達到1.85億,占總人口的13.7%,到2015年該數額將突破2億,老齡化人口將占到總人口的35%。另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中國財政政策報告》透露,到2030年,中國65歲以上人口占比將超過日本,成為全球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與老年人口增加相反照,我國少年兒童的人口占比因生育率的降低呈現出明顯的下滑態勢。據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從0~14歲少年人口占比來看,2010年我國為16.6%,相比2000年的22.89%下降了6.29個百分點,而2000年比1990年僅下降了4.8個百分點。為此,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預測,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從2015年開始將以366萬的年均速度遞減。
結果非常殘酷。據德意志銀行預測,到2050年,中國將變為約1個勞動力贍養1個老人。由于贍養比的大幅降低和人口替代率的下沉,新生勞動力的補給不足必然導致養老金增量供給的短缺。不僅如此,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研究報告,從1980年開始,中國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每五年上升約1歲,如此趨勢在未來幾十年內仍將持續,到2050年,中國的人均壽命很可能會達到82歲。如果按照目前的退休年齡和平均壽命預期計算,男女退休后的生存年限分別是22年和27年,粗略估計,領取養老金的老年人大軍在其退休后存活的歲月中所領取的全部養老金大約是其退休前所繳全部養老金的10~13倍。未來養老金的供給與需求壓力可見一斑。因此,德意志銀行測算,在未來38年內,人口因素帶來的中國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金累計缺口相當于2011年GDP的57%,人口因素帶來的機關事業單位養老金累計缺口相當于2011年GDP的14%。
當然,按照目前中國政府的慣性做法,一旦“現收現支”出現缺口時,中央財政會慷慨出手進行“補缺”。統計表明,從1997年起,中央財政對養老保險累計補貼金額達12526億元,這也就意味著,目前約1.95萬億元的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余有近三分之二來自于財政轉移支付。而且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公共財政收入117210億元,如此豐腴的財政對于目前僅700多億元的養老金缺口而言當然具備了足夠的“補缺”能量。但是,面對未來動輒高達數萬億乃至數十萬億元的養老金缺口,我國公共財政顯然無能為力。如果經濟不能持續增長,國人極有可能跌入老無所養的窘境之中。
尋找“補缺”的能量
充足的養老金供給保障不僅是一個國家經濟發達的體現,也是民眾生活質量優良的標尺,同時更是一個社會長治久安的“穩壓器”。自然,面對著日益擴大的養老金需求半徑以及不斷增大的養老金供給壓力,根本的出路就是擴開養老金的增量來源渠道,同時在存量上激發和放大養老金的增值功能。
延長退休年齡是不少學者從需求層面提出的應變性對策建議。這一建議的愿景是退休年齡的延長既可以增加在職人員養老金的繳付量,同時抑制養老金需求的過快增長。但據中國社科院的測算,我國退休年齡每延遲一年,養老統籌基金可增長40億元,減支160億元,每年減緩基金的缺口只有200億元,其對緩釋養老金支付壓力所起的作用只能是杯水車薪。不僅如此,由于人口基數比較大,中長期內我國仍面臨著巨大的就業壓力,而延長退休年齡將擠壓崗位供給,從而無益于勞動力市場的改善和就業人口的優化。更加重要的是,如果延長退休年齡從而帶來養老金的減支是以犧牲新增就業從而帶來養老金的增收為代價,這種政策安排不僅有急功近利之虞,而且得不償失。顯然,填補養老金的缺口還有待看得見的真金白銀。
除了可以適度提高繳費比例外,政府還能通過非財政性措施向養老金進行“輸血”。資料顯示,目前我國中央企業上交紅利比例是,除了煙草企業為20%之外,資源類央企是15%,一般競爭類央企是10%,軍工科研類央企是5%。如果按照國務院《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的最新定調,央企上繳紅利將普遍上調5%左右,相應地增加國資預算收入大約350億~500億元。盡管在政策取向上已經明確將該收入一部分用于社保等民生支出,但其所起的作用顯然是微乎其微。事實上,包括中央企業在內的我國國有企業每年實現利潤高達兩萬多億元,如果能夠將國有企業的上交紅利之比普遍提高至30%,并將該收益的20%用于補充養老金,每年可以實現的入庫存量就可達到1200多億元,養老金的支付壓力才能有實質性的減輕。
在加大國有企業紅利向養老金轉移力度的同時,向社保體系劃撥國有企業股權也應看作是一項有效的戰略安排。資料表明,目前中央和地方政府持有市值約12.2萬億元的上市國有企業的股份。其中,中央政府系統持有約9.7萬億股份,地方政府系統持有約2.4萬億元股份。作為試點,今后幾年內可以考慮將20%~30%的上市國有企業的股份劃撥到社保。國有企業股份劃撥到社保體系后,由社保繼續長期持有,這些股份的分紅將成為社保系統的一個重要的可持續的收入來源,同時社保也可以用套現收入投資于其他更有升值潛力的企業股份或其他資產。
體外“輸血”的同時還必須營造養老金自身的“造血”功能。目前,我國養老保險余額近2萬億元,但與企業年金4.1%的收益率和全國社保基金8.4%的平均年化收益率相比,過去10年間扣除通貨膨脹率的養老金年均收益率卻為負數。而據國家審計署的審計結果,目前養老保險基金結余有95.2%集中投資于銀行活期與定期存款。因此,拓寬養老金投資渠道,尋找新的市場受托人,以實現養老金的保值增值是管理層必須突破的瓶頸。從目前來看,除了廣東省宣布了將1000億元養老金委托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投資的政策取向外,其他地方政府養老金委托投資仍然處于僵持和觀望階段。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國家相關部門之間對此存在著非常大的意見分歧,受此影響,具有指導意義的宏觀層面養老金委托投資方案至今沒有出臺。因此,養老金獲取投資增值的真實能量還有賴于頂層設計和權威統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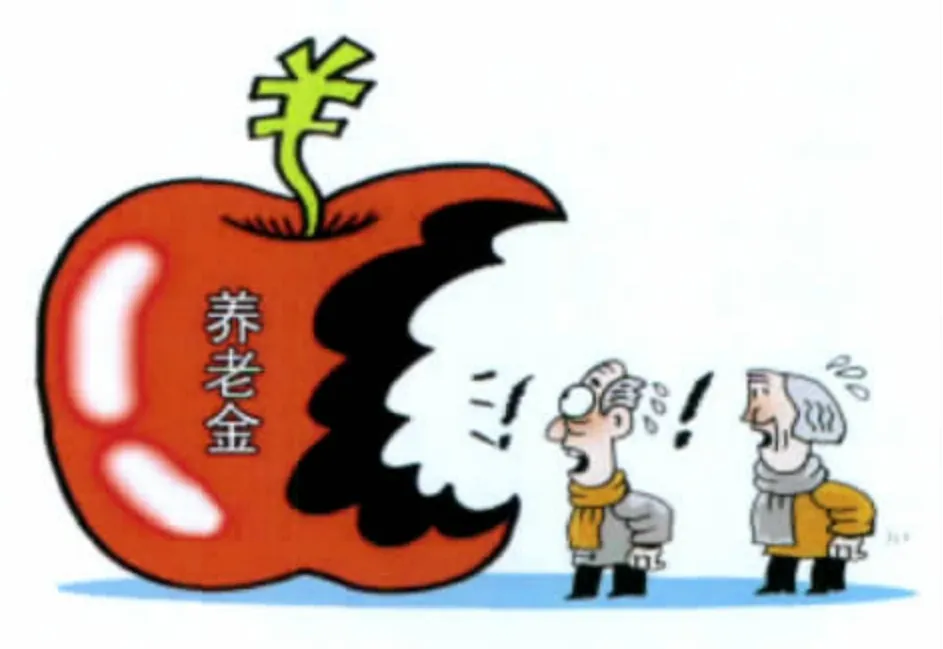
推動體制破局
撬動和壯大養老金對民眾安全保障的能量,除了做足和充實養老金賬戶之外,還可以通過體制變革營造資源再生機能,而變革空間的拓展既來源于政府管理行為的重構,也來源于市場層面的創新。
養老金“雙軌制”是一個被詬病多年的話題,這一話題所及的核心是:目前企業和職工必須同時繳納一定年限的養老保險費,而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在職時個人卻不用繳養老保險,退休后直接領取養老金。不僅如此,由于養老金的發放辦法不同,現階段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養老金高出城鎮退休職工養老金的1~3倍。因此,廢除養老金“雙軌制”,實現機關事業單位各項社會保險制度與企業的有效銜接已經成為一種非常強烈的社會呼聲。據人民網和人民日報日前所做的最新調查結果顯示,98%網民贊成廢除養老金“雙軌制”。

養老金管理的并軌除滿足了社會的公平訴求之外,還能夠強力彌補養老金的缺口。統計數據顯示,我國事業單位共有3000萬正式職工,全國公務員人數達702.1萬人,若按照企業職工養老保險政策規定繳納養老金,這個群體每年可以繳納上億元保險費,由于機關事業單位編制彈性較小,因此,到2050年積累下來的養老金可達38萬億元。作為試點,深圳已經邁開了機關單位養老保險改革的試點步伐,雖然改革仍局限于“增量”部分,即對新增公務員實行如同企業職工養老金繳納方案,但至少使人們看到了破局解題的希望。
與養老金“雙軌制”造成的保障結果不公平一樣,由于企業內部收入分配的嚴重失衡所引起的職工養老金取得之比也懸殊驚人。按照官方實際統計的平均結果,目前國企高管的收入超過一般員工的平均收入已經擴大至14倍,這其中還不包括一些高管所獲得的大量灰色收入。由于目前企業職工養老金調整增加額度按“本人養老金數額乘以相同的調整比例”計算,初次分配巨大差別必然使得薪酬越高的人養老增加的越多,相反增加的越少。據中國社科院發布的《2012社會保障綠皮書》和《中國社會保障收入再分配狀況調查》顯示出的最新結果,企業內部職工領取的養老金最低為200元,最高為10000元,二者相差50倍。同時調查結果顯示,有36.4%的人認為自己的養老金與周圍人相比不公平。因此,抑制高管過高的收入,并通過轉移支付的方式進一步充實到企業職工的養老金賬戶無疑是一項惠及民生的有益之舉。
解決養老金公平配置問題的同時,變革目前政府主導的公共養老體制繼而重塑新興的養老體系應當提到決策者的前臺。除了進一步完善以城鎮居民養老保險、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和新型農村養老保險為內容的基本養老制度外,還應該推廣企業年金制度。作為公共養老的補充,企業年金制度不僅能減輕我國養老儲備基金不足的壓力,還可實現儲蓄性養老向投資型養老轉變。資料顯示,目前我國企業年金參保人數僅占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的5%左右,基金規模占GDP比重僅為0.76%,大大低于全球38%的同類占比。年金計劃覆蓋面狹窄和步伐的滯后主要是稅收優惠激勵不足,因此,管理層有必要考慮在這方面大幅讓利于民。
●相關鏈接●
一、養老起源
養老起源于原始社會末期,夏商兩代繼承之,西周才在制度上臻于完善。《禮記·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養于鄉,六十養于國,七十養于學,達于諸侯。”這說明西周規定按年齡大小由地方或國家分別承擔養老責任,在政策上,不僅中央要負責養老,地方也要負責養老。凡年滿五十的則養于鄉遂之學,年滿六十的則養于國學中的小學,年滿七十的則養于國學中的大學。這種養老制度,自天子以達諸侯,都是相同的。不過一國的長老,由諸侯致養,若是天下的長老,則由天子致養。西周養老不僅鑒于老年人積累有豐富的知識經驗,更出于宗法的等級社會的需要:按長幼之序,定尊卑之禮。正如《王制》所說:“養耆老以致孝。”《禮記·鄉飲酒義》也說:“民知尊長養老而后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這就是西周重視養老制度的根本原因。
二、漢代養老
西漢初期,國家剛剛恢復安定,皇帝就頒布了養老詔令,凡80歲以上老人均可享受“養衰老、授幾杖,行糜粥飲食”的待遇。漢高祖詔曰,凡五十歲以上的子民,若人品好,又能帶領大家向善的,便可擔任“三老”職務,由鄉而縣,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盡免徭役,每年十月還賜予酒肉。漢文帝詔令:“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
到了成帝建始年間,又將享受這種法定待遇的老人最低年齡降到了70歲。每年秋天,由地方政府普查人口,對高齡老人進行登記造冊,舉行隆重的授杖儀式。如《后漢書·禮儀志》中記載:“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哺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尺,端以鳩飾。鳩者,不噎之烏也,欲老人不噎。”從這個記載來看,漢代的養老敬老,不僅務實,而且還有良好的健康祝愿。
據1959年在甘肅武威縣咀磨子18號漢墓內出土的一根鳩杖杖端系著的王杖詔書木簡,以及1981年在同一地點漢墓中出土的一份西漢王杖詔書令冊木簡記載,漢朝的養老敬老法規始終一致,沒有間斷過,而且每隔一段時間皇帝就要詔告天下。
最耐人尋味的是西漢詔書中明確寫道:“高年賜王杖(即前文中的玉杖),上有鳩,使百姓望見之,比于節。”“年七十以上杖王杖,比六百石,入官府不趨。”當時的“六百石”官職為衛工令、郡丞、小縣縣令,相當于現在的處級干部。那也就是說,漢代的七十歲老人在“政治”上享受處級待遇,持王杖進入官府不必趨俯,可以與當地的官員平起平坐。
漢代老人的“政治”待遇還體現在可以“行馳道旁道”。馳道是專為天子馳走車馬的,絕對禁止他人行走。即便是皇子,也不允許。可見漢代老人是何等特殊!
詔書還明確規定,各級官府嚴禁對高齡老人擅自征召、系拘,也不準辱罵、毆打,違者“應論棄市”。其中記載了汝南地區云陽白水亭長張熬毆辱了受王杖者,還拉他去修道路。這件事影響很大,太守判決不了,廷尉(相當于今天的最高法院院長)也難斷決,只好奏請皇帝定奪。皇帝說:“對照詔書,就該棄市。”張熬被判處死刑。今天看來不可思議。
也許是受漢代的影響,后來各朝各代對老人的待遇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逐漸形成了中華民族敬老養老的傳統美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便是金玉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