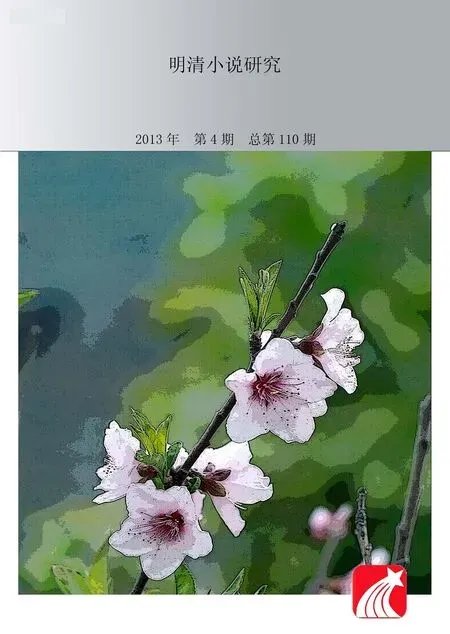清代瘟疫、夜游神民俗敘事的倫理意蘊
··
瘟疫和流行性疾病,嚴格說來雖不屬于自然災害,但卻屬于無可爭辯、恒久而普遍地危害人類安全與秩序的大災。何況,它往往由自然災害衍生而來,屬于自然災害的“次生災害”。對于瘟疫等的文獻載錄,限于醫學的發展局限和神秘思維的影響,可能有一些不確切的認識,但并不妨礙我們從文學倫理學角度加以探討,進而獲得有益于當代災害倫理體系建構的啟示。
一、瘟神、瘧鬼形象與特效藥敘事
小人、“二豎”,作為病魔的形象,早已出現在《左傳》中。而在明清兩代特別是清代人們的心目中,病魔形象,則變得豐富而具有多樣化趨向,蘊含著意味深遠的族群倫理觀念。
第一類是服飾古怪的童子。說蘇州李氏婦患瘧疾,昏亂中見一物如貓登其榻:“細視,乃一小童子,綠衣紅袴朱履,頭綰雙髻。向之笑,輒寒熱交作,至昏昏睡去,則不知何作矣。如是數夕,悟其為瘧鬼。欲驅之而無術也。一夕,甫登床,作退縮狀。婦返顧,見窗上有剖瓜刀一柄,因思必其所畏。次日,以刀置枕畔,果不敢近。婦取以擲之,物吱吱嗥叫而遁,自是病愈。”此描述當較直接地來自魏晉時代。《太平御覽》卷九二五引《錄異傳》稱宏老患瘧經年不愈:“后獨至田舍,瘧發,有數小兒,或騎公腹,或扶公手腳。公因陽瞑,忽起捉得小兒,遂化成黃鹢,余者皆走。公乃縛以還家,暮縣窗上,云明日當殺食之。比曉,失鹢處。公瘧遂斷。于時有得瘧者,但呼宏公,便瘧斷。”足見童子為病魔形象有一定普遍性,因醫學水平限制,古代兒童死亡率高,又得不到妥當安葬,童子化為病魔形象就成為群體愧疚心理的合理化想象,病由心生。
第二類是奇怪青衣人驅趕的鴨子。說步軍那木契冬夜見二青衣人驅鴨:“自是小兒多患痘疹,百無一生。那所見殆非無因也。蘭巖曰:鴨為兒厲,誠不可解。”敘事者突出冬夜驅鴨數百的怪異,與“自是小兒多患痘疹”的因果關系,見出清人關注疾病與家禽之間的必然聯系。
第三類是巨頭赤發金目模樣的瘟神形象。傳聞同治壬戌大疫流行,甲乙二人夜歸:“忽見燈燭輝煌,儀仗甚夥,數人舁一肩輿。輿中坐一人,頭巨如斗,赤發云擁,金目電飛,狀甚奇異。二人驚避道旁。眾紛紛,向西而去,殆疫神也。未幾,甲乙俱亡。”此類敘事是民間疫病傳說中各類神祇的常態。民眾所見只是瘟疫發生的慘狀,認為毫無憐憫之心的瘟神形象勢必兇惡。這當源于災害感知中無能為力的幻覺。
第四類是書生。范祖述《杭俗遺風·時序類》載,瘟神實為一位姓溫的應試讀書人,因舍身救濟蒼生而犧牲:“地祇元帥,封東嘉忠靖王,姓溫。傳說為前朝秀士,來省中應鄉試。寓中夜聞鬼言:‘下瘟藥于井中。’思有以救萬民,即以身投井。次日,人見之,撈起,渾身青紫,因知受毒。由是封神。五月十八誕辰,十六出會,名曰‘收瘟’,由來久矣。其井即在其東牌樓神座下,廟名旌德觀。”書生能“聞鬼言而以身試瘟”,行為簡單愚執些,卻挽救了當地百姓,獲封“瘟神”。與第三類相比較,書生瘟神屬于“收瘟”消疫之神,而非施放病疫的,頗可愛可親。畢竟民眾認為瘟神多屬慣于施災惡神型,喜看人類的眼淚和死亡,但還望能有一點同情心,留些人種給瘟神供奉香火,彼此都能獲益。“瘟神”的世俗化理想化傾向很明顯。
第五類是有“善行”的瘟神。清初平定西部叛亂時,即有痘神“顯靈”。董含《三岡續識略》卷上《痘神》載:“其地去京師遼遠,苦于無水……上一夕假寐,忽睹一神,身據甲胄,鞠躬拜跪曰:‘帝此行,必大捷,當鼓行而前矣。’俄見云旂露旆,橫戈躍馬者,充斥前后,不計其數。上問曰:‘爾何神?’曰:‘臣痘神也,特來護蹕。’擁眾去。上醒,甚喜,果大敗逆兵,因思神佑,遂加敕封。于是凡痘神廟俱行改建,塑冕旒像,丹□一新。”實際上,民俗敘事潛藏著一個爆發天花而部落滅絕的悲劇。準噶爾部落因一向缺少天花免疫力,抵御不了清兵帶來的天花病毒。而此段敘事回避了瘟疫的慘烈,將瘟神惡行轉化為助戰正義之師的善行傳說,這是典型的漢族中心主義口吻,將本無善惡的災害行為政治化倫理化了。《封神演義》第八十一回“子牙潼關遇痘神”也類似,討伐對象相反,轉換藝術敘事所展露的“痘神”正義感則一。
第六類是不明身份的“夜游神”。怪異的鬼神形象,可能與人不期而遇,吉兇卻不可一概而論。夜游神即然。如王某夜行見一數丈高巨人坐檐際,忽有人提燈籠而來,王亦欲隨之過,則巨人以足擋之,歸家后數日而亡。載錄者稱:“殆衰氣所感,鬼神揶揄之也。”某宦寓河北客舍,晚歸時也見到了巨人坐屋上,看自己所提之燈,光小如豆,然而歸后卻無恙。如果從醫學病理學角度看,后者顯然免疫力強;而前者則屬于亞健康狀態下被“時疾”感染。但從傳統倫理認為生死由上天決定,“天機不可泄露”,人們所見所聞常常就是征兆。敘事描述的“巨人”正是“夜游神”,見到者卻有不同結局,這明顯暗示著“夜游神”本身并無善惡利益歸屬,遭遇他的結果是由個體因素決定的。
瘟神瘧鬼形象描述的復雜多樣和敘事過程中的眾多不確定性,表明清人還未搞清楚瘟疫等惡疾的源頭,難以準確想象出瘟神瘧鬼的確切形象。應災的艱難困苦中民俗想象得以發揚,含混之中努力探尋瘟疫的生活真實。正如黑格爾對印度神話“采取了化身的形式或個體化的形式”的概括:“因為幾乎一切東西(神靈、著名的國王、婆羅門、瑜伽師、甚至動物)都被假定為(梵天的)化身,于是那似乎要規定自身為個體性的東西立刻就又消失在普遍性的云霧中了。”瘟疫等疾病與人類如影隨形歷史悠久,不能不令人困惑,以至杯弓蛇影地將其看作魔力無比的神靈,充滿希望地將人世倫理觀念投射到神靈形象中,探索解決途徑,緩解無時不在的精神壓力。至于如何及時療治,則不一而足。而醫藥經驗與神秘崇拜的綜合運用,則是抵御病魔來襲的相關傳聞內蘊。
首先,神秘使者送來靈藥。某日有長髯道士叩門求見祝宣臣,說來訪友。原來是呂純陽,他說:“此間一府四縣,夏間將有大疫,雞犬不留。我取葫蘆煉仙丹,救此方人,能行善者,以千金買藥備用,不特自活,兼可救世,立大功德。”因祝贈以千金,道士留藥十丸別去。道士所說的大瘟疫事實上并未真實發生,但敘事中提供了兩段重要的民俗記憶,一是恐怖的大瘟疫,二是仙丹靈驗。這種記憶在生活中可能隨時被喚醒,誘導人們為躲避瘟疫義無反顧地去獲取。
其次,有醫學經驗的博物者指示對抗傳染病的特效藥。李慶辰載楊青驛某場置碌碡一具:“有閩人指謂村人曰:‘此良藥也,宜寶藏之,數年后,此地當有大疫,研服可以活人。’村人均未之深信。壬戌歲,邑患霍亂,傳染輒死,巫醫僉窮于術,或取碌碡研而試之,奇效。于是全活甚夥。”敘事中的“閩人”生活在古人所謂蠻荒之地,對“霍亂”一類胃腸傳染病當不陌生,驛院“碌碡”的構成成分能有效治療霍亂,此應為經驗之談。相反,如不及時采取預防措施,真可能釀成悲劇。這牽涉到對于瘟疫嚴重性認識的問題,所謂“不可全信,又不可不信”。說“道光辛巳(1821)春夏間,瘟疫流行,始自閩、粵、江、廣,日遷于北。七月望后,京中大疫,日死者以千百數。其疾始覺脛痛,繼而遍體麻木,不逾時即死。治者以針刺舌腭逮紫血出,再服藿香正氣丸,始得無恙。然死者率多里巷小民,士大夫罕有染者。惟刑部侍郎覺羅承光,年逾六十,身素強健。清晨入署,聞有談是疾者,力斥其妄。逾時覺不爽,即乘輿歸,及抵家,已卒矣”。敘事以“京中”為例展示遭遇瘟疫的可怕情景,“日死者以千百數”,死亡人數多,速度快。有的人可治,有的人不可治。最重要的是敘事者發現:死者主要是“里巷小民”,而“士大夫罕有染者”。瘟疫除了有善惡之辨,似乎又有明顯的族群尊卑觀念。我們知道,瘟疫疾病本不存在善惡尊卑倫理觀念的,導致“小民”死得多,“士大夫”死得少,原因是尊卑者各自的生存環境。敘事者之所以流露出如是倫理思想,主要由于歷史上發生過的大瘟疫均以無數生靈死亡作結,救治者和統治者幾乎都無可奈何。驚人相似的瘟疫流布狀況描述,暗示某種神秘因素起主導作用。
其三,幸運的錯服藥。那些具有意外療效的特效藥,顯身往往在不經意之中。《客窗閑話·朮芷治痘》寫鄉人黃大患痘瘡,請醫生開藥方,鄰翁代買,因藥鋪伙計將兩包藥簽插反,導致黃大所服,藥效相反,黃大病竟被治好。后經名醫指點,得知確系庸醫誤用藥方,若黃大服用醫生藥方,必定被治死。竟出其不意地被不對癥的藥方治愈,由此生發“幸運”母題,帶有深刻寓意。《三異筆談》還載“驚嚇療痘”妙方。名醫秦景明授意僮仆調戲某女,女驚,原來:“是將出痘,然毒伏于腎,見點復隱,則不可藥。吾固驚之,俾毒提于肝,乃可著手。”他還用掘坑噴藥療救患痘疹小兒,一些患者的幸運常被談起,暗示民眾對有效遏止災疫的向往。
可見從醫學角度講,醫生的方藥對時疫有一定抑制作用,遭癘疫而幸運的獲救者大有人在。瘟疫敘事反復演繹“為善者幸運獲救”的道德故事,有效地將族群倫理與災害倫理結合,建構“善”的生態倫理體系應對災害。而從另一角度看,直到清代,“瘟疫”還沒有特效藥,而從加繆《鼠疫》來看,即使20世紀40年代仍無療瘟特效藥。如果完全依靠醫藥幾乎很難及時全面解救瘟疫肆虐下的民眾生命。
二、避災、驅疫鬼與送瘟神敘事
在瘟疫魔力日見膨脹又無法短時間內有效遏制時,民眾多采取哪些方式驅避瘟神呢?弗雷澤認為,在巫術中,人類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迎接所遇到的一切困難和危險,他確信在力所能及處建立起某種秩序,確信他能操縱自己的目的,而當他發現自己這一錯誤的想法,當他沉重地認識到他所設想的并想加以控制的自然秩序僅僅是一些幻想時,他就停止了自己的智力和獨立思考,而謙恭地聽命于某種不可見的隱藏于自然帷幕后面的巨大神靈的擺布。他還注意到民間宗教鬧劇的價值,其構成一是戲謔的哄鬧,二是假裝與化裝。如中國人送瘟神儀式:“常挑選身強力壯的男人充當替罪者。此人臉上涂抹著油彩,做著各種令人可笑的動作,意思是要誘使一切瘟疫邪惡都附集在他一人身上去。最后男男女女敲鑼打鼓,追逐他,飛快地把他趕出鎮外或村外。”而毗鄰印度:“旁遮普有個治牛瘟的辦法,是從卡馬種姓里雇一個人,讓他的臉背著村子,用燒紅的鐮刀給他烙印,然后叫他一直往林莽里走去,不許回頭看,這樣把牛瘟帶走。”瘟神替身是古代中國造神運動產物,一個被人們供奉尊崇收買的瘟神形象,為當地人們帶走可能在本地流行的瘟疫。
根據疫鬼行蹤與規律,御災防患于未然,是人們的理想期盼。說嘉慶十年(1805)某人在四川中壩為官,聞訊查考街上某處彈有墨線痕,其他城市皆同日彈有墨線,“不知何異”,而至立夏后,民間疫病大作:

在“路遇鬼吏”母題框架中展開敘事,也寫出了禳除方式:徐刺史根據瘟神“看龍燈方回”的夢中話語,決定以五月朔為元旦,“大張燈火”折騰,疫果止。這一禳災儀式中,民眾、僧道、官員通力合作,關鍵在于徐刺史及時破解了“行疫使者”的話語密碼,掌握了瘟神行蹤。看來與瘟疫交往除了民眾要有強壯身體,還需聰明肯干的官員運作,突出了救災過程中決策的重要,印證了驅“瘟神”功效在官民合作。



三、好義救災葬尸與染疫倫理歸因
瘟疫發生時禳災祈禱作用到底有多大?《封神演義》第八十回寫瘟神呂岳在穿云關以二十一把瘟癀傘,擺下瘟癀陣:“……遠觀是飛砂走石,近看如霧卷云騰;瘟癀氣陣陣飛來,水火扇翩翩亂舉。瘟癀陣內神仙怕,正應姜公百日災。”致周營官兵損傷慘重。云中子御瘟禳災,是符印與丹藥并用,卻并不能有效驅瘟。而最終破除瘟疫的是道德真君弟子楊任,用真君的“五火神焰扇”將瘟神及幫兇全部焚燒成灰,才解西周大軍瘟疫之厄。在此,敘事者反復強調瘟疫可怖的殺傷力和難以驅除。將帥的英勇戰斗不能損傷“瘟神”分毫,而僅用神扇輕扇幾扇,瘟神即刻煙消霧散。神力也有人力助,配合楊任正直諫臣的輔佐,最終才消滅了邪惡的瘟神。那么清代民眾對瘟疫又是怎樣的認識呢?




由上可見,清代瘟疫敘事的互文性特點表明,人們對瘟疫惡疾等有歷史性體驗與情感關懷。豐富多樣的病魔形象是人們不斷體察與思考的藝術化生成。雖關注并祈求各路神靈禳除“瘟神”病魔,也并未忽視人類自救努力。對瘟疫惡疾的倫理化探索與印證,期望藉此有效地改善澆薄世風。對“瘟神”越來越全面的認識與根除無望的沮喪悲嘆,或許會令人更聰明地學會與“瘟神”相處,更巧妙地處理人與外在環境關系,而這正是當代災害倫理學思考的又一問題。
注
:①③④⑦ [清]李慶辰《醉茶志怪》,齊魯書社1988年版,第266、119、259-260、114頁。
② [清]和邦額《夜譚隨錄》卷六《那步軍》,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04頁。
⑤ [德]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一卷,賀麟、王太慶譯,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33頁。

⑧ [清]昭梿《嘯亭雜錄》續錄卷四《瘟疫》,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309頁。
⑨ [清]許仲元《三異筆談》卷四《秦景明》),重慶出版社2005年版,第301-302頁。











*本文系遼寧省社科規劃基金項目“還珠樓主重構外來倫理思想研究”(項目編號:L12DWW008)階段性成果;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項目“清代災荒敘事與御災民俗想象研究”(項目編號:20100480227)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