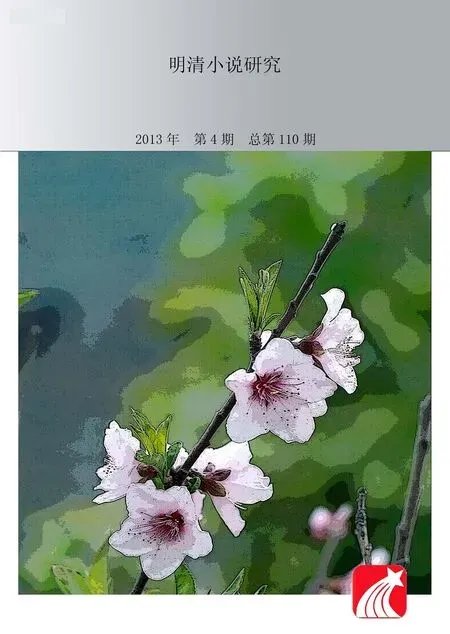詩書畫一體與中國古代文言小說敘事藝術(shù)
——以李昌祺《芙蓉屏記》為中心
··
一、問題的提出

2.如何研究?筆者以為,如上所提問題,絕非以邏輯方式在理論層面推導即可獲得解決。因為,當初古代文人創(chuàng)作小說,是從自我藝術(shù)感覺出發(fā),逐步摸索和實踐,而不是首先理清中國繪畫藝術(shù)特性,再搞清作為一體的詩書畫如何進入小說合乎小說藝術(shù)的特性才寫作的。解決此問題的實質(zhì)是對古代文人藝術(shù)實踐及經(jīng)驗的總結(jié)。即應該回到中國古代這類藝術(shù)現(xiàn)象去總結(jié)。到哪里去找這樣現(xiàn)象?這涉及到兩個現(xiàn)象,一是詩書畫何時出現(xiàn)?二是詩書畫何時開始進入小說?
關(guān)于第一個現(xiàn)象,程抱一教授認為,繪畫中出現(xiàn)詩歌不是發(fā)生在繪畫產(chǎn)生之初。宋代以前的畫上很少題字,雖有題畫詩卻不是寫在畫面上。“宋代開始了中國繪畫的真正的黃金時代”。創(chuàng)立于宋初的畫院,使得畫家們得以悠閑自在地深化古人遺留下來的技巧,拓展他們靈感的主題領(lǐng)域。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畫院的邊緣,誕生了由文人學士,也即非職業(yè)畫家從事的繪畫。這些藝術(shù)家,通常都是杰出的書法家,在某些體裁方面揮灑自如,尤其是歸入‘植物花卉’(竹、蘭、梅等)門類的主題——因為這個領(lǐng)域所要求的技巧憑借某種筆法,而這種筆法常常與書寫十分接近。他們最初的意旨不在于成就‘偉大的藝術(shù)’,而在于通過借助大自然的形象,表達一種心靈狀態(tài)、一種精神意趣,以及最終,一種生存方式”。這個傾向的代表性人物是蘇東坡、米芾、黃庭堅等。是他們“使人們最終接受了中國繪畫中如此特別的做法:在作畫的空白空間題寫詩文。這一做法最初的意圖在于使繪畫變成一種更‘完整’的藝術(shù),在這樣的藝術(shù)中結(jié)合了意象的造型性和詩句的音樂性,也即,更加深邃地結(jié)合了空間和時間維度”。到了元、明、清,隨著文人畫的發(fā)展、勃興,詩、書、畫就像孿生姐妹一樣,形影不離地一起出現(xiàn)了。這三者的結(jié)合,豐富了中國畫的形式,使之更有特點。其意義不僅是誕生一種合成性的藝術(shù)形式,更在于生成了獨特的合成性藝術(shù)觀念。
關(guān)于第二個現(xiàn)象,即詩書畫進入小說的時間,筆者以為,尋找和確定的邏輯應在宋以后的文人小說。只有成熟的詩書畫一體空間藝術(shù)現(xiàn)象,才有它進入小說的可能和如何進入的問題。那么,為什么到文人寫作的文言小說中去找?學界已經(jīng)獲得共識:中國文言小說從最初產(chǎn)生,即確定了訴諸于文人案頭閱讀的方式。從文言小說成熟表現(xiàn)的唐傳奇開始,一直到明清文人文言小說,不僅文字瑰麗華美,想象飛揚豐富,而且故事的營造和敘事結(jié)構(gòu)也更復雜,融入更多人文性思考。這些特點是容納詩書畫一體進入的條件。
藉此,筆者提出在宋以后的明清文言小說中尋找和研究詩書畫如何進入小說問題。即在此范圍內(nèi)找到藝術(shù)效果好的優(yōu)秀作品,分析其成功經(jīng)驗,以之為總結(jié)之基礎(chǔ)。個案性研究方式就此確定。
3.選取明代文人李昌祺的文言小說《剪燈余話》中的《芙蓉屏記》的理由。
筆者選取明代文人李昌祺的文言小說《剪燈余話》中的《芙蓉屏記》。

李昌祺精通于繪畫,是筆者選擇其《剪燈余話》的另一個原因。據(jù)記載,李昌祺喜好和善于寫作詩詞,他有詩集《運甓漫稿》和《容膝軒草》、詞曲《僑菴詩余》一卷等。現(xiàn)今只可見到《運甓漫稿》和小說集《剪燈余話》,其余作品收錄何處,不得而知。明代徐伯齡在《蟫精雋》卷十三所錄《錄運甓要》中說:“廬陵李昌祺先生名禎,以永樂甲申進士,歷官至廣西左布政使,工詩文,尤精畫。所著有《運甓漫錄》《剪燈余話》等集。學博而才富,識高而指遠。姑錄其詩詞數(shù)章,可以見其胸中矣。”《運甓漫稿》詩集共七卷。每卷收錄詩體不同。其“內(nèi)容大部分都是題畫題景、贈別悼亡、應制稱頌、祝賀壽喜之作詩。”可以推想,他在寫作小說時,會滲透對繪畫的喜愛,也會自覺不自覺地將繪畫元素和方式帶入小說。
《剪燈余話》收有21篇作品,以內(nèi)容可分愛情故事、靈怪故事兩大類,兩者互相有所交織。從詩書畫一體進入小說的角度看,特點最突出的是《芙蓉屏記》。筆者以此為個案分析研究。
二、《芙蓉屏記》的詩書畫一體以及如何進入小說?
1.《芙蓉屏記》故事梗概與淺層結(jié)構(gòu)。
崔英攜妻王氏赴任。舟主心生歹念謀害崔英夫婦。“沉英水中,并婢仆殺之”。因船主謀劃將王氏給小兒子做夫人而得以留下性命。“王氏佯應之,勉為經(jīng)理,曲盡殷勤”,后王氏趁主家不備,逃至一尼姑庵避難。一日于庵中忽見舟中失物芙蓉屏,“王過見之,識為英筆,因詢所自”,“即默識之。乃援筆題于屏上曰:……其詞蓋《臨江仙》也”。郭慶春到庵中辦事,“悅其精致,買歸為清玩”,正值御史大夫高公納麟退居姑蘇,郭便將芙蓉圖獻給高納麟,“慶春以屏獻之,公置于內(nèi)館”。恰巧,崔英賣字于高府,“英忽見屏間芙蓉,泫然垂淚”,高公得知崔英遭遇,又向郭慶春打探王氏下落,遂萌生促使崔英夫妻破鏡重圓之念頭。高公設(shè)計讓王氏來府上教習夫人佛經(jīng),然后在崔英即將赴任前讓夫妻二人重逢。實現(xiàn)了王氏題詩中“今生緣已斷,愿結(jié)再生緣”的愿望。故事以皆大歡喜結(jié)局。故事情節(jié)的淺層結(jié)構(gòu)為:遇難——分離——流落——受幫助——報仇——團聚。
2.詩書畫一體如何成為小說深層結(jié)構(gòu)?

3.詩書畫一體的芙蓉屏進入小說的藝術(shù)效應如何?


第三,芙蓉屏合成過程有助于塑造人物形象,展示人物心理世界。芙蓉屏合成中王氏題寫的《臨江仙》,究其實是加進了敘事因素,其內(nèi)容歸屬于具體的有著既往夫婦感情的歷史,是時間性的,自然也就加進去不少信息。“今日風流張敞筆,寫生不數(shù)黃筌,芙蓉畫出最鮮妍。豈知嬌艷色,翻抱生死冤!粉繪凄涼疑幻質(zhì),只今留落誰憐!素屏寂寞伴枯禪。今生緣已斷,愿結(jié)再生緣。”可見這是一對才子佳人,他們具備深厚的文化素養(yǎng),精于繪畫、通曉詩律,并且互敬互愛。此時,王氏只身流落尼庵無所寄托之時,丈夫所描畫的芙蓉畫陰差陽錯的來到她面前,心中的郁悶與對丈夫濃厚的思戀之情涌上心頭,她以自己特有方式將之抒發(fā)出來。王氏的題詞既為情節(jié),更是心理深度的展示。這首詩與畫面上嬌艷的芙蓉相互映襯,一種自憐自哀、斬不斷理還亂的情思透過紙背散發(fā)出一種凄涼之美、和諧之美,將人物內(nèi)心隱秘的感情呈現(xiàn)出來,而這夫妻之間的深情、王氏坎坷卻堅強的命途,恰是貫穿文章全篇的深層情緒。除了崔英夫婦之外,芙蓉屏合成過程也有助于高公的形象塑造。高公善良與公正、智慧與沉穩(wěn)的品性也借此展示。
三、由《芙蓉屏記》分析可能得出的幾點思考
如上《芙蓉屏記》藝術(shù)效果以及藝術(shù)價值形成機制的分析,業(yè)已顯示出《芙蓉屏記》詩書畫一體的元素和方式進入小說,積累了比較成功的經(jīng)驗。文學創(chuàng)作總是獨特的,詩書畫元素進入小說,每每有自己的方式。通過窮盡所有詩書畫進入小說類文本再行概括,在實際操作中不可行。筆者以為,創(chuàng)造性各有特異,既定的藝術(shù)效果和優(yōu)秀品質(zhì)卻有相通之處。可借助于《芙蓉屏記》分析,展開基本理論的討論。由此引發(fā)的詩書畫進入小說的思考路徑如下:首先,明確繪畫語言和小說語言各自具有怎樣的特性。其次,以小說語言基本特性和要求為基點,探索應如何處理繪畫語言和小說語言之間關(guān)系,其基本關(guān)系的原則是什么。再其次,在遵循基本原則前提下,可能有哪些方面進入。



2.其次,以小說語言基本特性和要求為基點,探索應如何處理繪畫語言和小說語言之間關(guān)系,其基本關(guān)系的原則是什么。
從前面對《芙蓉屏記》藝術(shù)效果分析中,我們已經(jīng)可以看到,它的成功是小說的成功,而不是繪畫或者詩書畫一體的成功,也就是我們依然是用小說成功的標準來衡量《芙蓉屏記》的。這是從藝術(shù)效果事實的角度推導基本關(guān)系的原則。從作家角度看,當作家以小說名之自己操持的文體時,他在潛意識中即與此文達成了默契:他將遵循該文體的特點和要求寫作。即便有其他文體乃至藝術(shù)形式因素進入小說,那也是為了小說,而不是為了其他文體乃至其他藝術(shù)形式,是為了讓小說更像小說,更有藝術(shù)魅力。

3.《芙蓉屏記》將繪畫語言納入小說語言的理論總結(jié)。
《芙蓉屏記》詩書畫一體的元素和方式進入小說,從較好的藝術(shù)效果看,確為比較成功的作品。筆者借用蘇軾的“隨物賦形”對其作總的概括。筆者在此用“隨物賦形”意思是,作家對小說藝術(shù)特性和繪畫藝術(shù)特性均有深入體認,審美主體對于審美對象(包括小說和繪畫藝術(shù))充盈自足的觀照,達到了自由書寫狀態(tài):總能發(fā)于心靈內(nèi)境,觸及到外物的小說之時,能隨物賦形應接自如,并借助于繪畫等其他因素,合于小說特性地納入小說之軌道。繪畫語言水乳交融地融入了小說語言。

注
:① 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zhuǎn)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23頁。
② 如程抱一就有《中國詩語言研究》(1977)、《虛與實:中國畫語言研究》(1991)。
③ 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zhuǎn)變》多處涉及此問題。


⑥ [明]李昌祺《剪燈余話·自序》,[明]瞿佑等著《剪燈新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122頁。
⑦ 皋于厚《〈剪燈二話〉與明代傳奇小說的發(fā)展趨勢》,《明清小說研究》2001年第4期。
⑧ [明]徐伯齡《蟫精雋》,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867冊,第157頁。
⑨ 謝雅琴《從〈運甓漫稿〉反觀李昌祺〈剪燈余話〉的創(chuàng)作思想》,《浙江教育學院學報》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