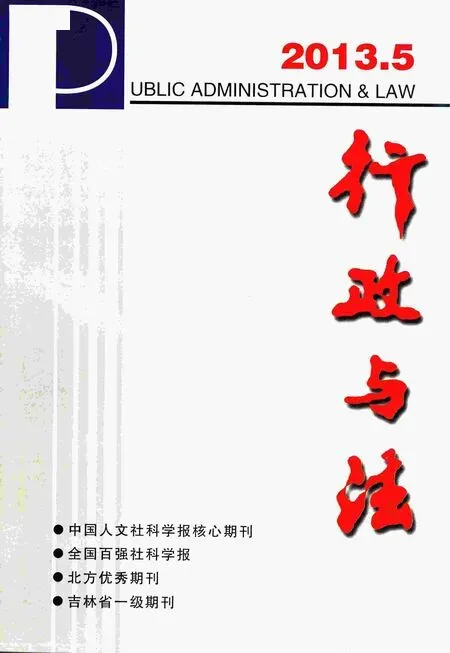論勞動規章制度集體協商——以杭州市工資集體協商為視角
□ 徐金鋒,李燕燕
(浙江農林大學,浙江 杭州 311300)
推行勞動規章制度集體協商,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機制,是貫徹落實“十二五”規劃綱要關于“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的要求,有利于市場機制調節、企業自主分配、職工民主參與;有利于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形成勞動分配激勵機制,理順企業分配關系,提升企業管理水平,增強企業核心競爭力,使職工能分享到企業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成果,促進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重要舉措。隨著經濟的轉型升級,社會勞資矛盾日益凸顯,并引發了如本田罷工等一系列事件。同時,筆者曾對康太炒貨等杭州市10家農產品企業做過調研,發現此類企業在涉及到勞動者切身利益的規章制度時仍存在不少問題,尤其是在諸如工資、福利待遇等事項的約定方面,缺乏勞動者意志參與。為此,構建勞動規章集體協商制度十分必要。
一、勞動規章制度集體協商的依據
(一)理論依據
就勞動規章制度(又稱工作規則)法律定性而言,存有多種不同學說,“法規說”認為勞動規章對勞動者的拘束力來自其作為社會法規的“制度性格”,可以不考慮勞工的真實意愿,僅僅因為勞動規章制度在事實上已經具備了強大的拘束力,故而其具有法律規范的性質。“契約說”則認為,勞動規章制度系由雇主單方制定或變更,本來只是一種單純的社會規范,嗣后經勞工之同意,成為勞動契約之內容,而得以規定勞工或勞動關系。集體合意說認為,勞動規章制度是介于“法規說”與“契約說”之間的折衷說,認為勞動條件應由勞資雙方合意共決,非經集體合意不得對勞動者產生效力,亦非單獨獲得勞工同意后生效,此說在一定程度上承認雇主單位享有的統制權,是勞資雙方利益均衡妥協的產物。[1]
筆者認為,契約說更多立足于勞動者個人意思自治,在契約說看來,勞動規章制度應當具有勞動者的意思同意,而單位單方制定出臺的勞動規章制度在未經勞動者個人同意之前本質上屬于“要約”,此種拘束力乃是源自于類似“附和契約”或“定型化契約”(一般契約條款理論),除非經勞動者明確表示反對,否則即推定勞動者之沉默為同意。而此種虛偽擬制勞動者意愿在本質上并不符合民法精神。法規說更存在明顯的漏洞,一般認為制定法律法規當屬于國家公權力機關之范疇,若放縱民事主體(用人單位)在企業范圍內創制法規,顯然違背了基本法治精神。黃越欽教授指出:“法規說過分提高工作規則之法律地位,不當地授予私法人立法權,使資方因此立于近乎國家對國民的統治地位。”[2]故而我們應當正視企業自治需求與勞動者權益之間存在的沖突,以集體合意的方式從源頭上控制勞動規章的出臺及其合理性,配合以勞動行政主管部門的適度事前或事后監管,更有利于保障勞動者權益。[3]
(二)制度依據
在2008年出臺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中,直接有關企業勞動規章的規定有第4條、第38條、第39條、第74條、第80條。其中第4條規定:用人單位在制定、修改或者決定有關勞動報酬、工作時間……等直接涉及勞動者切身利益的規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項時,應當經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全體職工討論,提出方案和意見,與工會或者職工代表平等協商確定。在規章制度和重大事項決定實施過程中,工會或者職工認為不適當的,有權向用人單位提出,通過協商予以修改完善。與1995年的《勞動法》相比有如下內容更新:⑴列舉加概括的方式明確了勞動規章制度之內容(勞動報酬、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勞動安全衛生、保險福利、職工培訓、勞動紀律以及勞動定額管理等直接涉及勞動者切身利益的);⑵區分勞動規章制度事項,唯直接涉及勞動者切身利益的事項須經民主制定(第74、80條予以重申),其他的屬于企業自決事項;⑶細化民主程序,須經“全體討論—提議—協商確定—公示”程序;⑷確立了勞動者異議修改權,在規章制度和重大事項決定實施過程中,工會或者職工認為不適當的,有權向用人單位提出,通過協商予以修改完善。⑸取消了勞動紀律作為勞動合同必備條款之規定。此外,在浙江、北京、湖南等高級人民法院出臺的《勞動合同法》實施指導意見中亦可明確2008年前企業制定的勞動規章與之后的具有本質不同,必須經民主程序才能對勞動者產生拘束力。從聽取意見至協商確定,其中變革不言而喻,《勞動合同法》意圖將與勞動者密切聯系的事項交由勞動者集體決定。筆者認為,《勞動合同法》第4條的規定應理解為“集體合意說”。[4]這也是實現勞動規章企業內集體協商的制度依據所在。
二、勞動規章制度集體協商的發展與存在的問題
工資集體協商又可稱工資集體談判,一般由雇主代表一方組織與工資勞動者代表一方,就勞動者的工資年度增長水平及其工資福利問題進行平等協商、談判,最后達成一致意見,并將一致意見簽訂為專門的工資契約或作為專門條款列入集體合同,作為約定期限內簽約雙方處理工資分配的行為準則。[5]
集體協商制度在調解勞資雙方沖突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呈現出以下特點:第一,約束性。集體協商的成果作為集體合同的具體條款對勞資雙方都具有相當的約束力,雙方必須如約履行,尤其是對于用人單位一方而言更是如此。第二,增進溝通。集體協商能在談判中實現勞資雙方有效溝通,就企業發展成果分配等問題達成諒解,協商可以定期或者不定期進行,討論諸如企業人員重組、冗員崗位安排、職業安全衛生、福利分配等事項,通過有效溝通從而促成勞資和諧。第三,法律地位平等。現有民法、勞動法等皆規定集體協商中各方代表享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法律地位平等,在平等的基礎上相互監督、制約。第四,互惠互利。利益最大化是集體協商雙方協調的主要目的,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企業和國家的利益。
根據《勞動法》、《工會法》以及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頒布的《集體合同規定》等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集體協商的內容主要包括:⑴程序性規定的內容。主要是集體合同的期限,變更、解除集體合同的條件和程序,履行集體合同發生爭議時的協商處理辦法以及違反集體合同的責任等內容。⑵勞動管理方面的內容。主要是勞動合同管理、用人單位裁員、用人單位對職工的獎懲等內容。⑶勞動條件和標準方面的內容。主要是勞動報酬、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勞動安全衛生、保險和福利、女職工和未成年工的特殊保護、職業技能培訓等內容。2005年11月,杭州市正式頒發了全國第一部關于工資集體協商的地方性規章——《杭州市企業工資集體協商試行辦法》。在該制度推行之初并未得到相關企業的回應,為此,杭州市總工會實行工資集體協商“要約行動”,對工會發出的“要約”,用人單位收到20日之內不給予書面回復、不開展工資集體協商或拒不履行工資協議的,上級工會要向用人單位發出整改意見書;逾期拒不改正的,由市、縣(市、區)總工會提請同級勞動保障行政部門責令其限期改正。在各級工會的主動要約下,杭州市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工作的開展駛入了快車道,特別是企業工資集體協商“百日要約行動”,有6088家企業工會主動向企業提出了開展工資集體協商的意愿,其中新簽和續簽工資集體協商協議的企業達4762家。不僅積極配合,還主動參與。在杭州,衡量一家企業的發展,不僅有財務報表上的產值數據,還有一個社會責任履行的評價分數。在《杭州市企業社會責任評價體系》中,總分值為1000分的評價體系,分值比重最大的是用工責任,為330分。比如工資方面,企業建立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且每年根據企業的經營狀況、社會平均工資的增長情況調整工資,工資增長高于杭州市職工平均工資增長率的,均可以得分。企業社會責任評估結果為優秀的企業,政府將以適當政策加以扶持;對不合格的企業加強監控,定期督查。
盡管杭州推行了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但形式大于實質的現象依然存在。并且由于一些小規模企業未建立工會,導致集體協商制度無法實行。具體表現為以下幾方面:
(一)相關法律法規不夠明確
我國現行涉及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立法主要是1994年頒布的 《勞動法》,2008年頒布的 《勞動合同法》,其他的規定都只是停留在政策層面。而工資集體協商被包含在集體合同內,只是作為選擇性條款,所以在施行中缺乏剛性約束機制。《工會參加工資集體協商的指導意見》是全國總工會的規范文件,雖然對工資協商的工資總額的增長與企業實現利稅等增長比例做出了相關規定,但約束力較差。此外,現行法律對企業不進行集體協商、不簽訂集體合同等相關問題沒有相應的處罰規定,這就使工會一方處于不利境地。為此,有關工資集體協商的法律法規亟待完善,現有的法律難以滿足和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
(二)協商主體存在爭議
工資集體協商所進行的談判,必須解決主體問題。協商主體就是能夠進行集體討論的個人或組織。在其他國家,法律明確規定的主體是工會和雇主團體。在我國,就協商主體方面的問題還有爭議。企業沒有可以代表的雇主組織,工會也無法明確自身的談判主體地位,再加上大量小企業工會建構率低,甚至難以派遣適格的工會代表。而對于勞動者而言,缺乏積極談判協商的意識。
(三)行政部門職能缺位
在集體協商過程中,政府具有主導作用,是推動工資集體協商的主要力量。但是由于經濟利益高于一切的觀念在一些地方官員當中根深蒂固,政府講究政績,片面追求經濟增長,廉價的勞動力成為招商引資的有力招牌,對勞動者的合法權益視而不見。此外,政府相關部門缺乏勞動監察力度,可作為而不作為,沒有做好宣傳國家勞動保障方針、政策和勞動保障法律、法規和規章;沒有督促用人單位遵守勞動保障法律、法規和規章;沒有依法糾正和查處違反勞動保障法律、法規或者規章的行為等工作。并且政府作為勞動市場、勞動關系的監管部門,如果直接參與集體協商談判,同時充當裁判與運動員身份,有違基本法律精神。
(四)工會地位不明
我國工會現階段的情況較為復雜,地方工會在地方政府的管理之下,地方政府往往對國家提高工人權益的政策和全國總工會的指導意見充耳不聞,而工會的經費也主要來自企業,因此工會大多成為幫助資方管理工人的機構,工會組織程度低,運作不獨立。工會在工人心中多為“俱樂部”的形象,即主要是組織文體活動、評選勞模等,工人在維權方面對工會的寄托較低。
三、推進我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實施之建議
從以上論述可見,通過行政推動的工資集體協商進而簽訂集體合同的方式存在諸多問題,并且大量中小企業往往將工資、福利等涉及勞動者切身利益的條款通過單方出臺企業勞動規章制度的方式來加以實現。故而筆者認為,要妥善解決企業勞動規章制度以及工資集體協商的諸多問題,兩者或可融合、相互借鑒。
(一)在企業內推行勞動規章制度的集體協商
用人單位為了整齊劃一地處理勞資雙方有關勞動工資報酬、福利待遇、勞動安全等事項,通過以出臺制定各類企業內部規章制度的方式實現,而按照現行《勞動合同法》,這類勞動規章制度在涉及勞動者利益時應當在制定過程中與工會或者勞動者代表平等協商確定,可見從立法本意上來講《勞動合同法》旨在要求在企業內部出臺此類勞動規章制度時實現企業內部的集體協商。當然通過此種方式出臺的企業勞動規章制度與通過《集體合同法》等集體協商簽署的集體合同是存在較大差別的,兩者在談判的主體、程序上都有極大差異。
筆者認為,在企業內部制定勞動規章制度時推行集體協商應當根據勞動規章適用對象來確定協商的對象,如勞動規章適用于全體勞動者則應當按照現行規定操作,若只適用個別勞動者群體的勞動規章則應重點聽取該部分勞動者之意見,可設置至少聽取多少以上人意見的規則。[6]《日本勞動基準法》 第90條規定,雇主于變更工作規則時,應聽取該企業過半數勞工組成之工會或未組織工會時以代表過半數勞工之人之意見。同時,對于未組織工會或者職工代表大會的企業,可規定應由全體或相應勞動者過半數同意方可制定。[7]此外,我國現行規定最大之不足在于未能明確規定凡未經民主協商程序的勞動規章為無效之機制,導致適用時將協商確定理解為僅商定勞動規章之內容而未將其作為生效要件。依據法理,強制性規范可分為命令型強制性規范與效力型強制性規范,現行有關勞動規章的規定屬于前者,將其上升為效力型強制性規范實有必要。
(二)完善勞動規章變更協商程序
我國現行《勞動合同法》規定,在規章制度和重大事項決定實施過程中,工會或者職工認為不恰當的,有權向用人單位提出,通過協商予以修改完善。瑞典1995年修訂的《工作場所共決法》第11條規定,在雇主作出會對其活動產生重大影響的決定前,應主動與根據集體協議確定的雇員組織進行談判。當雇主的決定會對雇員組織成員的工作或雇傭條件發生重大影響時,上述規定依然適用。[8](p80-90)筆者認為,勞動規章在修訂時仍須遵守制定時之民主程序,但對于提議權及其修訂協商程序需做如下完善:首先,立法應當區分提議權主體與程序啟動權主體,即工會與職工都具有提議權,職工除了有權向用人單位表達異議外,還可以向工會表達異議,但并非所有職工的請求都可以啟動協商修訂程序。建議通過立法確立啟動權的主體只能是工會或者與某勞動規章密切相關且一定比例(如半數)以上的勞動者,此項規定亦可防止勞動者濫權。其次,應當通過立法明確啟動協商修訂程序之后的時間、規則和法律責任。如《瑞典工作場所共決法》第16條規定:希望進行談判的一方,應當向對方提出談判的請求。在對方要求時,請求應以書面形式提出并說明其要求談判的事項。除了本法第11條至第13條規定之情形以及雙方另有約定者外,對方是個人雇主或者是地方雇員組織時,談判會議應當自收到對方的談判要求后2周內舉行;否則, 在收到對方談判請求之后3周內舉行談判。[9](p80-90)對此,我國也應當明確在合格主體向用人單位提出修訂請求之后多長時間內應當舉行協商,以及單位若不配合的相應法律救濟、法律責任等。
(三)發揮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
政府在集體協商過程中應積極作為,不管是立法還是具體的執行,都應該很好地履行職責。比如杭州市在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制度過程中將推進目標納入政府考核,此舉對工資集體協商推動極大。2004年,杭州市政府將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推進目標納入了地方任務考核中。未達到考核任務目標的,將問責地方勞動保障部門。2006年,杭州市委、市政府建立了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工作領導小組,市委副書記任組長,副市長任副組長,領導小組成員由市勞動保障局、市總工會、市經委等相關人員組成。2008年9月,杭州市政府還將工資集體協商工作納入 “杭州市爭創浙江省創建法治區、縣(市)工作先進單位”和“杭州市創建和諧勞動關系先進企業”的考核內容之中。近年來,頻繁打出政策組合拳的杭州市政府已經擔當起推動集體協商的主要責任者。政府牽頭抓集體合同的推進工作,也成為杭州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一大特色。可見,企業勞動規章制度的集體談判離不開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尤其是在早期試行階段,應當發揮好政府的此項職能。
綜上,由于現代企業經營規模日益擴大,用工人數急劇增加,并且業務分工合作事項日趨復雜,勞動規章制度的制定、變更往往牽扯到勞動者切身利益,因此,推行勞動規章制度的集體協商具有十分重要而現實的意義。同時推行此制度仍然離不開工會的作用,筆者認為,工會組織代表職工的利益,依法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是工會的基本職責。因此,必須認真落實《工會法》的規定,對25人以上的企業,各級工會組織要督促和幫助企業成立工會;還可以試點工會主席委派制,在完善制度的基礎上,逐步擴大實行范圍,同時各級工會組織應加強對工會主席和協商代表的專門培訓工作。只有扶持集體協商的代表組織與主體,培育企業內部集體協商的土壤,方有利于勞動者民主參與、意思參與的實現。
[1][3]徐金鋒.論勞動規章制度之法律定性[J].東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01).
[2]黃越欽.從勞工法探討企業管理規章之性質[A].政大法律評論[C].第17期.
[4][6]徐金鋒,李燕燕.勞動規章“協商確定”之辨析[J].求索,2012,(04).
[5]中華全國總工會.工會集體合同勞動合同工作概論[M].中國工人出版社,2006.
[7]劉志鵬:勞動法理論與判決研究[M].元照出版社,2002.
[8][9]葉靜漪,(瑞典)Ronnie Eklund.瑞典勞動法導讀[C].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