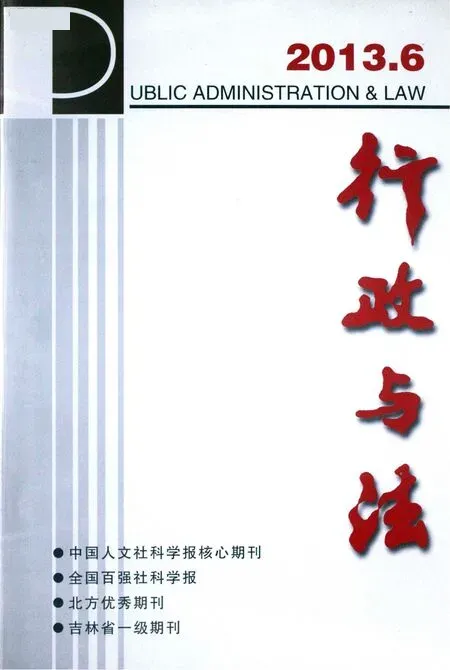戰后德國養老金制度變遷對我國的啟示
□ 李 勇, 王一峰
(⒈國家行政學院, 北京 100890; ⒉福建大學, 福建 福州 350108)
德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立起正式的社會養老金制度的國家, 其發展歷程可追溯至1889年俾斯麥時代的普魯士王國時期。經過120余年的完善,已建立起較為完備的國家養老保障機制。 在歷經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挫敗、1929-1933年全球經濟大蕭條的沖擊、1990年兩德重新統一后的短期財政困境、1993年歐盟成立后歐洲經濟“火車頭”長期責任的壓力以及近年來歐債危機所帶來的深遠影響之后, 德國的養老金體系仍然能夠持續地為全體國民提供較高水平的養老金待遇, 這也成為德國社會長治久安、國強民富的重要原因之一。無論從技術角度或是制度層面看, 戰后德國養老金制度的改革對于我國現階段社會養老保障機制的建設和完善都有著十分重要的可借鑒之處。
一、戰后德國養老金制度的發展歷程
(一)從基金積累制向現收現付制的轉變
早期的德國養老金制度屬于完全積累模式, 在兩次世界大戰中, 由于大量的積累基金被強制購買政府債券,導致戰后的養老基金名存實亡,最困難的時候僅夠維持14天的支出。為此,德國政府于1957年提出了將養老保險制度從基金積累制 (Funded Defined Contribution)逐步轉向為現收現付制(Pay As You Go),原積累制度下的基金結余部分在隨后的10年間用以償付使用的改革方案。由于百廢待興,勞動力年齡段人口大量死亡, 這一主張在當時迅速得到了選民尤其是得到了老年選民的支持。迄今為止,阿登納那句名言:“人們總要生孩子” 仍然是倡導現收現付制養老金模式的重要依據。
值得一提的是,同樣來自基督教民主聯盟內部,被譽為德國“社會市場經濟之父”并擔任過阿登納政府中經濟和勞工部長、副總理,后成功繼任聯邦德國總理的艾哈德始終激烈地反對阿登納的養老金改革方案,認為這樣的政策是不可持續的。 由于與阿登納政治觀點的沖突,再加上1966年的德國財政危機,使得艾哈德在1966年底被迫辭職。在僅有的3年任期里,艾哈德政府并未對阿登納政府的養老金方案做出根本上的調整,雖然其經濟發展的理論至今依然受到德國及許多國家的認同。 而現收現付制的基本養老金框架在德國也因此得到了最終的確認。
(二)慷慨的養老金計劃
20世紀70年代, 德國社會對于擴大福利的呼聲日益高漲, 勃蘭特所帶領的社會民主黨于1969年首次組閣成功。從價值取向上看,社會民主黨更傾向于社會的普通勞動者,尤其是1972年通過對養老金政策的改革,使德國成為世界上最慷慨的養老金發放國之一。 其主要的改革計劃包括:第一,實現高養老金替代率。對于有長期工作記錄的勞動者, 將獲得較高水平的養老金收入。例如:一個有著45年工作記錄的勞動者在退休后可以獲得退休前收入的70%以上, 而相應的養老金償付水平在當時的美國僅為53%;第二,變“強制退休年齡”為“退休窗口”。取消原有65歲強制退休年齡,對不同群體實行有差別的彈性退休政策。 對于35年及以上工作記錄的勞動者, 可以在63-65歲之間選擇退休,而對于殘疾、經常性失業人口和女性就業人口,則進一步放寬至60-65歲之間。
由于20世紀50-70年代德國經濟的恢復及快速發展, 尤其是70年代之后在西德馬克對美元的強勁升值的基礎上,出口仍然得到持續性的增長。作為同樣來自于社會民主黨的勃蘭特的繼任者施密特堅持了 “國家干預”的經濟主張以及福利支出的擴大化。因此,申請領取養老金的人數及養老金的給付標準均有所提高,而退休年齡卻有所降低, 尤其是提前退休的現象頻繁出現,使政府負擔越發沉重。這一現象也恰好與施密特本人的執政理念從早期的“凱恩斯主義”逐漸向赤字開支政策的轉變相吻合。
(三)削減福利的“節流”試驗
作為戰后德國執政時間最長的總理, 科爾在戰后兩德重新統一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的作用,同時,對于歐盟一體化進程也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在福利領域, 科爾也面臨著由于勞動者基數擴大和來自歐盟國家人口流動增加所帶來的養老金給付的挑戰。
科爾在任期內始終致力于全面恢復 “社會市場經濟”理念的實踐,對于社會民主黨留下的慷慨養老金計劃并不十分認同,短期內又受困于財政的壓力,因此縮減福利勢在必行。從1986年開始,關于養老金改革的整體計劃即付諸實施。“有一件事是確定的: 那就是養老金(改革)”。這樣的口號甚至成為科爾為謀求連任的主要施政綱領之一。1989年,新的養老金計算標準得到確認, 將養老金標準從與毛工資掛鉤轉變為與凈工資掛鉤(1992年開始實行),旨在維持替代率不變的基礎上,降低實際養老金的給付標準, 以期通過這樣的積累效應實現養老保險供給率從彼時的26.9%提高到2030年的36.4%,并且養老金的實際給付標準將從70%下降到64%。同時,聯邦財政撥款獎勵多子女家庭以鼓勵生育和擴大未來的繳費群體。
兩德合并之后, 由于原民主德國居民享有與原聯邦德國居民同樣的福利水平, 而原民主德國業已存在且不斷攀升的高失業率使科爾的計劃未能取得預期的成效;更出乎意料的是,非但養老金融資問題沒有得到緩解,與此同時,為鼓勵生育而進行的聯邦撥款卻呈不斷增加的趨勢。因此,關于法定退休年齡的修改也提上了議事日程。1992年,德國規定,從2001年起,除殘障人士63歲退休以外, 法定退休年齡一律為65歲。1997年,又提出將“人口因子”引入到養老金的計算公式中,防止“長壽風險”所帶來的對固有養老金制度的沖擊。
(四)強化個人責任的“開源”實踐
社會民主黨人施羅德所領導的“紅綠聯盟”在1998年大選成功后,隨即廢除了1997年的基于“人口因子”的養老金政策的大部分內容。同時,為了將養老金的供款率從20.3%下降到19.1%,施羅德政府不惜持續增加政府財政支出。 這一政策遭到了基督教民主聯盟的反對,甚至在社會民主黨內部受到了質疑。
為了確保施羅德政府財政政策、 勞工政策和養老金政策的可持續性, 黨內以勞工部長里斯特為代表的改革派于1999年開始對施羅德政策進行了修正。首先,對1997年改革中60-65歲之間的女性和失業人口的養老金領取資格加以確認。其次,對于工作年限達到35年及以上就業人口,可以保留“退休窗口”的選擇權,這項政策將在2017年全面施行。
2001年,里斯特計劃正式通過,該計劃規定,德國公民只要選擇指定的銀行或保險公司簽訂 “里斯特退休金” 合同, 便可獲得聯邦政府的財政補助和稅收優惠,并且聯邦補助將隨著投保年限的增加而提高。施羅德政府希望通過這一改革計劃使養老金替代率在2030年達到67-68%, 供款率在2020年以前維持在20%以下,以及到2030年不超過22%。截至2007年,參保人只要每月投入毛工資收入的3%(2008年起提高的4%),便可獲得114歐元的直接補助,同時,對有孩子的家庭,每個孩子可獲得138歐元的津貼,到2008年,孩子的津貼標準可提高到185歐元。該計劃在運行的頭5年內,便籌集了近700億歐元的資金,這成為施羅德政府關于養老金籌資模式改革的一項重要突破。 另一項養老金改革計劃“呂魯普養老”也開始實行,以建立可持續性發展的社會保險系統。與“里斯特計劃”相比,“呂魯普養老”計劃也享有聯邦的稅收優惠政策,并且具有更高的收益預期,只是無法獲得聯邦財政的補助。
“里斯特計劃” 的自愿參保模式并非改革的初衷,只是迫于工會聯盟和左翼政黨聯盟的反對, 方取消了該計劃的強制性。因此,其所形成的“多支柱”養老金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視為聯邦性的制度安排。 其被德國的學術界認為是改變德國養老金制度的基石,他們認為至此德國的養老金制度不再是純粹的現收現付制,而是一種帶有部分積累制(Partial Funding)的復合模式。而“呂魯普養老”計劃的出現,更是被認為帶有名義賬戶(Notional Defined Contribution)的某些特點和功能。
2004年, 施羅德政府再次通過一項新的養老金可持續發展的改革法案。 在養老金的計算公式中首次引入“可持續因子”作為計發標準之一,主要反映了供款人數與受益人數之間的變化趨勢,以便通過對“可持續因子” 的隨時調整以達到2001年改革計劃所既定的改革目標。
施羅德執政期間的養老金“開源”實踐,不僅為德國養老保險制度開辟了更廣闊的籌資渠道, 同時也使德國養老金制度告別了純粹的“現收現付制”時代,逐步降低了其在公共養老金替代率中的比例, 建立起了真正的“多層次、多支柱”的養老保險體制,強化了個人在養老金制度中更為重要的作用。因此,支持者們稱其為“世紀變革”。
二、德國養老金制度的優勢
(一)始終以德國民眾“老有所養”為目標,具有長期的穩定性
作為工業化強國,德國在戰后60余年的發展中,以養老金制度為主體的福利體系幾乎在每一屆政府中都進行了調整與改革, 經歷了從依靠個人積累向依靠政府供給的轉變, 同時也經歷了從政府大包大攬向更多地增加個人選擇權利和個人責任的轉變。 所有的改革政策都在不經意中體現了國家福利制度設計中對公平和效率的導向與側重,但事實的結果是,德國養老金制度在政策或機制上的調整并沒有從根本上影響德國老年人口的生活質量。即使從2000年開始,德國養老金制度更多地引入“私有化”的成分,也同樣能夠在基本穩定的繳費水平上提供較高水平的養老金供給, 在長達30年的養老金支付年度內, 繳費率穩定在18.3%-21.8之間,而替代率穩定在68%以上,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德國的福利政策正在發生一種示范性的變化,即轉向長期保持社會福利體系的有效性和支付能力。同時, 這樣的改革又不至于引起太大的社會震蕩。目前,德國養老金制度中所形成的基金投資等市場行為,其初衷仍然是保障養老金的償付, 是為了養老金的保值增值而投資, 并非為了促進資本市場的繁榮而建立一個可供投資的養老基金, 本末的關系在德國養老金制度中的安排是清晰的, 總體而言強調的仍然是養老金的待遇問題。
(二)具有較強的長遠規劃性和政策銜接性
在德國養老金制度的政策制定過程中, 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立足長期。 通常政策調整的目標是著眼于20年乃至更長時間段以后的政策效果, 而這樣的時間長度恰恰吻合了每個勞動者一生可能參與的工作年限。福利供給的憂患意識在德國社會表現得尤為強烈,也正是這樣的“時間預估”使得德國的每一代勞動者都能夠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在退休以后能夠獲得多少養老金待遇。 盡管不是所有人都贊成政府的每一項改革計劃,但由于歷屆政府對于改革都拋出了一個較長的“適應期”,因而這樣的長適應期對于大多數勞動者而言都是可以接受的。
同時, 雖然德國的政治架構處于政黨林立的狀態中,各黨派的執政理念和實施手段有較大的差異,但是出于選票的壓力, 在福利制度上的改革卻呈現出一種難得的默契。一個典型的例證是,在施羅德政府時期,代表社會普通勞動者利益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并沒有停止科爾政府所進行的“福利壓縮”計劃,而是從手法上變“節流”為“開源”,客觀上延續了科爾政府的改革方向,即縮小政府財政的轉移支付規模。同時,由于德國政治游戲規則中“政黨事先協商” 的傳統又使得看似“噪雜”的國會在重大問題上的決定能夠保證大方向的一致性。 以養老金制度為代表的德國福利體系并沒有因為政治左、中、右的黨派輪替而起伏不定,甚至有德國學者認為, 正是由于福利制度的剛性而模糊了各黨派的“個性”,使得黨派差異因此在逐漸消失。
(三)具有良好的通貨膨脹控制機制
對于養老金制度而言,由于積累時間長,受宏觀經濟波動的影響較大,因此,只有一個穩定的經濟體才能給國民的養老金待遇帶來良好的外部環境。 尤其是在當前全球強調養老金私有化和個人責任增強的背景下, 個人賬戶的有效積累更加依賴于溫和平穩的經濟運行。德國自2001年開始實行“李斯特計劃”,迄今為止,其總體通貨膨脹率始終位于較低且可控的水平,這也為德國整體養老金制度的多支柱化發展提供了便利的外部條件。
三、德國養老金制度面臨的問題
(一)人口老齡化的客觀沖擊
長期以來,德國一直是一個出生率過低、人口增長緩慢甚至是負增長的國家, 對于未來缺乏勞動力的擔憂, 一直出現在公眾和官方的話題討論中。 而與此同時,對于許多工業國家而言,人口老齡化的趨勢正在不斷加劇,退休或面臨退休的人口日益增加,德國也不例外。 德國長期以來穩定的養老金制度在人口結構異化的條件下,養老金給付的壓力也隨之增加,再加上德國政黨制度和福利剛性的存在,現有的“開源節流”政策依然難以阻止政府支出失控的趨勢。 德國政府對養老金的稅收轉移規模仍然從1991年的21%上升到了2006年的33%,在聯邦財政預算中,2006年,對于養老金的轉移支付總額已達770億歐元, 這其中還不包括550億歐元的對于參保人的附加支出以及110億歐元的對于私人養老儲蓄的津貼。
基于對政府財政支出失控的憂慮,也有學者認為,這樣的養老金制度將是不堪重負的, 甚至認為德國的養老金制度是一個過時的且成本巨大的體系。當然,這樣的說法僅僅是從純經濟的角度考慮。 而對于人口結構變化所帶來的影響, 德國政府試圖通過提高退休年齡的方式加以克服。 為解決這筆龐大的支出所帶來的財政負擔,2007年,默克爾政府通過了關于推遲退休年齡的改革方案,將法定退休年齡從65歲提高到67歲。
(二)外部的沖擊
自2008年以來, 以美國為首的全球經濟危機給各國都帶來了新的沖擊,德國也不例外。資本市場的風險和萎縮導致德國養老金基金的保值增值計劃也受到了阻礙,人們的收入降低,失業率增加,“里斯特計劃”的參與群體開始出現下降的趨勢。而與此同時,德國政府又出臺了對工作年限較長的員工增加工資以及對于某些特定經濟部門提高最低工資的政策, 這些政策甚至引來了對于德國經濟價值取向的爭論,但無論如何,對養老金制度的負面影響是確定無疑的。
2010年以來,由于“歐元危機”的影響持續發酵,德國作為歐洲經濟尤其是歐元區國家經濟的 “火車頭”,難免要承擔更多的經濟責任和負擔。一方面,以“歐洲四國”(Euro PIGS)為代表的歐洲高福利國家,為維持超額福利支出而導致的政府債臺高筑使德國不得不對其進行經濟援助計劃以保證歐元的“硬通貨”地位;另一方面, 無論地中海國家、 波羅的海國家或是北海國家, 大部分法定退休年齡都低于德國5年甚至更多,德國政府單方面地提高退休年齡政策的一個潛在風險就是: 德國高收入的精英階層有可能為逃避長期工作年限的約束而在職業生涯的末期選擇到其他歐盟國家工作, 而歐盟其他國家尤其是申根國家的長期失業人口則有可能在本國“退休”以后再來德國“碰碰運氣”,因為在歐盟國家間, 無論勞動力的流動還是養老金的跨國轉移都是十分便利的。 而這樣一來對德國可能造成的沖擊則是不可小覷的。因此,默克爾政府在實施“經援計劃” 的過程中始終呼吁歐盟各國提高法定退休年齡。
四、德國經驗帶來的啟示
不可否認,在社會政策領域中,中德兩國囿于政治架構、治理理念、經濟模式和社會發展階段的不同,在相互學習和借鑒方面顯得難以直接“嫁接”或“移植”,同時, 現階段我國養老保險制度建設的目標和德國養老金制度的標準也不相同。但是,對于養老保險乃至社會福利體系中所應共同遵循的思路以及對于相同或類似的社會因素所帶來影響的回應, 德國經驗或許是他山之石。
(一)不斷滿足人們新的、更高的要求
在所有的社會政策中, 公平與效率都是人們所爭論的焦點,養老保障制度也不例外。從社會養老保險的視角看, 政府或公共部門主導的養老保障計劃和以個人或私營部門為主的養老保障計劃, 將對社會生活的基本面產生極大的影響。 人們往往傾向于將現收現付制與社會公平更多地聯系在一起, 而將基金積累制與運行效率更多地聯系在一起。 德國自1957年確立現收現付制養老金制度之后的43年即2000年, 開始引入非強制性的積累制方案——“里斯特計劃”,同時,對于因人口和經濟條件變化所造成的對養老金制度的影響所進行的每一步改革基本都屬于“微調型”,同時給予全社會足夠的時間來消化和適應, 乃至盡量保證每一代人都生活在一種養老金制度下。 沒有大開大合的政策改變,也避免了大起大落的社會沖擊。我國自1986年首次提出“社會保障”概念之后,1995年確立了“統賬結合”制度,部分引入強制性的積累制,在2005年又調整了統籌賬戶和個人賬戶的比例, 個人賬戶規模從原來的11%下降至8%,下降幅度接近30%。在農村養老保險中, 我國從1992年開始至2009年, 經歷了農民個人積累、商業保險介入和財政補貼三種模式,并各自運行過一段時間。 這意味著我國在20多年的時間里向追求效率的方向邁了一大步, 又向追求公平的方向邁了一大步。 而這20多年又恰逢我國經濟改革和社會變革的重大歷史時期。對養老保障制度大刀闊斧的改革,既體現了人們的美好愿望, 也對全社會各個層面的適應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的管理思路”不斷出現的今天,有一點是共同的,即國家應該滿足人們新的、更高的需求。
(二)盡量縮短多重標準的持續時間
德國在二戰后開始的養老金制度建設的過程中,也經歷過擴大覆蓋面的發展階段,例如:在制度初期,礦工的養老金就獨立于社會養老金制度之外。1990年東西德合并之后, 原民主德國居民在享受權利和履行義務方面與原聯邦德國接軌也經歷了一段時間。然后,德國政府致力于盡快確立全社會統一的養老金政策(如繳費標準、運營模式、給付標準、優惠政策等),盡量縮短多重標準的持續時間,為公眾提供一個明確、統一的制度設計。目前,我國在擴大養老保險覆蓋面的過程中, 由于長期存在的城鄉差異、 區域差異和行業差異等,導致對不同人口的參保制度作出了主觀性的割裂,例如: 城市職工社會養老保險的繳費率和給付標準遠高于農村養老保險,而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又采用分級、定額的繳費形式,隨著人口流動的繼續加快、居民身份變更的日益增加以及城市化發展過程的快速推進,養老保險政策的分化又給未來統一社保政策造成了新的障礙,即一個分散化、撕裂化甚至破碎化的養老金制度既缺乏公平也沒有效率。因此,我國需要借鑒德國的做法,縮短多重標準的持續時間,縮小城鄉差異、區域差異和行業差異。
(三)延長退休年齡
同德國一樣, 我國目前也面臨著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形成了“蘑菇狀”的人口年齡結構。德國在解決人口老齡化的過程中,更傾向采用延長退休年齡的方式,而不輕易改變其養老金制度的基本結構。 德國目前已將退休年齡從65歲延長至67歲,而且,德國政府的經濟顧問已提交了一份繼續將退休年齡提高至69歲的政策建議。雖然長期以來德國也面臨著較高的失業率,至少從統計資料上看, 世界銀行所公布的我國近20年來的失業率均遠低于德國,但我國目前的退休年齡為60歲。因此,為保持我國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穩定性,尤其是保證統籌賬戶的支付能力, 適當延長退休年齡或許也是我國可以選擇的辦法之一。
(四)控制通貨膨脹
對于實行積累制或部分積累制的養老保險制度而言, 抵御通貨膨脹是社會養老基金保值增值的必要條件。由于我國目前資本市場的發育尚未成熟,因此,在“統賬結合”制度中,個人賬戶基金的投資基本局限于銀行存款和購買國債上。 自2008年我國為抵御次貸危機而實行種種經濟刺激政策以來, 一個很嚴峻的負面影響是物價上漲超過預期水平, 通貨膨脹的風險日益加劇, 并且有可能進入長期的經濟發展與通貨膨脹并存的狀態, 而這是社會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基金運營所始料未及的。我國自2008年開始,居民消費指數處于高位運行狀態。2011年以來,居民消費指數上漲的局面更加嚴峻, 已經遠高于目前長期法定存款利率。 如前所述,德國在引入部分積累制的過程中,較好地控制了通貨膨脹對國民經濟的影響,使得“里斯特計劃”能夠在良好的外部環境中實施。因此,要確保我國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基金的保值增值, 無疑只能在擴大資本市場投資比例和嚴格控制物價水平上漲的兩種可能性上進行政策選擇。
[1]German History in Documents and Images,Volume 10.One Germany in Europe: 1989-2009,The Pension Problem,February,1996.
[2]Axel H.Bбrsch-Supan,Christina B.Wilke: “Reforming the German Public Pension System”.AEA meeting,January,2006.
[3]Kai A.Konrad,Gert G.Wagner:“Reform of Public Pension System in Germany”.Discussion paper No.200,February,2000.
[4]Christine Ante:“Pension Policy Reforms in Germany”.Working Paper No.10 March,2008.
[5]Husmann Jürgen: “Germany:Efficiency and Affordability in Social Security through Partial Privatization of Provision for Risk”s,Bulding Social Security:The Challenge of Privatization,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Series,Vol:6,2001.
[6]Nicolas R?ssler:“The German Pension System:An Overvies”.Mayer Brown,2009.
[7]Holger Bonin:“15 Years of Pension Reform in Germany:Old Successes and New Threats”,IZA Policy Paper No.11.July,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