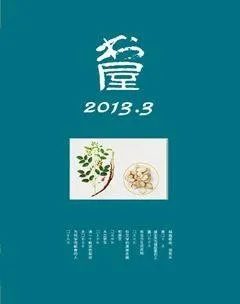白頭學(xué)作詩,溫舊實歌今
1949年是沈從文一生的轉(zhuǎn)折點,“反動文人”的帽子基本終結(jié)了他的文學(xué)生命,而只能無奈地轉(zhuǎn)入文物研究。但是作為曾經(jīng)的文壇符號,掌管意識形態(tài)的官員會不時地想到他,在“百花”時代,周揚就對《人民文學(xué)》主編嚴(yán)文井說:“你們要去看看沈從文,沈從文如出來,會驚動海內(nèi)外。”隨即,1957年7、8月《人民文學(xué)》發(fā)表了他的《跑龍?zhí)住放c《一點回憶,一點感想》。其實,沈從文仍在堅持創(chuàng)作,因為文學(xué)是他無法拒斥的夢想,也是一種現(xiàn)實訴求,即試圖擺脫生活的乏味。他在1957年12月7日接受采訪時這樣說過:“我的愛人是在《人民文學(xué)》搞編輯的,她非常希望我再從事創(chuàng)作。我現(xiàn)和她搞的這一行簡直無法結(jié)合,所以很難有共同語言,生活過得很乏味。”1957年3月,沈從文還給中國作協(xié)遞交過一份創(chuàng)作計劃,希望離開北京到別的地方住住,寫兩個以安徽、四川為背景的中篇或一些短篇游記,還特別提出可以為老紅軍撰寫有鼓勵教育作用的故事特寫,惜乎隨之而來的政治運動讓他的計劃付諸東流。1961年,文壇氣候稍微轉(zhuǎn)暖,中國作協(xié)給尚在歷史博物館上班的沈從文安排了創(chuàng)作假。出乎意料的是,他操持起了與小說迥異的另一種文體:古體詩,而這一切正是從1961年冬的江西之行開始的。
1961年12月13日《江西日報》第三版“文化走廊”刊登了《作家阮章競、戈壁舟一行八人來我省參觀訪問和創(chuàng)作》的信息:“最近中國作家協(xié)會組織了一批作家來我省參觀訪問和創(chuàng)作。沈從文、阮章競、華山、周鋼鳴、蔡天心、江帆、戈壁舟、安旗八人,已于11月29日到達(dá)南昌市。到南昌市后先后參觀訪問了八一起義紀(jì)念館、江西省博物館、青云譜八大山人紀(jì)念館,沈從文、周鋼鳴等五人還到廬山游覽了名勝,訪問了廬山墾殖場海會園藝場。作家們于近日前往革命搖籃井岡山,瞻仰革命遺址,訪問老根據(jù)地人民,有的同志計劃在井岡山較長期生活,創(chuàng)作反映井岡山斗爭的作品。作家們在井岡山定居后,還將去紅色故都瑞金、大茅山、景德鎮(zhèn)等地參觀訪問。作家們在南昌市期間,拜訪了我省黨政負(fù)責(zé)同志和老干部作家,會見了在市的本省業(yè)余作者。中國作家協(xié)會江西分會分別召開了小說散文、詩歌座談會,交談了有關(guān)創(chuàng)作上的一些問題,對到會的我省業(yè)余作者有很大的鼓舞和幫助。”
從報道中可見沈從文地位之尷尬,作家中以他最為聲名卓著,卻未出現(xiàn)在標(biāo)題上,而是選擇了黨員作家以及在中央或地方擔(dān)任文化界領(lǐng)導(dǎo)的阮章競與戈壁舟,但是在內(nèi)文中他卻排名第一。同行的多為各省文聯(lián)負(fù)責(zé)人,也不知道沈從文寫過什么作品,或搞過什么研究。只有新華社的華山稱贊“《蕭蕭》、《三三》等寫得真好”。信息中的日期與沈從文的記錄也有出入,查閱《沈從文全集》第二十一卷“書信”,得知他們是12月2日到達(dá)南昌的。
沈從文對前往江西充滿期待,動身之前在給大哥沈云麓的信中談到希望住在井岡山創(chuàng)作小說,而到景德鎮(zhèn)則可以了一心愿,“即可以有機(jī)會到景德鎮(zhèn)住住,并看看生產(chǎn),我的瓷器知識,學(xué)得不能如陳萬里先生扎實,惟瓷器造型和花紋藝術(shù)知識卻比較廣博,特別是對于改良生產(chǎn),搞印花噴花貼花技術(shù)時,會能提供一點意見,并介紹一些其他有關(guān)花紋材料。目下那邊缺少的正是這種知識”。駐留南昌、井岡山時,數(shù)次與兄長聊及該話題,如1961年12月16日的信中說:“在景德鎮(zhèn)則可作的事將更多了。因為我熟悉花花朵朵,又懂造型,且知道歷史人物形象,也多少明白些將來瓷器發(fā)展趨勢,和那邊研究所老師可商討的問題正多。即住一年把,為生產(chǎn)改進(jìn)顧問,和陶瓷博物館協(xié)助,都有條件。”12月31日又一次重提:“或有機(jī)會把個人所知道的一點常識協(xié)助一下那邊生產(chǎn)。特別是花紋和造型,我懂得較多,對部分老師傅必然還有益處。”沈從文確有努力融入時代大潮之中的念頭,急切地盼望已有的知識能為時所用。
沈從文江西之行的日程大致如下:1961年11月27日離開北京南下,從上海轉(zhuǎn)道西行,12月2日到達(dá)南昌。12月4日前往廬山,游覽了含鄱口、白鹿洞、觀音橋等地;12月7日返回南昌。12月9日,與同行作家在中蘇友誼館和江西作家座談,參加散文小說組討論。12月15日,赴井岡山,參觀了井岡山博物館,參加了山區(qū)建設(shè)四周年慶祝會、青年干部下鄉(xiāng)四周年晚會。12月29日,下山返回南昌。1962年1月15日,前往瑞金,參觀了沙洲壩及其周邊的紀(jì)念館。1月20日,赴贛州;次日,游通天巖、八境臺;1月27日,返回南昌。1月初,夫人張兆和前來會合,一起在南昌修養(yǎng)近一個月;期間,相偕參觀游覽景德鎮(zhèn)和大茅山。2月26日,離開南昌前往上海。出于王震的安排,以及中宣部、中國作協(xié)的介紹,江西方面對作家們熱情款待,“吃得好”,“住得極好”,上井岡山時還由省長邵式平的司機(jī)接送,這些使沈從文感到不適,“這里招待得太好,不免實使我們不安”。他倍覺惶恐,強(qiáng)調(diào)“有些不配享受種種特殊待遇”。除了領(lǐng)略江西的山光水韻,見識本地的風(fēng)俗民情之外,他觀看了當(dāng)?shù)嘏叛莸奶餄h作品《謝瑤環(huán)》以及地方劇《西廂記》(弋陽腔)、《西域行》(贛劇)、《四十八寡婦鬧江西》(采茶戲),數(shù)次被邀請參加座談會、舞會,還閱讀了幾部江西作家的小說。此外,沈從文在江西度過了1962年的春節(jié),以及自己六十歲的生日。
沈從文原本決定在井岡山住下,完成以1936年犧牲的內(nèi)兄張鼎和(張璋)為原型,敘寫一個世家子弟如何脫離本階級走上革命道路,及記錄二三十年代動亂的中國社會面貌和各種不同人物人生足跡的長篇傳記小說,他已經(jīng)為此書作了兩年的構(gòu)思及素材準(zhǔn)備。他在給沈云麓的信中說到:“如果能在這(井岡山)寫出四章,工作大致就可以正常進(jìn)行下去了。目下是明白了問題,充分準(zhǔn)備了材料,一切人和事都在頭腦中有個比較具體的輪廓,記錄也已差不多完備。只是不知從何下手,即可得到應(yīng)有效果。我已隔了十二年未寫什么小說了。”小說的試寫并無結(jié)果,只好作罷。時事遷移,井岡山已經(jīng)無法喚醒進(jìn)行此類題材書寫所需的體驗與回憶。更關(guān)鍵的是沈從文不隨流俗,拒絕時下通行的那種過于機(jī)械的、重概念的表現(xiàn)技巧,“我對一般方式(如《紅旗譜》、《青春之歌》)不擬采用,應(yīng)還有更合我本來長處的相配合的表現(xiàn)法,但是又受材料的現(xiàn)實性束縛,反而難于下筆。這點為難也近于一種反抗。我不希望用《紅旗譜》那種手法得到成功,可是自己習(xí)慣的又不大易和目下要求合拍。因之?dāng)R下來了。有待一種新的變化,即自己的簡練揣摩,也有可能到一定時候,便爾水到渠成。”而且,文壇屢興的批判讓他變得謹(jǐn)小慎微,不想因文罹禍。
在這段近三個月的旅程中,沈從文開始了古典詩的創(chuàng)作。他揀拾起古體,一方面在于舉國風(fēng)氣使然,最高領(lǐng)袖總是借用古典形式來抒發(fā)情感,引導(dǎo)了舊詩書寫風(fēng)潮,眾多作家、詩人都出現(xiàn)了向古代求索的傾向;而與他同行的也多為詩人,如阮章競曾以長篇敘事詩《漳河水》享譽(yù)解放區(qū)。途中他們相約和吟題贈。況且,沈從文本就有一種古詩情結(jié),十五六歲在軍隊作司書時隨一名蕭姓軍法長“作詩故事”,又跟從留日學(xué)者文頤真學(xué)作舊詩,認(rèn)真研讀過袁枚的《隨園詩話》,和過數(shù)百首詩,從而練就了一些基本功。在1962年1月28日回復(fù)張兆和的信中,他提及十多歲時因?qū)懽髋f詩而被人稱作“才子”的往事,“這份老本事過去很用過一點心,有時還寫香艷體,也十分儼然。古體固懂典故多,讀古文熟,又對漢魏五言詩有興趣,過去十多歲時還被人稱為‘才子’,即為了寫詩”。到北京求生活后,即再未試筆,一擱四十多年,而讓他心生感嘆,“六十歲重新寫舊詩,而且到井岡山起始,也是一種‘大事變’”。為此,他還賦詩“白頭學(xué)作詩,贈詩近自謔”以自嘲。
盡管作古體詩“比起寫短篇小說和散文特寫來,究竟用功久,下注本大,來得溜刷在行”,但是沈從文仍然秉持著虔誠的態(tài)度,會花費不少時間構(gòu)思、斟酌。在給妻子的信中,他描述了這樣的寫作狀態(tài):“寫詩有一大毛病,即一坐桌邊,會會即二三小時過去,因之吃飯反而成為負(fù)擔(dān)。晚上也難安眠。所以‘適可而止’,大致在山上即不再動筆了(至多只再寫一五絕)。”寫詩成了他甜蜜的煩惱與負(fù)擔(dān)。
1962年初,蔡天心、阮章競、華山在《江西日報》分期刊載了《詩五首》、《金星檞樹》、《井岡山三首》等作品。沈從文的《井岡詩草》(定稿于1961年12月30日)也在同年1月17日《江西日報》第三版發(fā)表,全篇如下:
資生篇
贊江西生產(chǎn)建設(shè)成就,兼及山川景物之雄秀壯美。由史起興,共成三章,計五百四十字。
一、史鏡
周公陳王業(yè),深明國事艱,勸民勤稼穡,植根八百年(用《尚書·無逸篇》)
齊地本貧薄,資生尊尚父,漁鹽創(chuàng)富基,生民知所處。管仲相齊桓,黎庶樂農(nóng)桑,錦紈衣天下,齊國獨富強(qiáng)(用《史記·齊世家》,《管晏列傳》,《范子·計然篇》)
荊楚及吳越,東南蠻野民,地利發(fā)金錫,生產(chǎn)驟躍增。丹漆曜五彩,華美證文明。術(shù)藝齊繁榮,始生楚靈均(用《史記·楚世家》、《吳越世家》,及《長沙信陽發(fā)掘報告》,《屈賈列傳》)
尚農(nóng)明法律,商鞅計慮深。農(nóng)兵相合一,天下屬嬴秦。奢泰失檢約,酷罰苦民生。揭竿起陳吳,長城由內(nèi)崩(用《史記·秦本紀(jì)》,賈誼《過秦論》,《賈山至言》)
歷覽前史冊,得民實首務(wù)。四民勤本業(yè),百工各有序。人民作主人,國基必永固。
二、建設(shè)新山村(干部下放四周年)
井岡天下勝,佳名久著聞。天險黃羊界,圣地大井村。煙云呈仙境,竹木蔚蕭森。未聞騎白鹿,還歌二羊擒。仿佛聞鼓角,敘舊余老成。星星燎原火,燃紅天上云。
山區(qū)重建設(shè),倏爾四經(jīng)年。青春冶一爐,鍛煉比金堅。上下同辛苦,建國立本根。水石齊馴服,生產(chǎn)日以繁。遺跡重恢復(fù),同驚面貌新。平地樓臺起,燈火曜列星。歲暮慶佳節(jié),我幸茲登臨,妙舞擬仙蝶,輕吹囀鳳音。天下好兒女,同羨“井岡人”。青春能預(yù)此,不負(fù)好青春。
三、回南昌途中
昔人在征途,歲暮百感生。江天渺蕭瑟,關(guān)河易阻行。王粲賦登樓,杜甫詠北征,食宿無所憑,入目盡酸心。遙遙千載后,若接昔苦辛。
我幸生明時,千里一日程。周道如砥矢,平穩(wěn)感經(jīng)營。連村呈奇景,遠(yuǎn)山列畫屏。待渡贛江南,江水清耳深。群峰幻青碧,千帆俱嶄新。倏忽白云馳,比翼雁南征。默誦王勃文,入目壯懷增。
還過永豐縣,綠桔萬樹榮。丹實勤采摘,社社慶功成。田疇布方罫,牛鵝總成群。老幼貌怡悅,冬衣各上身。生聚盡地力,謀國見典型。
白頭學(xué)作詩,溫舊實歌今。無淚濕青衫,才多慕廬陵。諸事難具陳,筆拙意樸誠。多謝賢主人,作客愧深情。
1962年1月5日,沈從文將所寫的四組五言古體詩寄給張兆和,看能否在《人民文學(xué)》發(fā)表,不成則遞給《詩刊》或《光明日報·東風(fēng)》。《資生篇》就是其中之一。沈從文與張兆和就此詩討論過多次,張建議把“史鏡”部分刪除,“因為這詩整個是談歷史,讀來比較干,和前后各篇以抒情寫景見長風(fēng)格調(diào)子不同”。沈則提出相反的意見,“來信說《資生篇》上部得去,那最好不發(fā)表。你們不懂前部分正和本題關(guān)系密切,和江西目下建設(shè)成就有關(guān),如擬用,最好莫刪節(jié)(和交響樂一樣)”。在1962年2月號《人民文學(xué)》發(fā)表時,“史鏡”部分最終還是被去除,第二、三章則作為兩首詩發(fā)表,標(biāo)題改為《建設(shè)新山村—干部下放上井岡山四周年節(jié)日》、《下山回南昌途中》。比較而言,第一章質(zhì)量不低,蘊含濃重的歷史感,又具備豐厚的當(dāng)代精神,頗有借古喻今之意。不過,它顯然不是“目下文學(xué)要求的重點”,也與《人民文學(xué)》代表的國家主流意識形態(tài)存在抵牾。為了符合報刊的定位以及社會氛圍,編輯們自然會對其詩作一定的修訂與刪改。因此,《井岡山之晨》在同一刊物發(fā)表時,詩名被更換,詩行被調(diào)整,詩句也被改易。如此這般,不禁讓沈從文生發(fā)出“寫詩不易,讀詩亦難”的喟嘆。
沈從文“下筆難自休”,假如不是“紅格行紙正式宣布完結(jié)”,不然“總還會有卅首流傳人間”。他在江西吟賦的詩歌有十?dāng)?shù)篇,除了上引《資生篇》外,其他如《廬山“花徑”白居易作詩處》、《廬山含鄱口望鄱亭》發(fā)表于1962年2月《人民文學(xué)》。《井岡山之晨》發(fā)表于1962年1月26日江西《星火》雜志第一期,又以《井岡山清晨》為題發(fā)表于1962年2月《人民文學(xué)》。《參觀革命博物館》、《慶佳節(jié)》發(fā)表于1962年1月26日《星火》雜志第一期。《游贛州通天巖》發(fā)表于1962年2月15日《南昌晚報》。《戲贈戈壁舟同志》、《贈安旗同志》、《贈阮章競同志》發(fā)表于1962年3月10日《光明日報》。《觀〈西域行〉》發(fā)表于1962年5月16日《光明日報》。
沈從文這些“情感集中,文字鋪敘素樸質(zhì)實”,“體舊,意思卻新”的詩作得到了不少人的稱贊,時任《人民文學(xué)》副主編陳白塵就“覺得驚異”,友朋也多贊“委曲盡致,真切感人”。張兆和則說:“各詩感舊歌今,不落俗套,寫景抒情,渾然一體,情真意摯,讀了鼓舞人,也給人以藝術(shù)享受。”許之有杜甫之風(fēng)。這批詩歌與幾篇未刊稿后來以《匡廬詩草》(三篇)、《井岡山詩草》(九篇)、《贛游詩草》(四篇)為名收入《沈從文全集》第十五卷。這也是“十七年”中沈從文發(fā)表文學(xué)作品最集中的時期。他對這些詩頗為滿意,認(rèn)為“結(jié)果似乎比黃炎培先生詞匯略多,比葉老也活潑有感情些些”,如“(《井岡山之晨》)除了三五句用時事,不免近打油,其他似乎還有氣勢、感情,文字也足相副”,又“《含鄱口》也寫得極好,妙在末尾二句,你們自己不到這里,反而想把末句改動,一改可就完全失去本詩應(yīng)有意思了。這詩并不比《花徑》壞。將來刻到含鄱亭上也值得的。”更重要的是,在《人民文學(xué)》、《光明日報》等權(quán)威媒體刊登作品意義甚大,讓他獲得了長時間失去的尊重。之后,沈從文也總把《井岡山清晨》等詩視為創(chuàng)作的標(biāo)桿:認(rèn)為《白玉蘭花引》避免了《井岡山清晨》的一些不足,而評價《紅衛(wèi)星上天》“比《井岡山清晨》沉重”。
游覽江西期間,沈從文與沈云麓、張兆和有大量書信往返,或記錄生活點滴,或談?wù)撛姼鑴?chuàng)作,其中既表達(dá)了對古典詩的認(rèn)知與取舍,“一般人多作七言,易寫難工,境格不高,常借助于三百首調(diào)動調(diào)動字句而已。我倒‘人棄我取’,專寫五言,因為古文底子好些,又記得較多典故,且熟讀漢魏詩,所以舊瓶裝新酒,寫來倒還有意思,和目下一般舊體詩不大同,像是近年趙樸初作詞,稍稍有些突破”。其中也記錄了對文壇風(fēng)氣的不滿與譏嘲,“現(xiàn)在因為看人到處題詩,都極俗氣的堆名詞,情、理、境三不高。還到處寫到處送人、發(fā)表(最不佳的恐是豐子愷)”。“近年來寫舊詩人甚多,打油成為風(fēng)氣,其實基本功不曾好好練習(xí),格多不高。舊詩未嘗不可寫得極有情感,有氣魄,而又不必借助于一些刺激性名辭。會看的人,一下筆即可知道功夫深淺的。裝內(nèi)行不易成功的。過些日子或許還可為你寫幾首真正有新意的白話詩看看。現(xiàn)在人搞這一行一般說基本功都不大到家,和郭風(fēng)作散文一樣,十分勉強(qiáng)的湊和成篇。攬事過多體力不抵用,只好讓人作大王了”。沈從文留給世人的印象往往是謙卑、隱忍,處事低調(diào),而信中卻表現(xiàn)了他的另一種性格:內(nèi)在的倔強(qiáng)與自負(fù)。
在江西的考察讓沈從文遠(yuǎn)離政治中心,心情舒暢(本地青年還向他索取新版的小說選),除了抱怨天氣寒冷外,心態(tài)較為輕松,從他幾首贈詩即可見一斑,語氣多帶調(diào)侃。此行也讓他受益良多,如張兆和所說:“全家都為你高興,問題不在于目前寫出多少首詩多少篇文,主要的是心胸開闊,情緒飽滿興致高,這對你身體有好處,也是重新拿起筆來寫出更多好文章的開始。”沈從文的小說夢未能續(xù)完(據(jù)沈虎雛介紹,沈從文試寫了一個章節(jié)),卻開啟了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另一個向度,對古體詩爆發(fā)出了難得的熱情,并在此基礎(chǔ)上有著持續(xù)的思考。離開江西后,沈從文還創(chuàng)作了六十余首古體詩,收在《青島詩存》、《郁林詩草》、《牛棚謠》、《云夢雜詠》、《京門雜詠》、《喜新晴》等中。這些詩歌與江西之行的作品相比在主題上更加繁復(fù)多元,如借詩歌探討社會影響與工藝、藝術(shù)的關(guān)系,或在詩歌中用文獻(xiàn)與文物的互證法分析社會的衍變;用事措辭、境界營造上也更勝一籌,不復(fù)之前的粗礪生硬。
關(guān)于沈從文的古體詩,黃永玉在《表叔沈從文的詩和書法》有過評價:“表叔也作傳統(tǒng)古詩。六十歲以后還作得很多,多而長。用意結(jié)體似乎是魏晉法度。”沈從文對之也很在意:1980年,他曾把一抽屜的舊體詩翻給前來尋訪的美國學(xué)者金介甫看,也有讓黃永玉給它們配圖的想法。現(xiàn)今學(xué)界關(guān)于沈從文小說的研究著作可謂不勝枚舉,對散文、文論的闡釋也頻繁出現(xiàn),但是對詩歌的解讀不多,古體詩的相關(guān)論述更是偶然見之,這顯然無助于呈現(xiàn)他的復(fù)雜性與豐富性。畢竟,這些詩歌也是他心性的投射與思想的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