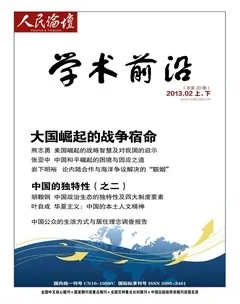中國和平崛起的困境與因應之道
摘要 中國崛起應該是一個文明體系的崛起。中國應建立完整而有系統的中華文化價值體系,以補充現有西方價值體系的不足,讓世界因中國的崛起而變得更為和平與繁榮。但主宰性的大國往往會用預防性戰爭、約束、遏制、交往等方式來因應崛起大國的挑戰。中國在現階段必須遵守現有的國際建制與規則,必須要妥善處理與它周邊的關系,讓西方了解中國的崛起是東方文明大國的崛起,是對西方文明大國的警醒,是一個能夠共同攜手為人類創造福祉與和平的崛起。
關鍵詞 中國崛起 和平崛起 兩岸關系 中華文化
中國崛起的內外誘因
2011年9月出版的《日蝕:生活在中國經濟主導的陰影下》一書中指出,如果以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為比較指標,2010年中國已經超越美國,居世界第一。該書以一個假設性的故事為開端:2021年,美國面臨財政危機,美國總統在發表就職演說后,從白宮前往位于賓西法尼亞大道另一端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與中國籍的總裁簽下一份紓困方案協議,在緊急融資三萬億美元的同時,承諾美國將遵循一系列限制條款。作者用感性的話語評論道,這一刻象征著世界主導權交接儀式的完成。①
中國是否已經崛起?若從幅員、面積、人口來看,中國是毫無疑義的大國。經過30余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實力已經超越日本位居全球第二。正如大多數人都想力爭上游一樣,每個國家都有企求崛起的天性,希望領先其他國家。作為一個大國,尋求國際地位與適度的影響力,更是必然之事。問題在于,它們強大了,能為世界帶來什么?中國崛起的目標是成為一個區域性強國,還是成為一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主導大國?中國雖然不想成為一個全球主宰性的霸權(dominant hegemony),但理應不排斥成為一個具有發言權與影響力的大國。要成為全球性的主導大國,僅靠物質力量的“硬權力”是不夠的,還要看能否倡議出一套更符合人類發展的價值觀以及讓現有大國皆能夠接受的話語體系。
要了解中國在崛起過程中會受到什么樣的挑戰,首先應該了解中國能夠在近十年內快速崛起的因素。在內在結構上,改革開放與世界接軌當然是中國快速發展的關鍵,②此外,改革開放前30年的政治社會運動也為中國建立了強大的動員體制,這個動員體制為全面性的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個動員能力極強的現代國家機制。這是所有其他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無法比擬的。相對西方的“大社會、小政府”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中國在崛起的道路上一出場就是以龐大的國家社會動員能力為基礎。這個基礎是中國追趕西方并迅速崛起的關鍵所在。
另一個因素是中國通過社會主義改革,累積了龐大的國有資產,使得在經濟社會建設過程中,國家有充分的資源可以運用與分配。由于擁有天生的廣大市場,中國充分發揮了計劃經濟、規范經濟的優勢,最終建立了完整的科技及產業體系。幅員與人口、國家資源與動員能力,這兩個因素推動著中國經濟快速崛起。
中國在過去十年間經濟快速發展,除了國家力量、人民勤奮以外,還有兩個重要因素不可忽視。第一,中國抓住了全球化的契機,接受資本主義自由貿易規則。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外資與技術大量移入,讓中國快速地從世界工廠走向世界市場。加入全球化使中國降低學習成本,并利用外資與技術,使技術革新與進步得以實現。第二,“9·11”后,美國突然改變其原本要在2001年將戰略重心從歐洲轉移到亞洲的計劃,③轉而與中國聯手,共同維護以反恐為主要訴求的全球安全。恐怖主義讓美國無暇遏制中國,為中國爭取到十年的戰略機遇期。
2003年11月3日,中央黨校原副校長鄭必堅曾在博鰲亞洲論壇上提出中國和平崛起”一詞。這個主張固然表現出“中國的雄心,但當時也是對中國威脅論作出的回應,以避免西方認為中國崛起必然會危害到美國等西方大國的戰略安全利益。2004年下半年以后,考慮到“崛起”對西方人而言頗為刺耳,和平崛起一詞在新聞、教育等政治傳播中逐漸淡出,并改為更低調的和平發展④,但其基本精神與內涵并沒有改變。
西方大國崛起的憑借與影響
現實主義是目前國際關系中的大理論(grand theory),權力與利益是這個理論的兩個核心詞,主張國家權力是維護國家利益的不二法則,沖突與戰爭不是偶然而是常態。
權力轉移理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⑤者認為,強大而不滿的國家很有可能成為國際體系的挑戰者。在現實主義者眼中,崛起的大國與原有的強權在權力轉移過程中必然經歷陣痛。這個陣痛不論是否為戰爭,都會經歷一段權力的較量或磨合期。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警告東方文明對西方文明的潛在挑戰。⑥從文明的進程角度來看,歷史上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國、德國、俄羅斯、日本、美國九個大國的崛起,都是西方文明勝出的崛起。他們都是采用現實主義的思維:一個大國的崛起必然導致另一個大國的倒下。在霸權競逐中,“只有第一、沒有第二”是它們的信念,它們之間從來沒有所謂的雙贏。誠然,它們的崛起也給人類帶來了進步,但更多的是滿足了霸權國國內的資產階級。它們崛起不是為了世界和平,而是為了本國或所屬文明的利益。沖突與戰爭是他們習以為常的手段,它們希望通過國際法或國際組織來維持世界和平,但是這些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無論是原則、規范都必須符合它們的基本價值。
這九個大國之間看似有不同的崛起道路,但其本質思維完全一致。從文明的角度來看,它們的世界觀(Weltanschauung)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中正義與邪惡的二元世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以及資本主義資源掠奪等組合。以鄰為壑是它們在崛起時處理周邊區域的態度,它們所制定的法律是它們要求其他國家必須遵行的規范,弱肉強食是崛起后的結果。這些霸權要維持它們的霸業,必須要創造出可以讓世界接受的價值與話語體系,不論是民主和平論、貿易自由論、霸權穩定論,看似為追求世界和平與穩定的理論,其本質卻是為了要維護其霸權。
中國已經確定將和平崛起或和平發展作為其崛起的必要原則。中國希望和平崛起,但是任何崛起必然會與現有的霸權產生摩擦,這不是理論,而是自然的定律。中國在面對這些摩擦時,到底應該如何面對,用什么態度面對,這不是用和平一個簡單的概念就可以處理的,而是涉及到自己崛起的政策。
既有霸權如何面對新興大國的崛起
每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在面對一個主宰性的大國(dominant power)時,都面臨同樣的挑戰:第一,它如何處理與周邊國家的關系;第二,能否解決自身內部問題;第三,能否能建立一套大國成長崛起的理論體系。
歷史上九個崛起的大國如何處理這三個問題?這九個大國均奉行基于基督教文明、物競天擇論、資本主義信仰所衍生出來的意識形態體系。在處理與周邊關系時,除了葡萄牙地理偏遠以及美國因東西兩面均為大洋,南北沒有足以威脅的天敵外,其他七國都曾與周邊國家發生沖突,勝者崛起,敗者讓位。這些崛起的大國內部有宗教、階級、族群問題,它們也都企圖用擴張來掠奪資源進而解決其內部矛盾。
權力轉移理論對于國際體系中霸權的認定,是指掌握國際體系權力資源優勢的主宰國(霸權國)。主宰國擁有國際體系內最大部分的資源,維持相對于潛在對手的權力優勢,以及運用可造福盟國并滿足其他國家需要的規則,管理國際體系,以常保其優勢地位。⑦主宰國創造了所謂的現狀,希望其他國家能夠遵守現狀。在維持現狀方面,物質權力是主宰國用來壓制新興大國崛起的工具,價值性的權力則是它們維護其霸權的結構性力量。
中國當然可以選擇不同于傳統大國崛起的思維與路徑,但在崛起的過程中,必然會遭遇到主宰強權的質疑與挑戰。主宰強權在與崛起大國交手中,通常會以預防性戰爭、約束、遏制與交往的方式來減緩崛起大國對它的挑戰。
預防性戰爭。當面臨國家重大利益抉擇時,霸權國家可能會發動預防性戰爭(preventive war),以遏止現狀國家(the revisionist state)的持續坐大。⑧之所以會發動預防性戰爭,是因為“現在就打一場從長遠來看不可避免的戰爭,遠比等到對手有擁有優勢后再打較好”⑨。這些觀點說明了預防性戰爭的三個意涵:第一,戰爭被視為不可避免;第二,威脅長期存在;第三,早打比晚打好。因此,預防性戰爭是一種在無法預期未來發展而采取的一種自認為發動戰爭對自己有利的預期性選擇。當領導者認為為和平所付出的代價高于未來戰爭的代價時,領導者會理性地選擇預防性戰爭。
對于哪一方較可能主動引發預防性戰爭,學術界的看法不一。吉爾平(Robert Gilpin)視預防性戰爭為一個正在衰弱的支配性大國面對一個崛起的大國時,最具吸引力的反應方式,當面對的選擇是衰落或是打仗,政治人物絕大多數會選擇戰斗。⑩但是奧根斯基(A. F. K. Organski)與古格勒(Jacek Kugler)則持相反意見,他們認為,對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而言,也會發動一場戰爭,早在他們具備了與主要國家抗衡的力量之前,就發動了對主要國家的戰爭。在他們看來,發動戰爭是邁向強權的重要手段。
從世界近代史來看,很少有霸權國家主動發起戰爭來預防阻止一個崛起大國對它的挑戰。18世紀的英國與20世紀的美國,都沒首先使用武力來對抗潛在的挑戰對手。由于既有的霸權會以滿足現狀的保守態度處理問題,因此,從歷史經驗來看,選擇戰爭而圖霸者,大多是一些正在崛起的強權。近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后發動的的甲午海戰、日俄戰爭和九一八事件。
崛起強權在挑戰既有強權時往往不容易成功,其結果反而造就了新的強權。例如法國挑戰葡萄牙與荷蘭,沒有成功,成就了英國;法國挑戰英國(拿破侖戰爭),沒有成功,英國繼續其第二周期的霸權;德國挑戰歐洲強權也沒有成功,卻成就了美國的霸業。
二戰以后,以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紛爭已是國際間的共識。隨著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大國之間武力沖突的可能性逐漸降低。不過,因為族群或意識形態沖突所引發的區域性沖突并沒有減弱。特別是美國為維護其全球霸權,發展出攻擊性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理論,主張先發制人以維持美國在某一個地區的主導霸權。
戰爭與沖突在國際關系上是兩個程度不同的概念。閻學通教授認為,和平崛起中的“和平”,不能定義為不使用武力,而應定義為沒有戰爭。如果將和平定義為“沒有軍事暴力行為的安全狀態”,和平崛起就絕對不可能。但是,如果將和平定義為沒有戰爭,絕大多數非戰非和狀態就都屬于和平范疇,小規模的軍事行為也包含在這一范疇之內。因此,用小規模軍事行動維護利益或是解決沖突,也有和平崛起的可能。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如何拿捏戰爭與沖突的分寸,必須充分考慮。
約束。對于一個既有大國而言,與其他國家結成同盟,有時候并不是為了自身力量的累積與擴張,反而是為了藉由聯盟來約束(binding)和控制參與國。對于參與同盟國而言,約束并不見得可以達到預期的效果。例如,美國、英國1922年與日本所簽訂的《五國關于限制海軍軍備條約》,動機之一是希望對日本進行控制與約束,但日本后來還是發動了對美國的戰爭。約束也有成功的例子,例如,美國在戰后與日本簽訂安保條約,其目的固然為圍堵共產主義的擴張,但是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為了約束日本,使其軍國主義不致再起,并使日本的軍備發展完全合乎美國的戰略需要。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成立,固然是為了對抗華沙組織,但是也同樣有約束德國和防止法國在歐洲稱霸的作用。
國際組織與國際建制的建立或多或少來自于以建立規范來相互約束這一戰略思想。約束政策有幾個目的:第一,通過接納新興大國進入現存的國際體系中,使其有一席之地,滿足崛起大國對于聲譽的需求;第二,新崛起的大國可以在多邊組織中有表達利益與觀點以及建立威望的機會,從而可以與既有大國共同建立新國際秩序的機會;第三,將崛起的大國放在政策網絡中,使其感覺到,它從現有體制中得到利益的代價比用力量改變體制的代價要來的小。
既有霸權往往通過國際經濟制度的安排來約束其他國家。依照“所有的規則都是由強權制定,而強權不會制定一個對其不利的規則”這個定律,既有霸權往往通過經濟、金融等手段來建立一個有利于本身的規則以確保其霸權。英國在其強盛期時建立金本位制,美國戰后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都是極明顯的例證。美元作為全球最重要的通行貨幣,也是美國成為全球金融霸權一個不可缺少的工具。在金融、經濟、人權、環境等議題上,美國均有價值上的話語權。中國雖然對外不結盟,但是要充分遵守國際建構與規則。如果無法在未來建立起自己在國際間的價值話語權,中國將會長久陷于美國這個既有霸權的約束中。
遏制。遏制(containment,又可譯為圍堵)戰略并不是尋求擊敗崛起的大國,而是防止它的進一步擴張,它是一種尋求保持均勢,而不是恢復原狀的戰略。卡迪斯(John L. Gaddis)將遏制分為對稱性與非對稱性反應(symmetrical and asymmetrical response)兩種。對稱性反應是指在當時、當地和依照對手所使用的方式從而對敵人的挑釁作出反應,例如美國在韓戰、越戰時的戰略方針。不對稱反應是指針對挑釁國的行為,由自己選擇時間、地點與方式來作出反應,以充分打擊挑釁者的弱點。肯楠(George Kennan)在冷戰初期對蘇聯所設計的遏制戰略,以及后來的大規模報復性(massive retaliation)戰略,都是屬于非對稱性反應。
冷戰期間,美國是以遏制戰略來防止蘇聯共產主義的進一步擴張。在遏制蘇聯時,美國是以非對稱性反應的戰略,但雙方代理人戰爭則是一個對稱性反應的遏制作戰方式。一般而言,非對稱性反應的遏制思維,需要以國家總體實力作后盾,它本身除了有遏制的功能外,還有創造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戰略意義,用以與對方作一場長期的武力競賽,進而與對方較量國家的整體實力。蘇聯瓦解的原因之一,即肇因于美國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戰計劃(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亦稱Star Wars Program,簡稱SDI),美蘇之間陷入了一場軍備競賽,其結果是蘇聯的經濟實力無法支撐軍備競賽而落敗,冷戰因而結束。
遏制戰略的另外一種表現就是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政策,也就是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聯盟來反對崛起國家或崛起國家與他國的聯合。崛起中的國家也會嘗試用正式或非正式的結盟來挑戰現有強權所建立的國際秩序。美國重返亞洲或再平衡戰略目標在于希望日本、韓國、美國在東南亞的盟友,甚至臺灣,都扮演著遏制中國大陸的功能。中國將面臨兩個選擇:第一,不斷增加軍備,但這樣是否會掉進美國所設定的軍備競賽、拖垮經濟的陷阱當中?第二,如何處理與周邊的關系?
交往。交往(engagement)政策是指以非強制性的方法來改善與崛起大國的關系,化解其不滿意現狀的因素,目標是確保崛起大國以和平方式來改變區域及全球的秩序。交往政策目的在于將不滿國家納入國際社會,接受現有國際秩序。交往政策與其他政策的不同點在于,前者依靠承諾給予恩惠,而不是加以懲罰性的威脅來影響威脅國的行為。簡單地說,在實踐上,交往政策是胡蘿卜優先于棒子的政策。
交往政策通常是為了實現下列三個目標:第一,既有強權可以通過交往政策來了解不滿意于現狀的崛起大國的真正意圖;第二,用以爭取重新武裝的時間和盟友,以因應未來可能的戰爭;第三,用以打破崛起大國可能的聯合,或者阻止他們進行聯合。如果成功的話,交往政策是解決不滿意現狀崛起大國的最有效且最合理的途徑。
不過,交往政策要獲得成功,崛起大國必須要有有限的修正主義(limited revisionism),即要有有限的改變現狀的認識,例如冷戰期間美國對于蘇聯與中國的認識就不一樣,美國認為無論在政權與文化性質上,蘇聯均是一個不滿現狀的擴張性國家,而中國在本質上并不同于蘇聯。因此,對美國來說,對蘇聯這個完全修正主義國家唯一的戰略就是“圍堵/遏制”,但是對中國這個有限修正主義國家來說,交往政策一直是美國對中國戰略的一個主流。
另一個交往政策不能成功的原因在于雙方之間認同存有不能協調的核心沖突,例如領土、主權等沖突,這些核心利益是很難通過交往政策改變的。
雖然交往政策是胡蘿卜先于棒子的政策,但是如果沒有足以威嚇的棒子,胡蘿卜將會流于所謂的姑息政策(policy of appeasement),只有在胡蘿卜與棒子并用的情況下,交往政策才有可能成功。
交往政策可以滿足希望維持現狀的既有強權與不滿足現狀的崛起大國的要求。前者希望通過交往政策約束后者可能出軌的行為,而后者希望能借此改變現狀的秩序。前者因而用利益回報或威嚇來影響后者,使得后者能依照現有國際規范來行事,后者則通常將交往政策視為逐漸和平改變現有秩序的一種工具。
交往政策是美國在冷戰后處理中國政策的主軸。從克林頓政府開始推動與中國的全面交往,一直到奧巴馬政府均沒有改變。對美國來說,全面交往政策不是姑息政策,而是一種帶有約束的積極性政策,其目的就在于促使中國進入西方價值體系,進而使中美雙方都能夠獲益。
中國崛起新的可能性路徑
和平崛起、和平發展一詞原本是為了消弭中國威脅論的表述。在了解西方大國崛起的理論基礎后,我們更希望看到或應該將中國的崛起詮釋為一個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崛起,是一個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后再融合中華文化的另一種文明的崛起。
中華民族有豐富的文明積累,只是近兩百年來在西方文明的巨大壓力下,逐漸喪失了對自己文化的自信。中國傳統的天下秩序觀受到西方西伐利亞國際法主權觀的挑戰,中國傳統的義理觀受到西方的利益觀挑戰,中國傳統的和平觀受到西方權力政治觀的挑戰,中國傳統的社群觀受到西方個人主義的挑戰,甚至中國傳統的幸福觀都遭遇到西方價值觀的挑戰。
文明不可能憑空崛起。首先,中國應該接受西方強權所設定的規范。舉例來說,即使中國不喜歡資本主義,但是在面對資本主義全球化時,也只得選擇接受資本主義的游戲規則。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就是一個典型的成功例子。同樣,即使了解到現代的國際建制與規則幾乎全都是由西方世界所制訂,中國在現階段也應該接受這個現實,中國所能做的也就是在現有的國際建制下,順勢而為、逐漸壯大。
西方面對中國崛起有一個基本性的認知,即當西方無法阻擋中國的崛起時,西方希望中國的崛起能夠按照西方的價值體系、在西方所建立的國際建制和所設定的游戲規中崛起,如此西方才會認為這樣的崛起對世界是沒有威脅與危害的。
西方現有強權的這種看法,或許只對了一部分。西方某些文明價值是好的,但是它們在落實的時候往往出了問題。如果中國按照歷史上九個大國的崛起方式崛起,用權力政治的思維去處理國際關系,用帝國主義的擴張思維去攻城略地,用資本主義的思維去建立生活價值,那么中國只不過是另外一個同一類型的大國崛起,崛起將會給世界帶來與以往大國崛起同樣的災難。
兩岸關系走向與中華崛起
在中國崛起過程中,不能犯下傳統大國通過擴張或崛起來解決內部沖突或矛盾的錯誤。不但要避免制造沖突,還要避免把外部矛盾引向中國,成為世界的矛盾焦點,以確保中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不過,有些事情是無法避免的,例如與越南、菲律賓的南海主權爭議,以及與日本在東海釣魚島的主權爭端,都觸動著中國是否要動武的神經。中國要思考的是,西方以美國為首、日本為輔的戰略思考,是不是期待南海或東海成為對中國崛起發動預防性戰爭的實驗場域?中國如何在沖突與戰爭之間妥善拿捏分寸?
中東的反恐告一段落后,美國逐漸將軍事、外交與經貿重心移至東亞地區,美國“重返亞洲”的具體作為主要通過“前沿布署外交”,強化美國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東南亞國家的雙邊安全聯盟,積極參與區域多邊組織,增加貿易與投資,擴大軍事存在,推廣民主與人權,全面對東亞地區進行權力再平衡的動作,以維持美國在東亞地區軍事、經濟與外交上的領導優勢。
美國對于中國“再平衡”的戰略,或許還不至于讓它主動發動一場“預防性的戰爭”,畢竟在這個21世紀全球相互依存的時代,誰都經不起一場戰爭的折騰,但是會通過與中國周邊地區的共同合作,對中國產生“遏制”的效果。
美國的目的非常清楚,即通過與中國周邊的合作,讓世界產生兩種不同的戰略認知。第一,讓中國威脅論持續在東亞或世界發酵,美國在東亞再平衡戰略講的愈多、做的愈多,愈凸顯出中國對周邊的威脅。如果崛起的中國是和平的,美國為何要將過半數的兵力布署在亞洲?在這樣的語境下,不論是黃巖島或釣魚島的行為,都容易被詮釋成為中國企圖改變現狀的一個威脅性作為。第二,美國反復暗示中國具有威脅性、企圖改變現狀的論述,使中國反復強調自己是和平、愿意接受國際規范的,如此可以促使中國進入約束的國際結構中。這又是美國等西方國家與中國交往戰略的另一個目標,即讓中國的崛起不能跳脫西方的價值體系。
在美國的東亞戰略規劃中,美國與日本、韓國有軍事關系,與東南亞國家亦有密切的軍事往來,澳大利亞是美國在亞太理所當然的伙伴,日本是美國在東亞堅實的盟友,韓國需要美國來處理朝鮮的核武等問題,東南亞國家需要美國平衡它們對中國經貿依存可能發生的被制約感。在這些周邊地區中,有一個是對美國戰略價值最高,但又是美國最不確定的“朋友”,那就是臺灣。
對于美國來說,自1949年以后,臺灣安全長期依附于美國,也是美國東亞戰略中不可或缺的扈從者,美國不會放棄臺灣這枚東亞戰略中的重要棋子。美國一方面用三個公報來約束臺灣不可以走向法理臺獨,另一方面又用《臺灣關系法》來讓臺灣有安全保障感,同時鼓勵兩岸和平交流。這有助于美國對大陸的交往政策,可以輕松地通過臺灣,向中國傳達西方的普世價值,另一方面又賣武器給臺灣,讓臺灣也能成為美國遏制中國大陸的一枚棋子。臺灣多元政治立場下的臺獨主張,也可以被美國用來牽動中國最敏感的那條神經,也可以作為向中國索取報償的籌碼。
美國的兩岸政策非常清楚,它贊成兩岸和平發展,它不容許看到臺灣獨立,但是也不樂于看到中國統一。如果中國統一,美國在東亞的戰略布局就缺了一道裂口,甚而全部戰略必須重新規劃。美國希望一個對美國友好的臺灣能夠繼續存在,它所期望的是兩岸永久分治,亦即永久的維持現狀,這樣最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不過,美國最擔心的也是臺灣,由于兩岸同文同種,自2008年以后兩岸進入大交流時代,一旦兩岸解決了政治爭議,兩岸進入大和解時代,美國的東亞戰略就可能出現漏洞。
兩岸關系對于中國大陸來說,已經不僅是兩岸關系而已,而是涉及到中國大陸是否能夠突破美國在東亞地緣為中國所設置障礙的戰略問題。
臺灣目前的戰略是政治安全依靠美國,經濟利益與大陸結合,在立場上是維持不統不獨,以維持現狀為目標。大陸希望兩岸能夠簽署和平協議,建立軍事互信機制,但是臺灣對于美國《臺灣關系法》的依賴已經成為所有臺灣安全與發展的一部分。中國大陸如果不能夠在兩岸定位與走向上給臺灣提供一個安心與信任的選擇,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臺灣將不容易改變與美國合作的戰略選擇,即一方面配合美國交往政策,另一方面又執行美國對中國的遏制政策。
十八大政治報告中提出,“希望雙方共同努力,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這段文字表明,中共已經理解一國兩制是統一后而非統一前兩岸的政治安排。
針對兩岸和平發展期的政治安排,筆者曾提出“一中三憲、兩岸統合”的主張。兩岸必須在尊重現狀之下,尋求一個既能顧及現狀,又能有助于統一的結構與路徑。目前的法理現狀是:兩岸在主權宣示上相互重迭,兩岸治權均來自于彼此憲法。兩岸若能在此基礎上簽署和平協議,相互承諾不分裂整個中國主權,并相互尊重彼此的治權,那么這個簽署后的和平協議就會成為一份兩岸均必須遵守的憲法性文件。未來有關軍事互信、國際共同參與、經濟、金融,甚至成立相關共同體的協議,均可以成為兩岸第三憲(一組憲法性的文件)的內容。這種兩岸共同建構未來的過程,不再是誰吃掉誰的選擇,唯有這樣才能夠讓臺灣安心地與大陸互動。
“一中三憲、兩岸統合”的結構,通過統合(即中國大陸所說的一體化)機制,兩岸可以在一些政策與事務上共同治理,這對于兩岸政府截長補短,共同為兩岸人民創造福祉有莫大助益。
當兩岸和平協議簽署時,這代表著兩岸的真正大和解,也是兩岸政治關系進一步深化的開始。在中國崛起過程中,這將是關鍵性的一大步,美國無法再利用臺灣來遏制或圍堵中國,美國第一島鏈至此斷裂。另一方面,北京能夠和平處理與臺北的關系,對于中國大陸在國際間去除威脅者的形象以及改變周邊國家態度,也會有正面的功效。
中華文明在崛起過程中的正向作用
西方文化里面有些內容是值得肯定的,例如對人的尊重,強調平等、自由等普世價值,問題在于當這些理念與國家利益結合時,好的價值就成了文化霸權的一些說詞或工具。在善惡二元論、物競天擇與資本主義向外擴張核心依據下,西方往往將它們所信仰的價值與自己的利益結合,強加于其他文化與民族。
西方人創造了民主與自由,但是在大多數的情形下,是在自己封閉的政治國度里面使用,但對于其它國家或地區,特別是會影響到它們的國家利益時,民主與自由的標準就由西方來詮釋。
九個崛起大國關心的是利與力,中國傳統對外關系重視的卻是和與合。從中國的《易經》中可以看出,中華文化強調的是和與合的融合與互補,而不是利與力的沖突。這也是九個大國崛起沒有給世界帶來和平的原因。中華文化中有一些價值內核是西方需要的,舉例來說,“仁”這個概念對于崇信物競天擇論者是陌生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資本主義信仰者無法理解的,“是非存乎一心”、“設身處地”更是西方善惡二元論難以理解的。
礙于篇幅,本文不討論文明崛起的具體內容,大陸的學者對于中國的外交新理念已有研究。如果要想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大國,除了要有強大的物質力量以外,還要有能力在話語體系上占踞主導地位。中國在崛起過程中,應該從哲學層面重新整理一套中華文化的世界觀、秩序觀和價值觀。這并不意味著取代西方的文明價值,而是補充和完善西方的文明價值,告訴西方為何中華文明的若干價值可以豐富或補充西方文明。中國的崛起就是要取得這種話語權與世界秩序的詮釋權。
沒有物質力量不可能成為一個大國,然而只有掌握了話語權與價值體系,才可以堪稱一個主導性的大國。西方大國目前已經出現了若干問題,它們解決問題的方法,無論在處理金融危機方面,還是在解決國際沖突方面,已經開始背離了自己的價值信仰。這是中國的一個機會,也是責任。應該讓西方了解,中國的崛起是一個東方文明的大國崛起,也是對西方文明大國的警醒,更是期望能夠共同攜手為人類創造福祉與和平的崛起。
注釋
Arvind Subramanian, 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 Washington, DC :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1, 1-3.
崔立如:“和平崛起:中國追求現代化的旅程”,《現代國際關系》,2012年第7期。
2001年10月美國國防部公布的四年期國防總檢報告(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2001)視中共為第一假想敵的企圖非常明顯,認為亞洲地區可能出現一個”具有可觀資源的軍事競爭對手”,使美國必須強化在西太平洋及東北亞的反應能力。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September 30, 2001.
紀碩鳴、周東華:《中國新政》,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0年。
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7; Jacek Kugler and A. F. K. Organski, "The Power Transition: A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Evaluation", Handbook of War Studies Unwin Hyman, 1989, 171-194.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Ronald L. Tammen, eds.,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Seven Bridges Press, 2000, 6.
Jack S. Levy, "Declining Power and the Preventive Motivation for War," World Politics, Vol. 40, No. 1(1987), 87.
Alfred Vagts, Defense and Diplomacy: The Solider and the Conduct of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King's Crown Press, 1956, 263.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91.
A. F. K. Organski &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13-63.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94/95), 19(3), 5-49.
閻學通:“和平崛起的分歧、意義及策略”,《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5期。
Paul W. Schroeder, "Alliance 1815-1945: Weapons of Power and Tools of Management" in Klaus Knorr, ed., Historical Dimensions of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s, Lawe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as, 1976 , 227-262.
Michael J. Green and Patrick M. Cronin, The U.S.-Japan Allianc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Washingto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
Randall L Schweller, "Rise of Great Powers: History and Theory", in Alastair Irin Johnsyon and Robert S. Ross ed.,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13.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郭震遠研究員認為:“現有的國際制度、國際規則、國際體系、中國對之不對抗、不挑戰、并對之積極參與、運用和完善,正是在世界深刻而復雜的變化中,順勢而為、塑造與發展中國現代化所必須的、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引自“中國爭取保持和平穩定國際環境的指導原則:對二十字方針的再認識”,《中國評論》,2013年第1期。
郭震遠:“中國爭取保持和平穩定國際環境的指導原則:對二十字方針的再認識”,《中國評論》,2013年第1期。
張亞中:《統合方略》,臺北:生智出版社,2010年;張亞中:“兩岸和平發展期應是統合期:以統合深化認同與互信”,《中國評論》,2013年第1期。
秦亞青:“中國文化及其對外交決策的影響”,《國際問題研究》,2011年第5期;秦亞青:“時代觀、安全觀與秩序觀——中國外交新理念的思想內涵”,《國際政治研究》,2003年第1期。
責 編/凌肖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