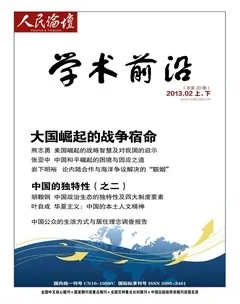在毀滅與和平之間
摘要 戰爭在某種意義上是國家對自己命運的賭博,戰爭決定國家命運成為一條歷史規律。考察中西方歷史,雅典、馬其頓、羅馬、英國、日本、美國等國家通過戰爭實現了崛起,羅馬、英國經過戰爭維持了權勢現狀,而羅馬、法國、英國、日本則因為戰爭而衰落。當今世界出現了一些有利于擺脫戰爭的因素,這些因素要求國家在發動戰爭前對利益訴求和代價進行權衡。
關鍵詞 戰爭 大國命運 崛起 衰落
人們考察國際關系史時會發現:戰爭在某種意義上是國家對自己命運的賭博。克勞塞維茨曾說過:“戰爭是充滿偶然性的領域。人類的任何活動都不像戰爭那樣給偶然性這個不速之客留有這樣廣闊的活動天地,因為沒有一種活動像戰爭這樣從各方面和偶然性經常接觸。偶然性會增加各種情況的不確定性,并擾亂事件的進程。”①在與外部世界矛盾沖突難以妥協,在運用經濟、外交等和平手段之后仍無法達成妥協時,許多國家便直接訴諸武力,把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押上了戰爭的“輪盤賭”。考察歷史上大國與戰爭的關系,大致不外乎三種情況:一是通過戰爭崛起;二是戰爭使之衰弱;三是經過戰爭維持權勢現狀。雖然結果類型很簡單,但每一種類型都有其自身特點和規律。即使是同種類型,每場戰爭也各有其獨特的經驗和教訓,并且會給后人不同的啟示。對于希望和平崛起的中國而言,如何擺脫傳統的戰爭崛起的歷史模式,探索建設21世紀新型大國關系,這些歷史經驗特別重要。因為,如果我們不深入研究戰爭,我們又怎能獲得持久的和平?
從戰爭中崛起的大國——雅典、馬其頓、羅馬、英國、日本、美國
首先來考察通過戰爭大國興起的情形。這種情況在中外歷史上舉不勝舉,比較典型的是雅典的崛起。根據富勒的觀點,雅典是通過薩拉米斯海戰的勝利而崛起的。這場海戰的勝利確立了雅典城邦國家的海上霸權地位,也是雅典的對手波斯帝國從攻勢轉成守勢的轉折點。這場勝利的結果是雅典確立了對波斯海權的絕對優勢,使得波斯陸軍后勤補給線因隨時會遭希臘艦隊的截斷而無法展開進攻,同時也確立了雅典對其他城邦的海上優勢,進而控制了愛琴海和東地中海地區的貿易權。軍事強大、經濟繁榮、外交老練、文化發達、產業興旺、宗教信仰堅定、尚武簡樸的健康風氣、自由民主價值觀的傳播構成了雅典崛起的內涵,使得雅典的崛起具有國家與文明同步的特征,它既是一個國家的崛起,也代表著一種文明的崛起。薩拉米斯的勝利如同強烈的催化劑,使得雅典國家和希臘文明的諸方面更趨鞏固和完善。
公元前449年,希臘聯軍在塞浦路斯島徹底擊敗波斯軍隊后,希臘、雅典和波斯簽訂卡里阿斯和約,此后在不到20年的時間內,希臘半島逐漸陷于內戰,這就是希臘世界里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在雅典、斯巴達、底比斯競相角逐、相互攻伐而力量衰退之際,北方小邦馬其頓乘機崛起,統一了全希臘。馬其頓國王腓力二世(Philip II of Macedon)的長遠戰略意圖是通過控制赫勒斯龐特海峽(今達達尼爾海峽),控制住希臘與黑海之間的谷物運輸線,并將“亞洲門戶”鑰匙拿到手,逼迫全希臘諸城邦在馬其頓的領導下,進攻一直在希臘半島上挑撥離間充當“離岸平衡手”的波斯帝國。
為阻止腓力二世的雄心,雅典、底比斯、科林斯等組成聯軍,于公元前338年同馬其頓聯軍進行了歷史上著名的喀羅尼亞會戰,結果腓力二世大獲全勝,實現了上述的戰略目標,迫使除斯巴達之外的所有希臘城邦加入馬其頓為盟主的科林斯同盟,繼而進攻波斯帝國。這與當今工業社會里,誰控制了石油通道誰就是事實上的霸主類似。馬其頓崛起還有個重要的地緣政治優勢,它崛起于遠離希臘世界沖突中心的邊緣地帶,避免了像雅典、斯巴達那樣過早地消耗掉自己的元氣。
羅馬是通過對周邊國家的一系列戰爭崛起的,其中關鍵對手是老牌海上強國迦太基。在馬漢看來,在戰勝迦太基的過程中,羅馬人奪取地中海制海權在戰略上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海權在布匿戰爭中是一種決定性的因素。”②從這一角度出發,第一次布匿戰爭中,發生在公元前260年的米列海戰、公元前256年的埃克諾穆斯海角海戰以及公元前241年的埃加迪群島海戰,對羅馬國家的崛起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聯系第二次布匿戰爭來看,最初的三場海戰勝利不僅奠定羅馬獲勝的基礎,而且也使迦太基一系列陸戰勝利成果化為烏有。
值得一提的是羅馬人的海戰戰術細節,為把羅馬士兵善于單兵格斗的陸戰優勢帶到海上,羅馬人巧妙地發明了一種叫做“烏鴉”的頂端裝有長鐵釘的吊橋,前甲板上固定一支柱,吊橋系在支柱上,可左右前后放下,海戰時逼近對方戰艦,吊橋重重地放下,死死鉤住對方艦只,羅馬士兵蜂擁通過吊橋進入對方艦船上白刃戰,俘獲或燒毀之。這一戰術是羅馬取得海戰勝利的關鍵,由此驗證了“細節決定歷史命運”的格言。
在英國崛起中,關鍵一戰發生在1588年7月21日~7月29日。為同老牌海上霸主西班牙爭奪海洋控制權,英國艦隊同強大的西班牙“無敵艦隊”在英吉利海峽展開大戰,英國艦隊利用航海技術、側舷交戰、火炮射程遠諸方面的優勢,在荷蘭艦隊的配合下,經過幾次交戰和追擊,幾乎全殲“無敵艦隊”。此戰打破了西班牙對海洋的控制,對美洲、亞洲殖民地的財富掠奪和對東方貿易的壟斷,導致西班牙失去了世界財富的控制權,很快衰落下去,而英國則邁出了走向海上霸權的第一步。“無敵艦隊”的覆沒雖沒有在精神上徹底摧毀西班牙的自信,卻喚醒了英國人的海權意識:“盡管是小國,其資源和本國的權力都極為有限,可是只要他們控制了海洋,則仍然照樣可以贏得和守住巨大的海外領土。反而言之,即令是泱泱大國,雖然他們是可以在海外獲得廣大的土地,可是除非他們能夠控制住海洋,否則一旦面臨著嚴重的挑戰,即會感到無法應付了。”③因此,從近代海權意識啟蒙而言,“西班牙艦隊的失敗,好像是一個耳語一樣,把帝國的秘密送進了英國人的耳中。在一個商業的時代中,贏得海洋要比贏得陸地是比較更為有利,也許在一五八八年,對這一點還并無太明確的認識,可是在以下的一個世紀中,這個耳語的聲音就變得越來越大了,而終于成為每一個英國人的呼聲。”④
日本也是在一連串對外戰爭的硝煙中崛起的,關鍵一戰是1894年9月17日日本聯合艦隊對中國北洋艦隊的黃海大東溝海戰。在此戰役中,中國北洋艦隊先后損失5艘戰艦,日本則一艘未沉。海上決戰結束后,日本完全控制黃海制海權,進而海陸并進,把北洋海軍消滅在威海海軍基地內,摧毀了清政府的作戰意志。甲午戰爭后,中國割地賠款,日本版圖擴大,索取了巨額戰爭賠款,進一步發展軍工企業,并完成資本主義金融體制改革。日本的勝利為后來在遠東擊敗俄國、特別是在對馬海戰中全殲俄國第二太平洋艦隊奠定了基礎。
還是“細節決定歷史”!對于這場決定東亞兩國命運的海戰,筆者曾專門對中日雙方參戰軍艦100毫米口徑以上主戰火炮的射速進行過詳細統計,參戰的兩國艦隊一小時可發射的理論數據為:日方為46242顆炮彈,中方為4372顆炮彈,火力射速比10.5∶1,日方是中方的10倍有余,盡管中日雙方參戰軍艦噸位差別不大,日方為37510噸,中方為34466噸。⑤以關鍵的開戰一小時內(當時平遠、廣丙尚未趕到戰場)計算理論上的射彈量,聯合艦隊為46242顆炮彈,北洋艦隊為2368顆炮彈,射速比是19.5∶1,日方火力幾乎是中方的20倍。雖然實戰中的射彈量與理論射速量有較大差距,但火力強弱懸殊的性質不會改變。日方“第一游擊縱隊”4艦在局部戰區內對我兩弱艦“超勇”、“揚威”形成主戰火炮38門對12門——即3.1∶1的數量優勢,而射速上更是形成44∶1的超絕對優勢,即射彈量理論數據為4896發對110發(實戰中雙方雖各打折扣,但火力極為懸殊格局不會變),理論上日軍火力44倍于清軍,遂解35分鐘內擊沉“超勇”、打殘“揚威”之謎底。另一則比較是100毫米口徑以上主戰火炮一小時理論發射數據:“吉野”為7200發,整個參戰的北洋艦隊僅為4372發,“吉野”一艘軍艦的火力射速就是整個北洋艦隊的1.6倍。這就可以理解民族英雄鄧世昌為何選擇向“吉野”撞擊,以期與之同歸于盡的心理了。⑥
作為戰敗的一方,中國在決戰時刻海軍火力不強,是清廷政治腐敗殃及海軍建設所致,非戰之罪也。馬漢認為:誰控制制海權即掌握了歷史命運,制海權由一場決定性海戰勝負決定,決定性海戰勝負由交戰雙方戰術火力強弱決定。⑦中日海軍黃海決戰以及后來半個世紀里兩國的發展差距再次驗證了馬漢的觀點。
有關美國崛起的幾個主要因素,筆者在《宗教、制度和文化帝國主義》一文做了初步探討,本文做點補充。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在老牌強國相互消耗得精疲力盡的關鍵時刻,投下自己重重的砝碼,并促使世界的天平朝著對自己有利的一側大角度傾斜,每一次擲下砝碼都極大地提升了美國的世界地位。
從兩次世界大戰會戰的角度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諾曼底會戰是美國登上世界霸權舞臺的標志性一戰。諾曼底登陸的成功,完成了置納粹德國于死地的東西夾擊的戰略勢態,使殘破的英國和被打趴下的法國起死回生,而西線戰場的開辟迫使德國從東線分兵,給在東線僵持的蘇聯注射了一劑強心針,蘇聯則不失時機直取柏林。歷史表明,美國人在諾曼底賭局中投下的砝碼把自己拋上了世界霸主坐席。
通過戰爭維持霸權——羅馬、英國
公元451年,在今天法國的沙隆地區(Chalons-en-Champagne),西羅馬帝國名將埃提烏斯(Aetius)和西哥特國王狄奧多里克(Theodoric)的聯軍同阿提拉率領的匈奴大軍展開會戰。“這是歷史上最為血腥的戰役之一:據說有16.2萬人陣亡,其中包括狄奧多里克。”⑧在這場歐洲與亞洲勢力的對決中,阿提拉的匈奴聯軍戰敗,暫時向東方退卻,標志著龐大的匈奴帝國已成強弩之末。誠如富勒所說:“這不是一個羅馬人的勝利,也不是一個條頓人的勝利,而是兩個民族聯合起來,對抗亞洲人的勝利,正好像薩拉米斯之戰的勝利是雅典人和斯巴達人對于波斯人的共同勝利一樣。這又是另一次東西方之間沖突、歐亞之間的沖突。歐洲人又是能夠暫時捐棄私怨和舊嫌,以來對抗一個共同的強敵。”⑨
沙隆會戰雖然勝利了,但對羅馬帝國來說,戰前戰后可謂命懸一線,戰前為同宿敵西哥特人達成聯盟而費盡心機,生怕西哥特人與匈奴人聯手滅了自己。據有關史料記載,戰爭取勝后,本來可徹底擊潰阿提拉的匈奴聯軍,但埃提烏斯惟恐盟友西哥特人乘機做大取代匈奴人成為羅馬帝國新的勁敵,故不敢全殲匈奴聯軍,被迫放虎歸山。于是,埃提烏斯提醒繼任的西哥特國王多里斯蒙德,他的兄長可能覬覦王位,后者撤離戰場回軍爭奪王位去了,埃提烏斯也讓戰敗的阿提拉從容退卻。留著已被擊敗的對手,以牽制在戰爭中崛起的同盟者,不愧為深謀遠慮。埃提烏斯利用沙隆之戰成功地達到了解除匈奴人威脅、讓西哥特人與匈奴人相互牽制的意圖,使羅馬帝國得以勉強維持搖搖欲墜的霸權。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英國總算保住原來歐洲大陸“離岸平衡手”的地位。英國的外交謀略可謂爐火純青,當崛起的德國覬覦歐洲霸主地位時,英國成功地與法國“連橫”,并說服俄國入伙,在東面鉗制德國。大戰爆發后,英國利用自己對海洋的控制,拼命向美國貸款購買其大量物資,成為美國的債務人,以巨大的債務誘惑把美國拽入自己戰壕。英國在外交上縱橫捭闔,巧妙地調動了世界幾股勢力為自己所用,終于擊敗挑戰對手,沒有從原來的權力位置上跌落下來。
英國持“光榮獨立”的外交政策,完全可以不介入歐洲大陸的戰爭,比利時中立被破壞只是一個借口而已,真正的原因是保住自己在歐洲的權勢,阻止快速崛起的德國挑戰自己,“我們必須在我們衰落之前進行戰斗”。⑩因此,根據戰爭的“窗口理論”,正在衰落的強大遇到正在崛起的弱小,就會誘發前者發動戰爭。所以,可以置身局外的英國顯然受到這種誘惑,不愿放棄這一“機會性窗口”,打了一場預防性戰爭。
英國能在一戰中享受其外交努力的成果,軍事上的關鍵一戰是1914年9月6日爆發的馬恩河會戰。德軍當時正按照預先的“施里芬計劃”穿過中立的比利時,向法軍主力深遠后方實施大迂回包圍運動。雖然德軍進展順利,但兵力不足的弱點卻暴露了出來,德軍不僅做不到“讓右翼末梢袖拂海峽”,連已經縮短的右翼都露出了大豁口,連續敗退的英法聯軍于馬恩河一線突然返身側擊德軍右翼,迫使德軍停止迂回行動,“施離芬計劃”六星期內擊敗法國,然后將全部主力東調對付俄國的戰略徹底破產。馬恩河會戰使德國陷于兩面作戰的尷尬境地,英國外交努力的成效進一步得到發揮。而俄國不等完成戰爭動員,即大舉進入東普魯士,終于構成英國夢寐以求的歐洲戰場的東線,德國則陷入東西夾擊、難以取勝的戰略困境。馬恩河會戰的勝利也為英國人取得美國的支持贏得了時間,為一戰最終勝利奠定了第一塊基石。一戰的勝利讓“日不落帝國”的米字旗繼續在全世界飄揚了一段時間,直到二戰后被星條旗所取代。
在戰爭中衰落的大國——羅馬、法國、英國、日本
公元378年8月9日,發生了標志著羅馬帝國衰落的會戰,史稱“亞德里亞堡會戰”。這天是羅馬帝國黃昏的開始,地點在今天土耳其埃迪爾內省會。當時羅馬帝國因太龐大而東西分制,東羅馬皇帝瓦侖斯(Valens)御駕親征,率東羅馬全軍主力同西哥特人展開決戰,激戰中,菲烈特根(Fridigern)統領的西哥特人、匈奴人及阿蘭人發揮了騎兵的機動性,全殲了以笨重僵化的“方陣”迎戰的羅馬軍團,皇帝瓦侖斯逃命時死于亂軍中,千年羅馬帝國從此一蹶不振,走向衰敗。此戰損失之巨堪比594年前(公元前216年)羅馬人在“坎尼會戰”時全軍覆沒。不過那時的羅馬民族處于上升時期,很快克服了危機,走向全盛。而“亞德里亞堡會戰”中的羅馬民族已經承平日久、老邁頹唐,再無重振雄風之力。戰后,西哥特人與東羅馬帝國簽訂和約,西哥特人取得色雷斯棲息地,充任羅馬帝國軍隊的兵源。至公元395年,狄奧多西大帝(Theodosius the great)去世,哥特人再度叛亂,與組成羅馬軍隊的哥特人聯合,于公元411年攻陷羅馬首都,帝國分崩離析。
亞德里亞堡會戰既是決定大國命運之戰,也是改變歷史進程之戰。讓人感到驚訝的是,雙方決戰之前完全處于戲劇性的誤判中。之前,定居在德涅斯特河與多瑙河之間的西哥特人被匈奴人打敗,蜂擁逃至羅馬邊境,哀求羅馬人讓其進入境內,發誓世世代代忠于羅馬,愿為羅馬帝國永遠守邊。羅馬皇帝答應了,但需交出武器入境。西哥特人為以防萬一,買通羅馬邊境官兵,私藏武器渡多瑙河進入帝國境內。羅馬吏治腐敗,對入境的西哥特人敲詐勒索,搶劫奸淫,無惡不作,西哥特人不堪忍受,仇恨日生。為防生變,羅馬方面擺下“鴻門宴”企圖誘殺菲烈特根,卻讓其逃脫,羅馬境內的西哥特人全面叛亂。這時西哥特人完全是喪家流竄、失魂落魄、夾雜著老弱婦孺的“流亡部落”狀態,即便反叛后,還幾次懇求與羅馬人和談,精神處于絕望狀態,毫無戰勝羅馬軍隊的信心,而羅馬的瓦侖斯皇帝也充滿了一舉撲滅西哥特人的自信,以至西哥特人被自己猝然取得的勝利弄得不知所措。
如果說這場會戰有什么教訓的話,那就是羅馬帝國在承擔拯救失去家園的西哥特人的“大國的責任”時,沒有意識到由于自身的腐朽墮落,早已喪失了這種承擔的能力。亞德里堡戰場的羅馬軍團,也早已不是500多年前坎尼戰場上吃苦耐勞、簡樸尚武的羅馬公民,耀眼頭盔、威武鎧甲包裝著好逸惡勞、貪圖享受之徒。于是,世界歷史上出現了罕見的戲劇性場面:一方是帶著盲目自信的羅馬帝國,另一方是沒有感覺到自身強大爆發力的西哥特人,雙方在亞德里亞堡戰場相遇,在一場“反客為主”的歷史游戲中,西哥特人在絕境中崛起,而羅馬人卻撞上了自己的末日。幾百年前,尚武進取的羅馬人從坎尼會戰慘敗中頑強地站了起來,幾百年后,生活墮落的羅馬人在亞德里堡災難中衰敗。
近代法國的衰落源于拿破侖在滑鐵盧會戰的失敗。由于拿破侖戰爭的最后破產,法國從此成為世界二流國家。在滑鐵盧之前,拿破侖的天才曾讓法國短暫地品嘗過一流強國的滋味。拿破侖的失敗首先是法國地緣政治的惡劣所致,法國一方面要對付來自東面的俄國、普魯士,另一方面要對付強大的英國海軍。法國的實力不足以同時應付大陸和海上的壓力,其外交戰略似乎也缺乏想象力,沒能創造各個擊破對手的戰略形勢以彌補實力的不足,最終造成向兩個方向同時出擊而顧此失彼的局面。此后,法國只能放棄海權爭奪,在一戰、二戰中與英國結盟,以同大陸國家勉強抗衡。
拿破侖戰爭前期勝利得益于實行普遍義務兵役制(它于1793年法國大革命期間頒布),法國軍隊因此能夠得到源源不斷的兵源補充;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法國最早解決了火炮的各種技術問題,法國工程師格里博瓦爾“成功地建立了一支強大的野戰炮兵部隊,這支部隊能夠跟上行進的步兵,因而能夠在戰斗中起主要的作用”。格里博瓦爾還解決了炮彈爆炸的引信技術,野戰炮兵進入軍隊編制,實現了野戰炮兵的戰場機動,“創造了真正可流動性的大炮”。那些排著密集隊形的步兵方陣,敲打著軍鼓前進的對手們,成為拿破侖野戰炮兵的最佳轟擊目標。拿破侖給后世留下了一句名言:“炮兵是戰爭之神。”不過,戰爭也是最好的戰術交流途徑,法國的對手們很快學會了如何使用野戰炮兵,拿破侖的戰場優勢漸漸失去,在滑鐵盧和萊比錫戰場,拿破侖連連失敗,無法再現過去的輝煌。
英國通過對拿破侖戰爭的勝利,爭取到了制約歐洲各大勢力的“離岸平衡手”地位。在這個位置上,英國勉強地維持住了自己的強勢地位。進入20世紀后,英國在對付取代法國崛起的德國時,漸漸感到力不從心。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英國同被自己打敗的法國聯手,和俄國一起在西方戰場形成一個僵持局面。一戰德國戰敗,英國消耗很大,但仍勉強維持其“離岸平衡手”身份。
回溯歷史可以發現,英國失去大國地位的軍事標志是二戰期間的敦刻爾克大撤退。作為“離岸平衡手”,英國在二戰之前一直左右歐洲局勢。拿破侖戰爭以來,英國在軍事干預歐洲的過程中,軍隊從未被趕出過歐洲大陸。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軍一直是歐洲戰場的主力,它借助美國贏得歐洲戰場的勝利,戰后美國從歐洲撤軍,英國似乎很自信能夠繼續立足英倫三島,施展“連橫”手段同法國一起控制歐洲。然而,希特勒德國的重新崛起使英國漸感力不從心。第二次世界大戰一開始,英國軍隊迅速被德軍擊敗,在敦刻爾克被趕下海,戰后又因為前蘇聯的崛起,英國無力制衡,喪失了“離岸平衡手”地位。美國開始長期駐軍歐洲,取代英國制衡歐洲大陸,英國從一流強國跌落至二流國家的位置。
盡管丘吉爾在自己回憶錄里,用詩一般的語言把敦刻爾克潰退描繪成“最光輝的時刻”,但現實卻無情地捅破這虛榮的粉飾,敦刻爾克的倉皇敗退是“日不落帝國”隕落的開始,而諾曼底登陸更凸顯了這種隕落:英國只有攀附美國才能重返歐洲,沒有美國就會被人踢下大海。
必須指出,文明興起與國家興起是兩碼事,二者有時合二為一,有時各行其道。雅典興起也是希臘文明的興起,但雅典的衰落卻不是希臘文明的衰落,因為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從雅典人手中接過了文明的火炬,繼續發揚光大。同樣,英國衰落了,卻把現代西方文明的接力棒傳遞給了美國,西方文明對世界其他文明仍然保持著強勢地位。
從19世紀末發動對外戰爭到20世紀中葉無條件投降,日本在半個世紀里經歷了急速膨脹到猝然破碎的暴起暴落。日本的失策在于沒有掌握好崛起過程的節奏,在用百米跑的速度去完成馬拉松距離,終因體力不支,中途一頭栽地。1941年之前,日本在差不多半個世紀里,被自己的一連串勝利所迷惑,在取得一連串勝利的同時,它也把自己系于一條脆弱的生存鏈條上,其中任一個環節的破裂都會導致生存鏈條的斷裂,從而墜入深淵。“七七事變”后,日本在中國陷入僵局,其擴張勢頭也就成了強弩之末,就在中日雙方精疲力竭時,美國投注了置日本于死地的砝碼。1941年夏,“根據陸軍部的研判,日本想結束在中國的戰爭還要有三年的時間”。但以全面戰爭計算,戰略石油儲備僅能維持戰場一年半,兩年后日本將耗盡所有石油儲備,其他戰略物資如橡膠、錫、鎳、銅等也極度缺乏,需要靠美、英等國貿易來解決。美國在此節骨眼上斷然對日本實施經濟制裁、石油禁運,要求日本放棄“南進政策”,并從中國撤軍,恢復到“九一八事變”前狀態。日本完全陷入了被動,要么拱手交出“九一八事變”后到手的巨型戰利品,要么搶占東南亞戰略資源產地,這就意味著同強大的美、英開戰。日本對前一選項無論如何也不甘心,而后一選項則要冒滅頂之災的風險。日本為不放棄到手的“贓物”,最終選擇了對美、英開戰,一廂情愿地企圖在對美作戰取得局部勝利后,與美國達成有利于自己的妥協。這樣日本就把國運押上了軍事賭局。這一過程表明,日本在崛起過程中沒有把握好一張一弛、進退緩急的節奏,急速擴張變成了呆板的機械運動,不可抑制地以有限的實力同時向數個方向出擊,最終在同中、美、蘇、英同時對抗中遭受滅頂之災。
在同美國的一系列海上作戰中,決定日本命運的毫無疑問是中途島海戰。美國海軍五星上將尼米茲認為:“這是最終決定日本命運的消耗戰的一個序幕。這次海戰是太平洋戰爭的一個轉折點。”在這場決定20世紀亞洲命運的會戰中,歷史進程又被兩個細節所左右,一是美國破譯了日本海軍的密碼,二是美國海軍轟炸機群借助云層掩護,隱蔽飛臨日本聯合艦隊上空穿云而出,“正好在日本航空母艦艦隊無法還手的恰當時刻來到”。日軍猝不及防,“赤城”、“加賀”、“蒼龍”、“飛龍”等主力航母被擊沉,美國海軍很快奪取了太平洋制海權。海洋國家命系制海權!日本的脊梁骨在中途島被美國打斷后,宣告了日本戰爭冒險徹底破產,也注定了日本短短半個世紀暴起暴落的命運。
歷史經驗證明,以往的大國崛起最終都以戰爭方式來確定,這似乎成了歷史的規律,任何大國都無法擺脫這一歷史宿命。當人類愛好和平的主觀愿望面對這一歷史宿命時,幾乎無能為力,因而,面對千年的歷史,難免滋生絕望之情。對于當今世界來說,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兩個重大因素:一是世界經濟體系一體化基本形成,二是毀滅人類的核武器出現。前者屬于康德認為的戰爭的天敵——“商業精神”,后者是抑制戰爭的毀滅性武器,這兩個前所未有的因素讓“國家們”用“商業理性”武裝頭腦,進行戰爭的成本計算,在發動戰爭的利益訴求與同歸于盡之間進行權衡,在毀滅與和平之間進行選擇。如此環境下,未來的大國崛起能否擺脫戰爭的宿命?也許人們不至于完全絕望。
注釋
[德]卡爾·馮·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第一卷),軍事科學院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69頁。
[美]A·T·馬漢:《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安常容等譯,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8年,第13頁。
[英]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第二卷),鈕先鐘譯,軍事科學院內部參考,1980年,第37、37、315頁。
另一說法是中方為34420噸,日方為36771噸(不包括“西京丸”),參見宗澤亞:《清日戰爭1894—1895》,北京:世界圖書出版社,fcFASq5ep3mJIFavxswtfqElstseWKPy7V9g/y5VYiI=2012年,第54頁。
倪樂雄:《文明轉型與中國海權》,上海:文匯出版社,2010年,第99頁。
馬漢這一觀點由美國研究馬漢的專家羅伯特·西格轉述為:“即獲得制海權或控制了海上要沖的國家就掌握了歷史主動權。……艦隊或軍隊在爭奪霸權中關鍵戰役勝負的大小與它們取得的戰術火力集中的成敗程度相一致。”見[美]羅伯特·西格:《馬漢》,劉學成等編譯,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第194頁。
[美]威爾·杜蘭:《世界文明史·信仰的時代(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9年,第56頁。
[美]斯蒂芬·范·埃弗拉:《戰爭的原因》,何曜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1、89頁。
[美]巴巴拉·W·塔奇曼:《八月炮火》,上海外國語學院英語系翻譯組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年,第35頁。
[美]麥尼爾:《競逐富強——西方軍事的現代化歷程》,倪大昕、楊潤殷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6年,第173、174頁。
[英]溫斯頓·丘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2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75年。
鈕先鐘編著:《西洋全史·第二次大戰》, 黎東方校訂,北京:燕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第378頁。
[日]服部卓四郎:《大東亞戰爭全史》(第1冊),張玉祥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229頁。
[美]C·W·尼米茲:《大海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海戰史》,趙振愚、殷憲群等譯校,北京:海洋出版社, 1987年,第313頁。
[日]外山三郎:《日本海軍史》,龔建國、方希和譯,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第155頁。
[英]亨利·莫爾:《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重大戰役》,尚鋼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第196頁。
[德]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127頁。
責 編/樊保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