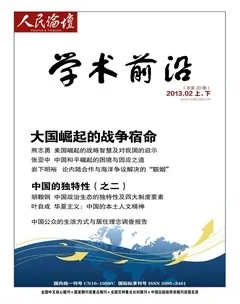中國古代王朝崛起的戰(zhàn)略精義
摘要 在中國歷史上,戰(zhàn)爭是實現(xiàn)王朝崛起的普遍模式。要順利達(dá)成武力崛起的目標(biāo),關(guān)鍵在于高明與卓越的戰(zhàn)略指導(dǎo)。在秦漢王朝崛起中,《漢中對》、《隆中對》、《商君策》、《客卿對》、《平吳疏》等在具體戰(zhàn)爭中具有關(guān)鍵的戰(zhàn)略指導(dǎo)意義,它們或全面分析戰(zhàn)略形勢,或高明把握戰(zhàn)略時機,或合理制定戰(zhàn)略預(yù)案,或兼而有之。全面總結(jié)古代王朝崛起戰(zhàn)略指導(dǎo)方面的經(jīng)驗教訓(xùn),可從中汲取于當(dāng)今國家強盛有益的智慧與啟迪。
關(guān)鍵詞 秦漢時期 戰(zhàn)爭 王朝崛起 戰(zhàn)略指導(dǎo)
戰(zhàn)爭是實現(xiàn)王朝崛起大業(yè)的基本模式
考察整個中國歷史,我們發(fā)現(xiàn),任何王朝的創(chuàng)立與崛起,其進程、規(guī)模、形態(tài)以及影響作用雖各有差異,但它們都呈示出一個有共性的基本模式:憑借或運用必要的武力,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摧毀對手的抵抗意志,乃是根本(也可以說是唯一)的途徑。換言之,希望踐履孫子所說的“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原則,以和平的方式來完成國家統(tǒng)一和王朝崛起,往往只是理想的追求而很難成為現(xiàn)實的選擇,除了極其個別的例子外(如北宋初年,割據(jù)浙江一隅的吳越懾于北宋強大兵威而被迫獻(xiàn)地歸附),都離不開武力。顯然,在中國歷史上,“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只能算是一種理論上的選擇,并不具有普遍意義。因為它只有在一方處于絕對優(yōu)勢,另一方處于絕對劣勢,且劣勢一方又因各種各樣的原因喪失了抵抗意志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出現(xiàn)。遺憾的是,這樣的現(xiàn)象極其罕見。相反,通過武力方式實現(xiàn)王朝崛起成為最普遍的模式。對此,歷代決策者都有十分清醒的認(rèn)識,他們雖然常常聲稱“傳檄而定”、“不戰(zhàn)而下”等,但這僅僅是作為鼓舞士氣、瓦解敵方的口號而已,其真正的注意力始終置放在如何運用武力粉碎敵方抵抗,達(dá)到王朝崛起目標(biāo)上。
在依憑武力完成國家統(tǒng)一和王朝崛起的根本前提下,決策者往往還根據(jù)不同的形勢和需要,選擇兩種武力運用程度有所差異的基本手段,具體指導(dǎo)和推動這個進程。一是所謂的“無限戰(zhàn)爭”(絕對戰(zhàn)爭),即以純粹的戰(zhàn)爭方式,毫不妥協(xié)地發(fā)起最堅決的攻擊,將敵人予以徹底的消滅,“毀其國,墮其城”,實現(xiàn)既定的目標(biāo)。楚漢戰(zhàn)爭中,劉邦堅持“窮寇必迫”的戰(zhàn)略方針,通過垓下會戰(zhàn),逼使西楚霸王項羽自刎烏江;東漢劉秀派遣大軍在成都城下與公孫述軍隊鏖戰(zhàn)多日,殲敵主力,最終平定巴蜀,完成全國統(tǒng)一;隋王朝起兵50余萬,兵分八路,分進合擊,粉碎陳朝的抵抗,攻入其都建康(今南京),俘獲陳后主;等等。這些都是“無限戰(zhàn)爭”在國家統(tǒng)一和王朝崛起進程中運用的典型例子。二是“有限戰(zhàn)爭”(可控戰(zhàn)爭),即“因剿寓撫”,以強大的武力為后盾,以軍事打擊為主導(dǎo),政治招降為輔助,以減少戰(zhàn)爭的傷亡,達(dá)到“兵不頓而利可全”的效果。在具體的操作過程中,采取先戰(zhàn)后和,以戰(zhàn)促和的手段,迫使對手放棄絕望的抵抗,完成王朝崛起的大業(yè)。這方面較顯著的事例很多,如:魏滅蜀漢之役中,鄧艾大軍在綿竹消滅諸葛瞻之部后,逼迫后主劉禪自縛出降;西晉滅吳之役中,晉軍連戰(zhàn)皆捷,勢如破竹,兵臨建業(yè)(今南京市),迫使吳主孫皓分遣使者奉璽綬向晉軍統(tǒng)領(lǐng)王渾、王浚、司馬伷乞降,并最后面縛輿櫬,親至王浚軍門投降。然而,無論是“無限戰(zhàn)爭”也好,“有限戰(zhàn)爭”亦罷,武力及其正確運用在王朝崛起大業(yè)完成過程中所起的關(guān)鍵性作用,乃是毋庸置疑的。西漢陸賈言“逆取順守”,所謂“逆取”,就是以武力完成崛起,這一點自古至今,概莫能外。
要順利達(dá)成武力崛起的目標(biāo),關(guān)鍵在于戰(zhàn)略指導(dǎo)的高明與卓越。所謂“戰(zhàn)略”,從狹義的概念說,便是指導(dǎo)戰(zhàn)爭全局的方略,其中包括戰(zhàn)略條件的分析、戰(zhàn)略方針的制定、戰(zhàn)略原則的確立、戰(zhàn)略方向的選擇、戰(zhàn)略時機的把握、戰(zhàn)略手段的運用,等等。王朝崛起與戰(zhàn)爭勝負(fù)息息相關(guān),而這類戰(zhàn)爭都是具有全局性意義的軍事行動、軍事戰(zhàn)略,對于從事王朝崛起戰(zhàn)爭無疑起著提綱挈領(lǐng)、總攬一切的指導(dǎo)作用。以下,我們僅以秦漢兩晉的歷史為對象,來討論戰(zhàn)略指導(dǎo)的得失及其與王朝崛起戰(zhàn)爭的關(guān)系。
正確判斷戰(zhàn)略形勢
綜合準(zhǔn)備充分是實現(xiàn)王朝崛起的基本前提,然而,它與王朝崛起的最終實現(xiàn)之間并不能簡單地劃等號,只是為王朝崛起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要把這種可能性轉(zhuǎn)變成為現(xiàn)實,歸根結(jié)底,則要通過正確的主觀指導(dǎo)下的戰(zhàn)爭實踐去實現(xiàn),戰(zhàn)略指導(dǎo)的正確與否非常關(guān)鍵。而戰(zhàn)略指導(dǎo)是否高明,首先取決于戰(zhàn)爭決策者對整個戰(zhàn)略形勢的判斷。綜觀秦漢歷史上大獲成功的王朝崛起戰(zhàn)爭戰(zhàn)略,其所具有的一個共同特征,就是戰(zhàn)略決策者能夠知彼知己,預(yù)見勝負(fù),對統(tǒng)一戰(zhàn)爭的整個格局、形勢以及前景有明確無誤的判斷。楚漢戰(zhàn)爭時期,韓信的《漢中對》有關(guān)當(dāng)時戰(zhàn)略形勢的分析與判斷,可謂這方面的典范之一。
秦王朝的殘暴統(tǒng)治被推翻后,出現(xiàn)了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局面,群雄中以西楚霸王項羽與漢王劉邦兩大集團實力最強,他們?yōu)闋帄Z全國統(tǒng)治權(quán),展開了殊死的斗爭,揭開了長達(dá)四年的楚漢戰(zhàn)爭的帷幕。鴻門宴之后,雄心勃勃的劉邦集團不甘心困居于巴、蜀、漢中一隅,他暫時的退讓是為了以屈求伸、以退為進,等待時機成熟,“還定三秦”,再圖天下。而項羽集團的政策失誤和戰(zhàn)略上的麻痹,則給劉邦提供了死灰復(fù)燃、東山再起的機遇。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韓信適時地向劉邦進獻(xiàn)了千古戰(zhàn)略名對——《漢中對》。《漢中對》的邏輯起點,是韓信出于轉(zhuǎn)化戰(zhàn)略優(yōu)劣態(tài)勢,幫助劉邦擺脫被動,爭取戰(zhàn)爭主動權(quán)的現(xiàn)實需要。當(dāng)時,項羽身為霸主,政由己出,兵多將廣,實力雄厚,具有壓倒性的優(yōu)勢。《漢中對》就是要在這種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從不利中發(fā)現(xiàn)有利,從被動中尋求主動,奠定以弱勝強,奪取天下,完成統(tǒng)一的基礎(chǔ)。
正確判斷戰(zhàn)爭形勢,是正確制定戰(zhàn)略方針的前提。《漢中對》之所以膾炙人口,首先是韓信對整個形勢以及發(fā)展趨勢的正確分析判斷和把握。韓信既看到敵強我弱的客觀現(xiàn)實,肯定項羽在諸多方面占有絕對優(yōu)勢,如驍勇善戰(zhàn)、地盤廣大、寬厚待下,等等。同時也從項羽貌似強大的表象中發(fā)現(xiàn)其致命的弱點:其一,剛愎自用,不能識拔和放手任用人才;其二,愛惜爵祿,不知道如何籠絡(luò)人心,因而無法調(diào)動部下的積極性;其三,排斥異己,任人唯親,“以親愛王”,結(jié)果導(dǎo)致諸侯忿懣不平;其四,缺乏戰(zhàn)略遠(yuǎn)見,自動放棄關(guān)中形勝之地,“不居關(guān)中而都彭城”;其五,不講信用,加之誅殺無度,殘暴酷虐,“所過無不殘滅”,失去了民心。“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于威強耳”,所以,項羽只是“匹夫之勇”、“婦人之仁”。他表面上雖然強大,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必然會由強轉(zhuǎn)弱,因而要想擊滅他是頗有希望的。在“知彼”的同時,韓信也能“知己”,指出劉邦勢力雖然暫時弱小,但卻擁有雄厚的政治資本,入關(guān)后“約法三章”,贏得了民心歸附,而未能如約“王關(guān)中”反被項羽趕到漢中一事,又使得劉邦獲得了廣泛的同情。這就為最終戰(zhàn)勝項羽提供了可靠保證。通過這樣的比較,韓信預(yù)見劉邦由弱轉(zhuǎn)強,統(tǒng)一天下的樂觀前景:“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韓信的分析,合乎當(dāng)時的軍事戰(zhàn)略形勢,具有很強的預(yù)見性。事態(tài)的發(fā)展果然未出韓信所料,項羽東歸不久,田榮于山東起兵反楚,項羽后院起火,陷入了戰(zhàn)略上的極大被動。而劉邦則遵循韓信在《漢中對》中所提出的既定戰(zhàn)略,乘機部署軍隊“明修棧道,暗渡陳倉”,迅速平定了三秦,奪取關(guān)中形勝之地,取得了戰(zhàn)略前進基地,并為最終消滅項羽集團,完成王朝崛起,創(chuàng)造了有利的條件。
吳如嵩先生認(rèn)為:“‘柔武’二字就是中國古典戰(zhàn)略的精義之所在。”①這種以“柔武”為特征的中國戰(zhàn)略文化傳統(tǒng),在秦漢時期王朝崛起方略的制定與運用上自然也有顯著的體現(xiàn)。在最初階段,實現(xiàn)王朝崛起的主持者大多處于弱小的地位,他們最后能成為優(yōu)勢的一方,往往經(jīng)歷了一個長期醞釀的過程,然后才逐漸完成雙方戰(zhàn)略優(yōu)劣態(tài)勢的轉(zhuǎn)換,如周之于商,劉邦之于項羽,劉秀之于更始、赤眉,曹操之于袁紹,等等,皆是如此。因此,在實施崛起戰(zhàn)略的最初時期,他們不能不隱忍靜柔,韜光養(yǎng)晦,固本待機,以時間換取空間,以弱轉(zhuǎn)強,以少勝多。由此可見,在秦漢王朝崛起戰(zhàn)略的制定和運用方面,貴柔隱忍、韜光養(yǎng)晦的精神宛如一條無形的紅線,貫穿于其中。
劉秀在勢力初興的階段,就采取了典型的以弱自處、以柔克剛的方略。其秘決就在于沉潛不彰,甘于守雌,力避過早成為矛盾之焦點,沉著冷靜地等待時機,廣泛招攬人才,積極爭取民心,致力于河北這一根據(jù)地的經(jīng)營,“延攬英雄,務(wù)悅民心,立高祖之業(yè),救萬民之命”。②利用處于各種勢力邊緣的機會,發(fā)展壯大自己的勢力,冷眼旁觀群雄之間的火并,待各方勢力自相削弱之后,再出面收拾殘局,轉(zhuǎn)弱為強,水到渠成地收復(fù)關(guān)中,兵下洛陽,據(jù)有關(guān)東,底定隴右,并吞巴蜀,席卷天下,實現(xiàn)統(tǒng)一,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高明把握戰(zhàn)略時機
秦漢歷史上的王朝崛起大業(yè)完成者,普遍強調(diào)如何正確捕捉和利用有利的戰(zhàn)略時機,將戰(zhàn)爭行動付諸實施。
審“時”就是要認(rèn)清時機,度“勢”就是要把握歷史規(guī)律,把握歷史的進程和發(fā)展趨勢。因此,對于王朝崛起大業(yè)實施者來講,首先應(yīng)該把統(tǒng)一作為遠(yuǎn)期或最終目標(biāo)來加以認(rèn)識和追求。但“知易行難”,要真正做到正確認(rèn)識和把握戰(zhàn)略時機問題并不容易。歷史上許多統(tǒng)一大略指導(dǎo)者,就是因為昧于“時”、“勢”,而在統(tǒng)一征途上遭受嚴(yán)重挫折。當(dāng)年曹操發(fā)動赤壁之戰(zhàn),結(jié)果讓孫劉聯(lián)軍一把大火燒得慘敗,遂使其“周公吐哺,天下歸心”之統(tǒng)一六合的雄心付諸東流,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在時機不成熟的情況下超前行動當(dāng)然是錯誤的,但是當(dāng)條件成熟時束手束腳,無所作為則尤為愚蠢。所謂“失利后時,反受其殃”。王朝崛起大業(yè)實施者是否有前途,往往取決于其有無高明的識見,是否善于駕馭全局,及時把握戰(zhàn)略進攻的時機,迅速展開軍事行動,使自己的最高戰(zhàn)略目標(biāo)盡快得以實現(xiàn)。赤壁之戰(zhàn)后形成了三國鼎立局面,經(jīng)過數(shù)十年的和戰(zhàn)更替,統(tǒng)一全國的形勢漸趨成熟。公元263年,魏滅蜀漢。兩年后,司馬炎通過“禪讓”的方式,滅魏自立,是為晉武帝,建立起西晉王朝。這樣,魏、蜀、吳三分天下的局面遂成為晉、吳南北并峙的戰(zhàn)略格局。晉武帝司馬炎即位伊始,就將滅吳統(tǒng)一全國作為最重要的戰(zhàn)略任務(wù)提到議事日程。這時,整個形勢對于實現(xiàn)這一戰(zhàn)略目標(biāo)非常有利。事實上,當(dāng)時的東吳政權(quán)軍事實力已經(jīng)明顯處于下風(fēng),“弓弩戟楯不如中國”。更為致命的是,吳國內(nèi)部勾心斗角,矛盾重重,上下離心,眾叛親離,社會危機已趨于全面激化,“上下離心,莫為皓盡力”③。在這種情況之下,一旦西晉大舉出擊,吳國方面必定是望風(fēng)披靡,土崩瓦解,相反,西晉則在政治、經(jīng)濟、軍事上占有明顯的優(yōu)勢,“大晉兵眾,多于前世;資儲器械,盛于往時”④。所以,只要把握戰(zhàn)機,制定出可行的戰(zhàn)略方案,果斷發(fā)動征伐,則做到一舉而克毫無懸念。因此,當(dāng)時西晉朝中具有戰(zhàn)略眼光的大臣,如羊祜、杜預(yù)、王濬等人皆紛紛向晉武帝上疏,請求充分把握戰(zhàn)略時機,及時發(fā)兵征伐,一舉混同南北,完成國家的統(tǒng)一,“吳人虐政已久,可不戰(zhàn)而克……宜當(dāng)時定,以一四海”⑤。他們一致認(rèn)為,如果錯過這樣的時機,勢必導(dǎo)致嚴(yán)重的后患,使王朝崛起大業(yè)的實現(xiàn)遭遇重大的挫折。他們的共同心愿,就是希望晉武帝千萬不可放過時機,蹉跎歲月,“若今不伐,天變難預(yù)。今皓卒死,更立賢主,文武各得其所,則強敵也。誠愿陛下無失事機”。正是他們在“乘機”問題上的一再強調(diào),才使司馬炎最終下定決心進兵伐吳,揭開了西晉統(tǒng)一天下的嶄新篇章。
需要特別強調(diào)指出的是,秦漢時期高明的戰(zhàn)爭指導(dǎo)者在國家統(tǒng)一和王朝崛起的斗爭中,普遍主張辯證看待軍事行動時機是否成熟的問題,注意避免因追求萬全、一味穩(wěn)妥而瞻前顧后、優(yōu)柔寡斷,以致不敢進取,錯失戰(zhàn)機。
追求萬全,是中國古典戰(zhàn)略的最高境界,歷代兵學(xué)家大多將“計出萬全”作為其決策定謀的努力方向,“全勝不斗,大兵無創(chuàng),與鬼神通,微哉!微哉!”。然而,這種努力實際上存在著主觀愿望與客觀條件相脫節(jié)的問題,從本質(zhì)上說,這或許僅僅是一種理想的追求,而在實際軍事實踐中往往無法做到。戰(zhàn)前準(zhǔn)備的充分只是相對的,戰(zhàn)機成熟的界定也同樣是相對的。在任何情況下,軍事行動都帶有一定的冒險性,完全明了敵情、擁有十成把握的指揮決心幾乎是沒有的,即使一時明了,但在我變敵變的動態(tài)運動過程中,也難以做到總是對敵情一清二楚,對戰(zhàn)機萬無一失。在這樣的背景下明確戰(zhàn)機與利用戰(zhàn)機,正確的態(tài)度無疑應(yīng)該是立足于以己為主,排除干擾,主要情況大致搞清楚了,就應(yīng)該制兵機之先,如準(zhǔn)備不夠充分而戰(zhàn)機有利,殲敵又有把握的,則應(yīng)抓住戰(zhàn)機,敢于冒風(fēng)險,在戰(zhàn)爭的過程中彌補準(zhǔn)備上的不足。這就要求戰(zhàn)略指導(dǎo)者能夠準(zhǔn)確掌握有準(zhǔn)備和有把握的“度”,把勇敢而不魯莽,大膽而不失謹(jǐn)慎有機結(jié)合起來,去積極能動地爭取一切可能的勝利。這方面,西晉杜預(yù)與羊祜的做法非常合理,恰到好處。杜預(yù)曾向晉武帝司馬炎具體分析了滅吳統(tǒng)一全國戰(zhàn)爭的時機得失,認(rèn)為“凡事當(dāng)以利害相較,今上舉(指伐吳統(tǒng)一天下)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于無功耳”⑥。這無疑是辯證看待時機的正確態(tài)度。很顯然,如果一味追求“萬全”,而在“十之一二”不利條件面前自縛手腳,患得患失,瞻前顧后,優(yōu)柔寡斷,那么,西晉滅吳的大業(yè)必將是舉步維艱,遙遙無期。
周詳制定戰(zhàn)略預(yù)案
“先計后戰(zhàn)” 是中國軍事文化的重要傳統(tǒng)。戰(zhàn)爭指導(dǎo)者為了確保戰(zhàn)爭的順利進行,圓滿實現(xiàn)預(yù)定的戰(zhàn)略目標(biāo),尤其重視根據(jù)主客觀形勢和條件,制定切實可行的戰(zhàn)略預(yù)案,使之作為自己整個行動的綱領(lǐng),并且依據(jù)戰(zhàn)爭進程的實際,及時進行必要的充實或調(diào)整。戰(zhàn)略預(yù)案制定是否合理,戰(zhàn)略預(yù)案的實施是否具有把握性,除了正確判斷戰(zhàn)略形勢、高明把握戰(zhàn)略時機等一般性要求外,還取決于一些具有關(guān)鍵性意義的環(huán)節(jié)處理或解決的好壞。這些環(huán)節(jié)概括起來說,就是制定戰(zhàn)略預(yù)案必須立足于長遠(yuǎn),放眼于全局,具有前瞻性;制定戰(zhàn)略預(yù)案必須建立在最復(fù)雜的戰(zhàn)略背景之上,致力于完成戰(zhàn)略上的根本轉(zhuǎn)折;制定戰(zhàn)略預(yù)案必須充分考慮到軍事行動的各種變數(shù),立足于以戰(zhàn)爭手段掃除前進道路上的任何障礙,因此應(yīng)該有很強的實用價值和可操作性。就“前瞻性”而言,是指制定戰(zhàn)略預(yù)案時必須優(yōu)先考慮到戰(zhàn)爭的前景,在此基礎(chǔ)上預(yù)測形勢,定下合理的決心,這是戰(zhàn)略預(yù)案是否成功的先決條件。而在貫徹前瞻意識的時候,還必須具備全局觀念,能夠做到以簡馭繁,高屋建瓴,辨析利害,掌控主動。
就秦漢歷史的范圍而論,在籌劃與制定崛起戰(zhàn)略預(yù)案的過程之中,貫徹前瞻意識與全局觀念,并取得相當(dāng)成功的典范例子,莫過于諸葛亮的《隆中對》。《隆中對》為劉備集團勾畫了求生存、謀發(fā)展、取天下、致統(tǒng)一的完整系統(tǒng)的戰(zhàn)略方案,被譽為文人戰(zhàn)略家戰(zhàn)略謀劃的典范、千秋獨步的戰(zhàn)略名對。這個統(tǒng)一戰(zhàn)略預(yù)案的高明,在于它具有全局觀念,同時又充滿長遠(yuǎn)眼光、前瞻意識。它高屋建瓴,統(tǒng)籌全局,提出了“跨有荊、益”、“兩路出兵”的“三分割據(jù)紆籌策”。諸葛亮指陳時勢,在總結(jié)歷史經(jīng)驗和分析現(xiàn)實形勢的基礎(chǔ)上,指出在各種集團的消長紛爭中,曹操是劉備的主要敵人。所以,劉備的現(xiàn)實目標(biāo)應(yīng)該是“跨有荊、益”,即利用各種矛盾,奪取天下要沖荊州和天府之國益州,以此為角逐天下的根本,實現(xiàn)三分天下有其一的霸業(yè)。
更為重要的是,《隆中對》的根本宗旨在于最終實現(xiàn)國家的統(tǒng)一,體現(xiàn)了戰(zhàn)略決策上的前瞻意識。所以,諸葛亮進一步提出了劉備集團的長遠(yuǎn)戰(zhàn)略目標(biāo),這就是“待天下有變”,由荊州、益州兩路出兵,構(gòu)成鉗形進攻態(tài)勢,兵鋒北上,收復(fù)中原,興復(fù)漢室。《隆中對》所反映的大局觀念與戰(zhàn)略前瞻意識,并不是諸葛亮本人閉門造車的突發(fā)奇想。它的可行性,建立在諸葛亮所提出的一系列實現(xiàn)戰(zhàn)略目標(biāo)及相應(yīng)方法手段系統(tǒng)完善的基礎(chǔ)之上。這些方法手段包括:第一,利用“天下思漢”的心理,憑藉劉備身為“帝室之胄”的優(yōu)越背景,爭取政治上的主動;第二,推行“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jié)好孫權(quán)”的方針,做好“外交”工作,從而保證自身的安全,創(chuàng)造出有利于自己發(fā)展壯大的外部環(huán)境和良機;第三,“內(nèi)修政理”,整頓吏治,清明政治,發(fā)展經(jīng)濟,積蓄實力。
就“及時性”而言,是指制定戰(zhàn)略預(yù)案之時必須充分關(guān)注到戰(zhàn)爭的具體進程,在此基礎(chǔ)上把握關(guān)節(jié)點,適時完成具有戰(zhàn)略意義的根本性轉(zhuǎn)折,使王朝崛起大業(yè)進入階段性乃至超越性發(fā)展的軌道。秦國統(tǒng)一六國的戰(zhàn)略運用,就鮮明地體現(xiàn)了戰(zhàn)爭決策者在制定戰(zhàn)略預(yù)案過程中注意時效性,把握轉(zhuǎn)折點,最大限度創(chuàng)造有利戰(zhàn)略態(tài)勢的基本特色。秦統(tǒng)一六國,完成于秦王嬴政在位階段。但是,秦始皇能夠成功,乃是秦國多代君臣長期奮斗的結(jié)果,他不過是為這一偉大事業(yè)畫上最后一個句號的歷史終結(jié)者。這中間曾有幾個具有特殊意義的轉(zhuǎn)折點,而它們又恰恰都被秦國戰(zhàn)略決策者所捕捉到并實施了相應(yīng)的戰(zhàn)略對策,從而確保秦國的崛起大業(yè)不斷由一個階段跨越到新的階段,循序漸進,終于大成。
秦國致力于天下一統(tǒng)第一階段的戰(zhàn)略預(yù)案,是商鞅提出的《商君策》。它的核心是從地緣戰(zhàn)略的高度指出了魏國為秦國的“腹心之疾”,提出秦國要揮師東進,爭奪天下,就必須先行掃除魏國這一障礙,“非魏并秦,秦即并魏”。對于秦國來說,除了以魏為主要對象,從其手中奪得中央核心地帶之外,別無其他的選擇。而一旦做到了這一點,則“秦?fù)?jù)河山之固”,便可“東鄉(xiāng)以制諸侯”⑦,在統(tǒng)一兼并事業(yè)中占據(jù)十分有利的戰(zhàn)略態(tài)勢。至于實現(xiàn)這一戰(zhàn)略目標(biāo)的條件,商鞅也作出了周密的論證。他指出:其一,繼續(xù)實行富國強兵的國策,造就實現(xiàn)“東鄉(xiāng)以制諸侯”這一既定軍事戰(zhàn)略目標(biāo)的堅強實力和后盾;其二,以外交配合軍事斗爭,謀求“諸侯畔之(魏)”的局面出現(xiàn),借力打人,坐收漁利;其三,充分利用自身有利的戰(zhàn)略地理條件,盡快占據(jù)山河之險,“據(jù)河山之固”,為東出中原角逐天下創(chuàng)造必要的機會。
歷史恰恰為秦國提供了實現(xiàn)這一戰(zhàn)略目標(biāo)的契機。一是當(dāng)時魏國的西進勢頭在受到秦國的頑強抵制后暫緩下來,并因秦的反擊和東、南兩個戰(zhàn)略方向的威脅上升而遷都于大梁(今河南開封),減輕了對秦國的壓力;二是東方的戰(zhàn)略形勢也發(fā)生了重大的變化,魏國的霸權(quán)受到齊國的有力挑戰(zhàn),魏、齊兩強利益的碰撞使得雙方戰(zhàn)爭已不可避免;其三,魏國與傳統(tǒng)盟友韓、趙二國的控制與反控制正在愈演愈烈,三晉一體的局面已瀕于崩潰。凡此種種,都為秦國的東進提供了良機。
秦孝公采納了商鞅這個戰(zhàn)略方案qR0SVzIcw9iceYcfun+uYvgRolRpad6C7+wfIO0ggtU=,堅決抓住魏國“大破于齊,諸侯畔之”,即馬陵之戰(zhàn)后魏國獨霸中原戰(zhàn)略格局被打破的大好時機,開始了秦國大舉東進的軍事行動。完全控制了西河(今陜西與山西交界處黃河南段)天險,從而能據(jù)崤、函之利,大河之險,東向以臨天下,獲得了進可攻退可守的戰(zhàn)略主動。
如果說,《商君策》是秦統(tǒng)一六國起步階段切實可行的戰(zhàn)略指導(dǎo)方案,那么范雎向秦昭王進獻(xiàn)的《客卿對》,則可以視為是秦統(tǒng)一六國關(guān)鍵階段用以指導(dǎo)崛起大業(yè)實踐的戰(zhàn)略預(yù)案。范雎入秦時,戰(zhàn)國的群雄爭戰(zhàn)已經(jīng)持續(xù)了整整二百年。秦國的大國地位更加鞏固,關(guān)東六國或早已輝煌不再,或日暮途窮。自商鞅變法奪取西河形勝之地后,秦國一直根據(jù)天下形勢和各國關(guān)系的變化,以外交配合軍事,交替實施東進和南下的軍事行動,并奪取了巴、蜀,另辟戰(zhàn)略前進孔道,一枝獨秀,雄視天下。
秦國要實現(xiàn)其統(tǒng)一天下的既定目標(biāo),主要有兩個戰(zhàn)略方向:一是東進,出崤、函進攻三晉,直取中原,控制戰(zhàn)略要地,切斷諸侯間的聯(lián)系,進而兼并六國;一是南下攻楚,解除側(cè)后隱患,爾后迂回中原,統(tǒng)一天下。為此,秦國在攻伐韓、魏、趙進展不大的情況下,調(diào)整戰(zhàn)略方向,派司馬錯大舉攻楚,得手之后,又派遣白起率軍攻下楚都郢城,迫使楚遷都于陳(今河南淮陽)。至此,秦國的勢力延伸到長江中游、漢水流域,統(tǒng)一的態(tài)勢更為有利。
秦昭王時期的這些成果是在其舅父魏冉的主持下取得的。魏冉曾主持朝政達(dá)二十五年之久。但他并無一統(tǒng)天下的長遠(yuǎn)目標(biāo),僅將對外用兵作為鞏固自己政治地位的手段。由此可見,一方面,秦統(tǒng)一天下的時機正趨于成熟,另一方面,由于權(quán)相個人意志的干擾,而不能使有利的戰(zhàn)略條件在崛起大業(yè)實現(xiàn)上發(fā)揮應(yīng)有的作用,這個矛盾使秦統(tǒng)一天下的征程此時已處于得失成敗的十字路口。而范雎在《客卿對》中所構(gòu)筑的統(tǒng)一方略,則解決了這個復(fù)雜的矛盾。
《客卿對》是一個系統(tǒng)嚴(yán)密的王朝崛起大業(yè)中期戰(zhàn)略預(yù)案,它的核心內(nèi)容是遠(yuǎn)交而近攻。在該方案中,范雎向秦昭王指出,秦國據(jù)地利之便,國富兵強,已擁有了統(tǒng)一天下的戰(zhàn)略優(yōu)勢。然而,實際情況卻不是這樣,秦國“至今閉關(guān)十五年,不敢窺兵于山東”,之所以遲遲不能成就一統(tǒng)天下的大業(yè),其根本原因在于“群臣莫當(dāng)其位”,“大王之計有所失也”,即執(zhí)掌實權(quán)的穰侯魏冉所制定的攻伐政策已經(jīng)不合時宜,而秦昭王本人也沒有制定出合適的戰(zhàn)略預(yù)案。范雎把自己的戰(zhàn)略構(gòu)想向秦昭王和盤托出,指明秦統(tǒng)一天下的唯一正確道路,乃是“遠(yuǎn)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也。”范雎強調(diào),這一戰(zhàn)略有其可行性:其一,與秦相鄰的韓、趙、魏三國地處天下中樞,所以兼并韓、魏是日后統(tǒng)一天下的關(guān)鍵,其他問題可隨之迎刃而解;其二,遠(yuǎn)交近攻要以奪得土地和人口為主,“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⑧,即奪取土地與消滅敵人有生力量并舉。
克勞塞維茨說過,通過戰(zhàn)斗和會戰(zhàn)消滅敵軍,是達(dá)成戰(zhàn)略目標(biāo)的真正重心。在范雎擬定的這份戰(zhàn)略預(yù)案中,他不僅提出了“遠(yuǎn)交近攻”的會戰(zhàn)目標(biāo),也提出了達(dá)成這一戰(zhàn)略目標(biāo)的具體方法步驟。即:首先要利用外交與軍事威懾,迫使地處中央地帶的韓、魏與秦結(jié)好,控制這兩國后,再威逼楚、趙使其屈服,進而威懾距離最遠(yuǎn)的齊國,齊國依附之后,就可放手兼并韓、魏兩國,而韓、魏兩國相較,則應(yīng)先取韓國,在此基礎(chǔ)上,再次第攻取其他各國,最終完成統(tǒng)一大業(yè)。秦昭王對范雎這一戰(zhàn)略預(yù)案至為推崇,徹底修正了魏冉等人的戰(zhàn)略方案,并拜范雎為客卿,主持軍事謀劃和兼并事宜,“卒聽范雎謀”。
瑞士軍事理論家若來尼曾說過,戰(zhàn)略之核心在于抓住全部戰(zhàn)爭的鎖鑰,集中兵力攻擊敵人的一翼或者一點,進行中央突破。范雎遠(yuǎn)交近攻的戰(zhàn)略方案,作為對秦國“連橫”戰(zhàn)略的具體化和系統(tǒng)化,正符合這一戰(zhàn)爭藝術(shù)原理。首先,它從地緣關(guān)系思考戰(zhàn)略問題,因為列強的爭奪和實力的增強,在當(dāng)時無非是土地,所以地緣問題對于軍事、外交意義重大。遠(yuǎn)交近攻即是對遠(yuǎn)方之國實行暫時的聯(lián)合,至少爭取其中立,然后騰出手來對鄰近之國實施軍事打擊,蠶食土地,增強實力。其二,這一戰(zhàn)略預(yù)案有其系統(tǒng)性,考慮到了每一戰(zhàn)略步驟及實現(xiàn)之具體方法,其原則是先弱后強,由近及遠(yuǎn),先據(jù)有中原樞紐,再向四周擴展。其三,遠(yuǎn)交近攻照應(yīng)了軍事與外交的綜合運用,強大的軍事實力是外交懾服之堅強后盾,而高明的外交又是軍事行動的準(zhǔn)備、先導(dǎo)以及補充,對于最大限度發(fā)揮軍事力量的效果具有重大意義。
至于秦王嬴政提出的“滅諸侯,成帝業(yè)”戰(zhàn)略預(yù)案,則是秦統(tǒng)一六國歷史進程進入最后階段時的收官之作,是一切就緒后為統(tǒng)一大業(yè)畫上的一個圓滿句號。公元前261年,秦軍主力在白起的統(tǒng)率下,在長平地區(qū)(今屬山西上黨一帶)同當(dāng)時山東六國中唯一可以同秦國相抗衡的趙國軍隊進行戰(zhàn)略決戰(zhàn),盡殲趙軍主力四十五萬之眾,從而徹底清除了自己東進吞并六國的最后障礙。
在這樣的形勢下,秦王嬴政把握歷史的機遇,于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8),采納李斯、尉繚等人的建議,最終下決心“滅諸侯,成帝業(yè),為天下一統(tǒng)”⑨。這標(biāo)志著秦國的統(tǒng)一戰(zhàn)略又一次有了帶根本性的轉(zhuǎn)變,即放棄傳統(tǒng)意義上的重創(chuàng)蠶食戰(zhàn)略,而開始執(zhí)行兼并六國的戰(zhàn)略。在此基礎(chǔ)上又解決了確定重點打擊對象的問題,把攻打趙國作為各個擊破的突破口。戰(zhàn)爭的進程表明,秦國這一戰(zhàn)爭預(yù)案是完全正確的,它使秦國避免了陷入多線作戰(zhàn)的被動局面,得以迅速各個擊破關(guān)東六國,最終順利完成了統(tǒng)一天下的宏偉事業(yè)。由此可見,秦崛起大業(yè)最后階段的順利推進,同樣離不開正確的戰(zhàn)略預(yù)案的指導(dǎo)。
就“操作性”而言,是指制定戰(zhàn)略預(yù)案之時必須充分關(guān)注到統(tǒng)一戰(zhàn)爭的技術(shù)處理細(xì)節(jié)問題,不僅要有宏觀的總體把握,更需要有技術(shù)層面上的駕馭控制。眾所周知,戰(zhàn)爭的具體運作更多是技術(shù)層面的內(nèi)容,作為實踐過程,它不尚空談,完全以利害關(guān)系為依據(jù),強調(diào)操作的合理化、細(xì)致化,注重主觀指導(dǎo)在駕馭戰(zhàn)爭機器時的功能與作用,注重方案的細(xì)節(jié)化、程式化,使之具有最大程度上的可操作性。
西晉滅吳統(tǒng)一全國的戰(zhàn)略預(yù)案,就是建立在認(rèn)真籌劃、正確部署的基礎(chǔ)之上,有相當(dāng)程度上的可操作性,實用價值至為顯著。它的基本內(nèi)容是根據(jù)羊祜所上的《平吳疏》中的建議確定的。羊祜在其《平吳疏》中為晉軍擬定了具體的作戰(zhàn)部署,闡述了正確的用兵方略,為晉武帝發(fā)動平吳統(tǒng)一戰(zhàn)爭,提供了一份可供具體操作的軍事進攻戰(zhàn)略方案。在方案中,羊祜為了確保滅吳之役達(dá)到預(yù)期效果,根據(jù)晉、吳雙方的戰(zhàn)略態(tài)勢,提出應(yīng)多路進兵,水陸俱下。羊祜認(rèn)為這個極具操作性的戰(zhàn)略預(yù)案一定能夠應(yīng)對復(fù)雜的戰(zhàn)略態(tài)勢和艱巨的戰(zhàn)略任務(wù)。因為這樣一來,吳軍勢必首尾不能相顧,其失敗的命運將不可避免:“以一隅之吳,當(dāng)天下之眾,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蜀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如此,則“軍不逾時,克可必矣”。很顯然,《平吳疏》的確是一份高明的統(tǒng)一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預(yù)案,它的顯著特征,是符合實用、可操作性強,充分體現(xiàn)了羊祜作為杰出戰(zhàn)略家求真務(wù)實的處事原則與態(tài)度。晉武帝司馬炎正是按照這份講求實用、可供操作的軍事戰(zhàn)略預(yù)案,進行全面的軍事部署,并于準(zhǔn)備充分、條件成熟之際,分派六路大軍,大舉伐吳,成就了一統(tǒng)南北的大業(yè)。
當(dāng)然,除了全面分析戰(zhàn)略形勢,高明把握戰(zhàn)略時機,合理制定戰(zhàn)略預(yù)案等基本要素之外,在王朝崛起戰(zhàn)略指導(dǎo)的體系結(jié)構(gòu)中,還包括認(rèn)真構(gòu)筑戰(zhàn)略方針、確定恰當(dāng)戰(zhàn)略目標(biāo)、正確選擇戰(zhàn)略方向、具體規(guī)劃戰(zhàn)略步驟、妥善運用戰(zhàn)略手段等諸多內(nèi)容。限于篇幅,本文就不一一展開闡述了。總之,秦漢時期作為中國歷史上大一統(tǒng)的開端,王朝崛起戰(zhàn)爭在當(dāng)時社會生活當(dāng)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在中國歷史上的王朝崛起戰(zhàn)爭里具有典范意義。通觀這一時期成功的王朝崛起之戰(zhàn)略指導(dǎo),我們可以從更高的層面概括出其普遍的共性特征。第一,“以文為種,以武為植”,強調(diào)政治、經(jīng)濟對軍事活動的制約與指導(dǎo)作用;第二,強調(diào)“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注重從宏觀上把握戰(zhàn)略形勢,高屋建瓴、統(tǒng)籌全局、爭取先機,把掌握戰(zhàn)略主動,營造有利于未來發(fā)展的戰(zhàn)略環(huán)境作為制定與實施王朝崛起戰(zhàn)略的出發(fā)點;第三,在王朝崛起戰(zhàn)略實施過程中,堅持文武兼用,剛?cè)嵯酀藫峤Y(jié)合,既重視政治攻心、招撫服遠(yuǎn),又不放棄強大的武力準(zhǔn)備,在必要的情況下,用軍事手段摧毀敵人的抵抗,達(dá)到崛起的目的;第四,在戰(zhàn)爭的具體戰(zhàn)役指揮與戰(zhàn)術(shù)運用上,強調(diào)持久待機下的速戰(zhàn)速決,示形動敵,出其不意,輕兵襲擾,重兵突襲,一戰(zhàn)而勝。
中國歷史上的王朝崛起戰(zhàn)略指導(dǎo)是一筆極其豐富的戰(zhàn)略文化資源,我們完全有必要加以研究和總結(jié)。實際上,古人在這方面早已有了清醒的認(rèn)識。南宋理學(xué)大師朱熹就有總結(jié)宋代以前王朝崛起戰(zhàn)略成敗得失的強烈愿望,曾向?qū)W生們表示過,他自己“嘗欲寫出蕭何、韓信初見高祖時一段,鄧禹初見光武時一段,武侯初見先主時一段,將這數(shù)段語及王樸《平邊策》編為一卷”⑩。很顯然,朱熹把國家統(tǒng)一與王朝崛起的戰(zhàn)略問題作為他總結(jié)歷史經(jīng)驗的重點。今天,我們當(dāng)然應(yīng)該比朱熹有更高的境界從事這項工作,積極弘揚中華優(yōu)秀的軍事文化傳統(tǒng),全面總結(jié)古代王朝崛起戰(zhàn)略指導(dǎo)方面的經(jīng)驗教訓(xùn),從中汲取有益的智慧與啟迪,以便為國家的統(tǒng)一和強盛、粉碎敵對勢力的戰(zhàn)略圍堵、維護國家和民族的戰(zhàn)略核心利益提供寶貴的借鑒。
注釋
吳如嵩:《徜徉兵學(xué)長河》,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第1~2頁。
《后漢書》(卷十六),《鄧寇列傳》。
《三國志》(卷四十八),《吳書·孫皓傳》。
《晉書》(卷三十四),《羊祜傳》。
《晉書》(卷三十四),《杜預(yù)傳》。
《史記》(卷六十八),《商君列傳》。
《史記》(卷七十九),《范雎蔡澤列傳》。
《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傳》。
《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五)。
責(zé) 編/樊保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