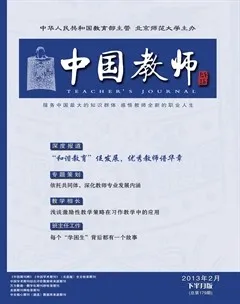與教師一道建構(gòu)理論
2010年秋季,我和另外幾名青年研究者因一個校本研究項目來到這所小學(xué)。在開始進(jìn)行研究工作之前,我與學(xué)校的管理者已經(jīng)獲得了一定的相互了解。我的一些研究理念,也得到了校方的認(rèn)可。在接下來進(jìn)行研究的一年多時間里,我得以自在地在這所學(xué)校穿梭,定點(diǎn)于具體學(xué)科開展工作,收集大量豐富的課例。同時,在參與學(xué)科組的教研活動過程中,我與廣大一線教師建立了密切的聯(lián)系。而“學(xué)科加工”這個概念,正是在此過程中建構(gòu)出來的。盡管這次“自下而上”的概念建構(gòu)過程漫長而周折,但這個概念不是“拿來”的,教師們對這個概念產(chǎn)生了親密感;概念建構(gòu)過程中始終有教師的參與,因此教師不會感到“與我無關(guān)”。
一、教師群體的認(rèn)可
在進(jìn)行這項工作之始,基于以前的研究經(jīng)驗,我清楚自己面臨的主要困難:如何才能取得教師們的認(rèn)可?
最初,我是以“游客”的身份進(jìn)入課堂。作為“游客”,我得到了殷勤的招待,但是主人的好客也意味著距離。因此,我給自己設(shè)定了目標(biāo)——要成為教師們的“自己人”。可是要突破的東西太多了,譬如,我要“通情達(dá)理”,能真正同情和理解教師們的種種境遇;我在個人興趣之外,要照應(yīng)教師們的“興奮點(diǎn)”;我要在自己的非專業(yè)領(lǐng)域,扮演“專業(yè)人士”的角色。與此同時,這個“自己人”又很“特殊”:我既要理解教師們自己的見識,又不局限于這種見識;我要盡量詳盡地了解教師,又要小心地回避校內(nèi)的種種人情糾葛和管理摩擦。總之,我很難擺脫“偽裝親善”的嫌疑,始終需要努力避免成為他人專業(yè)領(lǐng)域的“入侵者”。
在學(xué)校里,我一直帶上一臺迷你DV、一支錄音筆、一個聽課本。現(xiàn)場的觀感,隨時記在聽課本里;返回途中,也盡量對那一天的工作做一些口頭的點(diǎn)評;聽課時,我更愿意選擇前排位置,以便于面向教師和學(xué)生;在錄課時,我習(xí)慣拍攝孩子們的特寫,記錄他們的表情,觀察他們在做什么,并試圖揣摩他們的心思。總之,我希望能夠盡量詳盡地觀察課堂,不愿意套用已有的理論或工具。
在這一時期的聽評課上我采用了一種“漫無目的”的方式。學(xué)校教學(xué)處幫我安排好各學(xué)科課時7+mN2Jw7KicukUrjIKRXaA==,但我與聽課的教師還不熟悉。在這段最初的日子里,課后只是利用上午的一段時間進(jìn)行溝通,再無進(jìn)一步接觸。此階段我聽評的各種言論還沒有明確的、一致的方向與核心。因此,對這段時間的工作目的,可以概括為熟悉情況,尋找“有緣人”。
不久,我遇到了兩位與我頗有默契的教師——張老師和袁老師。張老師的教學(xué)信念較為開放,袁老師更為謹(jǐn)慎而敏感,但相同的是他們都年輕而富有熱情,愿意做出各種嘗試以改進(jìn)自己的工作。在張老師的課上,我們從一道練習(xí)題出發(fā),提煉出一節(jié)展示課。在袁老師的課上,我們一起反復(fù)研討不同的設(shè)計方案。在這個過程中,我嘗試分頭為兩位教師提供相關(guān)的文獻(xiàn)資料。在集中研討的那段時間,幾乎每次到校聽課,我們?nèi)齻€人都要碰頭。在余下的時間,包括休息日,我們也會打電話就自己的想法進(jìn)行溝通。
二、“學(xué)科加工”概念的提煉及應(yīng)用
有一次在學(xué)校遇到與區(qū)教研員共同評課的機(jī)會。那一次的評課,教研員和我的每一個觀點(diǎn)幾乎都是相左的。我們誰也沒有說服對方,但我們都意識到對方是在坦誠地表達(dá)自己的看法。現(xiàn)場中無論是執(zhí)教教師還是其他旁聽者,誰都沒有當(dāng)即直接做出草率的判斷。事后,我據(jù)此總結(jié)了點(diǎn)評一堂課的三個不同視角,并進(jìn)行了初步的概念設(shè)計,把我早先進(jìn)行的那兩次課例研究中的做法,概括為“學(xué)科加工”。下面這段話是對“學(xué)科加工”的描述:
“與其母學(xué)科相比,一節(jié)課要處理的知識點(diǎn),總是對應(yīng)于某些主題,服務(wù)于某些目標(biāo)。教師在教學(xué)設(shè)計過程中,試圖恢復(fù)教學(xué)內(nèi)容與其母學(xué)科之間的聯(lián)系,這就是學(xué)科加工。善于做學(xué)科加工的教師,在思考教學(xué)問題時,始終具有獨(dú)到的學(xué)科眼光。每一節(jié)課的教學(xué),都有較為明確的學(xué)科定位。屆時,一節(jié)課的目標(biāo)設(shè)計將不再是基于猜測或者靈機(jī)一動,而是有堅實(shí)的意義背景了。由此可見,教師進(jìn)行學(xué)科加工時所考察的不僅是單個知識點(diǎn),而是努力尋找該知識點(diǎn)與學(xué)科知識之間更廣泛的意義聯(lián)系。如果說教科書的編制過程,是由學(xué)科知識向教科書知識的轉(zhuǎn)換,那么,學(xué)科加工過程,即是回頭去尋找這些轉(zhuǎn)換線索。”
在我看來,“學(xué)科加工”不涉及具體的行動建議。所以在選擇研究合作者時,不必糾結(jié)執(zhí)教教師是否具有嫻熟的教學(xué)技能。所有人都可以坐下來一起研討課例,研究過程不再是一兩位經(jīng)驗教師的獨(dú)角戲,也不會過多干預(yù)最終的教學(xué)設(shè)計。我們的研討多是在尋找教學(xué)設(shè)計的知識基礎(chǔ)。我們常常追問:這樣設(shè)計有什么根據(jù)?因為這些知識基礎(chǔ)來自于廣大的學(xué)術(shù)研究界,本身有接受討論和期待更新的特性。所以,在尋找知識基礎(chǔ)的過程中,大家都是學(xué)習(xí)者,都是平等的。“學(xué)科加工”的這些特性,讓我相信自己有能力把握,也讓我相信它有在別處復(fù)制的可能。
在后面的聽評課過程中,我們選擇了另外一些課例,把“學(xué)科加工”的方式應(yīng)用到這些課例的研究過程中去。這時,我已經(jīng)有比較明確的努力方向。在教研團(tuán)隊中,我充當(dāng)了質(zhì)疑者和資源支持者的角色。譬如,在小學(xué)三年級的豎式除法教學(xué)中,質(zhì)疑的對象是豎式除法的教學(xué)重點(diǎn);在資源支持方面,我們從除法計算方法的多樣性入手,通過向執(zhí)教教師提供歷史上曾經(jīng)出現(xiàn)的幾種除法計算方法,進(jìn)一步凸顯除法作為“連續(xù)減”的意義。這樣,豎式除法的教學(xué)得到了一個更有意義的備選方案。又譬如,在小學(xué)一年級的兩位數(shù)認(rèn)識的教學(xué)中,質(zhì)疑的對象是兩位數(shù)與一位數(shù)的差異:這種差異僅僅體現(xiàn)為數(shù)值大小的不同嗎?在資源支持方面,我們提供了十進(jìn)制計數(shù)法的數(shù)學(xué)史知識。據(jù)此,執(zhí)教教師認(rèn)識到數(shù)位概念才是兩位數(shù)教學(xué)的關(guān)鍵所在。他們的教學(xué)設(shè)計因此獲得了新的備選方案,這種方案具有更加確實(shí)的知識基礎(chǔ)。
2011年春季,我把“學(xué)科加工”這個概念總結(jié)與教學(xué)處和研究團(tuán)隊的教師們做了溝通。我期望,大家可以用同一套概念來進(jìn)行對話以使溝通更加有效。后來的一些研討場合,經(jīng)常會有人說:“我知道,從您那個角度會這么看……”由此可見,這個概念總結(jié)已經(jīng)有了很好的“群眾基礎(chǔ)”:參與教研活動的教師了解我要做的事;學(xué)校教學(xué)處參與了事情的全過程;常務(wù)校長也理解我們的提煉。今后的努力方向,是把教研的影響面由個別“種子教師”,擴(kuò)展到更大范圍的教師群體中去;把一個“在地”的教育概念,擴(kuò)展為教師發(fā)展的行動路徑;由一個學(xué)科的提煉,進(jìn)入到更多學(xué)科的探索;由理論研究人員的幫助,變成教師自己獨(dú)立進(jìn)行……至此,我們可以比較有信心地說,與教師一道進(jìn)行理論建構(gòu)是可行的。這樣的概念建構(gòu),無論是過程還是結(jié)果,都與教師的行動密不可分。這種理論建構(gòu)是以教師體驗為素材,并服務(wù)于教師。最近,我開始嘗試把“學(xué)科加工”與自己更一般的教育思考聯(lián)系起來,這些案例具有一般理論探討的價值。
三、經(jīng)驗與反思
通過這次的研究歷程,我得出以下幾項基本經(jīng)驗:首先,如果教師沒有深度參與,便很難進(jìn)行深度變革。大規(guī)模的培訓(xùn)和“若即若離”的接觸,在我看來都很難保證教學(xué)研究的效果。其次,如果研究者沒有立體的支援,便很難維持長久發(fā)展。教師專業(yè)發(fā)展說白了是成人的一種自發(fā)革新。聯(lián)想到我們自身,就能理解這是一件多么困難的事情!總之,深度參與和立體支援是與教師合作進(jìn)行概念建構(gòu)的必要條件。然而在這次的研究歷程中,我也遇到了幾項基本難題:其一,個人偏好與專業(yè)身份的沖突。有些教師我更容易親近,有些教師與我更容易疏離;有些教師一開始就很熱情,有些教師一開始就抱著冷漠的態(tài)度。在這個過程中,如何處理我的個人偏好與專業(yè)身份的關(guān)系?這是一個相當(dāng)有挑戰(zhàn)的事情。其二,觀念激發(fā)與理論建構(gòu)的沖突。等到“自己人”的角色建立起來以后,討論就變得更加缺乏談話的技巧與策略,而更加直接、豐富。當(dāng)我們有了自己的概念建構(gòu)以后,如何繼續(xù)保持研究的開放性、理論的開放性,就成為難題。總之,身份與立場是在與教師進(jìn)行合作研究的過程中,需要謹(jǐn)慎處理的問題。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xué)教育學(xué)部)
(責(zé)任編輯:萬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