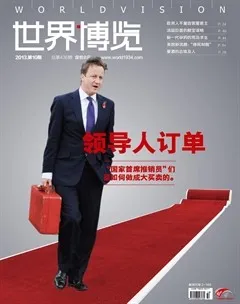“領導人訂單”,賠賺自知




領導人同時也是一個國家的首席推銷員,出訪國外卻空手而回,對領導人來說是最大的恥辱,是無能的體現。考量領導人訂單不能光看虧了還是賺了,因為有時,幫助別人就是幫助自己。
盡管法國總統奧朗德以前從未到過中國,但在這次短短37個小時的訪問里,他依然收獲了豐厚的訂單:中國航空器材集團公司和空客簽署60架空客飛機訂單;核能巨頭阿海琺和法國電力與廣東核能集團簽署三方長期合作協議;甚至還有阿海琺和中國核工業集團簽署建造核廢料處理設施意向書。
法國漢學家讓-呂克·多梅內克說,奧朗德這次真的是賺到了,因為“時間都花在該花的地方”。法國《世界報》和《回聲報》也分別指出,與薩科奇2010年的兩手空空相比,奧朗德此行的收獲令人滿意。
這種因外國領導人來訪或中國領導人出訪而簽署的訂單,常被戲稱為“領導人訂單”,領導人訂單往往并非單純因經濟和貿易的需要簽訂,而或多或少帶有政治、戰略或外交策略的考量。應該說,這種“領導人訂單”中外都有,甚至可以說,是西方工業化國家率先推行的,英國首相、美國總統都曾被本國媒體冠以“首席海外推銷員”的稱號,他們出訪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軟硬兼施,讓東道主簽署盡可能多的領導人訂單。同時為了表示友好、安撫、爭取支持或平衡,有時也會酌情在東道國留下幾份領導人訂單作為交換。某種程度上講,這幾乎可算是外交界的一種慣例。
近年來,中國的領導人訂單漸漸成為全球矚目的熱點,不僅各國朝野議論紛紛,國內也有許多觀點鮮明的爭議。
那么,中國的領導人訂單是怎么來的,為何又引起爭議?
“領導人訂單”,自古做的是人情
早在南宋,朝廷就開始和云南地方政權大理國間開展的馬匹貿易,明永樂年間鄭和出訪船隊與“南洋”各國間的貿易,中國寧波和日本長崎間的“勘合貿易”等,都可以被視為“領導人訂單”的雛形。
例如大理國特使訪問南宋,推銷本國所產馬匹,盡管地方官指出,大理所產馬匹品種不佳,不合戰陣之用,但南宋朝廷卻出于安撫、拉攏和“不欲邊境生事”的目的,象征性地購買若干。明朝對日本的“勘合貿易”,政治、外交色彩更濃,至于鄭和下西洋,更是是“貴入賤出”,做賠本買賣,其目的純在于“柔遠敦睦”和顯示明帝國的富強國力。
然而這種原始版本的領導人訂單存在許多令人詬病之處。最令人不滿的,則是片面強調訂單的政治、外交屬性而忽視經濟屬性。
如鄭和下西洋歷經東南亞、南亞、西亞和非洲許多國家,這些國家許多和中國有傳統的直接、間接貿易聯系,民間貿易原本有利可圖,但明朝片面強調“宣示國威”、“招徠遠人”,一方面把本可賣出好價的絲綢、瓷器、茶葉等以“友情價”半賣半送,不僅損失國家利益,還變相沖擊了本國民間商人的市場價格,另一方面,用國庫里真金白銀買回的各種海外產品,許多根本不合用。史料記載,鄭和下西洋所“進口”的一些外國產品,如硬木、香料等,因國內用途不大,嚴重積壓,官方不得不將這些東西折價充作各級官員的“實物工資”強行攤派。
怪不得鄭和死后多年,明朝皇帝試圖再次啟動下西洋“工程”,驚恐萬狀的戶部官員竟把鄭和留下的檔案藏匿、銷毀,其臺面理由主要是“政府財政吃不消”,不便說出口的理由,則是擔心“實物工資”攤派比例更大影響了自己的利益。但不論是哪個理由,中國古時候的領導人訂單重政治、外交而輕經濟效益,是造成這種怪現象的根源。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國曾長期處于被封鎖、被包圍和被孤立的狀態。為爭取外交空間,領導人訂單的現象同樣常見。
如號稱“新中國非洲進口第一單”的埃及棉花訂單,就是在當時(1953年4月)并不急需的情況下為爭取埃及而簽訂的。此外,如毛澤東主席第二次訪問蘇聯時購買的米格-19戰斗機(為照顧“老大哥”情緒將需要和暫不需要的型號都購買了一批),周恩來總理訪問伊拉克時進口的椰棗(俗稱“伊拉克蜜棗”,當時中國并不急需),華國鋒訪問羅馬尼亞時訂購的散貨船(當時中國已能制造且質量、價格都不遜色)和細鋼筋(中國當時不缺,為避免進口散貨船空駛回國而訂購)都屬于這類情況。
除了有形的“領導人訂單”,還有無形的。最典型的就是援助和援建。改革開放前,中國在非洲、朝鮮、阿爾巴尼亞等國援助、援建的許多大型項目,包括鐵路、公路、水電站、體育場館、政府辦公設施等,許多都是“領導人訂單”。這些項目不少起到了特殊的政治、外交作用,甚至為中國重返聯合國鋪平道路。但在當時中國自己經濟實力不強,國力、財力均不寬裕的情況下,這些項目在經濟上是并不劃算的。
當代訂單,幾家受益幾家肥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逐漸結束了以往“政治優先于經濟”的外貿、外援政策,開始注重經濟效益和政治、外交效應的平衡。那種不量入為出的“慷慨大方”,隨著1982年時任中國總理的趙紫陽訪問非洲11國、提出“平等互利、講求實效、形式多樣、共同發展”新四項原則和1995年下半年徹底改變援外方式,已發生了根本性扭轉。
上世紀90年代后期,中國經濟開始步入快車道,近10年來更有了突飛猛進的進步,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產品出口國,在全球范圍內的政治、經濟、軍事影響力與日俱增,全球利益不斷凸顯。新時期的“領導人訂單”,呈現出與改革開放前迥然不同的場景。
新時期“領導人訂單”最大的變化是,在購買發達國家產品方面顯得手筆很大,且往往是外國領導人“送貨上門”、“兜售到家”。
比如法國,2007年11月薩科奇訪華,“領導人訂單”包括價值100億歐元的160架空客客機,價值80億歐元的阿海琺-廣東核電集團民用核能領域合作協議,和法國電力-廣東核電集團合資建設170萬千瓦廣東臺山核電站一期工程;此次奧朗德訪華,“領導人訂單”又包括60架空客和一攬子核電合作項目。
比如德國,總理默克爾6次訪華,次次滿載而歸,“領導人訂單”除了空客飛機和汽車生產線,還有精密機械、光伏產品、地鐵設備等等。僅2012年8月的一次,就包括價值35億美元的50架空客,價值16億美元的空客天津組裝線,價值2.9億美元的大眾天津汽車零部件生產廠等。
比如英國,2010年11月首相卡梅倫訪華,簽署的“領導人訂單”總價值高達17億英鎊,涉及綠色技術轉讓、城市規劃、房地產開發、軟件支持和維修、碳足跡和能源利用、高校間人才建設、燃氣工程技術培訓和管理等。
比如美國,2005年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訪華,“領導人訂單”包括波音客機150架,價值90億美元;2006年胡錦濤主席回訪,“領導人訂單”又包括波音客機70架,價值40億美元。
而到了2012年2月加拿大的哈珀總理二度訪華,“領導人訂單”多達23項,總價值約30億美元,其中僅龐巴迪公司就有支線客機、地鐵牽引系統等多個大單。此外,羅-羅航發公司還獲得中國東方航空公司12億美元民用飛機發動機訂單。
同樣,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訂單”也不乏大手筆。例如與巴西,2011年4月羅塞夫總統訪華,僅支線客機E-190一項“領導人訂單”,就多達35架,總金額近20億美元。
其他諸如“老朋友”非洲,2009年埃及沙姆沙伊赫第四屆中非合作論壇部長級會議,中國許諾100億美元低息貸款;2012年北京第五屆部長級會議,貸款額增加一倍。
“領導人訂單”不僅包括有形的“購物”,也包括無形的買賣或特殊買賣。如默克爾訪華爭取到中國購買德國企業、繼續投資歐元區國債市場的承諾;卡梅倫訪華,則為倫敦爭取到人民幣歐洲離岸市場的“第一桶金”;哈珀訪華不僅爭取到中國對加拿大支柱產業——石油業的投資與合作,也解決了加中旅游目的地協定這個被認為每年可為加拿大創造至少1億加元旅游收益的“大單”,完成此前10年多屆政府未完成的夙愿,還如愿以償地租回了一對大熊貓;至于美國,人民幣匯率、知識產權保護協定等看不見摸不著,卻與經濟息息相關的“虛擬訂單”,在雙邊互訪中屢見不鮮。
別考慮虧不虧,幫助別人就是幫助自己
和以往相比,近年來中國在簽署“領導人訂單”時,特別注重經濟效益和政治外交效益、短線經濟效益和長遠經濟效益的平衡統一。
各國覬覦中國“領導人訂單”的目的各不相同。
美國、法國等發達國家,因和中國貿易逆差越來越大,一方面希望借“領導人訂單”推銷本國產品,平衡貿易逆差,另一方面希望中國潛力巨大的市場能幫助本國企業提高效益,緩解本國經濟危機和失業壓力。
此外,“欠中國錢最多”的美國,和深陷歐債危機、渴望中國出錢拉一把的歐洲,也同樣希望在這一領域獲得領導人訂單。
一些本身經濟形勢較好、和中國貿易平衡也保持得不錯的國家,如德國、澳大利亞等,則希望通過領導人訂單錦上添花,從中國獲得更多實際利益。
新興國家、發展中國家希望借領導人訂單搭上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順風車;一些本身經濟發展滯后的第三世界國家,則希望“先富起來”的中國能通過領導人訂單,在其最急需的基礎設施等領域施加援手,為其注入經濟持續增長的底氣。
對于中國而言,適當簽署一些領導人訂單除了獲得政治、外交收益,也不無經濟上的好處。
首先,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各主要經濟體實現貿易平衡,對中國長遠而言是有利的,惟如此,才能確保彼此間擁有持續、旺盛的購買力,在全球經濟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地球村”時代,意義十分重大。
和以往不同,如今中國是具有全球利益的大國,國民經濟已成為和全球經濟高度融合的組成部分,閉門自守,獨善其身,或只想“多出”,不欲“多入”,是很難持久的。再者說到,保護知識產權,維持人民幣合理幣值,在量力而行的基礎上協助其它經濟體紓困,對中國這個高度外向型巨大經濟體而言同樣具有積極意義。倘若這些重要市場和技術來源地遭受滅頂之災,中國自身經濟、就業等也會受到沖擊。而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和全球金融體系內話語權的提升,對知識產權、金融秩序的維護,就是在保護自身的利益。
另外對于新興國家、資源性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而言,在互惠互利的基礎上進行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投資,對于開發當地資源、市場具有積極意義。在中國經濟需要資源輸入,中國產能需要海外市場的背景下,在基礎設施等方面幫助別人,實際上也等于幫助了自己。
就怕收了訂單不辦事兒的
然而領導人訂單畢竟并非單純以經濟考量的產物,其出臺必然伴隨著許多非經濟因素。且由于政治和其它原因,中國和許多大經濟體相比,在這方面的騰挪余地較小,令不少“領導人訂單”的效益打了折扣。
如中美之間,一方面,美國不斷抱怨中美貿易逆差不斷增大,中國對美國產品開放度不夠,另一方面卻對中國最需要、最有購買意愿的美國商品,如高科技產品和技術,施加種種出口限制。如此一來,便形成“中國要買的美國未必賣,美國愿賣的中國未必需要”的怪圈,迫使中國給予美國的“領導人訂單”,往往集中在民航客機、農產品等狹窄的領域,中國人不滿意,覺得花大價錢買了一堆未必適用的東西,美國人同樣不滿意,覺得這點出口杯水車薪,和中國的逆差還在繼續拉大,結果便是“領導人訂單”不斷簽,貿易摩擦也未見減少。
在制造業的頂級領域,可供選擇的余地少之又少,如今能生產擁有全球商業飛行許可客機的,除了美國波音,就只有歐洲空客。中國自身在這一領域剛剛起步,尚不具備自給自足能力,要擴大民航機隊,就只能“非此即彼”。正因如此,一段時間里才出現了外媒所言,中國人“和法國鬧僵就大買波音,和美國鬧僵就狂購空客”的領導人訂單怪現象。數年回頭盤點,兩家都沒少買,“買方市場”仍是鏡花水月,借“熱一頭冷一頭”所欲達到的“非經濟”目的,也未必就真達到了。
有些國家的領導人,前腳捧走“領導人訂單”,后腳便翻臉不認賬,中國白白“豪購”,扔出大把真金白銀,卻并未換回期待的回報,只能用“下次再來也不會送訂單了”的表態聊以自慰。
還有極個別國家,對“領導人訂單”產生依賴、訛詐心理,拿到便抹嘴走人,不思回報,仿佛拿得天經地義,等吃光用光,便厚著臉皮再來伸手,甚至玩“會哭的孩子有奶喝”的手法。
此外,某些領導人訂單仍遺留有改革開放前“重政治輕經濟”、“窮大方”的痕跡,仍以客機訂購而言,盡管中國民航市場發展迅速,但近年來新增客機數量似乎有些過多,個別航空公司(如東航)因吃進太多新客機無力消化,業績每況愈下,有些匆匆購進的新客機甫一出場,便轉手流入租賃公司旗下,造成不必要的資源浪費。
由此可見,領導人訂單在新時期仍會長期存在,既能產生中國所期待的經濟、非經濟效益,也仍會繼續出現這樣、那樣的經濟、非經濟副作用。如何讓“領導人訂單”發揮更大效益,實現簽單初衷,達到雙贏目的,并避免種種副作用,是對中國決策者們的嚴峻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