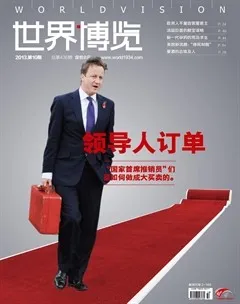拉贊助與打秋風
并非只有中國人喜歡去富人家吃拿卡要,世界人民都“打秋風”,只是沒這詞而已。
中國人,什么字都往雅了談。比如上門吃拿卡要,叫做“打秋風”。米芾札里有詞,曰“打秋豐”,想來意思很順:人家秋天豐收啦,你上門去打兩把,和“打土豪”差不多。但“打秋風”聽來就風雅了。《儒林外史》里,張靜齋拉著剛中舉的范進去縣令處打秋風;《紅樓夢》里,劉姥姥進大觀園,實質也是打秋風。
大的單位無比強勢,就不叫打秋風了,直接是拉贊助。日本戰國時,織田信長往京都去挾天子以令諸侯——日本謂之上洛;洛者,洛陽也,日本是慣例把京都當作中國漢時洛陽的,比如京都的城下町,就叫做洛外町——就往京都鄰近的自由貿易都市堺港去了趟,跟當地富商今井氏們聊天:兄弟我上了洛,要保京都一帶和平,你們商人們也不好意思干看著吧,那就有錢的捐錢,沒錢的捐點火繩槍和茶器吧……
中世紀時候,歐洲藝術家要么靠教廷貴人養,比如羅馬的藝術家作坊,或多或少,都能得些教皇接濟;但小地方的教廷和藝術家就慘一些,于是歐洲地方教廷,也得跟中國僧侶似的:化緣。比如,許多地方教會,有地位但沒錢,于是隔三差五,請當地領主、富商、大人物來聚聚,好比中國和尚請員外們來個法會。吃完喝完祭祀完,就讓教堂藝術家奉上曲子一首,恭祝領主富商們身體健康、得上帝的寵幸,最后領主們也識趣,知道上帝的音樂不是免費的,就會捐助一二。大家面子上都下得來,多好。巴赫、維瓦爾第這些巴洛克音樂大人物,都寫過類似的致敬曲子——實在是幫忙打秋風拉贊助。
大航海時代,肯砸錢的人多,打秋風的人更多。哥倫布這樣的大航海家如今自然是跨時代的不朽,但當初都是接了贊助商的錢,出門給雇主撈黃金的。話說,那時代更多的是小冒險家,沒大名氣,也沒發現過美洲、玩過環球航行,怎么蒙錢呢?于是有了個好玩的行當。那會兒,威尼斯頗多退役水手,轉行去做歌劇龍套的。如果一個小冒險家想打秋風,就雇些威尼斯出產的退役水手,裝滿一船,然后買幾張裝模做樣的推薦信,這里混一個印章,那里騙一封委任狀,最后裝點得一身金燦燦去找大貴族投資,一大筆錢到手后,沒出航就已經是大爵爺的款了。總而言之吧,借著未知的世界信息不對等拉贊助,外國人更駕輕就熟。
如今舉世都說,托爾斯泰的夫人如何不好,實際上,如果細加思量,托夫人一輩子在做的,就是拒絕各類打秋風的小混混。托爵爺不僅小說里寫了許多理想主義故事,現實生活里也打算解放農奴,做個道德高尚的人。他老人家道德高尚自然無妨,但托夫人卻得想法子:怎么讓家庭繼續運作,養著爵爺過舒服日子。而且托爾斯泰晚年,已成歐洲青年導師,五湖四海的俄羅斯有志青年都上門來,參拜瞻仰,住下不走。托爾斯泰等于養了一門子食客,大家天天吃飽無聊,就談論如何改造社會,如何培養道德,如何構筑人間天堂……而托夫人只好唱黑臉扮惡人,時不時趕走幾個青年,時不時對新來的青年說不,就差直接說了:你們就別仗著老爺子理想主義,打他的秋風啦!
打秋風這事,其實也是人看衣裝。印象派大師雷諾阿和莫奈二十出頭時,倆窮學生,經常聯手去蹭飯。當然,那會兒雷諾阿對莫奈有一點疑問:大家窮成這樣,你還打扮成貴公子、花衣袖、金紐扣,這像打秋風的樣子么?很多年后,他才明白真相。
話說1877年,莫奈打算畫圣拉扎爾車站。那時他明明窮得都沒法住巴黎,只好搬去鄉下了,卻還留著貴公子衣裳、花衣袖和金紐扣。于是昂首闊步,去找圣拉扎爾車站站長,張嘴就是“兄弟我是畫家莫奈!”氣度太大,站長都不好意思說“沒聽過,你是誰啊?”莫奈接著通報一個大新聞,“我決定畫你們車站了,本來想畫巴黎北站的,但你們站更有范兒!”站長受寵若驚,趕忙去安排。于是莫奈在站長室,一邊享用人家奉上的咖啡雪茄,一邊翹二郎腿看車站清場放煙,然后施施然出去,畫了一打兒畫,最后還接了站長遞上來的禮物,瀟灑離去——所以你看,打秋風拉贊助,佛靠金裝人要衣裝,全世界都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