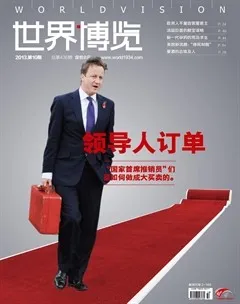在臺灣吃面
臺灣面食的蓬勃發(fā)展要感謝日本人、1949年以后入臺的各省移民以及朝鮮戰(zhàn)爭時美國支援的小麥,缺一不可。
閩、粵地區(qū)居民均以米食為主,17世紀(jì)以后,外省移民來到臺灣,也將原鄉(xiāng)飲食習(xí)慣帶入,但傳統(tǒng)臺灣食物也并未發(fā)展出面點。
日本人喜歡吃面,日據(jù)時期,日本飲食漸漸傳入,拉面一味自然少不了。此后,臺灣開始有了“大面”,除了熬湯的手法不同外,大致與日式拉面接近,還切了肉片點綴。小時候到外公家,總要弄碗大面,齒頰留香。
1949年以后,許多新移民入臺,來自北方的鄉(xiāng)親也不少,他們想念家鄉(xiāng)味,可是臺灣不產(chǎn)麥子,外匯又短缺,實在沒有太多余錢可以進口小麥,著實過了一段食不甘味的日子。
朝鮮戰(zhàn)爆發(fā)以后,美國開始援助臺灣,除了提供貸款外,也提供糧食,小麥?zhǔn)侵饕椖俊拇艘院螅_灣的面粉供應(yīng)增加,政府甚至鼓勵吃面,將節(jié)余的大米外銷。所以臺灣除了原有的大面以外,還出現(xiàn)了許多新品種面食,從蔥油餅到水餃,無一不全。當(dāng)時,臺北火車站人來人往,但凡能開個館子,無不生意興隆,還真有幾家館子賣面、賣水餃,店門前照例有一口大湯鍋,燉的是牛骨頭高湯,架子上有牛雜、牛肉,令人垂涎。還有些刀削面館,師傅胸前抱著面團,飛也似的快刀,面條一根根地落入鍋中,吸引許多人圍觀。
40年前,臺北火車站就已經(jīng)是人文薈萃之地,重慶南路書店街遠(yuǎn)近馳名,往東的南陽街則是補習(xí)班林立,要考大學(xué)、考公務(wù)員、留學(xué)語言考試都得到這,賣吃食的小館子應(yīng)運而生,就像《東京夢華錄》中的相國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