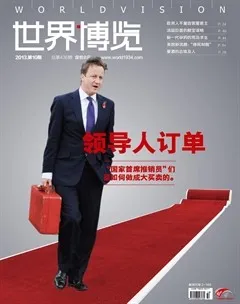推倒胡同的無形巨手
一個外國人在大柵欄胡同里快樂又憋屈的三年時光。
北京的胡同改造是一個充滿爭議的工程,涉及到文化遺產保護,城市規劃和危房改造,相關話題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一個來自大洋彼岸來的美國佬兒有什么資格也來啃這塊硬骨頭呢?
一般來說,最堅定和尖銳的胡同保護者都是歷史學家和游客們,他們沒有親身在胡同里生活過,都是被古老建筑和其細節吸引。而這位中文名叫梅英東(英文名麥爾)的“和平隊員”另辟蹊徑,他在北京大柵欄的胡同里一住就是三年。
麥爾說他受到法國建筑師柯布西耶的啟發,這位20世紀初的建筑大師鼓勵大家去開拓歐洲城鎮中狹窄曲折的小路,修建更寬闊的大道,他認為將中世紀居住條件當做文化遺產的觀點都是胡扯。柯布西耶說:如果你問問這些整日忙于寫論文和指導公共意見的戀舊人,他們住在哪里,肯定是某某小區,電梯公寓什么的,要么就是位于花園深處,舒服豪華的小別墅。于是2005年麥爾搬到大柵欄的楊梅竹斜街胡同里,在附近的炭爾胡同小學當上了英語老師,當初選擇大柵欄完全出于偶然,但這里正是觀察北京胡同變遷的絕佳之地。
1403年明永樂大帝在規劃嚴整,方方正正的內城之外的前門地區設立了一個商業區,里面有商店,錢莊,旅舍,茶館、戲院與男娼妓女齊全的“窯子”。1422年,城中的衛兵認為,這里通道眾多,竊賊在夜晚很容易逃竄。于是在胡同區的入口圍起了柵欄,在天黑之后上鎖,大柵欄由此得名。清朝的時候很多漢族人都被趕到皇城以外,搬到大柵欄。于是很多傳統的老北京文化,比如烤鴨、京劇,還有手工藝都轉移到了大柵欄地區。所以這里非常鮮明的反映了平民的生活。
一般來說,記者好象吸血鬼一樣,吃完就走了。但是寫這本書的時候麥爾變成一個沒有牙齒的吸血鬼,慢慢吃透了胡同里“接地氣的生活”。麥爾住的四合院有5個房間,一共住了7個人,他住了兩間房,被鄰居戲稱為“地主”。但這個地主完全沒有隱私,一切都清清楚楚地讓大家看在眼里。隔壁住的老寡婦總是不敲門就進屋,看他早晨五點鐘不起就罵他是懶蟲,不過她總是給懶蟲包餃子,煮麻醬面。此外,麥爾最愛去來自山西平遙農村的劉老兵一家開的刀削面館吃面,還會跟著胡同里的廢品王去城區外的廢品回收站。
他能大口喝豆汁,快樂地讀公共廁所墻上“治痔瘡,到東大”的廣告詞。他和胡同里的人一樣愛讀《北京晚報》警法版,“女孩往熟睡男友身上澆汽油”,每天細細研讀尋人版。麥爾作為英語老師也沒什么正形,他會給小孩子講菜市口無頭怪的鬼故事,交片警用英語說臟話。在居委會的英語學習班里,他告訴那些退休老人,五個福娃之外,應該再增加三個,他他,媽媽,的的,來代表真正的北京文化,讓“老學生”們笑作一團。
在胡同之外的人看來,這里就是貧民窟,但麥爾告訴我們,這里并非疾病與問題行為滋生地,也毫無貧民窟常見的絕望之氣,常常回蕩著哈哈大笑與熱烈的談話,人們彼此禮貌相待。經過三年的親身體驗之后,麥爾覺得自己找到了胡同現在存在的經濟價值,他說,大柵欄是一個大熔爐,讓外地人變成本地人。
但是胡同里也不都是幸福時光,冬天的時候胡同里沒有暖氣,蜂窩煤爐子又不安全,只能像凍僵的木乃伊一樣裹著三層毛毯瑟瑟發抖。麥爾還寫了他某天早晨朦朧中感覺到,一只蜘蛛試圖鉆到他耳朵里去,結果發現那只蜘蛛有巴掌大小,然后感覺前一天晚上吃的紅燒五花肉和油炸青豆在胃里翻江倒海。他跑到公共廁所,但還是晚了一步。麥爾寫道:“在把四角褲狠狠踢下廁所坑洞時,內心盼望著,回到家時“無形巨手”已經在四合院的外墻上畫上了那亮白色的“拆”字。”
書中很多處提到無形巨手,但是麥爾說,他不知道那個無形之手是誰,“一個作家需要去找一個反面人物,我在寫這本書之前一直祈禱說給我一個反面人物,比如說SOHO中國張欣,但它沒有一個具體的形象,沒有辦法站出來,這是北京現在最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