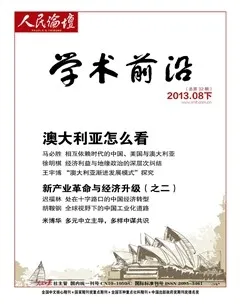“亞洲協調”機制能否平衡大國戰略訴求
摘要 中美關系是當今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系。中美關系的發展對亞太地區影響最大,而局勢變化所帶來的機遇與威脅令澳大利亞感觸最深。澳大利亞是一個典型的亞太國家,對戰略脆弱性的先天憂慮是其外交政策的主要驅動力。在澳大利亞短暫歷史的大部分時期里,亞洲更多地代表著威脅而非機遇。事實上,澳大利亞長期以來對美國堅定不移的支持對兩國均為不利。懷特的“亞洲協調”構想對全球經濟甚至國際力量對比的結構轉型作出了一種貌似合理的回應,但在澳大利亞難以得到響應,更不用說在美國或中國。
關鍵詞 中澳關系 中美關系 亞太共同體 亞洲協調
【作者簡介】
馬必勝(Mark Beeson),澳大利亞默多克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教授,《當代政治》雜志聯合主編。
研究方向:亞太地區政治、經濟和安全。
主要著作:
《Regionalism and Globalization in East Asia》、《Institutions of the Asia-Pacific》等。
王勇,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導,國際政治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眾所周知,中美關系是當今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系。無論從戰略意義和地緣政治對抗的可能性來看,抑或從兩國之間經濟依賴的廣泛性和政治風險性來看,①中美關系的發展將對雙方產生重大的影響。對國際體系內的其他國家尤其是中小國家來說,這同樣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中美關系的發展對亞太地區影響最大,而局勢變化所帶來的機遇與威脅令澳大利亞感觸最深。一邊是“中國崛起”所帶來的經濟機遇,另一邊是長期以來對美國的戰略依賴,澳大利亞的決策者在尋找平衡兩者之道,這不僅可以幫助澳大利亞決定自身的命運,還可使整個“亞太地區”的力量對比更加明朗。從理論層面來說,“相互依賴理論”(或曰“相互依存論”)有可能產生自由主義者所期望的良性影響嗎?②還是如現實主義者告誡我們的,做好可能爆發沖突的準備才是應對瞬息變化的戰略形勢的明智之舉?
為了回答上述問題,我們得評估各種區域性組織推動合作的能力。為此,我們主要聚焦于中、澳兩國的政策與立場。兩國均與現有的國際秩序休戚相關,而且從日益重要的雙邊關系中獲益良多。這里的關鍵問題是:由中、澳雙方共同主張的區域性組織是否內部融洽,運作有效,且能在一個新老大國日益對抗的不穩定區域發揮出建設性的作用?為此,我們首先要簡單回顧區域內部關系所發生P3CuTQzDUzvKXw7qYYqTgPJoMk5Ye0oPG+kt13pOBeM=的歷史、地理背景。在筆者看來,單是區域的界定就已夠麻煩了,更不必說理清其內部復雜的多維關系。對中、美而言,亞太地區是兩國外交政策著力和角逐的關鍵區域,這一基本現實由于近期美國的“轉向(亞洲)”或“重返亞洲”而愈發明顯。③在這一背景下,澳大利亞是一個典型的亞太國家,至少想要成為一個典型的亞太國家。事實上,澳大利亞采取了積極有力的外交政策,④并努力以自己的方式來促進亞太地區的發展與共識。但在這方面,澳大利亞有時并未得到中國或美國的幫助。
澳大利亞的情況凸顯出所謂“中等國家”⑤在平衡經濟利益和潛在的戰略沖突時所可能受到的制約。⑥澳大利亞這種國家能夠影響大國和整個國際體系的傳統方式之一是建立并加入多邊組織。奉行“多邊主義”確實被認為是中等國家的一大標志,⑦這也正是近年來澳大利亞外交辭令的核心內容。亞太地區的各種多邊組織越來越多,且相互競爭,各顯神通,意欲成為區域內最重要的組織。這些區域性組織是否能應對瞬息變化的地緣政治形勢,目前不得而知。如若不能,那或許證明了狹隘的國家利益較之區域性組織更為重要。對澳大利亞等中小國家來說,這使決策者不得不面對傳統的戰略忠誠與新的經濟現實之間的選擇。因此,在考察澳大利亞應對之策的具體成因之前,我們先得撇開澳大利亞,談談中國與美國為影響該區域發展所展開的對抗。
區域的界定:“亞洲”在何處
自19世紀成為潛在的太平洋大國(potential Pacific power)以來,美國便積極致力于影響亞太地區的發展。該地區的別稱有“環太平洋地區”、“太平洋亞洲地區”和最近流行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區”,以及更狹義但也更實用的“東亞地區”。⑧稱謂的多樣性反映出區域認同的變化性與爭議性。這一問題并非僅僅屬于詞典編撰家或話語理論研究者的興趣范疇。相反,區域認同或區域稱謂乃是現實世界中制度調整和發展的基礎——“金磚國家”的異軍突起便是一個鮮明的例子。⑨
理念和認同會產生實質性的影響,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制度創新在“亞太地區”層出不窮的原因:新的制度劃出了區域的范疇,并決定了哪些國家將能訂立協議并從中獲益。重要的是,近期的“東亞峰會”、東盟、“東盟10+3”國家集團等大多是由東亞國家發起。美國居然對這些倡議普遍表示冷淡。美國的態度并不矛盾:它盡管是二戰后國際體系的主要締造者,但并不喜歡過多地卷入那些影響和控制力有限的國際組織中。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對美國才有巨大的吸引力,因為它們往往有助于鞏固并加強一種能夠反映美國自由主義價值觀和規則喜好的(國際)體系。⑩
尤為引人注目的是,美國之所以有興趣參與亞洲的區域制度構建,全面調整戰略重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一個堅定自信、影響廣泛而且實力強大的中國的崛起。美國決定重視至今仍處于邊緣甚至多余地位的東亞峰會,這意味著東亞峰會有可能成為區域發展進程的中心角色。在某種層面上,此舉可被視為(美國)構建自由主義制度以及試圖解決“集體行動困境”(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s)的反映。但此舉也可被解讀為(美國)拋棄了傳統模式的地緣政治策略,不再尋求限制中國對這一本與美國無關區域的主導權。因此,中國對這一區域的看法與美國或澳大利亞截然不同。
中國是東亞國家,美國和澳大利亞卻不是,這一事實必然也一直影響著中國精英們的思維。就中國的領導人和大部分民眾而言,中國歷來就是東亞地區的中心。對中國國內日益喧囂的眾多“網民”來說,昔日臣屬國(如越南)不但挑釁中國的領土主權,而且還與美國建立更為親密的戰略關系,尤其令人惱火。無論是對是錯,許多中國民眾和意見領袖確實認為,越南、菲律賓在利用(美國)轉向(亞洲)來迫使中國讓步。每當中國解決南海領土爭端的政策遭遇重大波折時,這種考慮就會變得尤為突出。中國的政策不再是此前大獲成功的“魅力攻勢”,試圖讓鄰國相信中國的善意以及“和平崛起”可能帶來的好處,而是突然變得更加堅決起來,甚至說更具攻擊性。
無論我們如何評判這些變化,不可忽視的是日益喧囂的民眾在其中的推動作用。部分民眾認為政府在捍衛國家利益方面顯得過于軟弱,并對此大加抨擊。在這種令人感到焦慮不安的政治和戰略形勢下,澳大利亞這樣的國家必須盡量處理好可能難以兼顧的輕重緩急。前總理朱莉亞·吉拉德領導的澳大利亞政府,雖然極力強調“亞洲世紀”所可能帶來的經濟利益,但也宣稱:戰略形勢的變化并不意味著澳大利亞會改變依靠美國保護的傳統政策。結果,和這一區域的其他國家領導人一樣,澳大利亞的決策者也必須對其國內政策和國外政策作出復雜的調整。因此,談談這兩個方面是很有必要的。
澳大利亞的國際制度倡議
澳大利亞面臨著一系列與中國完全不同的挑戰。無論在實現其區域性目標中遇到什么困難,中國無疑是該區域(亞太)的一部分,澳大利亞卻并非如此。從歷史上看,澳大利亞的決策者在處理同“亞洲”的關系時往往舉棋不定,認識混亂。確實,在澳大利亞短暫歷史的大部分時期里,亞洲更多地代表著威脅而非機遇。看似矛盾的是,澳大利亞和這一區域卻有一個共同點,即歷史因素及其對當代關系的塑造。比如,在解釋東北亞地區“發育不良”(stunted)的區域主義時, 我們習慣于思考中日遺留問題的長遠影響,但我們也須認識到,亞洲以外國家的態度和關系同樣是由特定的歷史過程所塑造的。
再拿澳大利亞來說,對戰略脆弱性的先天憂慮是其外交政策的主要驅動力。用國際關系學的術語來講,即對“被拋棄”(abandonment)的懼怕總是壓倒對“被牽連”(entrapment)的擔心。一代又一代的澳大利亞決策者極力發展同前總理羅伯特·孟席斯(Robert Menzies)所說的“強大伙伴”(great and powerful friends)之間的親密戰略關系,至今依然如此。二戰中期,澳大利亞迅速而務實地將其主要依靠對象從英國轉向美國,此后,對美關系便一直是澳大利亞外交的重中之重。結果,澳大利亞朝野兩黨都極其重視并樂于維持澳美同盟關系,這在世界各國中相當少見。奧巴馬總統說得好,百年來,凡有美國參加的歷次沖突里,澳大利亞一直與美國并肩作戰。澳大利亞曾參加了越南戰爭、兩次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無論人們如何看待澳大利亞參戰背后的戰略邏輯或需要,根深蒂固的傳統憂慮或許能解釋為什么澳大利亞的決策者樂于為地緣政治安全付出如此高昂的代價。
澳美戰略同盟關系的堅實基礎及其重要意義值得一提,原因如下:首先,以美國為中心的“輻射型”同盟體系在亞太地區的長期存在必然會制約其他體系或戰略在這一區域的發展。這在冷戰時期表現得最為突出,當時,由于意識形態和戰略上的分化,東亞甚至亞太地區未出現任何形式的區域主義。可以想像的是,這一時期的中澳兩國聯系極少,而且是在互不了解和意識形態桎梏的迷霧中看待彼此。還應注意的是,1973年澳大利亞前總理高夫·惠特蘭(Gough Whitlam)踏上訪華的“破冰之旅”,恢復同中國的邦交,這實際上乃是步美國總統尼克松之后塵。即使是二戰后最為“激進”的澳大利亞領導人,也不會冒然走在美國外交的前頭。
于是,半個多世紀以來,澳大利亞在制定外交政策時始終保持緊跟華盛頓。然而,即使是澳大利亞保守派總理也開始意識到,在澳大利亞的北邊,亞洲的迅速工業化不僅改變著亞洲自身,也改變著澳大利亞與亞洲的關系。人們目前關注的是,中澳經濟關系以及中國的飛速發展對澳大利亞經濟的巨大影響,但這一幕由來已久。早在1966年~1967年,日本便已成為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伙伴,澳資源驅動型增長引發了一股“資源熱潮”(resource boom),而一場始料可及的“資源泡沫”也隨之而來。雖然如此,東北亞和東南亞地區所謂“四小龍”經濟的迅速崛起,極大地改變了澳大利亞在這一區域的立場。這確實使鮑勃·霍克(Bob Hawke)、保羅·基廷(Paul Keating)等新一代領導人認識到,若想確保澳大利亞的前途,就必須成為這一區域的一部分。
從制度創新和區域內部關系的角度來看,這一時期澳大利亞最重要的貢獻便是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關于該組織的論著頗豐,本文在此不再累述,但須對正在變得無關緊要(筆者以為此乃意料之中)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談談幾點拙見。首先,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所體現的區域構想過于龐雜和模糊,以至于難以形成凝聚力,更不必說對組織及其宗旨的認同了;其次,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的議程不可能激發其亞洲成員國對“批發式”貿易自由化的興趣,畢竟世界貿易組織的存在,使得亞洲經濟合作組織的這一職能顯得有些多余;其三,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采取了以自愿和共識為原則的“東盟模式”,這意味著它所能做的僅僅是敦促和疏導,缺乏許多成員國所希望的強制力;其四,在各種經濟危機面前,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始終未能發揮任何作用,它也無力處理中美經濟關系以及圍繞所謂中國“操縱”(manipulation)貨幣而產生的矛盾;最后,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不得不與仿效它而建立的類似組織相互競爭,回首過去,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的主要意義可能在于,它凸顯出澳大利亞決策者在影響亞太地區過程中所存在的困難。
澳大利亞近期在亞太地區所倡導的制度創新也面臨著同樣的命運。鑒于“東盟10+3”等東亞組織必然將澳大利亞排斥在外,陸克文(Kevin Rudd)主張推動建立一個完全由澳大利亞倡導的“亞太共同體”(Asia-Pacific Community)。在陸克文看來,該計劃的意義不僅在于將澳大利亞包括在內,而且也包括美國。此舉的目的首先是要確保澳大利亞不被任何潛在的重要區域決策組織所排斥,其次則是確保該組織不由中國所主導。這體現出近期澳大利亞外交政策一貫的陸克文色彩。在對華問題上,陸克文自稱“無情的現實派”(brutal realist)。他意欲使美國從戰略上鎖定亞太地區,這是對澳大利亞外交政策中精明圓滑的傳統風格的延續。因此,值得注意的一個看似矛盾的現象是,在這位會說中文普通話、深諳中國事務的“亞洲通”上臺后,中澳雙邊關系反而惡化了。
有許多評論者認為,“亞太共同體”之所以未能實現,是因為在爭取那些小心維護其在區域性組織的領導權、高度敏感的東南亞國家領導人方面所下的功夫還不夠,這種看法可能言過其實了。不過,也有人認為,“東亞峰會”就是陸克文的“亞太共同體”,只是名稱不同而已,因此這是澳大利亞外交的勝利。但毋庸置疑的是,“東亞峰會”由于美國的重視才得以蓬勃發展,這正是澳大利亞決策者極力保護的成果。當然,美國的利益調整及其在中國周邊地區的“制度性存在”絕不是中國樂于看到的結果——尤其是“東亞峰會”的成立是以“東盟10+3”為代價的。澳大利亞對美國及其重返亞太的熱情支持在歷史上早有先例,但如今卻發生在中國崛起而美國相對衰落的大變局形勢下。問題是,澳大利亞的策略還有意義嗎?特別是在中國經濟重要性日益增長的情況下。
國際利益與國家利益
一切國家都尋求國家利益,中國亦不例外。不過,界定和尋求國家利益的方式折射出各國不同的歷史境遇和地緣環境。中國所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顯然是其變化中的外交政策風格、目標以及對自身在國際格局中所處地位的認識的基礎。許多中國學者認為,中國應該進一步參與東亞地區的國際事務,以擴大其影響力。隨著中國逐漸融入國際政治經濟體系,它不得不適應國際體系各種規則的約束。這方面最重要的例子是: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就必須達到世界貿易組織所要求的準入條件。但如今,中國的決策者逐漸意識到,他們也有可能參與制定國際規則,而不是被動地接受規則。中國所積極主張的多邊主義或許并不完善,且帶有機會主義的特征和將之作為某種政策手段的動機,但這畢竟標志著中國外交及其政策內涵的重大轉變。對中國的鄰國來說,關鍵問題是:中國是否正在“融入國際社會”,并改變著自己的風格和外交方式呢?
至今所有的證據都表明,在眾多中國外交精英和決策精英中出現了一次大的文化轉向,至少在外交思維方面確實如此。約翰斯頓(Johnston)據理宣稱,“相當多的細微證據表明,從違反某些現實政治規則和慣例的角度來看,由于(中國)加入了這些(多邊)組織,中國的外交官、戰略家和分析家已經融入了國際社會。”我們之所以重點提到這一觀點,是因為它不符合中國歷來從現實主義角度來考慮政治決策和國家安全的傳統戰略思維。包括陸克文在內的許多觀察家都相信,中國存在一種權術文化,它使中國傾向于認為中國的外交政策應貼合政治現實,對國家利益則應精打細算。換句話說,筆者認為,盡管中國加入了各種多邊組織且表現日益突出,但中國的國家政策依然是由對國家利益的追求所驅動的,不可能在外部規則的影響下發生改變。在一些觀察家看來,“只要中國對其大國地位感到充分自信,它便覺得完全不再有必要遵守由西方所主導的國際體系規則”,這才是現實。
中國的鄰國日益緊張。對它們來說,我們的討論可不僅僅是學術之爭。要知道,盡管東盟大唱合作、理解和與鄰為善的高調,但它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為了在惡劣的地緣政治環境中尋求互助和自保。集體利益若能提供實現國家利益的途徑,便是值得追求的,而國家利益的重中之重則是捍衛國家主權。這一定律便是過去近50年里東盟地區內部關系的基石。然而,重要的是,“東盟模式”的影響已經超出了原有的東南亞國家,擴展至其他的東亞組織和亞太組織。就目前局勢高度緊張的南海問題來說,東盟地區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依然是也必然是該區域內最重要的組織。
東盟地區論壇的成立可謂生逢其時。然而,盡管亞太地區所有的重要國家與地區(如中國大陸、朝鮮,甚至中國臺灣地區等)都加入了東盟地區論壇,但它還是讓所有支持者都感到失望。東盟地區論壇不但無力應對區域性的重大問題如朝鮮半島問題、臺海關系問題以及日益嚴峻的南海領土爭端,而且它秉承東盟的“不干涉(內政)”原則,極力避免觸及國家主權和其他敏感問題。為了確保成員國的“零責任”,東盟地區論壇使自身盡量“最小化”。這樣做的實際后果早有批評者指出,東盟得到了只能避免沖突、不能解決問題的名聲。在最近召開的峰會上,東盟各成員國甚至無法達成聯合聲明,這表明東盟和東盟地區論壇在涉及重大國家利益問題時難以開展實質性的集體行動。
中國與其周邊的東盟國家一樣,視國家主權為至高無上,而國家主權正是建立真正具有改變能力的區域性組織的主要障礙。作為東盟地區論壇的運作模式,“東盟模式”起初是吸引(各國)參加論壇的因素之一,可中國不可能被迫做它不愿做的事情。東盟地區論壇無疑是一種多邊協定,但缺乏實質性的約束力,尤其對中國。反過來,中國顯然有能力運用其日益增長的經濟影響力和資源來爭取柬埔寨,加深東盟內部大陸國家和海洋國家之間的隔閡,使東盟在有關中國領土訴求的問題上無法達成一致。
這一結果不足為奇。如果我們看看中國更青睞的區域合作平臺——“東盟10+3”的發展和運作,會發現情況同樣如此。與東盟區域論壇一樣,“東盟10+3”喜歡不拘禮節,反對形式主義。在“東亞峰會”再次召開之前,“東盟10+3”有望成為代表中國崛起以及東亞地區訴求的最重要組織。然而,決定東亞地區認同和影響力的制度化方式是一場長跑比賽。中國熱情支持“東盟10+3”的原因是很好理解的。除了中國和東南亞國家,韓國和日本也加入了“東盟10+3”,澳大利亞和美國則未加入。簡而言之,正如東南亞各國和澳大利亞的許多外交官們所擔心的,“東盟10+3”國家集團可能成為中國發揮其影響力(如果不是區域霸權的話)的平臺。
我們之所以強調這種可能性,是因為“東盟10+3”強調功能性合作。“東盟10+3”原本便是亞洲金融危機以及承認東亞地區缺乏危機管理機制的產物,因此,“東盟10+3”必然致力于金融合作。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東盟10+3”在金融合作方面取得了一定進展,但討論較多的《清邁協議》(Chiang Mai Initiative)及其關于區域貨幣互換機制的具體倡議,在面臨首次重大考驗時卻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隨著雷曼兄弟公司破產后金融危機席卷全球,曾是區域努力重點和關注焦點的“清邁協議”機制仍然一無是處。這或許會對整個“東盟10+3”造成重大影響。由于“東盟10+3”擁有一個日益強大的競爭對手——“東亞峰會”,許多人質疑前者是否還有意義。“東盟10+3”籌劃亞洲統一貨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在歐洲危機爆發后,亞洲統一貨幣完全不在議程之中。因此,“東盟10+3”盡管得到中國的青睞,其前景卻大不如一兩年前,它最終將取決于中國是否有能力并愿意進一步擴大其經濟的影響力和國際化程度。
若僅考慮澳大利亞自身的區域構想,而不考慮對華關系的話,這一結果對澳大利亞可能是有利的。但是,“東盟10+3”畢竟不會邀請澳大利亞或其他非亞洲國家加入,這令人更加擔心東盟會成為排斥美國、擴大中國在該區域的野心的工具。但澳大利亞的經歷告訴我們,區域內部關系是如此復雜,而實現區域性的目標又是如此艱難。
權衡輕重緩急
澳大利亞等所謂“中等國家”應該如何權衡經濟與戰略兩者的輕重緩急呢?經濟相互依賴的內在推動力會改變并限制國家領導人的政策選擇嗎?我們很難從一個國家——尤其是歷史不長卻很獨特的澳大利亞——的經驗中推斷出問題的答案,但澳大利亞的情況表明,傳統的忠誠和觀念出現了一些變化。即便是在一個戰爭的可能性越來越小的時代,澳大利亞依然以傳統的(國家)安全為重。由于中國對鄰國大展“魅力攻勢”,澳大利亞仍舊無法徹底消除對中國崛起的緊張心理——近來南海局勢則使澳大利亞的擔心無從緩和。
然而,和這一區域的大多數國家一樣,無論澳大利亞的決策者喜歡或不喜歡,中國如今是澳大利亞最大的出口市場。更令人驚訝的是,中國也是澳大利亞商品出口的重要目的國,澳大利亞所生產的各類產品中有近一半銷往中國。這使(政府)對國內經濟的調控變得越來越難,尤其是澳大利亞的絕大部分礦業實際上由外資所控制——這一經濟現實尚未被中、澳雙方所意識到。可以肯定的是,由資源推升澳元所導致的“雙速經濟”正在使澳大利亞制造業和服務業逐漸失去競爭力。澳大利亞經濟結構的這一劇烈變化也影響著國內政治,導致了受益于經濟繁榮的產業和地區與未受益于經濟繁榮的產業與地區之間的分歧。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美國利用其經濟優勢和戰略優勢與澳大利亞達成一項對后者極其不利的雙邊貿易協定,也不會受到非議,更不會影響整個美澳戰略關系。相反,澳大利亞正越來越多地擔心中國經濟的影響及其對澳大利亞經濟和傳統的(國家)安全可能帶來的威脅。在這種形勢下,澳大利亞政府在擔心之余也提高了警惕,甚至對中國投資采取了歧視性政策。出于對中國政府通過國有企業在能源和食品行業的戰略性投資施加影響的擔憂,澳大利亞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對中國投資項目進行了干預,以確保其符合“國家利益”。
因此,盡管中澳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日益加深,但這并不必然轉換為一種友好或者說親密的政治關系。確實,兩國之間的外交聯系空前廣泛,以致于澳大利亞資源最豐富、最依賴貿易的西澳州州長宣稱,本州與北京的關系比與堪培拉的關系更重要。興旺的能源貿易使我們看到,同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打交道也并非毫無辦法。但是,中國經濟影響力和存在的迅速擴大的確使澳大利亞對長期安全的深層次的內在憂慮有增無減。
這一基本戰略現實的最明顯表現是美國在澳大利亞北部駐軍。雖然澳大利亞極力宣稱此處僅僅是美軍換防設施,而非美國軍事基地,但這仍足以顯示澳大利亞的戰略思維和對美的忠誠。對澳大利亞來說,澳美雙邊戰略互信仍是重中之重。從中國的角度看,此舉是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關鍵一步。澳大利亞則被視為美國遏制中國的熱心伙伴,這一看法又因擬建立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而進一步加強。從表面上看,“跨太平洋伙伴關系”是一個致力于推動貿易自由化的組織,但中國卻在很大程度上將其看作進一步孤立中國、擴大美國在亞太地區影響力的機制。正如賈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所指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帶有強烈的政治性和歧視性,它包括各種與貿易無關的議程,如勞工標準、資本管制等。這些議程不容討價還價,令中國根本無法接受。
正因為此,中國的決策者在這一勢態變化中感覺受到了侵害。從中國的角度來看,美國似乎正利用其依然強大的經濟優勢在中國的敏感區域內為所欲為。許多美國人會認為,此舉是“軟遏制”(containment-lite)的重要、有效的組成部分,但要注意的是,它煽動起中國國內憤怒的民族主義情緒,并損害了這一區域一些最重要的雙邊經濟關系。此舉對中澳關系的發展也毫無益處。 在中國看來,“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就好像是一群嫌疑慣犯聚在一起,想要阻撓被中國視為合理的目標和理想。簡而言之,中國確實擔心美國及其盟友可能對其實施遏制。這一問題在任何時候都存在,但在一個區域矛盾嚴峻而現有制度框架無力應對的時期,它尤其令人擔心。
從外向內看問題
我們主要聚焦于澳大利亞,因為澳大利亞的經歷突出反映了許多周邊國家所面臨的困難。與澳大利亞一樣,亞洲小國必須在相互競爭的經濟需要和戰略需要之間協商出一條道路。就此而言,澳大利亞還算幸運,因為它不必非得在中、美之間作出近乎可怕的選擇,盡管歷史表明它總是倒向美國一方。不過,若從近期趨勢來推斷,中國不僅必將在本世紀20年代前后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而且其經濟實力和戰略影響力亦會隨之增強。
在美國,許多頗有影響的評論家都認為,國際關系是一場在無政府主義體制中爭奪主導權的零和博弈。在中國,也有許多人持同樣的直觀看法,這一看法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赴美國名校攻讀博士學位而得到進一步加強。不過,冷戰的戛然而止和中國在全球政治經濟舞臺上的重新閃亮登場使我們看到:零和博弈的模型雖然從理論上說得通,但實際上往往做不到。這或許是一個值得慶祝的理由。正如太多的中國人和美國人都相信,中國國力的崛起和美國霸權的明顯衰落不一定導致必然的沖突。
作為當今世界強國和發展最快的國家,中國的國際地位勢必影響到其領導人看待世界的方式。這是一種歷史的使命感,抑或是尚未撫平的憤懣不悅,但要記住,我們也可以從其他角度來看問題。從外向內看問題,可能會有所不同。事實上,澳大利亞長期以來對美國堅定不移的支持可以說對兩國均為不利。澳大利亞的決策者未能發揮“調解人”(honest broker)或“亞洲之橋”(Bridge to Asia)的作用,總是放棄思維和行動的獨立性來交換所謂的安全利益——參加20世紀的每一場大的戰爭并為此買單,還不斷出現在21世紀最漫長的戰爭(指阿富汗戰爭)中。在自愿性的同盟中,一個較為冷淡的伙伴會促使美國更認真地思考其處理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的方式。
當然,放馬后炮是很容易的。不過,在如何使亞太地區的各種關系得以理清甚至制度化,從而避免某些人視為必然的沖突的問題上,還是有一些創造性的觀點。在一篇對拙文給予了極大幫助的文章中,澳大利亞分析家休·懷特(Hugh White)建議:美國和中國都應成為“亞洲協調”(Concert of Asia)機制的一部分。與19世紀的“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一樣,“亞洲協調”將站在中美之間的相對立場上,建立一種處理大變局時代的大國競爭和矛盾的機制。它還可以提供一個應對蔓延于這一區域的某些“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平臺。這樣的建議無疑令許多美國人和忠于美澳同盟的澳大利亞人瞠目結舌。懷特的觀點盡管對全球經濟甚至國際力量對比的結構轉型作出了一種貌似合理的回應,但在澳大利亞飽卻受攻擊。
如果“亞洲協調”的構想或者某種更具協作性、更為制度化地解決區域事務的方式在澳大利亞都難以得到響應,那么這在美國或中國則是更不可能的。但是,建立一種減少對抗、具有制度約束力的亞太區域機制,并非只有澳大利亞這樣的“中等國家”能從中受益。盡管存在失策和誤解,中澳關系告訴我們,即使是看似最不可能的合作伙伴,相互依賴也能帶來益處。如果中澳關系未曾受新興的中國與衰落的美國之間難分勝負的競爭所左右的話,那么中澳關系的現狀會更好。以可持續的方式來進行調整,符合各方利益。
注釋
Drezner, D.W. (2009), "Bad debts: Assessing China's financial influence in great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4(2): 7-45; Miller, K. (2010), "Coping with China's financial power", Foreign Affairs 89(4): 96-109.
Chaudoin, S., Milner, H.V. and Tingley, D.H. (2010), "The center still holds: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surviv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5(1): 75-94.
一位匿名評論家指出,巴拉克·奧巴馬實際上從未使用過“轉向”(pivot)一詞。然而,這一術語很快為人們所廣泛接受,用以描述美國政策的重大調整。參見Barnes, J.E. (2012), "U.S. plans naval shift toward Asia",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2.
在東盟地區論壇和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的成立以及推動東亞峰會召開的過程中,澳大利亞做出了比一般國家更大的貢獻。Capling, A. (2008), "Twenty years of Australia's engagement with Asia", The Pacific Review 21(5): 601-622.
“中等國家”一詞現在常被用來描述澳大利亞這樣的國力不強、影響不大的國家。重要的是,澳大利亞歷屆工黨政府一直選擇用“中等國家”來描述澳大利亞。該詞的含義及其所引起的批評,參見Beeson, M. (2011), "Can Australia save the world? The limits and possibilities of middle power diplomacy",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65(5): 563-577。
Layne, C. (2012), "This time it's real: The end of unipolarity and the Pax America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6(1): 203-213.
Cooper, A.F., Higgott, R.A. and Nossal, K.R. (1993), Relocating Middle Powers: Australia and Canada in a Changing World Order, Carlton, Victoria: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Korhonen, P. (1997), "Monopolising Asia: the politics of metaphor", The Pacific Review 10(3): 347-365; Iriye, A. (1967) Across the Pacific: 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New York: Harbinger.
眾所周知,縮略詞“金磚國家”(BRIC)由高盛投資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Jim O'Neil)首創,但這卻成為原本未合作過的四、五個國家舉行實質性會談的基礎。
Saull, R. (2012), "Rethinking hegemony: Uneven development, historical blocs, and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6(2): 323-338.
Zhao, S. (2012), "Shaping the regional context of China's rise: How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brought back hedge in its engagement with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1(75): 369-389.
Camroux, D. (2012), "The East Asia Summit: Pan-Asian multilateralism rather than intra-Asian regionalism", in, M. Beeson and R. Stubb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Asian Reg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375-383.
Beeson, M. and Li, F. (2012), "Charmed or alarmed? Reading China's regional rela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1(73): 35-51.
根據香港《文匯報》近期的一項民意調查,中國政府應采取更加強硬的姿態來捍衛南海主權完整。參見《文匯報》網頁: http://news.wenweipo.com/2011/06/13/IN1106130126.htm。
Hookway, J. (2012), "Sea tensions deepen with China's ris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7.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12), Australia in the Asian Century, CoA: Canberra.
Rozman, G. (2004), Northeast Asia's Stunted Regionalism: Bilateral Distrust in the Shadow of Globalis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alker, D. (1999), Anxious Nation: Australia and the Rise of Asia 1850-1939, St Lucia: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Acharya, A. (2011), "Engagement or entrapment? Scholarship and policymaking on Asian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3(1): 12-17.
澳大利亞—新西蘭—美國同盟(ANZUS)實際上僅限于澳大利亞和美國,因為新西蘭拒絕裝備有核武器或核動力艦艇停靠。對澳大利亞來說,這一同盟依然重要,也在澳大利亞民眾中獲得更普遍的支持。參見Hanson, F. (2011), Australia and the World: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Sydney: Lowy Institute.
Beeson, M. (2007), Regionalism and Globalization in East Asia: Politics, Secur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algrave Macmillan.
Keating, P. (2000), Engagement: Australia faces the Asia Pacific, Sydney: Macmillan.
See, Ravenhill, J. (2001), APEC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acific Rim Region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近期一份闡述澳大利亞國防重心的白皮書實際上將中國視為可能引發亞太地區局勢不安的根源,這正是陸克文的一貫看法。Manicom, J. and O'Neil, A. (2010), "Accommodation, realignment, or business as usual? Australia'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 The Pacific Review 23(1): 23 - 44.
Sheridan, G. (2010), "The realist we need in foreign affairs", The Australian, December 9.
參見譚亞:“美國‘回歸’后東亞合作的變與不變”,《人民日報》,2011年11月18日。
參見張蘊嶺:“對東亞合作發展的再認識”,《當代亞太》,2008年第1期; 黃永光:“東亞地區制度化進程中的問題與中國的選擇”,《國際經濟評論》,2009年第6期。
Lardy, N.R. (2002), 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e.
Kuik, C. (2008), "China's evolving multilateralism in Asia", in, K.E. Calder and F. Fukuyama, East Asian Multilateralism: Prospects for Regional Stability, Baltimore: John Hopkins Press: 109-142.
Johnston, A.I. (2008),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80-200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xiv.
Lynch, D. (2009), "Chinese thinking on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alism as the Ti, rationalism as the Yong?", The China Quarterly 197(-1): 87-107.
Chan, G., Lee, P.K. and Chan, L.-H. (2012), China Engages Global Governance: A New World Order in the Making? London: Routledge.
Yuzawa, T. (2012),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in, M. Beeson and R. Stubb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Asian Reg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338-349.
Jones, D.M. and Smith, M.L.R. (2007), "Making process, not progress: ASEAN and the evolving East Asian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2(1): 148-184.
Barta, P. and Tejada, C. (2012), "Sea dispute upends Asian summit",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15.
oDKVYGtB4e4XA3Zzhi/9Kw==Beeson, M. (2003), "Sovereignty under siege: globalisation and the state in Southeast Asia", Third World Quarterly 24(2): 357-374.
Storey, I. (2012), "Asean Is a house divided",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4.
Terada, T. (2012), "ASEAN Plus Three: Becoming more like a normal regionalism?", in, M. Beeson and R. Stubb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Asian Reg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 364-375.
Beeson, M. (2006), "American hegemony and regionalism: The rise of East Asia and the end of the Asia-Pacific", Geopolitics 11(4): 541-560.
Emmers, R. and Ravenhill, J. (2011), "The Asian and global financial crises: consequences for East Asian regionalism", Contemporary Politics 17(2): 133-149.
Pascha, W. (2007), "The role of regional financial arrangements and monetary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and Europe in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e Pacific Review 20(3): 423 - 446.
Terada, T. (2012), "ASEAN Plus Three: Becoming more like a normal regionalism?", in M. Beeson and R. Stubb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Asian Reg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 364-75.
Pinker, S. (2012),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 New York: Viking; Weissman, M. (2012), The East Asian Peace: Conflict Prevention and Informal Peace Building, Basingstoke: Palgrave; Tertrais, B. (2012), "The Demise of Ares : The End of war as we know it?", Washington Post 35(3): 7-22.
Hille, K. (2013), "Return of warlike rhetoric from China",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22.
Bureau of Resources and Energy Economics (2012), Resources, Energy and Tourism China Review, Canberra: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Edwards, N. (2011), "Foreign Ownership of Australian Mining Profits Canberra", Briefing Paper Prepared for the Australian Greens.
Colebatch, T. (2012), "Mining states bake while the rest shiver", The Age, February 22.
Capling, A. (2004), All the Way with the USA: Australia, the US and Free Trade, Sydney: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Press.
Dorling, P. (2011), "Labor's secret curb on China", The Age, March 3.
Uren, D. (2012), The Kingdom and the Quarry: China, Australia, Fear and Greed, Collingwood: Black Inc..
Vasek, L. (2012), "We'll become part of Asia if denied more GST funding, WA premier Colin Barnett says", The Australian, May 20.
Wen, P. (2012), "Cold War warning as China hits out at defence co-operation with US ", The Age, May 15.
例如:Wang Yong, "The Politics of the TPP Are Plain:Target China", Global Asia,Vol.8, No.1, 2013:54-56;李向陽,“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中國崛起過程中的重大挑戰”,《國際經濟評論》,2012年第2期,第17~27頁。
Bhagwati, J.N. (2012), "America's threat to trans-Pacific trade", East Asia Forum, January 10.
中日關系的惡化反映了經濟相互依賴的有限性。盡管存在遠近距離和沉沒成本因素,許多日本公司仍在考慮在印度而非中國投資——這一轉變具有潛在的地緣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雙重意義。參見Crabtree, J. (2013), "India benefits from Japan Inc shift", Financial Times, April 3.
許多中國分析家擔心,美國政府正在利用“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來遏制中國的影響。參見Kenneth Lieberthal and Wang Jisi, "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 the 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 at Brookings Institution, March 30, 2012, see http://www.brookings.edu/~/media/Files/rc/papers/2012/0330_china_lieberthal/0330_china_lieberthal.pdf. 但也有分析家認為,由于經濟衰退,美國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政策必定失敗。參見龐中英,“TPP就是一出空城計”,《環球時報》,2011年11月19日。
Wolf, M. (2012) , "Era of a diminished superpower", Financial Times, May 15.
強權政治的邏輯越來越具有影響力,在美國大學接受教育的現實主義學者如閻學通相信:傳統大國美國與新興大國中國之間的交鋒是不可避免的。參見閻學通:《中國國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Mearsheimer, J.J. (2001),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Friedberg, A.L. (2011),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New York: W.W. Norton; 王緝思:“美國霸權與中國崛起”,《外交評論》,2005年第5期,第13~16頁;陳健:“中美關系發展的思考”,《世界經濟與政治》,2012年第6期,第152~155頁。
White, H. (2010), "Power shift: Australia's future betwee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Quarterly Essay, 391.
責 編∕鄭韶武
Can the "Concert of Asia" Mechanism Balance World Powers' Strategic Demands?
—Australia, China and the US in an era of interdependence
Mark Beeson Wang Yong
Abstract: Sino-American bilateral relationship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 the world. No region will be more affected by this process than the Asia-Pacific, and no state will be more conscious of the threats and opportunities this transformation brings in its wake than Australia. Australia is the quintessential Asia-Pacific power, the principal driver of foreign policy has been a congenital anxiety about its perceived strategic vulnerability. Historically, Australian policymakers have experienced a good deal of ambivalence and cognitive dissonance when it comes to relations with "Asia". In reality, Australia's long-running, unequivocal, unquestioning sup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arguably done neither country much good. Despite providing a plausible response to what seems like an inescapabl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 and ultimately, perhaps, in the 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ower, White's idea of a Concert of Asia cannot get much traction in Australia, how much more unlikely is it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China for that matter?
Keywords: the Sino-Australian relationship, the Sino-American relationship, Asia-Pacific Community, Concert of As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