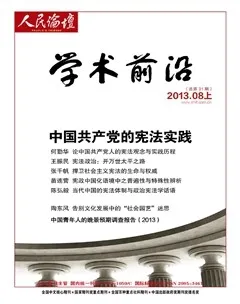當代中國的憲法體制與政治憲法學話語
摘要 中國的政治憲法學是新興的理論現象,盡管它受到西方理論的影響,但也有其特殊的背景。當代中國的政治憲法學話語值得研究,它提出一種與居于主流地位的規范憲法學不同的思路,它的思考進路有利于透視中國憲法體制轉型的真實狀況及其面對的困境。在當代中國政治憲法學的理論脈絡中,高全喜教授是一位重要的學術人物。本文介紹了高全喜的政治憲法學的核心概念和主要內容,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反思與評估。
關鍵詞 憲法 政治憲法學 轉型 革命 立憲
【作者簡介】
陳弘毅,香港大學法學院教授,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研究方向:憲法學、比較法學、法哲學、政治哲學。
主要著作:《法理學的世界》、《西方文明中的法治和人權》、 《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法治探索》、《法治、啟蒙與現代法的精神》、《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制軌跡》等。
在當代西方世界的自由主義憲法思想語境下,學者們在區別政治憲政主義(political constitutionalism)與法律憲政主義(legal constitutionalism)或司法憲政主義(judicial constitutionalism)的不同時,一個顯著區分就是前者將其思考重點放在憲法和其相關的政治體制所依存的政治基礎及其實施的條件上,而后者則關注憲法在司法層次上的解釋和適用,尤為關注法院對政府和立法機關的行為的合憲性的司法審查(違憲審查),以及憲法所規定的基本權利的解釋和實施。從比較憲法學的角度看,目前中國有關政治憲法學的討論是值得關注的,盡管這方面的討論的興起還僅僅是最近幾年的事。和西方政治憲政主義一樣,中國政治憲法學的特征也可從與司法憲政主義或規范憲法學的比較中呈現出來。但與西方有所不同的是,西方政治憲政主義學者的分析框架建立在西方式民主的政治體制之上,他們的研究主要是考慮在此基礎上,如何發展或進一步強化其原有的民主憲政制度,例如民主政治、民主選舉、議會運作、權力的制約和平衡、政治問責性、公眾審議和協商等;而當代中國政治憲法學討論的時代背景,則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政治體制、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社會結構的急劇改變或社會轉型以至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在這個語境下,對中國政治憲法學的研究,將有助于我們理解正處于現代化進程的一個十字路口的當代中國所面臨的困境。
本文將通過介紹和評論中國政治憲法學的主要倡議者高全喜教授的學術思想,來探討當代中國的政治憲法學。本文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將介紹高全喜教授在政治憲法學研究方面的主要學術觀點;在第二部分,筆者將就高全喜教授的有關學術觀點進行討論和評估。
高全喜的政治憲法學
高全喜教授主要研究西方和中國哲學,尤以對現代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為長。近年來,他開拓了政治憲法學這個研究領域,成為當代中國政治憲法學研究的主要倡導者。本部分嘗試對高氏的政治憲法學思想作一全景式描述,并且介紹其主要內容。
高全喜在其著作中表示,當代中國關于政治憲法學的討論起源自北大法學院陳端洪教授在2008年發表的一篇題為“論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法與高級法”①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陳表示他不同意那些主張“憲法的司法化”的學者的觀點,后者認為中國法院應該在憲法解釋方面扮演積極的角色,并且發展以憲法權利保護為中心的憲法學。與此相反,陳認為中國“在原則問題、價值問題、政治問題、意識形態問題上應走有中國特色的政治憲政主義道路”,雖然陳也支持“訓練司法的專業能力”和“發展日常的具體的法治”②。
陳端洪關于政治憲政主義的觀點反映在他對“制憲權”(constituent power)和“立憲時刻”(constitutional moment)的強調。他對“資本主義憲法”和“社會主義憲法”作出了區分。就中國人民共和國憲法來說,陳強調在立憲時刻行使制憲權的“主體”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在具體分析中國憲法的文本時,陳特別重視序言部分,他提煉出了中國憲法的五個“根本法”,并且依據其重要性排列了先后順序:(1)“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2)社會主義;(3)民主集中制;(4)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5)基本權利和人權保障。
高全喜意識到了陳端洪的文章在憲法學研究方面的重要性, 即首次在中國提出政治憲政主義和司法憲政主義的區分。高表示他贊賞陳的問題意識和方法論,但是在諸多具體觀點和研究路徑上,他與陳存在分歧③。尤其是,高批評陳傾向認同 “一切存在的就是合理、正當的”④,因而忽略了正當性和規范性的問題⑤。高把陳視為當代中國政治憲法學研究的左派:“我們兩人分別代表著政治憲法學的‘左’和‘右’,我們之間的差別,從某種意義上遠遠大于我們與規范憲法學及憲法解釋學之間的差別”⑥。
那么,高氏是如何理解政治憲法學的呢?他認為政治憲法學研究的主要是建國、制憲、立憲時刻、憲法的政治基礎、憲法變遷、“憲法精神以及內在的動力機制”⑦等課題。在借鑒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和布魯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的憲法學思想的基礎上⑧,高強調研究“立憲時刻”(即建國和制憲的時期)的重要性,并且對憲法制定的“非常政治時期”⑨(立憲時刻)和“日常政治”(即憲法運作的“日常狀態”或“日常的法治時期”⑩,包括其司法解釋)作出了區分。對于高而言,憲政的關鍵在于從“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的過渡、亦即從革命到憲政的過渡。
高氏關于政治憲法學的論述中,最為重要的觀點之一就是,伴隨革命所建立起來的憲政應被理解為一種“革命的反革命”,它的性質是在鞏固革命成果的同時建立起一個穩定的政治秩序,并以憲法規定的原則、制度和程序來約束和馴服那個由革命所產生的“利維坦”的政治權力。因此,高認為,雖然政治憲政主義的目的在于建立有限政府,但不要靜態地把政治憲政主義等同于有限政府。他指出,憲政必須在革命以至通常伴隨著革命的戰爭的語境中予以理解,在這種情況下,新的民族國家(即上述的“利維坦”)誕生,其人民取得新的公民身份,作為主權者行使其制憲權,從而創造一個新的政府架構。對于高氏而言,憲政的秘密在于“利維坦時刻”(即民族國家的建立)和“洛克時刻”(即用以規范和馴服這個“利維坦”和它的政治權力的憲政秩序的建立)之間的關系,這便是政治憲法學所最關注的課題,而司法憲政主義則忽略此課題。高氏認為,當政治憲政主義完成其任務,國家從“非常政治”過渡至“日常政治”后,司法憲政主義才有其用武之地。
高氏比較了英國和法國在政治憲政主義方面的實踐經驗。在高看來,法國大革命是人民行使其制憲權建立現代國家的典型,但是,法國大革命所釋放出來的能量是政治激進主義的而非憲政主義的。根據高的分析,唯有那種能夠限制伴隨革命而來的絕對制憲權的保守主義,才能帶來真正的憲政。而法國的情況正是缺乏這種保守主義的力量,而導致不斷地革命、流血,以及持續的“利維坦時刻”,遲遲未能建立一個穩定的政治秩序。因此,法國大革命雖然產生了現代民族國家,但沒有成功建立憲政。
在高氏看來,正是17世紀的英國,尤其是1688年的“光榮革命”,才為西方的政治憲政主義提供了成功的范式。根據他的分析,光榮革命是一場融匯了保守主義、傳統主義以及漸進改良主義等元素的革命,因而造就了憲政。高寫道:“我們理解政治憲政主義必須回到英國,回到英國的光榮革命。在英國光榮革命那里,才有一種激進主義的現代革命政治與憲政主義的保守主義的結合。我認為,政治憲政主義最經典的文本是英國的光榮革命。光榮革命既不是霍布斯的政治,也不是普通法的憲政,而是一種新形態——真正的政治憲政主義。”
高氏認為,光榮革命是體現“非常政治”的立憲時刻,一個現代國家由此誕生。但是,傳統勢力在其中也起到了限制專制王權的作用。保皇黨、輝格黨(Whigs)以及激進的共和主義者之間的斗爭最終導致了一個政治妥協。“利維坦時刻”得到了《權利法案》、《王位繼承法》和《寬容法》所代表的憲政措施的妥善安置。根據高的分析,這些憲法性文件“都具有這種政治憲政主義或保守主義的核心價值,它們有效地達成了利維坦時刻的憲政之反動,達成了革命與反革命(anti-revolution)的結合,實現了一種政治憲政主義的正義”。“這種正義瓦解或消除了施米特所說的敵友政治,制止了決斷時刻的重復循環,塑造了一個‘不分敵友’的公民政治統一體”。
在高氏看來,洛克的學說便是政治憲政主義和光榮革命的最佳理論表述。高強調,洛克的《政府論》不應視為僅關于常態政治的理論,而應該置于那個建立新的主權國家的“利維坦時刻”的政治背景中去理解。高認為,洛克所倡導的法治政府、有限政府、分權架構以及自然權利,其目的都是為了“安頓和守護”這個新生現代國家。根據高氏的分析,洛克的理論充當了從“非常政治”向“日常政治”轉化的理論“中介”。因此,高強調,雖然洛克的理論看來好像只是關于“日常政治”的基本原則,但只有置于“非常政治”和國家建立的“利維坦時刻”的背景中才能充分得到理解。這套理論可以作為中介,對從非常政治走向常態政治的過渡起到關鍵性的作用。
現在讓我們考察高氏如何把他的政治憲法學應用于中國的情況。首先應當指出的是,高強調歷史意識在中國政治憲法學研究中的重要性。他認為,我們必須采用一個至少包涵一個世紀的中國現代憲政史的寬廣視角,然后對這段歷史中的不同時期作出劃分,同情地理解不同的歷史時期的情況,以及從政治憲法學的角度,對每一時期予以分析和評價。
高氏以“時代精神憲法化”為基準,把中國的現代憲政史劃分為“三個時間層次”:(1)建立于1912年的中華民國及其憲政傳統(高稱之為“第一個現代中國”);(2)由中國國民黨在1928年建立的“黨制國家傳統”以及1949年由中國共產黨建立的“黨制國家傳統”(“第二個現代中國”);以及(3)從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包括1982年憲法的制定及其隨后的修改(“第三個現代中國”)。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現代中國的立憲史,高指出“至少從‘中華民國’開始,憲法意義上的中國大致出現了三個半,或者說,我們的現代歷史中大致有三個半的現代中國以及‘憲法中國’”:(1)建立于1912年的中華民國;(2)國民黨及其“黨國體制”領導下的中華民國;(3)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 )至今還未統一的中國,但是這個中國有希望有一天“凝聚為一個自由、憲政、民主的新中國”。
高氏認為,中國政治憲法學的研究應該同時兼顧描述性和規范性的研究;它應該揭示出中國的憲政或政治體制的真實情況,也要面對正當性、合憲性和正義等課題。高尤其著意于對隱藏于現代中國憲政史上那些事實、事件及文獻背后的憲政思考和政治形態的發現與挖掘。在《立憲時刻:論〈清帝遜位詔書〉》這部專著中,高示范了如何運用政治憲法學方法來研究問題。書中的研究對象是1912年的清帝遜位。
對1911年辛亥革命以及現代中國第一個共和國的誕生的憲法學研究,一般集中在1912 年3月在南京通過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憲法學者很少關注當時的清帝遜位事件以及由皇太后代表清朝幼帝于1912年2月頒布的遜位詔書上。高指出,從政治憲法學的角度來看,這一詔書是十分重要的,它在建構中華民國的憲法基礎及其正當性方面,具有相當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1912年初,辛亥革命的成功仍沒有得到保證。雖然很多省份都宣布脫離清帝的管轄,革命黨也在南京建立了共和國政府,但是清政府依然控制著北京和不少疆域,袁世凱依然掌握著能夠對革命黨發動內戰的強大軍事力量。正是在這種情況之下,清廷被迫宣布退位并把權力移交給袁。革命黨和袁達成交易,讓袁取代孫中山成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清帝遜位詔書》不僅宣布了清帝的退位,而且授權袁世凱與在南京的革命黨就建立共和政府和召開國會等事宜進行談判,以“構建‘共和立憲國體’”。同時,《詔書》的作用還包括把清帝國治下的多民族的臣民原來對清廷的效忠以及整個清帝國領土,都移轉給新的共和國,使“五族共和”成為可能,并確立了中華民國的領土疆域——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辛亥革命是由漢族領導并由反滿情緒所推動的。因此,高氏指出,新的共和國不僅僅是革命的產物,而且一定程度上是產生于權力從清廷向共和政府的自覺及和平的轉移。所以高論證說,舊政權的《清帝遜位詔書》和新共和國制定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一起構成了共和國的憲法基礎;這兩份憲法性文本共同構建了新的共和國。《清帝遜位詔書》所體現出的和平演變的精神對于革命的暴力和激進主義有遏制或平衡的作用:“這個和平方式的革命建國……彌補了辛亥革命建國的激進性和片面性”。因此,《清帝遜位詔書》代表了“真正的保守主義的憲法精神”,它成全了“中國版的光榮革命”。
雖然在1912年這個“相對來說比較好的政治時期或者立憲時刻”,革命的激進主義與和平的政權轉移得以成功地結合,但憲政卻始終未能在中國實現。對高氏來說,現代中國政治史上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從“革命”過渡到憲政民主的“日常政治”:“革命成功之后的常態化回歸……成為中國憲政的‘死結’”。在高看來,在現代中國史里,革命激進主義有余,“保守改良主義”或“革命的反革命”則不足,而“革命的反革命”卻是憲政的建立所十分需要的。比如,正如高氏指出的,雖然1949年的《共同綱領》(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臨時憲法)以及1954年頒布的第一部憲法初看起來是意味著從“非常政治”向“日常政治”的過渡,但是它們最終還是要讓路給“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激進主義。
高氏認為,即便是今日的中國,也未曾完成從“非常政治”向“日常政治”的轉化。他指出,今日中國的情況既非“非常政治”,亦非“日常政治”或“正常的憲政法治狀況”;它還處于自上個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改革開放”以來的一個過渡時期。高指出,在憲法的層面上,這個過渡反映于1982年制定的憲法以及其后的修正案。由于這個過渡還在進行中并且尚未完成,所以可以說中國的立憲時刻尚未完結。高認為,在這個過渡未完成之前,在中國實施司法憲政主義的條件并不存在,所以相對于研究司法憲政主義來說,對政治憲法學的研究更為迫切。高又指出,對于當今中國來說,西方在近代早期(也就是西方現代國家建立時期、從“非常政治”向“日常政治”過渡的時期)的憲政經驗更有參考價值,而不是西方今天所實行的司法憲政主義。
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政發展而言,高氏提出以下的三階段論:(1)起初是“革命憲法”(例如作為“文化大革命”時代的產物的1975年憲法),然后是(2)“改革憲法”(由1982年憲法及其修正案所代表),最終是(3)“憲政憲法”。這令我們想起孫中山先生關于革命建國的“三序方略”,也就是(1)“軍政”,接下來是(2)“訓政”,最后是(3)“憲政”。高指出,在他區分的三個階段的最后階段,便是“憲政國家”的形成,即完成邁向“民主憲政體制的轉型”。這也將標志著中國立憲時刻的完成。
在高氏近期的研究中,他討論到1982年憲法及其四個修正案,并從中國憲法長遠發展的角度去思考其意義。他認為1982年憲法是一部“改革憲法”(有別于先前的“革命憲法”),整體而言,這部憲法以及其修正案反映出一種“新的憲法精神或憲法設計”。基于1982年憲法及其四個修正案,他對中國終將演化到“憲政憲法”的階段持謹慎樂觀的態度。
高氏運用政治憲法學的方法研究了1982年憲法及其修正案。他指出,1982年憲法的主要目標或隱含于其中的主調,便是結束“文化大革命”時代的激進的意識形態和實踐——包括階級斗爭和“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論。在肯定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歷史邏輯及其成就的同時,1982年憲法把“革命”終結:它追求建立一個穩定的社會和政治秩序及有效的法制,并且恢復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一度停止運作的國家機構(如人大),又重新肯定憲法的最高權威。因此,高氏在這部憲法(及隨后的修正案)里發現了“革命與去革命化的雙重內涵”。他認為這部憲法標志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從“非常政治”向“日常政治”過渡的開端;它代表了“憲法出場,革命退場”的邏輯——高認為這一邏輯對于所有由革命誕生的現代國家是普遍適用的:亦即是說,以憲法作為根本法去限制和終結革命。高認為,在后革命時代的這個過渡過程中,憲法的政治性(如施米特所強調的)應該逐漸讓位于憲法的規范性和法律性。
高氏同時也分析了1982年憲法所體現出來的政治結構或“政治憲法”,在這方面,他主要援引了田飛龍博士——一位年輕的政治憲法學學者——的概念框架。根據田氏的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憲法結構”中最根本的原則或憲法之“道”就是人民主權,它在1982年的憲法中具體體現為三個“肉身”:(1)基于真理的共產黨的領導代表制,(2)基于程序的人民代表大會制,以及(3)“非代表制的參與民主制”。高氏分析了這三個體系以及它們各自的問題。
第一,關于黨的領導代表制,高認為0Yi2+7A7WRhEMmc0rypkEESUIR74VPajJvIrFMFJEPU=,中國最為重要的憲法問題就是“如何處理黨與國家的關系”,也就是共產黨的領導、憲法的至上性和人民主權之間的關系問題。他指出,1982年憲法已經顯示出政治體制從黨的領袖的個人統治向更為民主的黨的領導的過渡,并要求黨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也就是在中國的政治憲法中引進一個重要的規范性元素。高又認為,“三個代表”思想是關于共產黨領導和代表性的理論的重大發展。但是,最終的問題仍待解決,就是“黨的領導原則最終要規范于憲法的人民主權原則、人民民主原則和憲法法治原則”。
第二,關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高氏指出這一制度的確是人民主權的最直接的體現。但是,他認為,除非共產黨的領導真正地(而非只是象征性地)被置于憲法的制約之下,否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功能以及司法獨立的原則是難以完全實現的。
第三,關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以外的民主參與制度,高強調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重要性,他指出這個制度可追溯到國民黨執政時期,并在共產黨執政下有了新的發展。高認為這個制度未來將如何演變,以及它與人民代表大會和國家主權的關系如何,對于中國的政治憲法學研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對于1982年憲法的四個修正案,高氏作出了高度的評價,認為它們“蘊含……重大的憲法性意義”,“形成了一種不同于五四憲法乃至最初的八二憲法的新的憲法精神或憲法設計”。高氏指出,總體來說,這些修正案有三個主要特征。首先,它們“對‘人民共和國’……重新理解和定位”;第二,它們“將社會從國家中釋放出來,實現國家與社會的初步分離”;第三“是依法治國、私產保護和人權條款入憲,確立了新憲政設計的指導原則和精神基礎”。高氏指出,1982年憲法在經過四次修訂后,“形成了多元復合的憲法體系”,“構成了一部新的憲政設計。這個新的憲政設計寄生在舊的憲政結構中,在受到舊的憲政秩序擠壓的同時,又從中汲取生命的動力”。雖然“新的憲政設計今天仍是一種寄生性的存在,但悖論的是,這反而是其生命力之所在。……唯有寄生,才能存活并成長”。這便是“漸進式改革”的邏輯,也就是介乎“非常政治與日常政治之間”的“轉型憲政”。
最后,高氏指出,1982年憲法制定以來的修憲活動,反映出這樣的一個趨勢,就是“現代憲政的基本價值”和原則已經逐漸被納入中國憲法。從這個角度看,1982年憲法(及其修正案)不僅僅是對“文化大革命”的極左思想的摒棄和對原有的1954年的社會主義憲法的“簡單回歸”,它已經“超脫了單純的社會主義憲法的教義性設定,而有著回歸百年中國共和憲政主脈的強烈價值指向與制度協同”。高氏所說的百年中國憲政傳統,就是開端于1911年辛亥革命、清帝遜位和1912年中華民國的建立這段歷史的憲政傳統。高氏的“大回歸論”的理論視野還涵蓋“一國兩制”在港澳的實踐和“海峽兩岸的最終和平統一”;有了這個視野,“以大陸中國為主體的現代中國的憲政轉型才能夠具有真正明確的價值基礎和制度取向”。
反思和評論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實行社會主義政治體制。從比較憲法學的角度看,現代中國所走過的憲政道路以及其未來的發展路向,是一個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十分重要的課題。在這方面,高全喜的政治憲法學為我們對現代中國的憲政實踐和其未來發展的可能性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十分有用的概念框架。
在當代西方國家,由于法院已經在涉及憲法性權利和其他憲法解釋及適用的問題的案件中建立了大量重要判例和憲法學原則,所以憲法學學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律憲政主義和司法憲政主義而非政治憲政主義,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正如上文指出,中國的情況與西方不同,在中國大陸,法院無權對憲法作出解釋或在案件的訴訟中對人大制定的法律和政府的行為進行違憲審查。雖然如此,但在西方學術思潮影響之下,近年來,在中國憲法學領域,對憲法條文的解釋和對憲法性權利的內容的規范性研究逐漸興起并成為學術主流,這便是高全喜所謂的規范憲法學和憲法解釋學。高氏的政治憲法學研究的主要學術貢獻之一,便是提醒我們,規范憲法學和憲法解釋學的研究并沒有處理當今中國的憲法、政治和法律體系所面臨的最核心、最關鍵的問題。相對于規范憲法學和憲法解釋學,政治憲法學似乎更有能力去揭示和理解這些問題,并為其解決提供有力的學術資源。高氏正確地指出,當今中國憲法的最根本問題是政治憲政主義或政治憲法學的問題,除非和直至這些問題得以解決,否則司法憲政主義或法律憲政主義(及以它們為基礎的規范憲法學和憲法解釋學)只能流于學術空談,并無現實意義。 因此,高氏批評那些專注于規范憲法學和憲法解釋學的學者,認為他們忽視了中國憲法體制的真實狀況和具體問題。筆者認為,高氏在政治憲法學上的學術工作,主要是在理論、哲學和宏觀歷史的這些層次。在本文這個結論部分,讓我們回顧他在這些領域的學術貢獻。
可能是由于在20世紀,革命對于中國人來說是最深刻的經驗,革命塑造了中國的現代史,所以高全喜的政治憲法學強調的是“革命”和“憲政化”兩者之間的關系、張力和互動。這里說的“憲政化”,是指一個現代憲政國家的建立,即國家權力受到憲法的有效規范和約束。很多現代國家——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內——誕生于革命之中,但是,革命并不必然導致憲政化,中國的個案便是一個例證。高全喜的洞見之一,便是指出了“革命”和“憲政化”兩者之間確實存在著張力和矛盾。革命通常是以激進的方式去打破一個現存的政治和社會秩序,很多時候是通過暴力的、流血的行動。而憲政化或憲政的制度化,則要求建立一個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秩序,并對革命力量作出限制和規范。革命涉及的是敵我的區分,憲政化則意味著這種區分的取消。
由于革命和憲政化之間存在著矛盾,所以高全喜提出一個有創意的理論觀點,就是需要某種“革命的反革命”,才能成就憲政化。“革命的反革命”是一種具有保守主義色彩的力量,它的取向是和平的、改革的,而非暴力的或革命的。在一場革命期間或者在革命之后,這樣的保守力量是否存在以及是否起作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憲政化能否實現。因此,高氏把十七世紀英國的“光榮革命”視為憲政化的典型,并把洛克的政治哲學視為憲政化的經典文本。在現代中國,憲政化之所以未能成功,似乎主要是由于激進的革命力量過于強大,以及支持憲政化的保守力量的虛弱。所以高氏回到中國的現代憲政史中,去尋找一種傾向于和平改革的保守主義力量,并終于在1912年的《清帝遜位詔書》里找到它的典范和體現。此外,他又從1982年的憲法及其修正案中,找到漸進改革力量的作用。
至于當前中國憲政的狀況,高全喜的“診斷”結果是,今日中國既非處于正在建立新憲的“非常政治”狀態,亦非到了司法憲政主義可以或者應該取代政治憲政主義的“日常政治”狀態,而是處于一個過渡階段。這個過渡時期的挑戰包括若干政治憲政主義的根本問題的解決,比如黨與國家(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關系問題,以及人民主權、憲法至上與共產黨的領導的關系問題。就中國未來的憲政發展來說,雖然高氏未曾提出具體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但筆者認為,他提出的關于憲法發展的“三段論”和“大回歸論”對我們有很大的啟發,是他的政治憲法學最重要的貢獻。“三段論”區分了 “革命憲法”、“改革憲法”和“憲政憲法”,并指出“憲政憲法”便是當代中國憲法體制向前邁進的目標和理想。“大回歸論”則提醒我們,歷經四次修訂的1982年憲法,已經不能純粹被理解為對1954年的社會主義憲法的回歸,它已經有所超越,甚至可理解為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憲政主義大傳統的“共和憲政主脈”的回歸。高氏未有細述這個“共和憲政主脈”的具體內容,他把豐富的想象空間留給了我們——我們可以重新審視百年中國的憲法史和政治史,從而發掘可用于促進未來中國憲法發展的資源。
注釋
陳端洪:“論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法與高級法”,《中外法學》,2008年第4期,第485、486頁。
高全喜:“政治憲法學的興起與嬗變”,《交大法學》,2012年第1期(創刊號),第22、32、25、24、26、27~28、29、38、40、41頁。
高全喜:《從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9年,第50頁。
高全喜:《立憲時刻:論〈清帝遜位詔書〉》,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6~7頁;高全喜:《從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9年,第25頁。
高全喜:“政治憲法學的興起與嬗變”,《交大法學》,2012年第1期(創刊號),第31頁。
高全喜:“政治憲法學的興起與嬗變”,《交大法學》,2012年第1期(創刊號),第24~25頁;高全喜:《從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9年,第50頁。
高全喜:“政治憲法學的興起與嬗變”,《交大法學》,2012年第1期(創刊號),第27頁;高全喜:《立憲時刻:論〈清帝遜位詔書 〉》,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1頁;高全喜:《從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9年,第29頁。
高全喜:《從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9年,第18、18、30~37、22~39、27、24、27、28、28~29、29、26、32、34、34~35、36頁。
高全喜:“政治憲法學的興起與嬗變”,《交大法學》,2012年第1期(創刊號)第27~28、36~37頁。
高全喜:“政治憲法學的興起與嬗變”,《交大法學》,2012年第1期(創刊號),第27、42、42、32~36頁。
高全喜:《立憲時刻:論〈清帝遜位詔書 〉》,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6~7、106、134~139、97、111頁。
高全喜:《立憲時刻:論〈清帝遜位詔書 〉》,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0、111頁。
馬國川(訪談):《告別皇帝的中國:辛亥百年訪談錄》,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08頁(高全喜:“憲法出場,革命退場”)。
高全喜、田飛龍:“政治憲法學的問題、定位與方法”,《蘇州大學學報》,2011年第3期,第72、74頁。
高全喜:“政治憲法學的興起與嬗變”,《交大法學》,2012年第1期(創刊號),第25、36、36、42頁。
高全喜:“政治憲法學的興起與嬗變”,《交大法學》,2012年第1期(創刊號),第36~37、42頁。
高全喜:“政治憲法學的興起與嬗變”,《交大法學》,2012年第1期(創刊號),第3頁;高全喜:《立憲時刻:論〈清帝遜位詔書 〉》,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4頁;高全喜:《從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9年,第40、42頁。
高全喜:《從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9年,第43~46頁。
高全喜:“政治憲法學的興起與嬗變”,《交大法學》,2012年第1期(創刊號),第3頁;高全喜:《從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9年,第9、16、40頁。
高全喜:“政治憲法學的興起與嬗變”,《交大法學》,2012年第1期(創刊號),第40頁;王人博等:《中國近代憲政史上的關鍵詞》,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164~213頁;郭寶平、朱國斌:《探尋憲政之路——從現代化的視角檢討中國20世紀上半葉的憲政試驗》,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
高全喜:“政治憲法學的興起與嬗變”,《交大法學》,2012年第1期(創刊號),第28頁;高全喜:“革命、改革與憲制:‘八二憲法’及其演進邏輯”,《中外法學》,2012年第5期,第907頁。
高全喜:“革命、改革與憲制:‘八二憲法’及其演進邏輯”,《中外法學》,2012年第5期,第923、926、911、909、912、913、916頁。
高全喜:“政治憲法學的興起與嬗變”,《交大法學》,2012年第1期(創刊號),第39頁;高全喜:“革命、改革與憲制:‘八二憲法’及其演進邏輯”,《中外法學》,2012年第5期,第916頁。
田飛龍:《政治憲政主義——中國憲政轉型的另一種進路》,北京大學法學院2012屆博士學位論文。
高全喜:“革命、改革與憲制:‘八二憲法’及其演進邏輯”,《中外法學》,2012年第5期,第917、917~918、918、920、921~922、923、924、924、925、925、925~926、925、925~926、925。
參見高全喜對施米特關于“政治是區分敵友”的思想的討論和批評:高全喜、田飛龍:“政治憲法學的問題、定位與方法”,《蘇州大學學報》,2011年第3期,第25~26頁。
高全喜:“革命、改革與憲制:‘八二憲法’及其演進邏輯”,《中外法學》,2012年第5期,第925頁。
責 編∕鄭韶武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and the Discourse of Political Constitu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Following the Century-long Conventions of Constitution in Gao Quanxi's Academic Thoughts
Albert Chen Hung-yee
Abstract: Political constitutionalism is a new school of thought in China. Despite being influenced by its Western counterpart, Chinese political constitutionalism has its unique roots. The current Chinese discourse of political constitutionalism is worth researching because it provides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dominant normative constitutional studies and has a strong analytical power in elucidating the dilemmas and challenges facing China's co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Professor Gao Quanxi is a leading scholar of political constitu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key concepts and main content of his thoughts about political constitutionalism, and reflects on and assesses their significance.
Keywords: constitution, political constitutionalism, transformation, revolution, constitution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