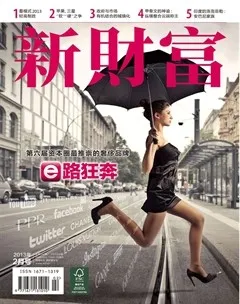數字化的博柏利格紋







通過定位于更年輕的消費群體、鎖定核心市場,并大規模使用包括社交媒體在內的數字化營銷模式,當年已近“遲暮”的英國服裝制造商,又重新回到了炙手可熱的國際時尚品牌之列,而其標志性的格紋也越來越清晰地打上了數字化的標簽。
當現任CEO安吉拉·阿倫德茨(Angela Ahrendts)于2006年走馬上任之時,由于無序的產品線擴張,博柏利似已邁入“遲暮之年”,零售和批發業務的同比增長僅為2.2%,遠低于約13%的行業平均水平。
然而, 6年之后的今天,通過定位于更加年輕的消費群體,鎖定核心市場,并大規模使用包括社交媒體在內的數字化營銷手段,這家當年埋在一堆故土中的傳統英國服裝制造商又重新回到了炙手可熱的國際時尚品牌之列。伴隨品牌影響力的提升以及銷售規模的不斷擴大,博柏利的品牌價值日益增值,是為數不多連續四年登上Interbrand品牌價值百強榜的奢侈品牌(圖1)。
歷史悠久的“年輕”品牌
在博柏利位于倫敦威斯敏斯特5萬平方米的總部里,1200名衣著光鮮的員工穿梭其中,他們中70%的年紀都在30歲以下。同樣年輕的還有博柏利的目標客戶群。
為了讓這個誕生于1856年的老品牌重新煥發新的活力,阿倫德茨在上任之初便為博柏利重新定位。首先進入她視線的,是當時被多數奢侈品牌所忽略的年輕一代,而剛剛開始啟動的新興市場同樣引起了她的興趣—這一市場的奢侈品消費主力要比歐美市場的消費者年輕15歲左右。于是,在著手收縮授權業務、拓展直營店之余,博柏利調整產品線和設計,以期能夠吸引新的目標客戶群的目光。
在此定位之下,日益多樣化的互聯網應用,成了博柏利與年輕客戶群有效對話的重要途徑,而在當時,多數奢侈品牌仍對與互聯網的進一步結合持觀望態度。
2009年,博柏利正式組建數字化專業營銷團隊,很快它便成為了奢侈品牌中數字化轉型的先行者—第一個通過網絡直播時裝秀,第一個運用3D技術舉辦時裝秀等。不久的將來,它還將成為第一個使用Square移動支付技術的奢侈品牌,屆時顧客可以在手機或平板電腦上完成刷卡付款。
同樣擔當著加強與年輕消費者之間互動作用的,還有日益風行的社交網絡。在Facebook、Twitter和Google+三大社交網絡上,博柏利都是擁有最多粉絲的奢侈品牌,甚至連綜合排名都擠進了前30。相對新興的Pinterst和Instagam,博柏利同樣是最早的一批注冊用戶之一,并且粉絲數量增長迅猛。在中國,新浪微博、優酷、開心和豆瓣上也均能覓得博柏利的身影,其在優酷上的視頻已經連載至275集,播放次數超過1100萬次(附表)。
和社交網絡上的粉絲同步上升的,還有博柏利的業務規模。過去6年,博柏利的銷售收入和經營利潤翻了一倍有余(圖2)。即便在2012年9月發布盈利預警后蒸發了10億英鎊的市值,其股價也比2006年時上升近200%,同期的表現雖略遜于愛馬仕,但與LVMH集團以及同屬“新奢侈主義”范疇的Coach和蒂芙尼(Tiffany)相比,優勢明顯(圖3)。
而最新的財報顯示,2013財年三季度(2012年10-12月)集團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長了7%至6.13億英鎊,其中貢獻了76%收入的零售業務攀升了11個百分點。最為關鍵的同店銷售也實現了6%的增長。
玩轉“社交”
盡管難以單獨衡量數字化轉型的投資回報,但博柏利近幾年出色的業績表現,斷然少不了它的一份功勞。在創意總監克里斯托弗·貝利(Christopher Bailey)眼中,博柏利已經不僅僅是一家時裝設計公司,同時還是媒體內容的生產者。如今,博柏利每年的推廣成本中有50%都投向了數字化媒體,這個曾經以格紋、風衣和英倫氣息為代名詞的百年品牌,早已在多年的歷練中成長為一個“社交”高手。
博柏利最早的嘗試,圍繞其經典產品風衣而展開。在由其推出的照片分享網站“風衣藝術(Art of the Trench)”上,布滿了各式各樣身著博柏利風衣的人物照片,除了部分出自專業的攝影師外,它們中的絕大部分都來自于品牌的粉絲。在“用戶生產內容(UGC)”模式的基礎之上,前來上傳照片或是純粹欣賞的用戶不僅可以挑選出各自的最愛,還能通過Facebook或是Twitter轉載照片,并附上自己的點評。在風衣愛好者的力挺之下,上線半年時間有余,網站的流量就超過了700萬,迄今已經吸引了來自200多家國家的2100萬人次的瀏覽。
不僅如此,博柏利還把新產品的推廣也搬上了社交舞臺,借助社交網絡的力量, 制造話題,吸引潛在消費者。在新香氛Burberry Body上市前,博柏利一改在時尚雜志上大量投放廣告的傳統做法,而是選擇了在Facebook上建立單獨的品牌頁面,向每一位“like”它的用戶派發免費試用裝。待到產品正式發布時,Facebook的頁面又成為了一個在線銷售平臺,同時出售的還有其他相關產品,開辟了一條新的銷售渠道。
與類似的小規模作戰相比,博柏利最擅長的,還是整合多個平臺,將影響力最大化。2011年的秋冬時裝發布會,博柏利在Twitter上開辟了專門的“Tweetwalk”,在走秀開始前就開始貼出后臺的造型照片,關注度空前暴漲。此后,每到有發布會,通常都是Facebook、Twitter、YouTube、Instagram、Pinterest和Google+等社交網站多管齊下,最近新浪微博也得以加入其中。各種形式的圖文和視頻直播,把原本是品牌、媒體和買手間的圈內游戲,變成了一場所有人都能實時參與的盛宴。
為了保證各個平臺內容的“獨家”,各大社交網站還會各司其職。Facebook和Twitter主打走秀的模特造型照片,YouTube負責播出有關該季產品的介紹短片,而Instagram和Pinterest上發布的照片則會聘請專業人士操刀。如此排兵布陣,吸“睛”效果不言而喻。
在博柏利的示范下,近兩季,越來越多的奢侈品牌加入到了時裝發布會網絡直播的隊伍中。但博柏利還有高招,在觀看網絡直播的時裝秀時,即時進行預訂,通常6-8周后商品就會被送上門。通過這一系列的“組合拳”,博柏利強化了與消費者的互動,同時還從可能出現的仿品手中搶回了時間優勢。
虛擬“照進”現實
作為數字化戰略的核心組成部分,2010年年底,博柏利官方網站在全球45個國家全新上線,成為了其提升消費者網絡體驗的綜合平臺,品牌歷史、走秀視頻、電子商務外,旗艦店體驗都被納入其中,甚至連音樂都是由其網羅的音樂人獨家原創的。打開網站,一張2013年秋冬男裝秀的海報照即刻映入眼簾,“您可于時裝秀結束后限時購本季最新走秀款”一行字則被置于照片上最醒目的地方。
2012年秋,博柏利全球旗艦店在倫敦攝政街(Regent street)揭幕,網絡版的“博柏利世界(Burberry World )”完整落地。這家4000平方米的旗艦店面里共設有100塊屏幕和500個音箱,品牌全部13條產品線的各式商品,產品目錄與其官網上的分類如出一轍,甚至網站上獨樹一幟的風衣定制服務也被搬到了店鋪的二樓—顧客可以依據喜好選擇面料、配件、衣領式樣定制專屬于自己的風衣,甚至用自己的名字首字母組合出獨一無二的圖案—網絡上的自由選擇成為了專賣店里的一對一服務。此外,出售的商品還被事先裝上了RFID芯片,當顧客拿上其中一件走到特殊的鏡子前,鏡子就變成了屏幕,呈現服裝的T臺效果或是手袋的制作細節。
過去,讓網絡具備與現實相同的購物體驗是博柏利的愿景。如今,當越來越多的奢侈品牌加入到電子商務與社交網絡的行列時,博柏利又忙著把網絡體驗搬回現實。因為,越來越多的消費者在網絡上瀏覽商品的詳細資料,做足功課后到實體店來購買。
倫敦攝政街的旗艦店并不是博柏利將虛擬照進現實的第一次嘗試。2009年開始推出的“零售劇院”已經走入了87家店鋪(截至2012年3月),而2012年4月臺北101大廈的旗艦店開業時,“博柏利的世界”已經以3D版的形式在現實中上演。由此剪輯的視頻在Facebook上獲得了數十萬的點擊量,隨后又在門店播放;譬如,2012年11月底開張的芝加哥旗艦店。不僅如此,從“風衣藝術”網站上挑選出的芝加哥當地人身穿博柏利風衣的照片在店鋪中滾動播出,同時還出現在城市的廣告板上和各種社交網站上。線上和線下的交互運用,虛擬和現實的彼此融合,目的只有一個,吸引更多的消費者為品牌買單。
“數字”中的隱患
從2013年春天開始,在倫敦攝政街的旗艦店里,已經成為博柏利銷售助理標配的iPad將具備一項新的功能。據《經濟學人》報道,通過一個名為“360度顧客”的計劃,銷售助理手中的iPad上將會詳細羅列出到訪客戶的過往購買記錄、個人偏好,以及他們在Facebook或是Twitter上發布的有關品牌的言論,目的自然是為了讓顧客在享受更好的服務之后能慷慨地打開自己的錢包。可是,盡管博柏利聲稱,顧客有自主選擇是否加入該計劃的權利,但可能涉及的隱私泄漏以及出現的尷尬場面,著實不得不讓人為博柏利的“高科技”捏一把汗。
擔心還不僅如此。
受累于品牌在中國市場的增速大幅放緩,2012年7-9月,博柏利整體收入增幅僅為2.6%,遠低于之前兩個季度的11.2%和16.1%。在發布盈利預警后,其股價暴跌18%。博柏利的數字化戰略因此受到質疑。雖然其后一個季度的收入增幅有所提升,但仍有市場人士認為,“過分沉溺于‘數字’,分散了一個奢侈品牌打造核心業務的精力”。對此,阿倫德茨并不以為然:“奢侈品行業必須跟上現代人的腳步,他們不再撕下雜志上的照片,而是直接下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