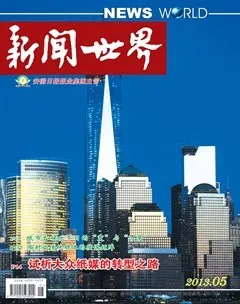當代中國電視綜藝節(jié)目的四種“瘋癲”
【摘 要】本文根據(jù)福柯的觀點,就當代中國電視綜藝節(jié)目的表現(xiàn),認為其體現(xiàn)出福柯所歸納的“瘋癲的四種形式”:浪漫化的瘋癲;狂妄自大的瘋癲;絕望情欲的瘋癲;正義懲罰的瘋癲。在泛娛樂化時代,電視綜藝節(jié)目的“瘋癲”影響了其自身的健康發(fā)展。
【關鍵詞】綜藝節(jié)目 福柯 瘋癲
《瘋癲與文明》是福柯的博士論文,也是他早期的代表作。福柯認為,瘋癲表現(xiàn)出四種形象:浪漫化的瘋癲,狂妄自大的瘋癲,正義懲罰的瘋癲,絕望情欲的瘋癲。回顧當代中國電視綜藝節(jié)目的發(fā)展軌跡,從主持人到明星嘉賓,從參與者再到普通觀眾,本文認為其話語表現(xiàn),娛樂和游戲的形式,體現(xiàn)了福柯所歸納的“瘋癲的四種形式”。
一、浪漫化的瘋癲
福柯認為“浪漫化的瘋癲”是最重要,也最持久的,瘋癲反映出人類的各種想象力,“甚至最漫無邊際的遐想”。“這些想象是模糊的、騷動的,卻又在一種共同的妄想中奇怪的相互妥協(xié)。”①
這與綜藝節(jié)目用千奇百怪的創(chuàng)意才能贏取收視率的道理一樣。在綜藝節(jié)目中,游戲的招數(shù)或者是游戲的結果越是出人意料,越是有著超乎尋常的價值,它常常介于真實與非真實之間,滿足著人們的想象空間。
舉例來說,近期在臺灣觀眾和在網(wǎng)絡上下載臺灣電視節(jié)目的內(nèi)地觀眾中大受歡迎的《全民大悶鍋》,就是這樣一檔真正“出奇制勝”的綜藝節(jié)目。《全民大悶鍋》明確打出“解悶救臺灣”的口號,讓電視演員模仿政治人物、用出神入化的“模仿秀”和戲謔鬧劇去戲仿臺灣政治生活、諷刺政壇現(xiàn)象。現(xiàn)以《全民大悶鍋》節(jié)目現(xiàn)場來了解一下這檔節(jié)目是如何體現(xiàn)“浪漫化的瘋癲”的:
節(jié)目的主題是“花400億救高鐵,花5億打造李安第二……政府錢這樣花,你是爽還是悶?”。在當天的直播現(xiàn)場,演員邰智源扮演的“周玉扣”(戲仿《臺灣高峰會》節(jié)目主持人周玉蔻)穿著一個大披肩登場了,“她”嫵媚地說:“恩哼,我是扣扣周玉扣,現(xiàn)在看我的節(jié)目不容易了,你們只能聽廣播,要看我主持的節(jié)目只能看這臺了。”作為當晚《全民大悶鍋》的主持人,“她”更加嫵媚地搖了搖手,像所有的主持人一樣喊出節(jié)目的口號:“解悶救臺灣!”全場三聲“解悶救臺灣”之后,鏡頭搖到“她”的右手邊——是“被質(zhì)詢卻沒有辦法站起來的蘇貞昌蘇院長”,郭子乾扮演的“蘇真昌”還是以禿頂示人,揮動著右臂:“大家好,我就是行政院長蘇真昌———沖!沖!沖!”鏡頭切到依舊穿著紅夾克、拿著小教鞭的“李熬”,扮演者唐從圣揮舞著教鞭熟門熟路地開場:“我是李熬李大師,男人都偏好女色,女人都偏好男色,但是政治最好不要有顏色,無論你是藍色還是綠色,都要看我的狠角色。”惟妙惟肖的模仿亮相之后,是各路“仿真政界人馬”視演播室為“立法院”,唇槍舌戰(zhàn)你來我往叫罵不休,將嚴肅的政治討論在形式上娛樂化,包袱一個接一個抖開,節(jié)目氣氛也節(jié)節(jié)高升。
“悶鍋”這種“浪漫化的瘋癲”連接了臺灣島內(nèi)輕松的娛樂和沉重的政治,打出一張極富想象力和策劃力的王牌,大獲成功——2005年11月播出僅10個月的《全民大悶鍋》就獲得臺灣電視金鐘獎最佳綜藝節(jié)目獎。
二、狂妄自大的瘋癲
福柯認為,瘋癲的主體“通過虛妄的自戀而與自身認同”,“虛妄的自戀使他將各種自己所缺少的品質(zhì)、美德或權力賦予自己。”他還認為,“自戀是瘋癲的第一個癥狀……在這種虛妄的自戀中,人產(chǎn)生了自己的瘋癲幻想。”②
各種類型的綜藝節(jié)目都有一個共同的本性,那就是試圖為自己加冕,為自己建立權威地位,說到底,就是獲得權力。早期《綜藝大觀》類型的綜藝節(jié)目以成為“最好”、“最受歡迎”來獲得對嘉賓和觀眾的支配力:比如驅使明星們形成以上《綜藝大觀》為成功的標志的觀念,支配觀眾“約會收視”、“按時開機”。《超級女聲》等選秀節(jié)目賦予自己權力的手段同出一轍,經(jīng)過超女遍及全國聲勢浩大的“海選”和一兩個幸運兒的出名獲利,一些少男少女把參加超女超男、進入決賽視為實現(xiàn)自我、邁向成功的顛峰體驗,《超級女聲》這樣的選秀節(jié)目也就從這些青少年“華山一條道”的成功觀中掌握了自己渴望的權力。
主持人往往是所在節(jié)目牟取權力之路上的急先鋒。比如《康熙來了》的主持人小S就屢屢問及來上節(jié)目的嘉賓:“崇拜的明星偶像是誰?”,該節(jié)目有一個潛在的規(guī)則——所有嘉賓都應毫不猶豫的回答:“你呀!”盡管這個問答程序只能說是節(jié)目搞笑的一個小把戲,但小S的確藉此憑借主持人的身份享受了一次有人配合的自戀,而為她提供這樣一個“將各種自己所缺少的品質(zhì)、美德”賦予自己的機會的正是綜藝娛樂的“瘋癲”時代。
三、絕望情欲的瘋癲
理性時代中人們對情感和欲望的放縱、對自我的寬容,往往也是瘋癲的一種形式。這種瘋癲,在目前的某些綜藝娛樂節(jié)目中被放行甚至被放大,形成了飽受評論界詬病的重癥之身。與臺灣相比,大陸相對正統(tǒng)的文化和娛樂環(huán)境使各檔綜藝節(jié)目在這個方面很少出格。
在臺灣有“娛樂天王”之稱的吳宗憲主持著一個名為《綜藝最愛憲》的綜藝節(jié)目,它的前身《綜藝旗艦》便以諸如“向嘉賓潑餿水”、“用腳踩糞便”等一系列“惡搞”游戲為噱頭吸引觀眾,而真人“如花”的出現(xiàn)除了將《綜藝旗艦》更名為《綜藝最愛憲》以外,更給了觀眾與吳宗憲一道放縱欲望,戲弄他人,施加惡意的機會。播出短短三周,《綜藝最愛憲》就一度沖上臺灣綜藝節(jié)目收視榜首。這樣肆無忌憚的放縱作惡與審丑的欲望,竟然形成了集體圍觀的盛況,叫人不得不反思這個媒體的瘋癲時代是否已經(jīng)蔓延成為一種社會病癥?
面對臺灣知識界和婦女界、社工組織代表的抗議,吳宗憲的回答是:“節(jié)目要有收視才有工開,所以我們都是提著頭在做事。既然頭都提了,臉也就不需要顧及了。”如果戴上瘋癲的面具就能獲得作惡與放縱的權力,這的確是一個娛樂瘋癲的時代。
四、正義懲罰的瘋癲
在綜藝節(jié)目的競賽環(huán)節(jié)特別是肢體游戲中,懲罰與獎勵往往是同時出現(xiàn)的,答錯題目或者競爭失敗的參與者會遭到節(jié)目預定程序的“修理”,早期綜藝節(jié)目中常見的有被強氣流轟頂、被砸蛋糕、被噴水等把戲,近期的綜藝節(jié)目的游戲懲罰則發(fā)展得越來越殘酷越來越離奇,如江蘇衛(wèi)視《非常周末》節(jié)目中有一個游戲環(huán)節(jié),要求選手和主持人站成一排接力唱歌,每人所唱的歌中必須帶有數(shù)字,然后把手中的“地雷”(節(jié)目中的道具,類似擊鼓傳花游戲中的花朵)傳給下一個人,如果在手中的時間太長,“地雷”就會冒火花,唱不出歌的人就要接受懲罰,要去坐“電椅”。 “電椅”的電壓并不是220伏,但不幸的選手依然被電得面部表情扭曲,而且可以看到在電流通過人身體的那一瞬間,在電椅的下邊冒出了電火花。這些懲罰與獎勵一道,屬于游戲既定規(guī)則的一部分,在相對封閉的節(jié)目現(xiàn)場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游戲空間。另外一些時候失敗者或表現(xiàn)不佳者會遭到節(jié)目主持人或者評委明確的批評甚至是羞辱等語言懲罰,這種情況在選秀節(jié)目中表現(xiàn)最為集中和直接,除了評委能直接對選手進行語言懲罰以外,選秀節(jié)目開放空間讓場外觀眾也能夠通過即時通訊工具發(fā)表對選手的看法,拓寬了懲罰的來源。
如果說觀眾進行肆意批評甚至語言攻擊是因為他們并不與主持人和參賽者處于同一物理空間、不受人際交流壓力的影響的話,那么評委作為節(jié)目現(xiàn)場的另一表演主體,他們的語言表現(xiàn)將最直接的與現(xiàn)場選手進行面對面互動,這時候,評委的點評語言就不僅僅是個人意愿的表達,也是節(jié)目立場的組成部分了。令人擔憂的是,出于制造高收視率的需要,有的評委的“麻辣點評”已經(jīng)開始漸漸漫出邊際,轉化為人身攻擊而成為電視文化的羞恥了。廣電總局在《關于進一步加強廣播電視播出機構參與、主辦或播出全國性或跨省(區(qū)、市)賽事等活動管理的通知》中明確規(guī)定,“評委點評要實事求是、積極健康、平等善意,不搞不切實際的吹捧,不搞令參賽選手難堪的責難,不以非理性的褒貶來取代知識性的引導。”③在這種背景下 “毒舌”評委仍然頻頻制造出格的語言懲罰就更顯得過頭和不可理解。
分析“麻辣點評制造高收視率”背后的原因,筆者認為評委的麻辣語言和砸蛋糕一樣,作為對失敗者的懲罰帶給觀眾虛擬想象的執(zhí)行快感,能夠使某些觀眾潛意識中的自卑、恐懼等心理壓抑得到釋放和宣泄,從電視經(jīng)營的角度來講,就是高收視率的保證。
福柯認為瘋癲能夠“懲罰頭腦混亂的同時還懲罰心靈混亂……通過懲罰本身而揭示出真理”,④那么可以認為,在綜藝節(jié)目中真理就是快樂,如果參與者的失敗和對失敗的懲罰能帶給觀眾快樂,那么正義就得到了彰顯,一切存在似乎都成為合理。在任由娛樂至上的媒體時代占據(jù)我們思維的時候,理性和人性中的美好與寬容都被迫讓位給了瘋癲。
結語
特定時代的瘋癲有啟蒙與革命的正面意義,福柯對瘋癲一直不乏正面的論述,巴赫金的狂歡化理論也從另一側面書EcTfLaoMXxCd+gaMj9NhRg==寫了狂歡與瘋癲特有的主體解放與民主啟蒙功效,但他們的論述都或多或少地指向宗教與政治專制,具有特定的歷史與文化語境。當代綜藝電視節(jié)目中的瘋癲標示了人的感性存在,是對僵硬與機械的日常生活的反抗,是不斷累積的不良情緒的宣泄。但他們失卻了福柯或巴赫金式瘋癲話語中的人文情懷,成為一種沒有理想的瘋癲。于是,當代社會的瘋癲頻頻突破藝術或道德的界限,成為一種只破壞不建設的顛覆性力量。
參考文獻
①②④[法]米歇爾·福柯 著,劉北成、楊遠嬰 譯:《瘋癲與文明——理性時代的瘋癲史》,三聯(lián)書店,2003:25、90-92、26
③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官方網(wǎng)站,http:
//www.sarft.gov.cn/manage/publishfile/21/3559.html。
(作者:四川大學09級研究生、平頂山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教師)
責編:葉水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