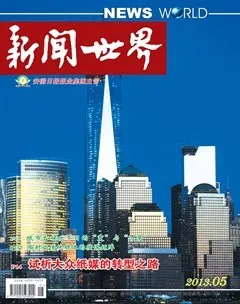論“鏡子說”譜系演變下的羅伯·格里耶
【摘 要】本文將通過新小說派的領袖羅伯·格里耶的典范之作《橡皮》闡釋新小說“純物主義”的視覺作用方式,旨在表明,他的創作理論是用冷靜客觀的眼光去觀察事物,捕捉現象世界的直觀映像;但是絕對的寫物主義從不脫離人的知覺而顯現,描寫物時總有人的眼光在看,有思想在審視,有欲望在改變,這是一種“主觀的極端主義”形式。
【關鍵詞】“鏡子說” 視覺 純物主義 主觀
一、“鏡子說”譜系的演變
在古希臘人的觀念中,世界是一元的,神無所不在,不僅是一種神秘的力量,而是存在于一切現實事物之中。希臘人的視覺思維主要體現為美學領域中的模仿,他們使藝術形象只依賴現實本身,與象征無關。希臘神人同在、神人一體的思想使得希臘人對創造性的想象活動并不關注,而更多再現的是生活中的對象本身,藝術的真實性來自于生活的真實性,藝術和生活水乳交融,兩者并沒有實質上的區別。
柏拉圖認為鏡子只能從外形上畢肖現實,卻達不到真正的實體。用他的話說“圖畫只是外形的摹仿”,柏拉圖以鏡子比方來闡明藝術的本質。亞里士多德不贊成摹仿就是對外在物象的復制或鏡像反映,他認為:“摹仿不是忠實的復制現實,而是自由的處理現實,藝術家可以用自己的方式顯示現實。”
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杰出的藝術家達·芬奇在其論畫的《筆記》中多次用“鏡子”作喻來表現藝術與現實的關系。如“畫家的心應當像一面鏡子,永遠把他所反映的事物的色彩攝進來。前面擺著多少事物,就攝取多少形象。而文藝復興時期的‘鏡子說’特別重視對人的刻畫和描寫,師法自然也兼顧人的主體性,主張模仿和創新的統一,從而深化了傳統摹仿論的內涵。”
古典主義時期的“鏡子”式的摹仿則強調“一般的再現”,不著重描寫個體人物的性格,而是對某一種類型的闡釋和表現,對自然的描摹或再現人的激情,突出的是個別中的一般,強調共同性和普遍性,造成人物類型化、單調性的特點。
同樣喜歡用鏡子作比方來闡釋藝術的摹仿或本質的現實主義,創造性的提出現實主義“典型理論”,所謂典型塑造就是以現實生活為基礎,將自然的、分散的生活現象、真實的細節,經過抽象和概括,提煉成一幅統一的、完整的生活圖畫。后來的自然主義藝術家在創作原則上追求現實主義“屏幕理論”,鏡子內涵從“再現說”的自治標準偏向了“模仿說”的他治標準,企圖極力營造一個與現實生活完全相似的幻想世界,也就是“鏡子式”照搬原樣生活。
二、法國新小說“純物主義”
新小說派主要指20世紀50年代初的四位嶄露頭角的作家:羅伯·格里耶,娜塔莉·薩洛特,托布爾和西蒙。新小說一直在對小說形式進行著新的探索。他們雖然不反對巴爾扎克以來的傳統現實主義小說,但是其徹底突破了傳統小說的規則,作為新小說“客體小說”派的代表,羅伯·格里耶把對“物”的描寫置于小說創作的首要地位。
1、對傳統小說的革新
以羅伯·格里耶為代表的法國新小說“視覺派”似乎把西方現實主義主導性視覺模式——“鏡子式”的逼真反映發揮到極點,將自然主義的“屏幕”理想推到極端,即追求一種與現實生活完全相似的非人格化的“純物主義”的現實世界,一種零度狀態的“視像”。為此他們要求排除作者和人物的自我意識,他們的眼睛好比不帶主觀感情的攝影機鏡頭,要求不帶任何主觀感情色彩的語言,即“僅用衡量、界定和限制的視覺性或描繪性的形容詞,冷靜、仔細地去描寫他們視線所及的外部世界。”
對新小說派的作家而言,傳統的小說中作家以全能造物主的姿態出現,他們以自己的思想意志去架構情節、設計人物的命運走向,以自己主觀的意圖和看法去反映現實生活,這是為他們所不能認同的。因為新小說派認為,若以人的觀點強加于物,一切以人的眼光觀察世界,則削弱了物的本體的真實性,掩蓋了事物的原有面貌,讀者就不能正確和自由的去認識世界。
2、淡化人物,寫物為主
在羅伯·格里耶的小說中,沒有對人物形象的刻意塑造,他筆下的人物已經失去了傳統小說以人物為中心,表現人物性格的功能,“他否定現實主義人物塑造,情節鋪成的手法,他要寫‘物的小說’,”人已經被物所代替,所淹沒。格里耶認為在這混亂的時空里,只能對眼見存在的事物客觀忠實的描寫,只能涉及現實本身,不可能表現含有任何寓意價值的思想和情節,只有通過對物不厭其煩的瑣碎描繪,才能達到一種純粹、更高意義上的真實。新小說派認為在日常事物的表面下,隱藏著深刻的、不為人知的東西,只有通過細致、周密的觀察和描寫,努力探索潛藏在事物表面之下的秘密,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質。因此,在新小說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往往一個細節能寫上一章,一件小事就能一連寫上幾十頁,這樣就顯而易見的把對物的描寫提到了首要的位置。
試看他對切開的番茄長達三百多字的描寫:“這一片番茄真是完美無缺,它是用機器從一個組織結構對稱完善的果實上切下來的。它四周的果肉緊密勻稱,具有像化學劑中那種鮮艷的紅色,夾在發亮的果皮和子房之間,既肥厚又勻稱。子房里的黃橙橙的種子,按著大小排列,層次分明;一層綠色透明的凝固物使種子粘附在果心鼓起部分的邊沿。那淺粉紅色的、表面微呈顆粒狀的果心,從底部凹陷處伸出一束白色的條紋,其中一條伸至種子附近——但它延伸的方式有點難以明確。在這片番茄的上面頂端,發生了一種幾乎無法察覺的意外情況:有一小塊皮離開果肉約一兩毫米,現在微微的翹起。”
用直觀的視覺和純描寫性的詞匯對一個番茄的描寫可謂是精微細致,為了把物象描摹的更為精確,逼真,作者用幾何學式的語言不厭其煩的對其顏色,形狀,紋理等多方面進行精雕細刻。格里耶對一個番茄進行解剖式精細的描摹,并不顯得枯燥而又瑣碎,反之這種觀察的周密和逼真仿佛讓物象躍然于眼前,如此細致的程度可謂是淋漓盡致,讓人嘆為觀止。
“新小說派認為,作家只需要把自己所觀察到的事物和人的捉摸不定的存在方式展現出來就行了。作家應該以超脫的態度站在純客觀的立場上,不帶任何感情地冷眼觀看世界,只向讀者提供見證,不應當提供價值判斷,因為‘世界是沒有意義的,但也不是荒誕的。就是那么簡單’。事物就是事物,人就是人,兩者之間沒有什么神秘的聯系或相互感應的現象。從這種觀點出發,有些評論家把這一流派稱為“‘物體派’;‘視覺派’”。
格里耶主張拋棄以人的觀點、感情去解釋和反映世界的觀點,而要如實的把人看成是外在客體的“見證者”,用他的話來說:“必須毅然決然站在物之外,站在他的對立面,我們既不能把它變成自己的,也不能把某種品質加諸他們、它們從來就不是人。”“格里耶要求作家以一種絕對客觀的態度來描寫事物,他認為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摒棄一切與物接近的主觀企圖和方式。”
《橡皮》的第一章開頭,經濟學家杜邦被槍擊之后,內務部長派瓦拉斯來到杜邦所在的這個外省小城偵破這一案件。瓦拉斯在深夜到達該城,第二天一早,他在這個錯綜復雜的街道上行走,作品在長達20頁的篇幅中,詳盡的記錄了瓦拉斯所看到的街道兩旁的各種各樣建筑,各種公司,商行,商店,鋪子及其招牌的名字,以至一幅畫、一塊橡皮、一個明信片,作者都不厭其煩的予以詳細描寫和交代。尤其是對咖啡館店堂大理石桌面上一小塊污點的多次描寫更是一個經典的例證。
3、心靈的外化——主觀的極端主義
羅伯·格里耶視覺主義的物本觀,絕對冷靜的對事物進行瑣碎描寫的文體風格,很容易被貶為反人本主義。這是一種誤讀。首先,羅伯·格里耶并沒有否認人,他明確指出現實主義并非只是某些作家的專利,在《自然、人道主義、悲劇》一文中,他也申明他并不否認人,他否認的只是把事物與人類相混淆的傳統人道主義。
他在《新小說》中重申:“書中的每一頁、每一行。每一個字都有人,盡管人們在小說中看到許多‘物’從未脫出人的感應之外呈現出來。”“這似乎是一個悖論:純粹的再現或‘鏡式’地反映外在物,結果卻是物被降低為一種帶有人性的構造物,試圖完全排除人類認識的嘗試卻相反的邁向絕對的主觀性:不存在事物,只存在對事物的認識。”
在《橡皮》中我們看到作品描寫到的人物一方面處于那些“無所不能“的經濟政治集團的統治下,一方面處于機械化,電氣化的物質世界包圍中,只能感到軟弱無能,無法自主,孤獨煩悶。對物的偏執強調其實是要揭示人被淹沒在“物”的海洋中,人缺乏自主性,面臨這精神困境,毫無出路;“反映出現代西方社會‘物’對人的擠壓和人、‘物’關系的顛倒。”
因此純“鏡式”的客觀性實質是主觀的一種極端形式。格里耶自己也宣稱“新小說追求的是完全的主觀性”。這同20世紀普魯斯特、喬伊斯等現代派作家注重心理意識的捕捉,表現心里內容的隱秘與流動,注重描寫精神上發生的事件是如出一轍的。
結語
筆者認為,格里耶的小說并不存在純粹的物主義小說,他并不排斥人物的參與,淡化人物的同時并不排斥寫人,寫人的目的是通過人的視覺去觀察物,寫物更加是為了寫人,他并不直接表現人的思想情感,而是暗示在物的充斥中人們的精神狀態。所以通過對物的描寫來揭示對人的命運的堪憂。所以盡管新小說派立意追求純粹的客觀主義,但在一定意義上說,也同樣在表達人類內心深處的主觀感受和意識自覺。這種集“極限的客觀”與“完全的主觀”于一身,正是新小說對傳統小說的繼承與革新,也是其最具價值和影響之所在。
參考文獻
①曾軍著:《觀看的文化分析》[M].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8
②肖偉勝:《視覺文化與圖像意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③吳越添:《法國小說發展史》[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4
④鄭克魯:《法國文學史教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⑤張唯嘉,《格里耶的寫物理論》[J].《佛山科學技術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2)
⑥亢西民,《“新小說”的典范之作——讀羅布·格里耶的小說〈橡皮〉》[J].《名作欣賞》,2001(4)
⑦楊劍,《新小說派對小說藝術的探索》[J].《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1994(2)
⑧羅伯·格里耶,《未來小說的道路》[J].《當代外國文學》,1983,(1)
(作者: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研究生)
責編: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