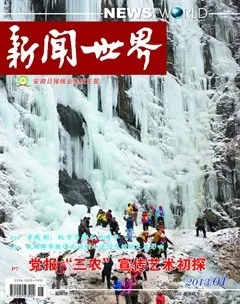《自由中國》對臺灣反對運動的影響
【摘 要】在臺灣幾十年民主進程的發展史中,報刊媒體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他們從開始的崇黨崇政到后來的反省覺悟,爭取新聞民主自由,期間與新聞媒體工作者的奮戰不可分割。通過《自由中國》當年轟動一時的十五篇社論或許能窺見緣由。本文通過對這一半月刊社論的分析來探索臺灣新聞事業對臺灣反對運動進程的影響和關系。
【關鍵詞】《自由中國》 反對運動 政治社論
一、《是什么 說什么》概述
1957年的臺灣社會風氣日益敗壞,各領域毫無生機。由于對當初國民黨政府刻意塑造開明形象,但后期進行高壓政策、政治滲透進教育和蔣介石三連任等違反民主憲政程序的統治感到不滿和憤怒,雷震等人自五四運動以來深植于心的自由主義意識覺醒,認為要用“民主”來對抗“威權”。①但雷震也因此入獄,雷震事件即自由中國事件。
《自由中國》編輯部認為有必要在此時撰文點名當前時局。第一篇就是殷海光執筆的《是什么 說什么》,這一篇社論開啟了對臺灣當時社會問題的抨擊,《自由中國》一針見血指出現今最應該做的是端正態度、正視現實。而且這篇社論重點是在于喚醒知識分子的覺悟。
“我們所處的時代,正是需要說真話的時代,然而今日我們偏偏最不能說真話。”開篇第一句就點明了當時臺灣的時局和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心態。雷震、殷海光、胡適等人都經歷了五四運動,屬于五四先鋒,民主、自由口號正是這些知識分子所最看重的。撤退到臺灣后,隨著二二八事件的發生,蔣介石獨裁的本質彰顯無遺,讓這些從大陸遷臺的知識分子感到十分寒心。針對當時這樣一個環境,他們首先是對出現這些情形的原因進行探究。殷海光等人認為在一個嚴格控制的社會里,表面的整齊壯觀下掩蓋的是窒息萎縮的社會。“這七八年臺灣的思想言論形之于表面的,除了極少例外,幾乎都是官方或準官方的思想言論了。”對于這一點,是這些知識分子所最擔心的。
而蔣介石政府又是通過什么樣的形式來蠱惑民眾呢?殷海光把手法指向語意學:“近幾十年來政治場合里的語意現象,大都是用一切光明的字眼,掩飾一切陰暗的里層。”作者也將特征一一列出來:“一、言不由衷;二、空話連篇;三、推拖抵賴;四、威脅利誘;五、諾言滿紙;六、敵友無常。”官方言論尚如此,又怎能成為引導民眾的行動指針?除此之外,自由中國》批判蔣政府還將此引入到教育系統中,并將原因歸根于蔣政府“政黨即是政府,而政府即是國家”的思維邏輯。由于這群知識分子崇尚西方式民主,因此,對于臺灣的時政也希望能采用西方民主,當然,生搬硬抄不能符合實際,中國歷來就由于傳統的愛面子心理,錯用了“隱惡揚善”的觀念,在政治上的壞事不讓大家說穿。“諱疾忌醫”的心理使得大家都愿做“良民”寧可隱忍,而對此,殷海光提出:“我們與其諱疾忌醫,讓病這樣拖下去,到頭來不可收拾,不如趁早診斷明白,及時醫治。”
解決的辦法就是立言。 “我們立言的基準只有這樣的一條:是什么,說什么”。講真話,本是人最基本的一條基準,直到現在,全世界也只有較少數的人在較少的時間以內才能接近這一條基準,而中國人難以做到這一點的原因,殷海光也點出有兩方面原因,一是歷史原因、本土文化原因,“先知先覺們對于一般人民在知識方面存著輕視的心理,說什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這種氛圍和傳統下,沒幾個人能夠想到講真話。二是,雖然科學能做到這一點,但是科學的出現也是近百余年來的事,不少真理學說在剛出現時也遭遇到迫害。由此兩點,“我們要實現‘是什么,就說什么’乃一件既不簡單又需作很大奮斗的事。”雖說如此,但是不說真話結果會更糟。至于要說什么,《自由中國》講出,政治、軍事、經濟、財政、司法、思想、文化、教育、宣傳等等主題作為十五篇社論的總綱,而且比提出問題更重要的是嘗試著解答這些問題,“我們提出來,激發大家思想,共同尋求答案”。
最后,這篇社論還是回歸到人本問題,是誰能在這個要緊關頭來領導大眾去反思,并做出行動,還是知識分子。“中國近幾十年來的進步與革新,知識分子常為主導力量的中堅。”整篇社論中心明確,從提出問題、問題的緣由、解決問題,如何正視現實,誰來領導,幾個方面層層深入,圍繞著講真話這個主題,從主客觀和中外的經驗來論證。政治論述最重要的一點是在于一針見血,揭發時政弊端及背后真相,引導人們正確思考,引發社會群思,如果不能起到開發民智的作用,社論也無法體現其價值。通過這篇社論,也可以看出這批報人的辦報思想:輿論是為民、為國家;媒介可以影響政治;知識分子應該起到首當其沖的先鋒作用。這篇社論開啟了十五篇社論的序幕,也是臺灣反對運動中最先的思想運動,對后期報刊雜志的政治社論體影響至深。
二、政論雜志《自由中國》對臺灣反對運動進程的影響
1、《自由時報》對臺灣民主化進程和反對運動的積極意義
臺灣民主化理論有著很多不同的看法,除了現代化理論之外,選舉制度早就反對黨和反對勢力,統治菁英分裂等觀點,都可以解釋臺灣民主化行程。但是縱觀現在的情形,選舉制度是最能體現臺灣民主立場的一個方面,也是推動其進程的最大影響力,而在選舉中,媒介對其的傳播主導力量不言而喻,選舉與政論相輔相成,媒介展現出其傳播介質在政治平臺中的重要性。
在戒嚴時期,威權體制與媒介的關系是從上而下的掌管,是一種控制與隸屬的關系。《自由中國》從開始的聽從政府指示到后期反省,開始呼吁追求民主自由,正是一個時代的寫照。這份雜志喚起了當代政治參與者的支持和反對意識。通過勢力雙方的不斷爭論,取得了共識和討論的空間,在后期也舉行了選舉座談會等相關運動,而參與其中的民眾也大多是通過《自由中國》這份半月刊得到相關的政治訊息,媒介的教育功能不言而喻。至于到后期成立了新的反對黨并加以實踐,意味著媒介在反對運動中成為一種權威或發動的角色,有力的發動并控制事件,甚至管制訊息的流動方向,成為反對運動中重要的角色。②
除此之外,《自由中國》在爭取新聞自由,堅持媒介應有的價值觀念,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殷海光的《是什么 說什么》除了政治意義,更是堅持了新聞工作中真實的理念。通過社論這一形式,讓更多的受眾參與其中,引起其深思,媒介的教育功能和宣傳功能完美結合,也深刻的影響到現實生活中,這是《自由中國》在臺灣報業史上光輝的一筆。
2、《自由中國》的局限
盡管對臺灣民主進程和反對運動有著深刻的影響,但是《自由中國》也并不是十全十美。這份雜志有其局限之處:第一,理論多于實際。從“今日的問題”十五篇社論開始,《自由中國》就著重在提出問題,引發反思,但是對于怎樣去解決,并沒有實際有效的方法,只是“激發大家思想,共同尋求答案”。第二,外省人意識和少臺灣在地觀點。這是當時大陸遷臺報刊雜志的共有問題,從《自由中國》的編輯隊伍來看,胡適為發行人,主要編輯人員雷震、戴杜衡、徐復觀等人都是所謂的“半山”,即曾經居留大陸一段時間又再返回臺灣的臺灣人。他們大多是任職于國民黨政務系統內,在行動上擁護國民政府,這樣的“半山”族群是無法真實體會到底層人民的心聲。尤其是仍對國民黨政府抱有希望的雷震,他的人生前半段都是在國民黨政府體系中工作,曾任職政治協商會議秘書長,在三十年代,可以說是風光一時。即使是到后期,蔣介石政府開始有所壓制新聞事業,雷震也是對其抱有希冀,他曾在《自由中國》社論中引用春秋時代鄭國子產對執政者子皮的一番話:“子于鄭國,棟也,棟析衰崩,僑將壓焉,敢不盡言。”③來說明他當時對于國民黨“不得不信賴”的心情。之后,他還曾發話:“無論大家對于國民黨的看法如何,我們決不能對它灰心。現實擺在眼前,臺灣是太平洋颶風季節中的一葉扁舟,這扁舟的掌舵者是國民黨。國民黨如果走錯了路線,國運前途就不堪設想。因此,在國民黨七全大會閉幕不久的今天,我們還得對它再致殷切的期望。”由于這種政治意識的尚未徹底性,導致其論述多偏離實際問題,脫離了當時最普遍的臺灣民眾,在地意識少,所以所能提出和解決的問題也只是政治體制上的不公,未能深入觸及政治結構。
第三,省籍意識強烈,外省人和本省人的矛盾尖銳。二二八事件正是外省人與本省人矛盾沖突的爆發點。國民黨多外省人,都是從大陸遷到臺灣的高層精英,而反對黨多是本省人,《自由中國》反對一黨專制,主張反對黨的建立,可是其自身也有強烈的省籍意識,雷震的獄中手稿提到:“臺灣人的心目中,總覺得大陸人都是統治階層。”而編委會委員戴杜衡甚至說過:“把臺灣人搞起來,大陸人將來是要受其欺壓的。”這樣的民族狹隘意識的存在,是《自由中國》所無法避免的,也是牽絆其思考層面的一塊石頭。他們多把問題關注在菁英階級和上層建筑,很少提及臺灣最根本的、日益嚴重的省籍認同問題,所看待問題的角度有種高高在上的姿態,這也是《自由中國》無法深入到最基層民眾的主要原因。
結語
綜合而言,《自由中國》這份雜志以其專業性和政論性,為當時的受眾思想啟發與民智開化起到很大的影響,也為臺灣后期的反對運動開啟了媒介政論影響政治的先河。無論從結構層面、技術層面、功能層面還是理論層面,《自由中國》的十五篇社論都聚焦了當時臺灣的社會現狀和時局,對于政治體制、政治團體合法性;政黨選舉的制度層面;反對黨存在的意義和引發民眾對公共事務的關心這幾個層面來說,都是具有深刻影響的。雖然作為一份從大陸遷臺的雜志,缺少其在地性和本土化,缺少了民眾基礎,不過其媒介所發揮的功能代表著當時臺灣媒介在民主社會的演進中必備的力量。□
參考文獻
①任育德:《雷震與臺灣民主憲政的發展》,臺北:政治大學歷史系,1999
②王振寰,《反對運動與臺灣的政治轉型》,臺北:《臺灣社會研究》,1993:21-60
③范泓,《民主的銅像:雷震先生傳》,秀威資訊,2008
(作者:廣西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傳播學碩士)
責編:葉水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