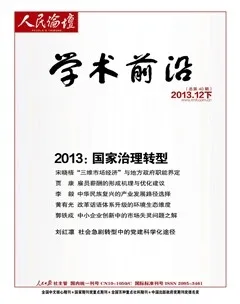改革話語體系升級的環境生態維度

【作者簡介】
黃有光,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經濟學系教授、暨南大學經濟學院訪問教授。
研究方向:中國經濟問題、福利經濟學與公共政策,提創綜合微觀、宏觀與全面均衡的綜觀分析。
主要著作:《福利經濟學》、《經濟與人生》、《經濟與快樂》、《快樂之道:個人與社會如何增加快樂?》等。
摘要 經濟高速發展而人們滿意度相對低下,什么是今后中國應有的發展方向?筆者提出以環保負責的“快樂國家指數”替代國內生產總值,作為國家(以及各省縣)的主要成功指標。本文也討論與此指標有關的一些話語,包括快樂、幸福、福祉等。它們之間有沒有差別?為什么偏好使用“快樂”?從快樂研究的成果,能夠得出什么政策含義?如何以“輕度家長主義”的方法增加人們的快樂,而避免弄巧反拙?
關鍵詞 轉型 經濟發展 環保 快樂國家指數
在中國,自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幾十年來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全世界有目共睹。2012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38420元,較1978年增長了16.2倍,年均增長8.7%。這樣的成就在人口基數這么大的國家,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然而,現在中國的人們是否滿足?是否快樂?社會是否和諧?是否穩定?中國能否長治久安?可否實現繼續發展?即使是像筆者這么天生樂觀的人,也不敢排除負面答案的很大可能性。造成如今生產消費大量增加而人們不滿、不快樂,社會不很和諧的原因,以及其解決方法涉及的因素很多,包括環保、收入分配、權力的濫用與貪污、制度、道德等。筆者針對今后改革的應有方向,以及有關的改革話語體系問題,提出應該以環保負責的快樂國家指數替代國內生產總值,作為國家(以及各省縣)的主要成功指標。本文也討論與這個指標有關的一些話語,包括快樂、幸福、福祉等,以及一些政策含義。
環保負責的快樂國家指數
對于快樂的心理,社會學與經濟學者們近幾十年的研究所得出的相當一致的一個結論是,在溫飽與小康之后,更高的消費并不能,至少不能顯著地增加快樂,尤其是在全社會的范圍而言;個人可能可以通過相對地位的提高而略微增加快樂(Diener等,2010;黃有光,2013)。這個發現顯然指明,至少在達到小康之后,不應該再用GDP或GNP(國內與國民總產量)為主要的成功指標。Borghsi & Vercelli(2012,212頁)認為“真正的悖論是還在堅持使用GDP為人們幸福的主要指標”。因此,類似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總國民快樂)等基于快樂的指標的提出非常必要。以GNH替代GNP,是以快樂替代產量,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中國國內近幾年來對這類指標的提出與討論,是令人振奮的。筆者也很喜見國內經濟學者(如于席正、江莉莉,2012)對快樂問題的討論。
然而,作為比較精確的指標,GNH是不完善的。GNH是總國民快樂。我們應該極大化的不是總快樂,而應該是凈快樂。其次,一個國家如果極大化當年的GNH,可能會對其他國家以及將來的人們造成危害,比如對全球環境造成破壞。因此,筆者(Ng,2008)提出比較容易接受的(尤其是每年度)國家成功指標——環保負責的快樂國家指數(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happy nation index,縮寫為ERHNI,“娥妮”)。“娥妮”主要為音譯,但也取“娥妮”(美麗女孩)的美好意義,因此,ERHNI是美好東西的指數。
只是一天快樂,馬上死去,肯定不好。因此,長期研究快樂的知名學者Veenhoven(1996,2005)提出“快樂年數”(happy life years)的概念。比如一個人的快樂年數=平均快樂×生命年數。如果平均快樂(滿分為1)等于0.7,生命年數為80,則快樂年數等于56。
然而,如果一個人評價自己的快樂指數是0到1中的0.5,通常只是勉強及格,總快樂量與總痛苦量大致相等,凈快樂約等于零。簡單起見,不考慮對他者與對將來的影響。與其有情況A:0.4的平均快樂指數(凈快樂等于負的),而長命200歲(很長的受苦生命),得到等于80的快樂年數,不如有情況B:只活80歲,而有等于0.8的平均快樂,雖然快樂年數只有64。因此,這種計算法的快樂年數有誤導性。
筆者認為應該以凈快樂取代快樂,只算0.5以上的快樂量。根據這修正了的凈快樂年數,上述情況A的凈快樂年數是負20【(0.4-0.5)×200】,而情況B的凈快樂年數是正24【(0.8-0.5)×80】。
考慮到該國對他國與將來的影響,因此,計算每個國家的平均凈快樂年數,必須扣除這國家的人均環保(對他國與將來的)危害,才得出該國當年的環保負責的快樂國家指數。因此,環保負責的快樂國家指數(娥妮)=平均凈快樂年數-人均環保危害。
由于必須使用相互可比的數據(包括快樂與危害之間),因此上述指數的計算并不簡單。不過,正如筆者(Ng,2008)論述過,娥妮是可以計算的。筆者與研究員梁捷博士也正在進一步(在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資助下)改善娥妮的計算與快樂的調查方法,使它更加可靠,可以進行人際比較。
如果用娥妮取代(至少是補充)GDP,就能夠使人們與各國政府比較注重真正有利于提高人民的長期快樂的東西。例如,政府就應該更加重視避免“高速公路變成停車場,然后又變成垃圾場”(2012年國慶長假出現的情形),而不只是重視汽車的產量。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重要問題,例如環保、平等、食品安全、和諧、清廉、道德等。
對世界各國提出以娥妮取代GDP,大致是正確的(將來還可以進一步考慮通過科技、文藝、戰爭等對他國與將來的外部作用)。但從一個國家本身來看,鄧小平強調的綜合國力,也是重要的。雖然快樂會促進和諧而增加國力,但GDP也有相當大的貢獻。因此,在還沒有達到或接近世界大同時,不能夠單單看當前的快樂,還要維持與增加綜合國力。因此,對于本國而言,還只能用娥妮作為主要而不是唯一指標,補充而不是完全取代GDP。
幸福、福祉、還是快樂?
人們習慣上傾向于使用“快樂”來指當前的快樂,而使用“幸福”來指比較長期的快樂。福祉或幸福也是比較正式的講法。給定同樣的時段,不考慮講法的正式與否,則快樂(happiness)、福祉(welfare)、和幸福(subjective well being)都是完全同義的詞。如果某人當年幾乎每天的凈快樂量(快樂量減去不快樂或痛苦量)都是很高的,沒有很痛苦的時候,則他當年是很快樂的,也是很幸福的,當年的福祉也是很高的。
英文的快樂(happiness)與中文的幸福的概念的歷史演變,有一個相像的地方。根據《牛津英文字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等權威文獻(詳見Oishi,2010,38頁),幾百年前(1530)“happiness”的定義是“好運,幸運”,尤其是關于財富方面的。1591年后,開始引入“心中感受為好”的“happiness”的第二個定義。再后來第二個定義取代第一個定義。這與中文的幸福的字面上的“幸”與“福”的好運意義,以及現代“幸福”的主觀感受意義是類似的。筆者猜想,這種轉變可能是由于人們幾百年前還在溫飽水平線上掙扎時,能夠在財富方面有好運,大致可以保障快樂。在溫飽之后,財富方面的好運,未必對快樂有很大的貢獻。
很多人(包括阿里士多德)認為“幸福”應該排除不道德的快樂。例如一個強奸犯在某天可能因為強奸得逞而很快樂,但不能說他很幸福。筆者認為道德的問題很重要(詳見黃有光,2012),但完全可以通過考慮對將來與對他者(不說“他人”,因為不排除動物)的快樂的影響來處理。那位強奸犯是把自己當天的快樂(說成幸福或福祉都無所謂)建筑在他人更大的痛苦上(多數也是建筑在他自己將來的痛苦上),因而是不道德的,是必須受譴責的。問題不在于他當天的快樂本身,而是他當天的快樂對他者及對將來快樂的負面影響。
用道德來定義幸福或快樂,筆者認為是因果倒置。用什么來定義道德呢?(道德不能是一個最基本的概念,必須用其他概念來定義)筆者用快樂來定義道德。終極而言,不道德主要就是對他者快樂的負影響。可能有人會問筆者:“那你又用什么定義快樂?”快樂是一個基本概念,不必也不能用其他概念來定義,但可以解釋如下:一個主體(例如一個人)的快樂是其主觀感受中感覺為好的或正面的感受(positive affective feelings),包括肉體上的快感與精神上的欣慰。快樂的反面是痛苦,也是包括肉體與精神上的。(所謂肉體上的快感或痛苦,實際上最終也是精神上或主觀意識的感受。強調快樂包括肉體與精神上的,主要是避免被誤會為只包括純粹肉體上的感受)凈快樂是快樂減去痛苦。
在任何一個時點,一個人的快樂的強度(intensity)可大可小,可正(快樂時)可負(痛苦時),多數時間可能等于或接近于零。一個人大部分時間沒有快樂的感受,也沒有痛苦的感受,快樂值等于零或很接近于零。當他生病、受到傷害(肉體上或是感情上)或憂傷時,他的快樂就是負值。當他有感官上或是心靈上的享受時,他的快樂就是正的,而快樂或痛苦有不同的強度。在任何時段,凈快樂量是這快樂強度在這時段中的積分。如圖1所示,用橫軸代表時間,正縱軸代表正快樂的強度,負縱軸代表痛苦的強度,則快樂強度可以用一條曲線來代表。凈快樂量是通過原點(或零點)的橫軸以上的面積(等于正快樂量)減去以下的面積(等于負快樂或痛苦量)。于是,盡管存在不同類型的快樂方式,總的快樂卻是一維的。
對于下圖,筆者需要做幾點說明:第一,快樂只包括正的或好的(快樂)與負的或不好的(痛苦)感受,不包括中性的、沒有苦樂的感受,或把這種中性的感受算為零。例如,我現在可以看到墻壁是米色的,如果我對這個視覺沒有正的或好的,也沒有負的或不好的感受,而且此外沒有其他感受,則此時的快樂量為零。
第二,快樂包括所有正的或好的與負的或不好的感受,不論是肉體上或精神上的,不論是高級的或低級的,如果可以分高低的話。其實快樂本身,除了不同的強度,沒有高低之分。只有在一些另外的意義上,才有高低之分。例如,某種快樂感受,需要長時間的培養或訓練,才能感受到,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是比較高級的。
第三,快樂本身也沒有什么好壞之分。為什么有些快樂或享樂方式被認為是好的,有些被認為是不好的呢?這是因為有些享樂方式會直接或間接地(例如通過對知識或健康的影響)增加將來或他者的快樂,有些會減少將來或他者的快樂。如果沒有影響,或有同樣的影響,則不同的快樂只有強度的不同,沒有好壞的不同。
當然,不同的快樂感受有性質上的不同。欣賞音樂的快樂感受與吃冰淇淋的快樂感受,即使在時間與強度等方面都是一樣的,他們之間有很大的主觀感受上的性質上的差異,即哲學家所講的不同的qualia。然而,不論是音樂還是冰淇淋,如果給予感受者同樣程度的快樂,又沒有對將來或他者的快樂有不同的影響,雖然感受不同的qualia,其快樂量是一樣的。人們一般會褒欣賞詩詞與古典音樂或閱讀的快樂感受,而貶吃冰淇淋的快樂感受,有一些原因:首先,前者一般可以通過陶冶性情或增加知識而增加將來或他者的快樂,而后者一般會通過增加體重而減少將來的快樂。其次,吃冰淇淋的快樂感受不需要通過培養,人人知道,而欣賞詩詞或閱讀的快樂感受需要培養,很多人對此重視不夠。然而,除了對他者與對將來的快樂的影響,這些不同卻沒有影響快樂的總量。許多哲學家對這簡單的道理依然有很大的迷惑,正像他們對快樂是唯一有終極價值的東西依然有很大的迷惑一樣。(詳見黃有光,2011,附錄G)
為什么偏好使用“快樂”?
如果說快樂、幸福與福祉都是一樣的概念,為什么筆者偏好使用“快樂”?如果嚴格根據筆者所使用的意義,則使用任何三者之一都無所謂,因為它們是完全一樣的(在給定同樣的時段)。然而,其他人對這三個概念的領會是有所不同的。筆者對這三個概念的理解或定義是純粹主觀感受的,客觀因素只能通過對人們(包括現在與將來;為了敘述方便,“人們”可以包括動物)的主觀感受來影響快樂,不能夠直接影響快樂。這是(包括動物的)人本主義或福祉主義的最基本原則。多數人會接受“快樂”是這種純粹主觀感受的概念。然而,很多人認為“幸福”與“福祉”含有或應該含有一些比較客觀的東西,例如上述對于道德方面的要求。
在此舉例說明:如果張三身體健康,收入豐厚,妻子美麗賢惠,孩子聽話上進等,有人就認為他是幸福的。筆者認為,這些客觀因素,只是在許多情形下,有助于使此人幸福。張三是否是幸福的,要看他是否真的能夠在其主觀感受上有高度的快樂感受。如果他天生是悲觀的,不知足的,或是后天受到某些心理傷害,使他在多數時間是痛苦的,則即使具備能夠使大多數人得到快樂的客觀條件,他卻是不快樂的,因而也是不幸福的。
由于上述對快樂與幸福(或福祉)在主觀與客觀要素上的理解可能有差異,因此,使用“快樂”可以避免人們受錯誤的客觀主義的影響,避免人們在應該針對主觀感受時,不適當地混雜一些客觀的因素。這些客觀因素并不是不重要,而是在定義快樂或幸福時,是無關的。
其次,由于類似的原因,強調快樂可以避免一些濫用權力者使用像幸福或福祉的美麗概念,去進行一些表面上宏偉的措施,而實際上并沒有真正提高人們的快樂。被誤導的人們,可能還接受自己是“幸福”的,雖然并不快樂。實際上,如果不快樂,絕對不能夠是幸福的!
為什么許多人偏好使用“幸福”?
中國有許多優良傳統,筆者非常支持恢復或加強對這些傳統的重視。當然,傳統中也有一些不合時宜的東西,其中一項是禁欲主義傾向。在人口密度高而文化教育與法治水平不夠高的情形下,某種程度的禁欲主義,可能對于維持社會安定有一些貢獻。這也可能是禁欲主義傾向傳統形成的一個原因。然而,從人民快樂的觀點出發,尤其是到了現在,與其依靠禁欲,不如用加強法治、提高收入分配平等與提高教育水平等方法來維持社會安定。(詳見Ng,2002)
由于禁欲主義傾向的傳統,人們還有貶遏享樂的思想,把享樂主義當成洪水猛獸。其實,享樂本身是好的,應該被批判的是損人利己。鼓勵為人民服務是對的,但最終而言,并不是“人生以服務為目的”(孫中山語)。“為人民服務”不應該是以服務為最終目的,而是要使人民快樂。如果服務是最終目的,則類似文革的情形,人人都痛苦地為人民服務,不就是一個理想社會了嗎?經歷了文革的洗禮的中國人民,更應該認識到這個謬誤。
由于禁欲主義傾向的傳統,人們對“快樂”還有所保留,因而偏好使用“幸福”。如果使用“幸福”比較容易被受傳統影響的人們所接受,未必不是一個好策略。目標針對幸福,總比針對GDP(產量)要好得多。不過,即使使用“幸福”,應該認識到“幸福”就是長期快樂,不是什么客觀的東西。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主任王紹光教授于2010年9月17日在《21世紀經濟報道》的文章中,問:“什么是好的生活?”筆者的答案很簡單,終極而言,好的生活就是能夠達致長期高度快樂(包括自己、他人、甚至動物的快樂)的生活。然而,怎樣的生活能夠達致長期高度快樂呢?這就需要很多跨學科的學者進行長期的研究,以及各界人士的討論。
快樂還是幸福?與徐景安教授的討論
筆者有幸于2011年10月參加了討論幸福問題的威海峰會。這個峰會主要是中國幸福管理研究院院長徐景安教授主導的。徐老不但在主辦討論幸福的會議、倡議《21世紀幸福宣言》等理論層次上致力工作,而且通過提供咨詢,在實際改善許多機構與企業員工的快樂上,也有很大的貢獻。徐老與筆者在關于快樂或幸福問題上有大致共同的看法,但觀點也有重要的不同。
筆者認為幸福與快樂是一樣的。徐老認為幸福與快樂不同,幸福是比較高級的快樂,只有人能夠感受幸福,動物只能夠感受快樂。以筆者的定義,一只狗可能比一個人更加幸福,但徐老認為狗完全不能夠有幸福感。我們在會議上討論,彼此沒有說服對方。
人類肯定能夠有比動物更加復雜與比較高層次的精神上的快樂與痛苦。(關于“子非魚,安知魚之樂?”的濠梁之辯,見黃有光2011,附錄F)比較低級或簡單的物種,多數完全不能夠有精神上的苦樂,只有肉體上的苦樂;更低級的物種,多數連肉體上的苦樂也沒有。(詳見Ng,1995或黃有光,2010,關于福祉生物學一文的論述)筆者認為黑猩猩與狗等物種,應該能夠有某些精神上的苦樂。為了給徐老比較大的空間,讓我們排除能夠有精神上的苦樂的動物,假定只有人能夠有精神上的苦樂。
如果徐老定義幸福是精神上的快樂,或是某種(本節下文略去這條件)精神上的快樂,則根據這個(與筆者的不同的)定義,不能夠感受精神上的苦樂的動物,當然不能夠有幸福感可言。因此,根據徐老對幸福的定義,他的上述觀點是正確的;根據筆者的定義,筆者的看法也是正確的。如果只是定義上的差異,不必討論,但是還有一個重大問題。
為了討論上的方便,本節下文采用徐老的定義。根據此定義,幸福與快樂是不同的。幸福是快樂的一種,是精神上的快樂,不包括肉體上的快樂。吃冰激凌的快樂,不是幸福;性愛的快樂,也不是幸福。這類快樂,動物也有。你晚上回想這一天(或一生),認為成就(不論是在享受、事業、家庭、社會貢獻等方面)很大,感到欣慰,這是幸福。
上述重大問題是,個人以及社會,應該極大化幸福還是包括幸福的快樂?徐老顯然認為應該極大化幸福。筆者認為應該極大化包括幸福的快樂。
先考慮個人的情形。假定對他者與對將來的快樂沒有不同的影響,你選擇下述兩項中的那一項?
甲:一生極度的肉體上的快樂(例如快樂量為九千萬億個單位)加上高度的精神上的快樂(即幸福,例如幸福量為九萬個單位)。
乙:一生極度的肉體上的痛苦(例如痛苦量為九千萬億個單位)加上很高度的精神上的快樂(即幸福,例如幸福量為十萬個單位)。
從極大化包括幸福的總(凈)快樂量的觀點,肯定選擇甲,但極大化幸福量要求選擇乙。
可能有人認為,在乙的情形,雖然肉體上很痛苦,幸福感依然很高,可見對社會作出了重大貢獻。因此,從社會的觀點,乙可能更好。從社會的觀點,應該極大化所有人(假定不影響動物的快樂)快樂的總和,則也并不排除選擇乙。(詳見黃有光,2008年的有關論述)
對于社會的選擇,把上述甲與乙維持不變,只加上“社會上每個人都有”,則極大化幸福要求選擇乙,而顯然地,選擇甲才是合理的。若然,應該強調包括幸福的快樂,雖然并不排除對幸福的重視。
如果采用筆者的定義,幸福與快樂是相同的。如果采用徐老的定義,幸福與快樂是不同的;但終極而言,我們應該極大化包括幸福的快樂,而不是排除快樂,只極大化幸福。
不久前讀了徐景安于2011年11月14日對“以幸福為核心理念:推進中國新文化建設”問題的答記者問。徐景安說:“人怎么會產生幸福感?它會無緣無故產生嗎?不會。這是重要需求獲得滿足而產生的愉悅感。當餓的時候,有饅頭吃是重要需求的滿足。對三餐無憂的人,吃饅頭就不是重要需求了。幸福是需求客觀性與感受主觀性的統一。”
上述對幸福的討論顯然在幸福中包括肉體上的快樂,也顯示動物能夠有幸福感。狗餓的時候,有肉骨頭吃是重要需求的滿足,會有幸福感。
徐景安也說:“幸福來源于物質幸福、情感幸福、精神幸福,鼓勵人們在追求物質幸福的同時,重視情感幸福與精神幸福。”
既然幸福包括物質幸福,當然包括肚餓吃東西的肉體上的快樂,狗等動物當然也有這種幸福感。
其實,“重要需求獲得滿足”,只是通常能夠產生愉悅感的有利條件,不是愉悅感、快樂、或幸福感的充分條件,也不是必要條件。當你肚子很餓時,填飽肚子是重要需求。不過,如果我只讓你吃非常苦澀腥的食物,你為了不餓死,勉強吃了,但感受很不好,苦澀腥的負感受超額抵消吃飽的正感受,沒有正的凈愉悅感。因此,重要需求獲得滿足不是快樂的充分條件。假設有位學者,自認為并沒有達到獲得諾貝爾獎的水平,對諾貝爾獎沒有需求。然而,如果她意外獲得諾貝爾獎,還是會有很大的幸福感的。因此,重要需求獲得滿足不是快樂或幸福的必要條件。
還有,幸福感不會無緣無故產生嗎?很多人認為黃有光經常會無緣無故忽然大笑。(雖然這是真的,但也是半開玩笑的)
快樂研究的一些政策涵義
本節著重談對公共政策的涵義,關于快樂研究對個人快樂的涵義(個人如何增加快樂),及科技發展如何能百倍地提高我們的快樂水平等問題。
快樂研究的一個相當一致的結論是,在達到小康水平之后,經濟水平的繼續提高并不能增加快樂。對個人而言,比較有錢的人的平均快樂水平,比一般的與比較窮的人略為高一些,但有許多比金錢更重要的因素。(詳見Diener等,2010)然而,對全社會而言,人均收入水平的數倍增加,并不能顯著地增加快樂。這是為什么呢?
第一,溫飽之后,在很大的程度上,影響一個人的快樂水平的是相對收入或消費。有錢的人比較快樂,因為他們的收入比其他人高。然而,當全社會的收入水平隨經濟增長而增加時,不但你自己的收入增加了,其他人的收入也增加了。因此,快樂水平沒有顯著增加。由于相對收入效應,一個人(尤其是富人)的收入或消費的增加,減低其他人的快樂,可以說有外部成本,應該征稅。傳統經濟學分析強調稅收的反激勵效應(打擊人們的生產積極性),認為稅收有扭曲作用或超額負擔。其實,一般的收入稅或消費稅,即使單單從效率上而言,而不考慮平等,實際上有糾正作用,超額負擔是負數(小于零)。
涵義一:由于相對收入效應,征收收入或消費稅,尤其是對富人有糾正作用。
第二,對人們生存環境的破壞,隨著生產與消費之增長而增加。這在中國的情形,尤其明顯。世界銀行的Easterly(1999)曾經分析得出,隨著經濟增長,約有比50%多一些的生活質量指標上升,但也約有比50%少一些的生活質量指標下降。這也部分解釋為何經濟增長沒有顯著增加快樂。另一方面,隨著時間與科技的進展,多數生活質量指標明顯上升。
涵義二:由于對環境的破壞,征收收入或消費稅,有糾正作用。
第三,像松鼠與老鼠等動物一樣,人類也有累積的本能。加上人際競爭與無所不在的商業廣告的影響,人們犧牲對健康、快樂、甚至生命更重要的東西,拼命賺錢。這對競爭性極強、物質主義橫行的東亞各國,尤其是中國,更加明顯。像茅于軾所說,“用危害道德的方式賺錢,用危害健康的方式花錢”,長期快樂如何能明顯增加呢?
根據Gruber&Mullainathan(2005)的研究,對香煙征稅,增加抽煙者的快樂,因為少抽煙實際上對他們好。這也和傳統經濟學分析背道而馳。(也參見Lucas,2012的反面論述)
涵義三:由于過度的物質主義,征收收入或消費稅,有糾正作用。
在大多數國家,上述三項,每項都應該征收至少20%的稅。合起來,征收40%~50%的稅,都還是屬于糾正性范圍,根本不須要擔心稅收的超額負擔。可能有人認為筆者估計太高。其實,根據Blanchflower&Oswald(2004)的研究,人們認為相對收入至少有絕對收入一半的重要性。因此,單單根據相對收入作用,就應該征收約33%的稅。
當然,稅收的收入應該用在對人民的長期快樂有利的方面,包括環保、科技、教育、公共衛生、廣義的基礎設施等,而不是被貪污與浪費,才能夠真正有效率。但這些問題超越本文的討論范圍。(詳見Ng,2003或黃有光,2008)
近年的研究顯示,相對收入對快樂的影響,不但對有錢人來說是很重要的,甚至對相對貧窮的中國與印度鄉村農民,也比絕對收入更加重要(Luttmer2005,Knight等2009,Knight&Gunatilaka2010,Linssen等2011, Guillen-Royo 2011,Fontaine & Yamada 2012)。有些數據甚至顯示,“所有作用都是相對收入作用”(Layard等于2010年所做的結論)。古人說,不患貧而患不均,至少是在溫飽之后,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關于環境破壞的嚴重性,更加明顯。很多環境科學家認為人類只剩下二三十年的時間來避免因環境破壞而滅亡。單單溫室效應或全球暖化這一問題,若沒有及時處理,就可能要人類的命。
2006年前,不但英國皇家學會宣稱,人類經濟活動造成全球暖化已經是和地心吸力與進化論同樣肯定的事實,連商界名人也出來強調環保的重要。那些到現在還不承認空氣污染、全球暖化等環保問題的嚴重性的經濟學者,不是躲在象牙塔,就是被其極端右翼的、認為市場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意識形態所迷惑。(詳見黃有光,2007)
其實,有效率地處理污染問題,對其征收等于污染的邊際危害的稅,并不會造成很大的經濟負擔。如果只是工廠甲必須付污染稅,則其負擔很重,可能必須關門。如果只是中國必須減少污染,其成本也可能很大。不過,如果全世界各國對所有造成大量污染的生產與消費,都必須付污染稅,則市場會通過價格的調整,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調整,使絕大多數工廠還能繼續生產,而且污染稅的收入,可以用來進行環保投資,人們可以換去做環保的工作。
有人認為根據污染的邊際危害的稅應該是多少,很難估計。筆者(Ng,2004)論證,至少應該征收等于減少污染的邊際成本的稅,而這比較容易估計。
當你在挨餓時,可能會說寧愿毒死,不愿餓死。已經溫飽了,應該更加重視,就長期與全社會而言,對快樂更加重要的是環保、科技、衛生保健、教育等問題。
正像我們現在的人均實際收入是一百年前的七、八倍,如果地球的生態環境沒有被我們過度破壞,一百年后,我們的子孫的人均實際收入,也會是我們現在的五、六倍(如果以環保負責的速度發展)或七、八倍(如果以環保不負責的速度發展,而假定沒有中途滅亡或至少發展停頓)。在此筆者提出一個問題:讀者們,你們是愿意子孫們有安全健康的生存環境,但是只有我們五、六倍的人均實際收入,還是會選擇達到七、八倍的收入,而冒著使人類滅亡,子孫們根本沒有機會出生的危險呢?
輕度的家長主義(Soft paternalism)
如果根據傳統經濟學的簡單分析,人們是有充分理性的,也具有有關的知識,所做出的選擇,是在有關約束條件下,把其效用極大化的。除非有像壟斷力量、外部成本(如污染)等造成市場失誤的因素,市場的自動調節,“如水之向下”,自然會使經濟達到帕累托最優(除非讓一些人的情況變壞,不能讓任何人的情況變好的效率最高的情形)。因此,除了可能需要適當的財富重分配,政府完全不需要干預人們的選擇。
不過,根據心理學與行為經濟學的研究,人們的決策既受信息不充分的影響,又有很大的不理性的成分。(詳見Kahneman,2011)若然,是否應該讓政府來實行中央計劃,才能夠達到最優呢?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在這方面的經驗,已經證實這多數會更加糟糕。市場有失誤,中央計劃未必更好。我們應該避免傳說中類似于羅馬皇帝的失誤。這個傳說中的羅馬皇帝,要選出全國最好的歌手,在全國比賽,得出最后兩個最好的歌手后,要通過殿試,由皇帝親自御定哪一位應該獲獎。皇帝聽完第一位歌手唱完后,馬上把獎牌賜給還沒有試唱的第二位歌手。怎么知道第二位歌手(中央計劃/政府干預)不是更加糟糕呢?
像世界上許多事情一樣,在市場與政府干預之間的選擇,最好的不是全黑,也不是全白,而是適度的黑白相間,中庸之道。市場調節能夠大致有效,沒有重大失誤的地方(多數情形),由市場調節;市場有重大失誤的地方,例如環境的嚴重破壞,食品安全問題等,必須由政府補充。政府如果還是做得不好,則必須設法改進,總不能夠等死!除了極端右翼的無政府主義者,絕大多數經濟學者都會同意這種中庸之道。然而,對于一些理性不足的選擇,政府是否應該干預,則還沒有很一致的看法。筆者的看法依然是中庸之道。
首先,政府在這方面的干預,不能夠太細,不可以對人們指手畫腳。這不但會增加行政成本,更加重要的是影響人們的自由。自由對快樂有很大的正作用。即使人們的決策是錯的,政府的決策是對的,政府也不可以在私人決策范圍取代私人。即使短期看來是改進的,對自由的影響,長期而言,多數會是災難性的。經過反右、大躍進與文化革命這三大災難洗禮的中國人民,對自由的重要性應該有更加深刻的體會。
當人們的決策有相當程度的失誤,后果又相當嚴重時,政府雖然還是應該避免使用粗暴的手,但卻可以考慮采取“輕推”(nudge)的方法。Thaler & Sunstein于2008/2009年發表的書,就以Nudge為名,論述如何用輕度的家長主義或符合自由的家長主義(Libertarian paternalism)的方法,鼓勵人們作出更加適合的決策。其中一項建議是要求廠商給消費者的合同必須簡單與容易理解。現在的絕大多數合同,不但長篇細字,內容也很難讀通,使多數消費者(包括筆者在內)連看也不看。(參見Sunstein,2011)
一項在西方國家很成功的輕推政策,在中國可能不需要,但可以參考其原則,用在其他方面。多數西方國家,人民的儲蓄率很低,多數國家實行以低稅率鼓勵(甚至用強制要求)人們在養老金賬戶存錢的政策。美國國會的極右的保守派與左傾的自由派(liberals)聯手通過“明天儲蓄多一些”(save more tomorrow)的輕推政策。這方案不要求人們馬上增加儲蓄,因為這樣人們比較難接受。它要求當將來薪水增加時,自動開始增加儲蓄。由于不需要馬上減少消費,人們比較能夠接受。
除了美國,包括英國與南韓在內的一些國家都接受了輕度家長主義的政策。英國政府成立了一個小組,應用行為科學來幫助政府。這小組的正式名稱是“行為洞見隊”,但人們稱其“輕推隊”。Richard Thaler教授是這“輕推隊”的顧問。
許多國家讓人們在駕車執照上選擇關于意外死亡時人體器官的捐贈。有些國家是采用“選擇參加”的方式,一個人只有簽名填寫愿意捐贈,意外死亡后才可以采用其器官;有些國家是采用“選擇不參加”的方式,一個人如果沒有簽名填寫不愿意捐贈,意外死亡后就可以采用其器官。換句話說,有些國家的默認選項是不捐贈;有些國家的默認選項是捐贈。人們完全可以選擇任何一個。然而,絕大多數人是根據默認選項,很少人選擇填寫與默認選項相反的選擇。因此,類似文化的國家,由于默認選項的不同,愿意捐贈的百分比差別很大,例如在瑞典是86%,奧地利是接近100%,而在德國是12%,丹麥是4%。(詳見Johnson&Goldstein,2003)
絕大多數人并不強烈反對捐贈,但也很少人強烈要求捐贈。因此就隨默認選項,沒有采取填寫與默認選項不同的選擇。不過,所有國家都很缺乏可以救人命的器官。因此,絕對應該把默認選項定為捐贈,以增加人體器官的供應。為何很多國家還沒有這么做,這是筆者很不理解的。只要有足夠的保障,不讓人還沒有死,就盜取器官,捐贈肯定是正確的選項。既然已經死了,能夠救活他人,不是很好嗎?在澳大利亞并沒有在駕車執照上讓人們選擇,而其默認選項是不捐贈。筆者雖然強烈支持捐贈,但由于時間、拖延等原因,也等到約十多年前才做了器官捐贈注冊。其實,不必在駕車執照上填寫,所有國家應該采用所有人的默認選項都是捐贈。你不愿意,可以填寫選擇退出或不捐贈。你沒有填寫,就假定同意。這肯定是正確的做法。
不只是在器官的捐贈上,在其他所有選項上,如果有一個是專家與具有相關知識的多數人都同意是正確的選項,都應該在所有情形,盡量讓它們成為默認選項。例如,全谷面包比白面包健康,衛生部應該規定,除非條件真的不允許,在公共食堂,尤其是學校食堂,應該供應全谷面包,并且把全谷面包列為默認選項。人們如果只是說要買面包,必須提供全谷面包,明言要白面包,才可以提供白面包。
中國的改革開放與經濟發展,已經到了必須以對提高人民的快樂的重視,替代對經濟方面的數量的重視的時刻。快樂問題牽涉很多因素。筆者提出的“環保負責的快樂國家指數”只是作為國家成功的主要指標。希望中國不但能夠繼續發展,人民也能夠提高快樂水平。關于改革與發展方向與話語的討論,只是繼續向前走的第一步。
參考文獻
于席正、江莉莉(2012):“試論消費決策與幸福:動機—精神力場—行為假說”,《經濟學季刊》,11(3):969-96。
黃有光(2007):“跳下地獄?走上天堂?人類面臨滅亡與極樂十字路口”,《經濟學家茶座》,元月,第4~7頁。
黃有光(2008):《黃有光自選集》,“當代華人經濟學家文庫”之一,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
黃有光(2010):《從綜觀經濟學到生物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黃有光(2011):《宇宙是怎樣來的?》,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黃有光(2012):“道德水平低下的成因與對策”,《經濟學家茶座》,第二輯。
黃有光(2013):《快樂之道:個人與社會如何增加快樂?》,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BLANCHFLOWER, David G. & OSWALD, Andrew J. (2004), "Well-being over 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8(7-8): 1359-86.
BORGHSI, Simone & VERCELLI, Alessandro (2012),"Happiness and health",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26(2): 203-33.
DIENER, Ed, HELLIWELL, John F. & KAHNEMAN, Daniel, eds. (2010),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ell-Be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ASTERLY, William (1999), "Life during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4(3): 239-276.
FONTAINE, Xavier & YAMADA,Katsunori (2012), Economic Comparison and Group Identity: Lessons from India, hal-00711212, version 2.
GRUBER, J. & MULLAINATHAN, S. (2005), "Do Cigarette Taxes Make Smokers Happier?", Adv. Econ. Anal. Policy, 5:1-43.
GUILLEN-ROYO, Monica (2011), "Reference group consumption and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poor in Peru",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59-272.
JOHNSON, E. & GOLDSTEIN, D. (2003), "Do defaults save lives? ", Science, 302:1338-9.
KAHNEMAN, Daniel (2011), Thinking, Fast and Slow.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and Giroux.
KNIGHT, John, SONG, Lina & GUNATILAKA, Ramani (2009),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rural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4): 635-49.
LAYARD, Richard, MAYRAZ, G. & NICKELL, S. (2010), "Does Relative Income Matter? Are the Critics Right?", In Diener, et al. 2010, pp.166-216.
Rik, Luuk&Gerbert(2011),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Rural India: The Curse of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01(1): 57-72.
LUCAS, Gary, Jr. (2012), "Saving smokers from themselves: The paternalistic use of cigarette taxes",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Law Review, Vol. 80.
LUTTMER, Erzo F. P. (2005), "Neighbors as negatives: Relative earnings and well-be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0(3):963-1002.
NG, Yew-Kwang (1995), "Towards welfare biology: Evolutionary economics of animal consciousness and suffering", Biology & Philosophy, 10(3):255-285.
NG, Yew-Kwang (2002), "The East-Asian happiness gap",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7(1):51-63.
NG, Yew-Kwang (2003), "From preference to happiness:Towards a more complete welfare economics", 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 20:307-50.
NG,Yew-Kwang (2004), "Optimal environmental charges/taxes: Easy to estimate and surplus-yielding",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8(4):395-408.
NG,Yew-Kwang(2008),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happy nation index",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8, 85:425-446.
OISHI,Shigehiro (2010)," Culture and well-being: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Diener, et al.(2010).
SUNSTEIN, Cass B. (2011)," Empirically informed regul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78(4): 1349-1429.
THALER, Richard H. & SUNSTEIN, Cass R.(2009)(updated edition), 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 New York: Penguin.
VEENHOVEN,R.(1996),"Happy life-expectancy: a comprehensive measure of quality-of-life in Nation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39,1-58.
VEENHOVEN, R. (2005), "Apparent quality-of-life in nations: how long and happy people liv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71(1-3),61-86.
責 編∕楊昀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