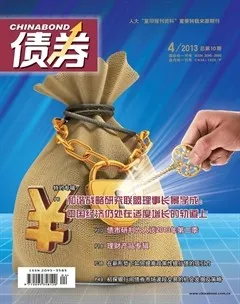尋找債市的核心驅動變量


摘要:本文對過去十年債市走勢進行回顧和總結后發現,通脹而非經濟增長是影響債市走勢更為核心的因素。展望未來十年經濟基本面進行分析后,筆者認為未來經濟增長或替代通脹,成為債市的核心驅動變量,未來長期看債市機會大于風險,加大配置仍是主題。
關鍵詞:核心驅動變量 經濟增長 通貨膨脹
影響過去十年債市走勢最為核心的驅動變量——通貨膨脹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影響債市走勢的關鍵因素無非有三大方面:一是長期方面,看債市供給層面;二是中長及中期方面,看需求層面,即經濟基本面;三是短期方面,看貨幣政策實施及資金面供需層面。其中,經濟基本面是最核心的影響因素,不管是供給層面,還是貨幣層面,最終都是圍繞經濟基本面演變的。而且經濟基本面對債券市場的影響也更直接、更明顯,尤其是在“經濟增長+通脹”核心驅動因素對債市走勢的影響分析中,百試不爽。
從某種意義上說,經濟基本面是影響債券市場的最根本、最關鍵的因子(如圖1所示)。債市走勢基本與經濟基本面保持著一一對應的影響關系,雖有經濟基本面與債市相脫離的情形發生,但這一點可以解釋為政策面的滯后效應所致,或者說政府行為與市場預期出現了偏差,從而對經濟形勢產生了負面影響,但這種影響是短期的,不會改變債市的整體運行軌跡。
從市場的運行周期來看,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2002-2004年,經濟基本面即經濟增長與通脹共同主導階段,乘著加入WTO的春風,我國經濟增長迅速,而且世界經濟也在互聯網等IT技術因素的推動下,進入高速增長期,社會需求不斷得到夯實,進而帶動通脹中樞大幅上移,致使債市收益率中樞顯著上移;第二,2004-2005年,背離階段,此時通脹下行,經濟下移,但收益率繼續上移,這與政策的滯后效應有關(經濟體自身會對抑制經濟過熱的緊縮政策產生部分“免疫”效應),背離持續的時間和空間相對較小;第三,通脹主導階段,自2005年以來,債市走勢與通脹走勢吻合程度最高,就算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全面爆發的特殊時期,這種“如影隨形”的關系也得到了市場的印證。
沿著上述思路繼續向下探討,縱觀十年來的債券市場走勢,不難發現,相比經濟增長,通脹對債券市場的影響更為明顯,這也很好地解釋了當前市場基本都憑借對通脹的走勢來判斷債市行情的現象。從圖1至圖3中可以發現,相比基本面變化,債市行情較基本面變化平均滯后3-6個月。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債市對經濟基本面的反應越來越敏感,尤其是2011年以來,債市的滯后周期平均已在1-2個月之間。而從目前的市場行情來看,債市基本與經濟形勢保持同步,甚至可以提前反應出經濟基本面的部分特點。筆者認為,隨著利率市場化的進一步深化,市場預期的有效性大大加強,這種市場預期的偏差效應正在逐步削弱。
但如果將考慮問題的角度拉到更精細的周期層面,債市也在尋找收益率與基本面之間的平衡。以2012年的行情為例,債券市場呈現出先抑后揚再抑的態勢,分階段來看,第一階段是通脹高于預期,收益率中樞上揚;第二階段是經濟增長低于預期,通脹低于預期,政策面配合,收益率中樞下移;第三階段是經濟增長超預期主導行情。由此,債市收益率中樞的波動主要是在修正預期偏差,是對預期透支、未兌現的一種再消化。
沿著上述探討邏輯,在承認上述猜測的前提下,反觀近十年債市走勢,為什么是通脹而非經濟增長是影響債市更為直接的因素?是否可以考慮,擾動通脹的因素太多,通脹預期偏差過大,而2002年以來,經濟增長一直保持著8%-10%的高速增長,預期偏差幅度不大,尤其是政策面對經濟增長的保障較為可靠(基建+房地產對經濟增長推動更為有效與簡單),而對通脹的控制力度較弱,政策面滯后效應的負面沖擊還很強,致使通脹對債市收益率的影響更為凸顯。
換一個角度,從“債市收益率”概念反映的經濟學意義來看,這種影響似乎更加容易被理解。經濟增長與通脹對債市收益率的影響,可形象地體現在對收益率中樞運行區間上限與下限的影響上。從過去十年的經濟增長率來看,經濟保持高增長的黃金態勢(基本維持在9%以上),市場對經濟增長預期偏差影響的邊際效應不顯著,而通脹波動范圍較大,其對債市收益率中樞運行區間下限的影響顯著是不言而喻的。通常,債市收益率中樞對上限的敏感性相對較弱,而對下限的敏感性更強,因此通脹對債市收益率的影響也就更為顯著。
債市核心驅動變量由通脹向經濟增長轉移
以當下作為界點,將過去十年與未來十年的經濟基本面特點作一比較,或者說將過去的預期修正與未來的預期偏差作對比:過去十年,相比黃金態勢的經濟高速增長,通脹預期的不斷修正是擾動債市的最核心因素;而未來十年,結構轉型引發的經濟潛在增長率中樞下行似乎更難預測,其產生的預期偏差應該更為顯著,而結構轉型期,政府繼續優化資源配置,央行貨幣政策不斷完善,通脹壓力不大,超預期風險或將愈來愈小。
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精神,產業升級與結構轉型被推到了更高的政策層面,以“城鎮化”為主題的經濟改革正在重塑國內經濟增長模式,而且收入分配深化改革、城鎮化推進、培育內需新增長點等有關國計民生的問題再次被推到幕前,“沒有水分”的概念范疇要求國內經濟消除不利的泡沫因素,甚至不惜犧牲經濟增長速度。
(一)經濟增長下移有超預期的風險
在國內財政擴張的刺激下,2013年經濟增長反彈基本沒有懸念,這其中有基建投資增長、房地產市場回暖以及外貿增長等方面的因素推動,更有“城鎮化”的概念推動,但在國內經濟缺乏內生增長性的背景下,經濟就算恢復高增長,還是產能拉動產能的過程,長此以往,勢必形成資產泡沫,甚至發生經濟危機。所以,中央提出“沒有水分”的經濟增長,筆者相信政府作為,城鎮化只是作為緩釋經濟下滑風險的重要工具與載體,而不是再以GDP為綱的經濟發展理念,按照經濟學的產出理論,未來的經濟發展模式一定是以經濟增長下移來換取產業升級與結構轉型,為經濟體的健康發展夯實基礎。
如果上述猜測正確,那么財政擴張一定是有序的,不會像以往那樣全面鋪開,始終要淘汰一些高耗能的產業,要削除風險愈來愈大的資產泡沫。考慮到政策面在增長與轉型的平衡選擇上,會有一些時點風險,經濟增長下移的超預期概率較大,也許2013年經濟增長會有8%以上的速度,但2014、2015年經濟增長的下移幅度可能將大大出乎市場的預料。如果再保守一點來看,一旦政府投資政策拉動經濟增長的邊際有效性出現回落,那么今年四季度,甚至下半年,可能重新燃起市場對經濟下滑的預期。同時考慮到資產泡沫的風險敞口問題,政府已經不會再有像以往那種大規模投資的沖動,而且還有收緊的可能性,所以,可預見的未來,經濟增長下移幅度超預期要比上移超預期的概率更大。
此外,隨著利率市場化的不斷深化,央行穩健貨幣政策的主題不會改變,雖然央行逆回購政策以及SOL政策的逐步落實,有意壓低市場利率,但像以往那樣短周期內大幅度降息、降準的政策不會再出臺了。因此,央行政策出臺只是在完善利率制度(利率雙軌制向銀行間市場利率單軌靠攏),市場只能期待中性偏寬松的市場利率狀態,不要過度期盼央行政策的大幅放松,或者市場利率的大幅下降,中性偏寬松應是最理想的調控狀態,這也對經濟增長的單邊上移形成較大壓力。
(二)通脹漲幅可控,超預期概率偏小
在經濟潛在增長率中樞下移的前提下,通脹并不具備大幅抬升的條件,而且政府一直在強調要加大供給,改善物流,因此筆者認為,只要不出現極端的天氣情況,或者其他不可抗力的因素,物價不會出現明顯上漲。同時,央行數據顯示,一年多以來,貨幣供給M1始終在個位數徘徊,說明企業財務賬面現金流量不足,生產端經濟屬性異常不活躍,也從側面說明社會需求風險很大,這與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宏觀經濟運行數據顯示的情況基本一致。所以,供給端在增強,需求端在減弱,通脹漲幅基本可控,超預期概率愈來愈小(一年多以來,通脹基本在預期之內,而且低于預期次數明顯偏多)。
值得注意的是,最大的風險在于輸入性通脹壓力。近期外圍出現量化比拼的貨幣環境,歐、美、日三大經濟體不斷放大貨幣供給,容易引發風險偏好升溫,特別是對新興市場國家會造成不可預期的通脹壓力(變相承擔世界經濟衰退成本),如我國外匯占款已經出現了明顯回升。但這種不可預期甚至不可控的輸入性通脹對我國造成的沖擊應該不具備可持續性,除了政策層面會有防范的舉措外,美國、日本此輪的救助方案依然有其局限性,不如前幾次的量化寬松政策沖擊那么大,整體對國內通脹的負面影響也屬可控范圍之內。
整體來看,經濟增長中樞下移超預期的可能性更大,就算用投資可以“砸出”一定的GDP增長,但也不具備可持續性。如果政策按照“健康城鎮化”的概念模式推進的話,2013年經濟增長將在8%附近(如果拋除政府投資以及其他形式推動的“有水分”的經濟增長,國內經濟的潛在增長率中樞不會高于7%),而2014、2015年經濟增長勢必要沿著下移的趨勢運行,結構轉型力度大一些,超預期下移的幅度就會大一些。而且從政府態度來看,中央表現出可以容忍經濟增長出現一定幅度的下移,如2012、2013年經濟增長的政策目標均為7.5%,以后的政策目標或將下移至7.0%甚至以下,而這是市場在過去十年間沒有經歷過的,市場難免會出現或多或少的預期偏差,就像前期對通脹產生的預期偏差一樣(主要對社會需求、經濟結構缺乏深度認知)。而且這種新的預期偏差剛剛開始,有增大的趨勢(市場由于慣性思維,往往不愿意接受新的經濟周期與運行軌跡,需要相當時間的磨合期),需要市場不斷反復修正與完善。
根據上述解釋,中長周期層面,產業升級與結構轉型成為周期性主題,需求面累積風險持續放大,政策邊際效應持續下降,經濟潛在增長率中樞下移不可避免,而通脹因素弱化顯現,由此可推斷,影響債市的最核心因素正在向經濟增長層面過渡,也就是說,由通脹主導的債市行情將讓位于以經濟增長為核心驅動因素的行情。
未來債市機會大于風險,加大配置仍是主題
立足當下,“潮頭再立”或許能更恰當地形容當前的債市態勢,配置盤應順勢而為,果斷建倉、加倉。
結合成熟債券市場的運行態勢(見圖4)來看,我國債市收益率中樞還有更大的下降空間,這主要因為:一是最大的預期偏差——經濟增長下移推動;二是利率市場化政策框架推動。當前,利率市場化還處于初級階段,若要為結構轉型周期提供更好的政策環境,必須要降低融資成本,為產業升級提供有力支持。嚴格來說,在結構轉型周期的關鍵期內,經濟體需要債券市場的支持,以度過攻堅期、困難期,完成空前的產業升級,反過來說也成立。如果債券市場不經歷一個大的牛市周期,承擔起必要的改革成本,那么經濟也不會好起來。
因此,從經濟周期與資本市場的角度來看,債市還會在不久的將來迎來新的春天,即使短期的經濟回暖加劇調整行情,但調整的空間與時間非常有限,充其量是未來牛市行情的一個插曲、一種鋪墊。反觀債市盤面,2012年四季度以來,行情出現戲劇性逆轉,收益率曲線由“扁平化上移”轉為“陡峭化下移”,這主要是受到資金面的影響,但需要注意的是,中長久期利率品的收益率中樞不上不下,表現異常穩定。筆者認為,短周期層面經濟反彈與長周期層面的經濟潛在增長率下移相互交織,造成市場缺乏趨勢性方向;近期股市的上揚并未對債市產生明顯的負面沖擊,反過來說明長周期經濟基本面并不支持債市收益率的上漲,致使債市面對經濟基本面的全面改善,愈發走出超預期的獨立行情,也說明未來幾年經濟增長下移的預期正在得到不斷修正,預期偏差正在營造更大的利多氛圍,為配置盤創造了較理想的投資時點。
作者單位:哈爾濱銀行
責任編輯:羅邦敏 夏宇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