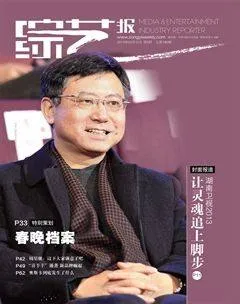李安的成色
伴隨著中國元素在世界文藝的日漸流行,歐美人更愿意從歸化他們游戲規則的亞洲作品,而不是純正的內地或港臺作品里,指認他們價值方面的選擇。
李安憑借他的商業寓言《少年Pi的奇幻漂流》,力挫斯皮爾伯格的歷史大悶片《林肯傳》,在文化圈和傳媒圈引發一片聒噪。熱情的華語片支持者與從業者們,似乎一下子在暗夜的海上,見到了久違的航燈。不過,實質或許與他們的理解有些偏差。
《少年Pi》的拍攝成本據說是1.2億美元,如果按照正常的電影盈利公式,這部片子票房需到3.6億美元才算賺錢。由于還要角逐奧斯卡,公關費用、加上各地的放映宣傳費用還要花上一些,估計真正盈利需要賣到4億美元上下。《少年Pi》北美票房一般,過億而已;但北美市場以外的票房卻達到4億多美元。全球凈賺正邁向兩億美元,談不上什么大勝,但賺錢總歸比賠好,向來,李安的電影能上2億票房就算好成績了,《少年Pi》算是創了一個新高。
有人說,《少年Pi》的成功,可能會使美國影商日后更加重視中國市場。這話有些遲鈍。其實早在《少年Pi》做投資收益預測時,電影公司就認為該片的亞洲票房會高于北美。說美國人不重視中國市場,未必。只是美國電影目前還不知道怎么討好中國觀眾。早先從斯皮爾伯格來華拍片用中國演員開始,一直到后來用周潤發和章子怡,中國元素一般很難在美國片中占據主流位置,這一直是構成美國電影在中國市場地位起伏的因素。目前除了《功夫熊貓》,美國人暫時還沒找到有效的解決辦法。
不管是原來的2億美元票房上下,還是今天的突破5億美元,李安的市場成績都只是小有盈余,與輝煌無干。他這樣的導演在美國,或許會被視為來自東方的文藝范兒導演。但究其影片“文藝”的純度,恐怕又比拍《杯酒人生》的亞歷山大·佩內、拍《迷失東京》的索尼婭·科波拉要遜色不少。甚至比拍美國版《無間道》時的馬丁·斯科塞斯都要遠遠不及。當年《臥虎藏龍》雖然拿的是專門獎勵文藝片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可《臥》除了拍點竹子和山頂的云霧,實在看不出它跟《竊聽風暴》《美麗人生》《莫斯科不相信眼淚》《天堂電影院》《芳妮和亞歷山大》有什么內在的精神與人文牽連。《臥》片放到港臺,不會被承認為合格的功夫片,當然更不會被認為是文藝片,它的奧斯卡緣分里,美國人對中國的誤讀和李安的幸運,占了很大關系。
同理,無論是沒爭議的《斷背山》,還是爭議性的《色·戒》,都很難說是標準意義上的文藝片。倒更像是一個經過了商業片洗禮的導演,所制作的美或欲的銀幕甜點。它們中有陰柔的顛覆與挑戰,與李安的早期影片在柔和度上一脈相承,卻又多了不少對曖昧和催眠觀眾的執迷。如果說執迷也算是“文藝性”的一種,那我就沒什么好說的了。只能說李安實在太幸運,畢竟希區柯克在捍衛自己風格時更執迷,卻僅僅拿過一個安慰性質的奧斯卡終身成就獎。
伴隨著中國元素在世界文藝的日漸流行,歐美人更愿意從歸化他們游戲規則的亞洲作品,而不是純正的內地或港臺作品里,指認他們價值方面的選擇。李安在國際聲譽上的高成功率(恐怕是黑澤明以后的第一人),得益于他風格和性格上的討巧,也得益于白人主流文化對有色人種文化的選用。這是一個基本事實。只要模仿者不太多,對華語電影本身算不上傷害。不過,怕就怕新一代影人修為不深,文藝范兒再未泯,循著李氏成功曲線一路復制下去,擋風玻璃上難免又要撞爛一堆蛾子。雖說每個人都難逃宿命,但大家好賴也是性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