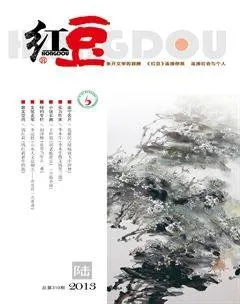山水人文總相關
與外地朋友相聚,大家說得多的往往是廣西的山水。如北海的銀灘,巴馬的命河,欽州的三娘灣,防城港的海港,南寧的綠等,至于“桂林山水甲天下,陽朔山水甲桂林”,那就更不用說了。我們這代人上小學時就熟悉賀敬之的《桂林山水歌》,如畫似夢的桂林山水早已成為令人神往的所在。而電影《劉三姐》盡管融入了階級斗爭的意識形態色彩,但也以視覺方式將桂林山水的美麗畫面深深刻印在人們心中。
這說明在很多人印象中,美麗山水及良好自然生態是八桂大地的顯著特色,對廣西的人文歷史與人文環境卻還關注不多。對于人類的生存,自然環境當然重要,人文環境也同樣重要。沒有良好的人文環境,即使天天面對美麗山水,也會覺得缺了精神寄托。
1935年新年伊始,胡適曾來南國一游。后來寫了篇《南游雜記》,包括《廣州》和《廣西》二則。前者寫的是作者在廣州幾天的險惡遭遇,后者描述了作者在廣西十多天的愉快逗留。也就是說胡博士這次南游,在廣州與廣西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兩重天。胡博士這次反差鮮明的冷暖遭遇,恰恰與當時兩地的人文狀況有關。文章非常詳細,將兩地的冷暖遭遇過程講述得一清二楚。雖是一種個人際遇的歷史記載,今天讀來仍然頗有啟示意義。
先看胡適《廣州》中所描述的險惡遭遇。
1935年1月9日,接受了香港大學博士學位的胡適從香港到廣州。按事先計劃,胡博士要去中山大學、嶺南大學、第一女子中學、青年會、歐美同學會等多處演講。四天時間有十次演講,可謂要馬不停蹄地忙碌了。廣州青年學生知胡適要來演講,都非常興奮。廣州青年會提前賣聽講券,一個下午就賣出二千多張。中山大學更為重視,專門發布了全校停課兩天的通知,以使更多學生能聽胡適演講。
不料風云突變。不僅所有原定講演都泡湯,胡適還差點被“徑付執憲”。
廣州是座有民主革命傳統的城市。如有辛亥革命前奏的黃花崗起義,如是國民革命軍北伐的出發地。但胡適卻是在一個錯誤的時間到來。當時廣東軍政正大力提倡尊孔讀經,胡適恰恰在香港華僑教育會演講中對廣東文化保留“祖宗遺物”表示了非議,當然也反對借讀經復古的做法。因此胡適到達廣州前一天即1月8日下午,廣州召開的西南政務會議上,廣東要員們對胡適的香港演說就非常不滿,已決定抵制胡適的廣州之行。
胡適的廣州安排當然在這之前。關于演講題目、時間順序、單位協調等具體事項,都是由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吳康負責。胡適1月4日給吳康的一封回函中,就說到了委托吳康作自己廣州之行的“廣州總指揮”的事。吳康顯然盡了力,因此才有了大張旗鼓的安排。
但西南政務會議效果很快顯示。遑論講演,胡適剛到廣州就接到吳康一信,信中轉達了中大校長鄒魯的如此意見:“此間黨部對先生在港言論不滿,擬勸先生今日快車離省,暫勿演講,以免發生糾紛。”剛踏上廣州就遭遇這種事情,突如其來的大煞風景,當然讓胡適不快。但胡適是明白人,能夠體諒中大校方的難處。雖然不能講演,但胡適不想匆匆走掉。因為這是他第一次來廣州,干脆就借此在廣州觀光幾天。
這時陪同者問胡適是否想看望一下廣州當局,胡適與廣東省政府主席林云陔為舊交,于是就去看望林。兩人交談后,經林云陔提議,胡適又去看望廣東省總司令陳濟棠。陳濟棠原本有事(正準備出去給剿匪的軍隊訓話),聽胡適要來,特意推遲訓話時間,要同胡適面對面談談尊孔讀經事。林云陔沒去,陪同胡適的只有廣東地方法院院長陳達材。
胡適開始并不清楚一介武夫的陳濟棠,正是當時廣東提倡尊孔讀經的核心人物。而陳濟棠對胡適在香港華僑教育會演講本來就有氣,結果談話一開始就有了火藥味。胡適與陳濟棠的交鋒雖然有點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但唇槍舌劍你來我往還是有多個回合。胡適告訴我們:談話約一個半鐘頭,兩人說話時間各占一半。雙方的主要觀點如下:
陳濟棠開口就對胡適直言不諱的宣稱:“讀經是我主張的,祀孔是我主張的,拜關岳也是我主張的。我有我的理由。”陳濟棠擺出的理由主要有兩點:一是“生產”,這生產建設可以大量用外國的科學、外國的機器,甚至不妨用外國工程師。二是“做人”。而如何做人,就必須回到中國古文化傳統,就應該走古代的圣賢之道,就應該提倡尊孔讀經。
陳關于“生產”與“做人”的區分,胡適謂之“二本”主張。因此胡適告訴陳濟棠:自己與伯南(陳濟棠字)先生的“二本”主張只有一點不同,就是不僅生產要用科學知識,做人同樣要科學知識。也就是兩者都要以科學知識為“一本”。胡適進一步說明,自己并不反對古代經典研究,但“我不能贊成一班不懂古書的人們假借經典來做復古的運動”。
胡適所說“一班不懂古書的人們”這句話,肯定刺傷了陳濟棠。因為陳濟棠不僅高聲大氣起來,而且斥責胡適:“你們都是忘本,難道我們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嗎?”
胡適回答:老祖宗當然有知道做人的,但大多老祖宗很多方面不能成為“做人”榜樣。如中國女人裹小腳,裹到把骨頭折斷,這種“全世界的野蠻民族都沒有的慘酷風俗”流行千年,很多大圣大賢(胡適舉了宋明理學代表人物)都沒抗議,這難道是做人的好榜樣?
胡適的舉例說明,導致陳濟棠一時瞠目結舌,無法反駁。當然是更生氣了。
從胡適關于雙方觀點的記載看,陳濟棠主張明顯還是循了“中學為本,西學為用”的洋務運動思想。這種“中體西用”的改良主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受到批判。而由于當時中國社會狀況,導致了新文化運動的激進主義,將傳統與現代、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截然對立,存在矯枉過正問題。胡適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倒并不偏激。同為五四新文化運動領導者,相比明顯激進的陳獨秀,胡適就較平穩,曾提出“整理國故”的著名觀點。
不過客觀看,陳濟棠提倡尊孔讀經也表現了對傳統文化的尊重。中國傳統文化畢竟有不少東西需要繼承。作為一介武夫也算難得。而他認為科學、民主之類的新文化新教育都是“亡國教育”,則當然是極端了。讀胡適記載我還有個感覺,雙方針鋒相對的激烈爭論,除文化觀念的明顯差異,還與談話氛圍緊張有關。胡適對陳濟棠的蠻橫態度就頗有不滿:“這種久握大權的人,從來沒有人敢對他們說一句逆耳之言,天天只聽得先意承志的阿諛諂媚,如何聽得進我的老實話呢?”胡適是個寬厚人,一般不對個人品性發微詞。不過胡適的不滿也涉及一個重要問題:如果對權力人物只是阿諛諂媚,確實容易形成難言真話的人文環境。
德高望重的胡大師不怕陳濟棠,不過針鋒相對卻帶來更糟糕的結果。很快中大文學院院長吳康又送來一信,這次就直接告訴胡適,中山大學的演講已經取消。吳康信中有此解釋:“鄒先生云:昨為黨部高級人員包圍,渠無法解釋。故中大演講只好布告作罷。”惹怒了陳濟棠的結果,不僅是中大演講作罷,其他多處的原定演講也全部被取消。
胡適撰文非常注意實證材料,讓事實說話,文中專門錄下中大布告,不妨照錄:
國立中山大學布告第七十九號
為布告事。前定本星期四五兩日下午請胡適演講。業經布告在案。現閱香港華字日報。胡適此次南來接受香港大學博士學位之后,在港華僑教育會所發表之言論,竟謂香港最高教育當局,也想改進中國的文化,又謂各位應該把他做成南方的文化中心。復謂廣東自古為中國的殖民地等語。此等言論,在中國國家立場言之,胡適為認人作父。在廣東人民地位言之,胡適竟以吾粵為生番蠻族。實失學者態度。應即停止其在本校演講。合行布告。仰各學院各附校員生一體知照。屆時照常上課為要。此布。
校長 鄒 魯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九日
胡適知道中大校方難處,但這份更改原定計劃的布告,還是讓胡適不快:“這個布告使我不能不佩服鄒魯的聰明過人。早晨的各報記載八日下午西南政務會議席上討論的胡適的罪過,明明是反對廣東的讀經政策。現在這一樁罪名完全不提起了,我的罪名變成了‘認人作父’和‘以吾粵為生番蠻族’兩項!”正如胡適所說“讀經是武人的主張”,未必能夠讓廣東民眾信服,而抓住胡適在香港華僑教育會演說中的片言只語,斷章取義,胡適反對讀經就變成了“認人作父”和“以吾粵為生番蠻族”的罪名,就容易激起民眾的“同仇敵愾”了。
這還不說。中大有兩個提倡尊孔讀經的教授的表現也令人大跌眼鏡。兩個教授聯名發了兩個“真電”給廣州各報。兩份電文內容,都是先列莫須有罪名,再要求嚴懲胡適。而所列罪名,核心觀點就是呼應陳濟棠與西南政務會議的看法。中大布告還顯得相對溫和,而“真電”完全是一種危言聳聽的激烈討伐。胡適文章將兩份電文都照錄了。由于所列罪名基本相同,筆者這里就只錄發給廣西政要和教育界領導的第二個“真電”:
送梧州南寧李總司令,白副總司令,黃主席,馬校長勛鑒,(前段與上電約同)今聞將入貴境,請即電令所在截留,徑付執憲,庶幾亂臣賊子稍知警矣,否則公方剿滅共匪,明此教戰,而反容受劉豫張邦昌一流人物以自玷。天下其謂公何,心所謂危,不敢不告。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主任古直教員李滄萍鐘應梅叩,真午。
胡適告訴我們:電文所列的李滄萍先生,事前并不知情,后發表談話否認了列名真電。而我們從發給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馬君武的這第二個“真電”的用詞與語氣中,確實感受到了一種完全是上綱上線的思維,而“徑付執憲”則可謂充滿殺氣。
面對古直這類思想僵化,而且還依附權勢的教授,胡適是瞧不起的。這與胡適素來堅持的人文立場與獨立意識有直接關系。胡適雖然長期游移于“道統”,參政議政多,任過北大校長,當過國民黨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預備會議臨時主席,但他始終不棄“學統”立場。他參與創辦的《新月》雜志批評過國民政府;1929年國民政府下了保障人權命令,胡適立刻在《人權與約法》中舉了很多例子來論證這道命令的破綻。1932年胡適與丁文江創辦《獨立評論》,又明確提倡“獨立精神”,宣稱決不“依傍任何黨派”。這使得蔣介石對胡適的態度相當矛盾,既想借助胡適威望,又討厭胡適給他難堪。1960年代臺灣出了個“自由中國”事件,當事人雷震被關押,胡適去找蔣介石說理,兩人爭起來,結果徹底鬧翻。這都能夠說明胡適是個真學者。季羨林在《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追憶昔日和胡適交往時,就特別強調了胡適的善良厚道,認為其本性是一介書生。季老談了些“小事”:如有次在北圖開評議會,匆匆趕到的胡適首先就聲明他還有個重要會議,要提早退席。會議間有人談起《水經注》,此話題讓胡適忘乎所以,談到散會還興猶未盡,“大有挑燈夜戰之勢”,把那重要會議忘到腦后了。新中國成立前夕北平學生經常游行,但凡有學生被逮捕,胡適就一定要奔走各衙門,逼迫當局釋放學生。這些“小事”不僅顯示了胡適學者性情,且非一般學人能為。
再來看胡適在《廣西》中所描述的溫暖回憶。
廣州的險惡遭遇,委實讓胡博士有些驚心動魄,當然也氣憤,其心情可想而知。幸運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當時的廣西政要和教育界領導卻熱情歡迎胡適前來。
得知胡適要到廣州的消息時,廣西這邊就提前發出了邀請。中華書局大陸版《胡適來往書信選》(之前在香港出版),收有1935年1月8日白崇禧與黃旭初聯名發給胡適的一封急電。其遣詞用句頗有些文縐縐,但盛情相邀的情真意切則躍然紙上。電文如下:
急,廣州轉胡適之博士鑒:久慕鴻名,未親雅范,關山迢遞,仰跂為勞。頃聞文旆遠游,已抵羊城,粵桂相距非遙,尚希不吝賜教,惠然來游,俾得暢聆偉論,指示周行。專電歡迎,佇候賜復。白崇禧、黃旭初叩。庚(一月八日)印。
從電文可以感受到廣西首腦對胡適的尊重,甚至可謂達到極致。這固然與胡適的文化地位及社會影響有關,但這種盛情相邀也反映了當時廣西政要對文化建設的高度重視。
1925年秋廣西宣告地方統一后,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三位廣西首腦,提出了“建設廣西,復興中國”的口號,全省實行軍事化管理,采取了自衛、自治、自給的“三自”方針,施行了寓兵于團、寓將于學、寓募于征的“三寓”政策,并且規定各縣長必須兼任地方軍事學校校長。這種全民皆兵的軍事化政策,與當時中國軍閥割據狀況有關。但自力更生、自成一體的努力卻卓有成效。廣西經過多年建設而成為國民政府的模范省份。胡適作為中國新文化運動和新教育體制的領袖人物,歡迎他來廣西“賜教”也確實具有推進作用。
胡適與白崇禧是早先認識的熟人。年齡也相差無幾:胡適1891年生人,白崇禧1893年生人。雖然一文士一武人,兩人卻似乎很投緣。胡適告訴我們:因朋友羅爾綱先生及其家人在香港那邊等他回港,再一起北上,胡適本已定好兩天后返港,但由于白健生(白崇禧)的盛情留客,原本只計劃呆兩天的胡適,只好托人將自己與羅先生一家的船票都改期。這一改,胡適竟然在廣西足足逗留了十二天。白崇禧非常有意思,他挽留客人的方式是“警告”胡適:如果不改行程日期,他可以實行古直先生們的“真電”,封鎖水陸空交通,從而“將我扣留在廣西”。白崇禧的幽默顯示了“小諸葛”素來的聰明。這使我想起蔣介石邀請白崇禧參加北伐時,“小諸葛”也給蔣介石玩了個花招。蔣介石起先讓白崇禧任北伐軍參謀長,白崇禧則不僅要求參謀長前面加個“總”字,還提議由李任潮出任總參謀長,自己則以副總參謀長之職代行總參謀長之責。知道“小諸葛”有名堂,但蔣介石也接受了。白崇禧后來回憶:他所以如此,是因為深知蔣公太精明,且事必躬親,自己受不了這種管得太多的婆婆,有些事情就可讓李任潮出面應付。
“小諸葛”如此盛情,胡適頗為感動,也就客隨主便,痛痛快快玩了個夠。
逗留廣西期間,廣西的神奇山水自然讓胡適心曠神怡。胡適說“廣西的山水是一種特異的山水”,并認為這種山水奇異體現在很多方面,由此用了很多文字來說明。還不斷引經據典,如引用了南宋著名詩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和徐霞客關于廣西山水巖洞的很多精彩描述。“桂林山水甲天下,陽朔山水甲桂林”,桂林之行尤其讓胡適感慨不已。泛舟漓江時,同船的一位桂林女子能唱柳州山歌,胡適邊聽邊記,竟然記下三十多首。這些優美民間文化與美麗山水相映成趣,更添了一種生態環境的文化色彩。
山水怡人,廣西的自然環境固然給胡適留下美好印象。但廣西提供的人文環境,則讓胡適深為感動。廣東不讓胡適演講,廣西卻讓胡適演講多次。僅在梧州,胡適就演講了二次:廣西大學演講一次,梧州中山紀念堂演講一次。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先生是胡適的老師,而校中教職工師有不少還是胡適的老朋友,所以胡適非常高興,“我在梧州住的一天是最快樂的”。當時梧州與南寧都有自來水供應,這也使得胡適感到意外:“內地省份有兩個有自來水的城市,是很難得的。”胡適說馬君武先生是他的老師,我沒有去查這種師生關系的出處,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這對師生在文學方面還有共同話題。何也?1882年生人的馬君武,雖然留學日本時學的是工藝,留學德國則是習冶金,但馬君武平素愛好文學,不僅能夠寫自由體的格律詩(有《馬君武詩稿》),而且還用歌行體翻譯過拜倫、席勒的作品。在日本參加過同盟會的馬君武,民國成立時任過孫中山臨時政府實業部次長,可惜1939年就去世了。
從當時省份經濟看,廣西比不上廣東。但從文化環境看,當時的廣西卻比廣東有開明和包容的態度。
胡適個人經歷中,這次廣州與廣西的冷暖遭遇,由于反差太鮮明,無疑讓他刻骨銘心。也使忙碌的他才用了很多筆墨來講述這次的兩重天遭遇。《南游雜記》也使我想起文中涉及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如國民黨桂系領袖李宗仁與白崇禧,作為國民革命軍人、北伐名將、抗戰功臣,都是戎馬生涯的鐵血軍人,能夠如此尊重胡適這種新文化新教育的推動者,那還真是不錯。確實,無論何處何時,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都是互為聯系而相得益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