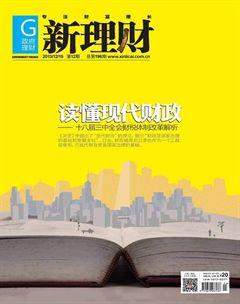國企改革破局
喬欣

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傾注了眾多筆墨對公有制經濟、國有經濟、國有資本、國有企業改革等進行了闡述,外界普遍認為,《決定》所釋放的信息將開啟新一輪國企改革大幕。對于這項改革的預期,消極與樂觀的態度并存。截至記者發稿前,有消息稱,滬版國資國企改革方案發布在即。
亮點頻現?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說:“在看到《決定》所涉及的具體改革舉措后,有些方面是超出預期的,對國有企業改革中的關鍵問題都有所涉及。”并將其歸納為幾大亮點。
李佐軍表示,首先,《決定》提出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同時強調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這就賦予了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平等的財產權力。其次,《決定》提到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同時提出國有資本投資項目允許非國有資本參股。這是從所有制層面上對國有企業進行很深層次的改革。第三,提出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組建若干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支持有條件的國有企業改組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由過去的國有資產向如今的國有資本轉變,其間差別很大,國有資產經營意味著國有企業進行著大量具體的經營活動,而成立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或投資公司,意味著國有企業主要從資本的層面進行運作,具體運營則交給各種類型的企業,這樣使得國有經濟的經營體制機制更加靈活。”
盡管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夕,有研究人士直言:“不要對國企改革抱過高期望,相關改革不會觸及問題本質,國研中心出臺的‘383方案也僅僅是對其進行‘技術性改良,從中已經可以窺見改革的局限性,背后是難撼的既得利益。”
不過,在看到《決定》全文后,李佐軍認為涉及到國企改革部分的第四個亮點就是,《決定》提出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會保障基金,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2020年提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此舉影響了國有企業的既得利益。文件同時強調加大國有資本對公益性企業的投入,而不是競爭性領域。其實競爭性領域恰恰是比較賺錢,而公益性領域是不太賺錢甚至是不賺錢的,這對國有企業來說無疑也是利益的調整。”
此外,《決定》還提出強化國有企業經營投資責任追究,合理確定并嚴格規范國有企業管理人員薪酬水平、職務待遇、職務消費等等。“為什么說這些都是亮點?因為它們都是我們多年來一直在討論,但是一直沒有解決的問題。很多人一直比較關注‘國進民退。這一系列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針對‘國進民退,更多的保障非公有制企業的平等權益。”李佐軍說。“過去之所以沒有解決這一問題,是因為改革沒有得到及時的推進。在‘非公36條和‘新36條實施之后,非公有制企業始終還是覺得遭遇‘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都說明改革滯后。《決定》提到的這些改革如何真正落到實處?需要有一個系統性的保障措施。非公有制企業如果要涉足原來的壟斷行業,可以采取特許經營的方式,下一步要專門制定有關的管理辦法,這對于非公有制企業而言,沒有什么進不去的領域。”
艱難30年
今年以來,中央多次提出通過體制改革,放寬民間投資市場準入,并在多個領域向民資開放,其中不乏堪稱“民資禁區”的壟斷行業。李佐軍說,“放寬準入涉及到非公有制經濟進入的廣度和深度,如果只是讓它有很邊緣的進入,或者是進入的領域非常有限以及深度不夠,那它當然掙不了錢,充其量僅算是敲邊鼓,在邊角余料領域做點事情。現在要讓它進入,不僅要范圍更寬、程度更深,還要更多的保障其產權,并相應的減少審批,推進稅費改革等,以及給予政治上的平等待遇。”
民營企業家呼喚應有的政治待遇已經不是新鮮事。作為我國民營企業家中旗幟性人物的聯想控股董事長柳傳志就曾公開呼吁“應該給民營企業家一個明確的政治身份,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
日前,記者在某財經論壇上見到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時,他說:“這次三中全會,我仔細看了看,感覺非常高興的是對非公有制經濟地位的進一步深化。強調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并且毫不動搖的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這些表述我覺得都非常重要。”
回顧改革開放30余年的歷程,同時也是一段跌宕的國企改革史。最初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企在生產經營上沒有任何自主權,并因為受當時管理體制束縛而導致運行僵化、供需脫節、效率低下,為了解決這些弊端,國家開出“放權讓利”的藥方,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讓企業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與此同時,國家還以兩步利改稅政策對國家與國企的分配關系進行了調整,將國企上交利潤改為繳納所得稅。
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然而在此后的10年里,隨著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試辦經濟特區、全方位對外開放,我國初步形成了多種所有制經濟的有效競爭,但剛剛被推向市場的國有企業,在日益激烈的競爭中顯得力不從心。在中央多項指導下,現代企業制度得以穩步推進建設的同時,國有經濟逐步向關鍵性和國民經濟命脈行業集中,特別是20世紀的最后三年,國有企業通過建立企業法人治理結構,促進投資主體多元化,轉換企業經營機制,抓大放小,關閉破產,分流富余人員,債轉股等形式解決企業債務負擔過重等問題,基本實現了改革與脫困目標。
2003年4月初,新成立的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的掛牌,被業界認為是新一輪國企改革的發軔,國企改革進入了以股份制為主要形式的現代產權制度改革新階段。
10年間,央企經過整合重組,由2003年的196家演變為今天的110余家。同時也被外界貼上“壟斷”“國進民退”“大而不強”的標簽。一方面,國有資本逐步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形成對非公資本的擠出。據統計,目前央企80%以上的資產集中在國防、能源、通信、冶金、機械等行業。另一方面,在改善民生、國家長遠發展的重要領域中,國有資本的作用沒有充分發揮。
國家審計署于今年5月公布的對部分國有企業2011年度財務收支的審計結果指出,中版集團、國家核電、華能集團等一些國有企業,特別是其下屬機構違規列支資金,以購買保險(放心保)、發放購物卡、建設住宅樓等各種方式為職工發放福利,涉及金額超過數億元。
這一結果使外界對國企改革的討論再次升溫。有研究機構認為,中央要對國有企業改變管理方式,以共同基金的方式改造國企。有經濟觀察人士認為新一輪國企改革的突破點和關鍵環節在股權創新。國研中心專家指出,從國有資本層面,深化改革的重點在于:一是按照“混合所有制”模式進一步推進產權制度改革;二是進一步完善國有資本管理體制和運營機制。同時強調,國企改革必須把宏觀層面的“管資本”改革和微觀層面的“管企業”改革結合起來。另外,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不僅僅是企業層面的問題,不少都與相關黨政部門有關。
市場呼喚公平正義
回看國企改革的歷史,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的差異從一開始就存在。然而,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是一支不可或缺的經濟力量,有數據顯示,以民營企業為主體的中小企業繳納的稅收占我國稅收收入的50%左右,同時它還是吸納社會就業、創造社會財富、方便群眾生活的重要渠道。
劉永好的創業經歷同時也見證了國企改革的歷程,對于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的關系,他有著深刻體會。他說:“1992年到1994年間,我收購了30多家國有企業,那時只有國企才有糧食指標,所有的飼料企業都是國有。后來糧食放開了,這些國企的優勢沒有了,很多就倒閉了,而我們蒸蒸日上。到今天,我們收購的這30多家飼料廠全部都健在,而且發展的很好。而我曾經跑過的七八十家沒有跟我合作的國有飼料廠,如今已經全部都倒閉了。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允許民營企業一定程度的參與國有企業的一些合作,我覺得這是大好事。不過,我仍然心有余悸。跟國有企業的合作確實還是有壓力的,盡管國有企業只占了我們5%、10%的股權,但是它的代表,它的權威,它的影響是非常大的。實際上我們幾乎所有的民營企業都遇到過同樣的問題,當公司出現一些問題到法院告狀的時候,往往被受理的幾率小很多,而國有企業被受理的幾率就大很多,這就是不平等。未來我覺得不管外資企業、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的兼并收購完全要按照市場規則去做,這是最好的。”